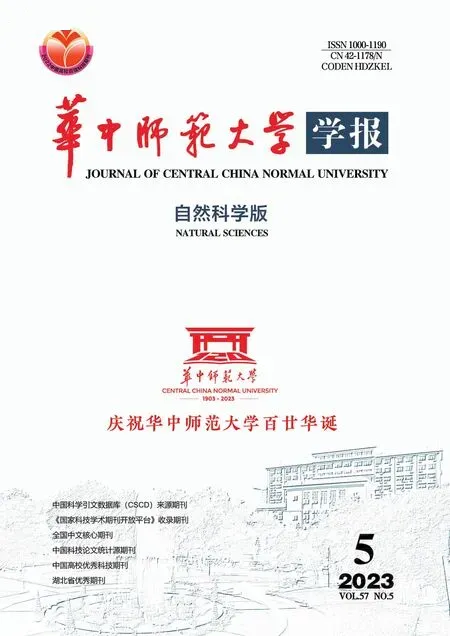湖北省1949年以前瘧疾流行的時空規律及驅動機制
張 濤, 曾雨欣, 陳志禹, 閆晉博,梅 琳, 王曉偉, 石國寧, 龔勝生*
(1.華中師范大學地理過程分析與模擬湖北省重點實驗室,武漢 430079;2.華中師范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武漢 430079;3.山東女子學院旅游學院,濟南 250300;4.邯鄲學院經濟管理學院, 河北 邯鄲 056006)
瘧疾是一種經按蚊叮咬或輸入帶瘧原蟲者血液而感染的蟲媒傳染病,屬于中國乙類法定傳染病.早在距今3 500~3 000 a的殷商時期便有瘧疾記載,歷史文獻多以“瘴”來描述惡性瘧疾[1].當前,關于過去3 000年來中國疫災流行總體時空特征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已較為成熟[2].關于瘧疾流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對瘧疾時空分布的探討.2000年來,中國惡性瘧疾(瘴)分布的北界逐漸往南退縮,從秦嶺淮河一線向南退縮到長江一線,最后退縮至南嶺山地[3].先秦兩漢時期瘧疾主要分布在中原地區[1],宋元時期集中在以廣東、廣西為主的嶺南地區[4],明清時期主要分布在我國西南地區[5].清代的瘧疾流行風險程度呈東南向西北遞減的分布特征[6].晚清民國時期,云南地區瘧疾主要在其西南、南部、東南的河谷地區流行[7].民國時期,兩廣地區有80余縣市暴發過瘧疾,主要分布在兩廣的山區[8].現代中國仍有瘧疾流行,2010—2017間,云南、廣西、海南為中國瘧疾發病率的熱點區,但有向東部擴散趨勢[9].二是對瘧疾流行影響因素的分析.溫度會對瘧疾流行起到復雜的相互作用[10].瘧疾容易在氣溫升高的時候發生,尤其在雨季開始后,相對濕度高,更容易滋生適于瘧原蟲生長的環境[11].瘧疾流行程度還與人口流動、生態條件、醫療衛生服務及其他因素相關[12].歷史上北人南遷帶動了南方地區土地開發,改變了原有的生態環境條件,對于瘴病逐步消失起到了關鍵作用[13].三是關于瘧疾流行應對及影響的研究.在瘴氣廣泛傳播的西南邊疆民族地區,人民在生活實踐中逐漸形成防瘴治瘧的方法,促進了民間瘴瘧醫典的興起[14].在醫療衛生條件較為落后的古代社會,瘴氣對民族分布格局產生不可忽略的影響[15].四是關于湖北瘧疾流行歷史的研究.民國時期湖北省在發生特大水災之后惡性瘧疾嚴重流行,1949年以后湖北省也常暴發大范圍的瘧疾流行事件[16].2004—2011年間湖北省瘧疾分布呈現空間集聚態勢[17].氣溫對湖北省瘧疾流行的影響作用更為顯著[18].湖北省1974—2015年間的瘧疾流行過程經歷了高發、急劇下降、低發和消除階段,影響瘧疾的自然因素仍然存在,要加強對輸入性瘧疾的控制和監測[19].綜上所述,當前關于中國瘧疾流行的研究在時空分布、影響因素、應對及影響等方面已較為深入,但對于非傳統瘴域的關注還不夠,對于湖北歷史瘧疾的研究缺少歷史地理視角的時空變遷分析,影響因素分析不夠系統且缺少機制探究.本研究從歷史醫學地理視角出發,基于瘧疾史料和環境數據,對湖北省1949年以前瘧疾流行的時空分布規律及其驅動機制進行深入研究,為瘧疾防控提供歷史參考.
1 研究區域、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湖北省位于長江中游地區,地勢自西北向東南傾斜,東、西、北三面環山,中部低平,略呈南向洞庭湖敞開的不完整盆地.除高山地區外,大部分屬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長江、漢江從境內穿過,湖泊眾多,素有“千湖之省”的稱號.湖北地理位置居中,水陸交通發達,古稱“九省通衢”,今為國家東西南北的交通樞紐.基于研究時段,本文以1946年行政區劃為標準制圖,該年湖北省共分71個縣市(圖1).

注:本圖參照《湖北省明細全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和《中國分省新地圖》(亞光輿地學社1947年版,第24、32-33頁)改繪.圖1 湖北省1946年行政區劃圖Fig.1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map of Hubei Province in 1946
1.2 數據來源
1.2.1 瘧疾流行數據 瘧疾流行數據主要采自《中國三千年疫災史料匯編》[20],該匯編史料豐富,涵蓋正史、檔案、實錄、文集、地方志和近代報刊等;少量通過查閱民國時期的《武漢日報》《大剛報》等獲得.在史料基礎上,以縣為基本單元,統計各年發生瘧疾的縣數以及各縣發生瘧疾的年數,編制湖北省瘧疾流行年表.
1.2.2 影響因子數據 自然因素包括年均氣溫、年降水量、海拔高程、河網密度、旱澇災害等,其中氣候數據來源于國家地球系統科學數據中心,海拔、河道數據運用ArcGIS 10.7軟件從DEM圖中進行提取,氣象災害數據據《中國氣象災害大典·湖北卷》[21]《湖北省近五百年氣候歷史資料》[22]整理.社會因素包括人口密度、路網密度、戰爭動亂等,其中人口數據以民國時期的人口平均數據為樣本,采自《湖北通志》[23]《內務統計 民國五年分湖北人口之部》[24]《民國十七年各省市戶口調查統計報告》[25]《湖北人口統計》[26]及《湖北人口三十五年冬季戶口總復查實施紀要》[27],路網數據通過ArcGIS 10.7在湖北歷史地圖中矢量化獲取,戰亂數據據《中國歷代戰爭年表》[28]《中國戰爭史·第四卷·民國至新中國初期》[29]整理.
1.3 研究方法
1.3.1 趨勢周期分析方法 使用M-K(Mann-Kendall)檢驗分析瘧疾趨勢變化,小波分析方法提取瘧疾變化周期.M-K趨勢統計檢驗用于評估一組數據值在給定時間序列內任一方向的趨勢是否具有統計學意義,即是否存在線性單調趨勢,這是一個與Kendall相關系數概念密切相關的非參數趨勢.它不受時間序列長度和缺失數據的影響,且不要求數據正態分布,是用于評估序列變化趨勢的重要工具[30].本研究采用M-K趨勢統計檢驗來確定湖北省瘧疾的變化趨勢和突變時間點.小波分析方法是基于傅里葉變換的新式窗口函數,顯示作為周期和時間函數的變化強度[31],能夠反映時間序列的多種變化周期,從而更好地揭示序列隨周期的變化情況[32].基于小波分析方法,對湖北省十年瘧疾縣數時間序列進行周期性檢驗,確定湖北省瘧疾的變化周期.
1.3.2 空間自相關模型 空間自相關分析用于衡量空間變量的分布是否具有集聚性,是評估變量空間聚集程度的重要工具.它可以在全域或局部尺度上揭示研究單元屬性之間的相關性.本文使用全局Moran’sI和局部Moran’sI評估空間自相關性.空間關聯程度在散點圖中顯示,局部空間關聯指標(LISA)并在研究區域地圖上顯示.
全局Moran’sI是對空間數據整體聚類的一種衡量,被定義為
(1)

空間關聯的局部指標(LISA)利用Moran’sI是單個交叉產物的總和這一事實,通過計算每個空間單位的局部Moran’sI,從而評估每個單位的聚類情況并評價其統計學意義.其式如下:
(2)
利用歸一化屬性值和鄰域平均值乘積的正負符號來對四種類型的空間對象進行分類:HL(高-低)、LH(低-高)、HH(高-高)和LL(低-低),其中HL指的是被低值(低于平均值)包圍的高值(高于平均值),其余說法類似.HL和LH表示具有不同值的空間異常值,而HH和LL對應于具有相似值的空間聚類.然而,即使在所有值都高于平均值(或低于平均值)的HH(或LL)聚類中,一個對象與其鄰域之間的局部差異也可能很大.類似地,如果HL或LH異常值及其相鄰值都接近平均值,則它們可能相似.
1.3.3 疫情重心模型 重心的概念源于物理學, 常以全局視角探測在不同地區空間作用下形成的平衡點[33],疫情重心是某區域疫情分布在空間平面上力矩達到平衡的點.重心的分析方法包括空間定位和重心遷移[34],其分布趨勢可表示瘧疾流行縣數在空間分布的均衡程度,而重心遷移則反映了區域內瘧疾流行地域的變遷趨勢,其公式為:
(3)

1.3.4 地理加權回歸模型 地理加權回歸是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的延伸,它通過評估局部加權回歸系數偏離全局系數的地方來建立關系,即通過建立空間范圍內每個點的局部回歸方程用來探索研究對象在某一尺度下的空間變化及相關驅動因素,可以用來量化空間異質性,在流行病學中具有很高的實用性.其公式為:
(4)
式中,yi是第i個樣本的因變量,(ui,vi)是第i個樣點的空間坐標,β0為(ui,vi)處的的截距項,xij為第i個樣本的自變量k的取值,βj為xij的回歸系數,εi是第i個樣點的隨機誤差.
2 湖北省瘧疾流行的時空分布規律
2.1 湖北省瘧疾流行的時間變化
2.1.1 流行概況 湖北瘧疾流行歷史久遠.東漢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戰時,“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本次大疫有瘧疾之說,曹操軍隊經豫南越過桐柏山脈,遍走武當山、荊山,進入江漢平原和湖沼地區,都是在瘧疾傳播季節[35].隋唐五代時期施州(治今恩施)、峽州(治今宜昌)、荊州(治今江陵)、鄂州(治今武昌)都有瘴病分布[3].唐代詩人王維在《林園即事寄舍弟紞(次荊州時作)》詩中寫道“地多齊后瘧,人帶荊州癭”[36].元代朱丹溪謂“吳楚閩廣之人患瘧獨多”[16].明代暫未見湖北瘧疾史料.清代瘧疾記錄逐漸增多,雍正十二年(1734年),武昌縣(今鄂州)“鄉村疫瘧”[20].道光十三年(1833年),宜城縣(今宜城)“瘟瘧流行,人及六畜多死”[20].統計來看,1644年至1911年清朝統治的268年間共有14個瘧疾年份,頻率為5.2%.民國瘧疾愈加頻繁,38年間共有20個瘧疾年份,頻率為52.6%.瘧疾縣數較多的年份有1943年(11縣)、1946年(9縣)和1941年(8縣).
2.1.2 變化趨勢 使用M-K檢驗對湖北瘧疾變化趨勢進行分析.由于民國以前瘧疾頻率較低,誤差較大,因此僅對民國各年瘧疾縣數時間序列進行檢驗(圖2).結果顯示,UF值在1912—1949年間呈現波動變化,在1912—1916和1920—1941年間小于0,在1917—1919和1942—1949年間大于0,表明民國時期瘧疾在1912—1916和1920—1941年間呈下降趨勢,在1917—1919和1942—1949年間呈上升趨勢.其中在1923—1937年間UF值超過了0.05顯著性臨界線,表明此時段內瘧疾減少趨勢十分顯著.UF和UB曲線在1940年相交,且交點在臨界線之間,則1940年為瘧疾時間序列開始突變增長的時間點.

圖2 湖北省1912—1949年瘧疾縣數Mann-Kendall檢驗Fig.2 Mann-Kendall test of counties of malaria in Hubei Province from 1912 to 1949
2.1.3 波動周期 小波系數實部等值線圖能反映瘧疾縣數序列不同時間尺度下的周期變化及其在時間域中的分布情況.湖北省民國1912~1949年間瘧疾疫情存在15~21年、8~11年、3~5年等三類時間尺度的周期變化(圖3).其中在15~21年時間尺度上存在輕-重交替的3個準振蕩周期,在整個研究時域上表現穩定,具有全域性.在8~11年時間尺度上存在輕-重交替的3個準振蕩周期,主要發生在1920—1940年間.在3~5年時間尺度上存在輕-重交替的7個準振蕩周期,主要發生在1925年之后.小波方差圖能反映瘧疾縣數序列的波動能量隨時間尺度的分布情況,從而可以確定瘧疾縣數變化過程中的主周期.湖北省1912—1949年間的瘧疾序列存在2個明顯的峰值(圖4),分別對應著18年和4年的時間尺度.最大峰值為18年時間尺度,為湖北省瘧疾變化的第一主周期,第二峰值為4年時間尺度,為第二主周期.在18年時間尺度上,瘧疾縣數的平均變化周期約為12年,經歷了3個周期的輕-重轉換,疫情偏輕的時段為1912—1916年、1923—1928年,1935—1940年、1947—1949年,疫情偏重的時段為1917—1922年、1929—1934年,1941—1946年.在4年時間尺度上,瘧疾縣數的平均變化周期約為3年.總體來看,湖北民國時期瘧疾每隔約12年發生一次大流行,約3年發生一次小流行.
2.1.4 季節分布 1833—1949年間,湖北省瘧疾流行季節明確的年份有27個,累計流行瘧疾的季節52個,其中:春季8個(15.38%),夏季 17個(32.69%),秋季21個(40.38%),冬季 6個(11.54%),夏秋兩季占比73.07%.27個流行季節明確的瘧疾之年累計波及84縣,其中:春季12縣(14.29%),夏季 26 縣(30.95%),秋季38縣(45.24%),冬季 8縣(9.52%),夏秋兩季占比76.19%.從瘧疾流行季節和各季瘧疾流行縣數統計來看,湖北省瘧疾流行以夏秋季節為主,春季次之,冬季最少.

圖3 湖北省瘧疾縣數序列小波變換系數實部等值線圖Fig.3 Contour map of the real part of wavelet transform coefficients of malaria counties series in Hubei Province

圖4 湖北省瘧疾縣數序列小波方差圖Fig.4 Wavelet variance plot of malaria counties series in Hubei Province
2.2 湖北省瘧疾流行的空間分布
2.2.1 總體特征 1833—1879年間瘧疾稀少(圖5a),71個縣中只有宜城和鄂城有瘧疾發生,且發生年數都只有1年.1880—1889年疫情依然較輕(圖5b),宜昌和鄂城兩縣分別有3年和1年有疫情.1890—1899年瘧疾主要分布在武漢三鎮及宜昌(圖5c).1910—1919年疫情有所減緩,瘧疾流行縣數降低至2個(圖5d),其中宜昌有4個瘧疾年份.1930—1939年瘧疾疫情開始加重(圖5e),瘧疾縣數升至14個,形成分別以武漢三鎮和宜昌兩個疫情中心.1940—1949年瘧疾疫情迅速擴散至33個縣(圖5f),以武漢三鎮和宜昌為中心向周邊蔓延形成兩個瘧疾流行區.總體來看,1833—1949年間(圖5g),湖北省瘧疾流行呈現出蔓延擴散的特征,由斑塊散狀分布發展成集中連片分布,武漢三鎮和宜昌是兩個疫情中心.
2.2.2 空間集聚 湖北省瘧疾疫情在空間上呈現顯著集聚態勢(圖5h),Moran’sI值為0.2,p值小于0.05,Z值為2.72.高高集聚區主要分布在武昌、漢口、漢陽和宜都,高低集聚區只有竹山,在宜昌周邊形成一條由興山、遠安、當陽和長陽等縣組成的低高集聚帶,未出現低低集聚區.

圖5 湖北省瘧疾流行空間分布及集聚圖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clustering map of malaria epidemic in Hubei Province
2.2.3 重心變遷 計算1870—1949年間每十年瘧疾疫情重心(圖6),其中1900—1909年、1920—1929年無瘧疾疫情.1870—1879年疫情重心位于鄂東的大冶,隨后十年大幅度向西北遷移到宜昌,1890—1899年又向東遷移到漢川,1910—1919年再向西回到宜昌、遠安和當陽交界地區,之后十年又向東移到漢川,1940—1949年疫情重心向西北落于鐘祥境內.總體來看,湖北省瘧疾重心一直在幾何中心附近東西向擺動并逐漸向北偏移,反映了疫情分布不穩定并逐漸向北加重.

圖6 湖北省瘧疾疫情重心遷移圖Fig.6 Migration map of malaria epidemic center in Hubei Province
3 湖北省瘧疾流行影響因素及驅動機制
3.1 湖北省瘧疾流行影響因素的回歸分析
基于地理加權回歸模型對湖北省瘧疾流行的影響因素進行定量分析.選擇海拔(x1)、年平均氣溫(x2)、年平均降水(x3)、河網密度(x4)、澇災年數(x5)、旱災年數(x6)、NDVI植被指數(x7)、總人口(x8)、人口密度(x9)、路網密度(x10)、戰亂年數(x11)等11個指標,為消除多重共線性問題,通過OLS模型計算各指標的方差膨脹因子(VIF)值,將年平均氣溫(x2)、NDVI植被指數(x7)、總人口(x8)陸續移除.在ArcGIS10.7中使用地理加權回歸工具,選取各縣疫災年數作為因變量,剩余8個指標作為自變量,選擇FIXED核類型并使用“Akaike信息準則(AICc)”確定核的范圍.結果顯示,擬合優度R2=0.27,各縣局部回歸模型的標準化殘差分布范圍在[-1.61, 5.58],其中99%以上在[-2.58,2.58],表明地理加權回歸模型的標準化殘差值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是隨機的,僅有1個縣未通過殘差檢驗,模型整體擬合效果較好.結果顯示,從回歸系數的正負來看,海拔、河網密度、旱災年數、人口密度、戰亂年數等5個指標的回歸系數均為正值,表明對瘧疾流行均具有正向效應,年均降水、澇災年數、路網密度等3個指標的回歸系數均為負值,對瘧疾流行均具有負向效應.從回歸系數的絕對值大小來看,河網密度、路網密度、戰亂年數、旱災年數等4個指標的回歸系數較大,表明對瘧疾流行的影響更為強烈,以自然斷裂點法將其回歸系數結果空間可視化(圖7),對其影響因素的空間分異進行分析.具體來說,河網密度(圖7a)、戰亂年數(圖7c)、旱災年數(圖7d)等3個指標的回歸系數均為正值且均呈現“西低東高”的空間分布特征(圖7a),說明河網、戰亂、旱災等因素對瘧疾流行均具有促進作用且在鄂東地區更為顯著.相反,路網密度的回歸系數為負值且呈現“西高東低”的空間分布特征(圖7b),說明說明鄂西地區路網的完善對瘧疾流行的抑制作用更為強烈.

圖7 湖北省瘧疾流行影響因素的空間分異Fig.7 Spatial variat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malaria prevalence in Hubei Province
3.2 湖北省瘧疾流行時分布的影響因素
3.2.1 湖北省瘧疾流行時間變化的影響因素 氣候在大空間、長時間尺度上對疫災流行有較大的影響[37].瘧疾在夏、秋季節流行,一是因為夏、秋季節炎熱多雨,高溫高濕有利于瘧疾的主要傳播媒介蚊子的活動,如《申報》載:“夏五月,天氣悶燥異常,患瘧疾及喉癥者甚多.”[20]二是因為洪澇等自然災害容易發生在夏秋季節.極端氣候常會引起自然災害的頻發,間接誘發重大疫災的形成,尤其是水旱災害,與疫災流行密切相關[38].洪澇災害往往容易誘發瘧疾,如《襄陽縣志》載:“夏六月,大雨,漢水暴漲,水退后,痢、瘧流行.”[20]湖北省瘧疾在20世紀40年代的快速增長中國氣溫的暖周期有一定的關系,湖北省處于溫度回暖的時期,氣候較之前暖濕程度增加,為蚊蟲的繁殖和生存創造適宜的條件.同時,湖北省在20世紀30—40年代為抵御日軍侵華先后進行了武漢會戰、隨棗會戰等數次重大戰役,戰爭容易造成物資匱乏,環境變得惡劣且長期行軍打仗對士兵生理健康造成傷害,極易形成疫情持續多發的狀況[39].
3.2.2 湖北省瘧疾流行空間分布的影響因素 武漢三鎮和宜昌是湖北省瘧疾的兩個中心,其周邊地
區也始終為瘧疾流行的高值地區.這些地區是湖北省的重鎮,人口密集,經濟發達.人口是疫災發生和傳播的重要基礎.人口的增加和集聚影響著疫災分布的空間格局.一般來說,人群越密集的地區疫病越容易傳播,隨著人口的增加和集聚,疫病的發生概率和流行強度也會隨之提高.同時,這些瘧疾頻發地區大多位于長江沿岸,水網密集.瘧疾主要以蚊蟲為傳播媒介,蚊蟲的繁殖離不開水源,而在受污染的水源中更易滋生蚊蟲.從地理加權回歸結果分析河網密度對瘧疾流行的影響呈正相關,以史料記載來看,水源因素是影響瘧疾流行的重要因素,如《申報》載:“宜昌中元后,城內亦有以痢疾轉瘧者,幸此癥尚輕,惟長江上下一帶最重.”[20]《大公報》載:“江水退甚慢,三鎮濕痢瘧死者日以百計.”[20]以武漢三鎮地區為中心輻射出水陸交通網,交通發展便利的同時加速了人員流動,促進了各類疫病的傳播.對路網密度與瘧疾流行年數進行相關分析,未通過顯著性檢驗.究其原因,瘧疾主要通過蚊蟲的叮咬傳播,一般不會在人和人之間直接進行傳染,因此交通因素帶來的人員流動在瘧疾傳播中并非關鍵因素.總體來看,水源因素在瘧疾的傳播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時人口因素和交通因素也為瘧疾的流行提供了社會經濟條件.
3.3 湖北省瘧疾流行的驅動機制
參考健康地理學視角下的傳染病研究理論框架[40],湖北省瘧疾流行的驅動機制由瘧疾流行的基本環節、影響因素和時空規律等三個方面組成(圖8).瘧疾流行的基本環節包括傳染源、傳播途徑及易感人群,必須同時存在才能構成瘧疾的流行.如果某一環節缺乏或阻斷三者的聯系,流行過程就會被中斷.瘧疾流行的影響因素包括自然因素、人文因素和個體因素,不同因素都或多或少影響不同的基本環節,能夠推動或遏制基本環節發揮作用.如氣溫高低決定了瘧原蟲孢子增殖期的長短,瘧原蟲幼蟲習慣生活在低洼潮濕的水環境中等.同時,因素之間也能夠互相影響,如氣候條件與河床條件會影響旱澇災害的發生.瘧疾流行的時空規律是影響因素作用于基本環節所呈現的時空分布格局,包括時間上的趨勢性、周期性和季節性以及空間上的集聚性和蔓延性.運用M-K檢驗、小波分析、重心分析、空間自相關分析、地理加權回歸分析、定性分析等方法可以將驅動機制的三個方面有機聯系起來.

圖8 湖北省瘧疾流行驅動機制示意圖Fig.8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malaria epidemic in Hubei Province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1) 從時間變化來看,湖北清代之前瘧疾記錄較少,清代(1644—1911)268年間共有14個瘧疾年份,頻率為5.2%,民國(1912—1949)瘧疾愈加頻繁,38年間共有20個瘧疾年份,頻率為52.6%.民國瘧疾流行呈現波動變化趨勢,1940年為瘧疾開始突變增長的時間點.民國瘧疾疫情存在18年和4年兩個時間尺度的波動周期,平均每隔約12年發生一次大流行,約3年發生一次小流行.流行季節以夏秋為主,春季次之,冬季最少.
2) 從空間分布來看,湖北省瘧疾流行呈現出蔓延擴散的特征,由斑塊散狀分布發展成集中連片分布,武漢三鎮和宜昌是兩個疫情中心.湖北省瘧疾疫情在空間上呈現顯著集聚態勢,高高集聚區包括在武昌、漢口、漢陽和宜都,高低集聚區只有竹山,在宜昌周邊形成一條由興山、遠安、當陽和長陽等縣組成的低高集聚帶,未出現低低集聚區.湖北省瘧疾重心一直在幾何中心附近東西向擺動并逐漸向北偏移,反映了疫情分布不穩定并逐漸向北加重.
3) 從影響因素和驅動機制來看,河網、戰亂、旱災等因素對瘧疾流行均具有促進作用且在鄂東地區更為顯著,鄂西地區路網的完善對瘧疾流行的抑制作用更為強烈.瘧疾流行時間變化特征主要受氣候和戰亂因素的影響,空間分布規律主要受人口、河網和交通因素的影響.瘧疾流行的驅動機制由瘧疾流行的基本環節、影響因素和時空規律三個方面組成,并通過各種分析方法有機聯系起來.
4.2 討論
現有研究表明湖北宜昌一帶有過約10年為周期的暴發性流行,先后有1881年、1890年、1900年、1911年和1916—1919年等五次瘧疾流行[41],與本研究發現的平均每隔約12年發生一次瘧疾大流行結論接近.現有研究也關注到氣象因素與瘧疾流行的關系,如李月通過分析瘧原蟲發育及蚊蟲繁殖發育環境發現從傳播媒介上看均受氣象因素例如溫度、濕度、降雨量等因素的影響[42].莫曉彤等認為瘧疾流行程度與人口流動、生態條件、醫療衛生服務以及其他因素相關[12],由于歷史時期人口流動及醫療衛生服務的數據難以獲取,本文暫未將這兩種因素納入分析.因部分地區未搜集到瘧疾史料而按無瘧疾流行統計,可能與實際情況不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回歸分析模型結果的準確性.后續研究中,可通過進一步發掘瘧疾及環境史料,創新研究方法,深入揭示湖北省瘧疾流行的時空規律及驅動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