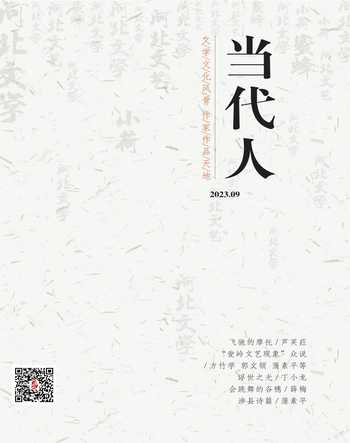珍惜文學給生活帶來的無限可能
2023-10-20 20:57:54云舒
當代人 2023年9期
關鍵詞:歷史
從“甕嶺文藝現(xiàn)象”中,我看到了廣袤的文學空間。在“讀”甕嶺、“爬”甕嶺中,刺玫、黃連、蛇莓、連翹等大自然饋贈人類豐富多彩的物種長滿山坡,爬滿古道,它們以最本真、最頑強的生存狀態(tài)彰顯著強大的生命力。看到郭文鎖用思想的鐮刀劈開古道荊棘,看到一個又一個甕嶺文學愛好者匍匐攀登的那一刻,我忽然感悟到他們不就是甕嶺上昂揚著蓬勃生命力的一朵朵花、一棵棵樹嗎?因為心中有詩、眼里有光,因為對甕嶺愛得深沉、對文學愛得執(zhí)著,他們才能堅守大山一隅,向陽而生、靜靜地長、淡淡地香。
從“甕嶺文藝現(xiàn)象”中,我讀到了可喜的文學生存狀態(tài)。在甕嶺最讓我感動的是巖石上印著歲月斑痕的黃色小花,它是風化的綠苔,也是歷史古道上千百年的包漿。這一現(xiàn)象的可貴之處,在于它將那些朝圣者的汗滴、挑夫的腳印、抗日學生的犧牲從時光深處打撈出來,記錄下來,珍藏起來,給予她們生命的溫度、歷史的厚度,把這朵自然之花、歷史之花培育成文學之花,升華為中國式現(xiàn)代化建設河北篇章上的希望之花。
稻盛和夫說過:“人生一世,如果自己臨走時的心性,比自己來時的心性層次更高了,那么這一世就沒有白來。”甕嶺因為有了文學、文藝的加持就變成了文學的甕嶺、文藝的甕嶺;甕嶺文學人因為甕嶺文藝現(xiàn)象的形成就沒有白白努力。在甕嶺,我再次看到了堅守和努力的意義,看到了文學帶給生活的無限可能,也更加堅定了沿著文學道路走下去的信念。
(云舒,原名張冰,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河北文學院簽約作家。)
猜你喜歡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shù)英綜合(2022年2期)2022-03-30 11:38:17
環(huán)球時報(2022-03-16)2022-03-16 12:17:18
作文大王·笑話大王(2019年8期)2019-09-09 07:34:21
全體育(2016年4期)2016-11-02 18:57:28
小天使·四年級語數(shù)英綜合(2016年9期)2016-10-09 22:40:45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6期)2015-10-13 07:21:18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9期)2015-09-22 07:36:52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8期)2015-08-14 07:13:06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7期)2015-07-25 07:42:53
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5年5期)2015-05-26 07:2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