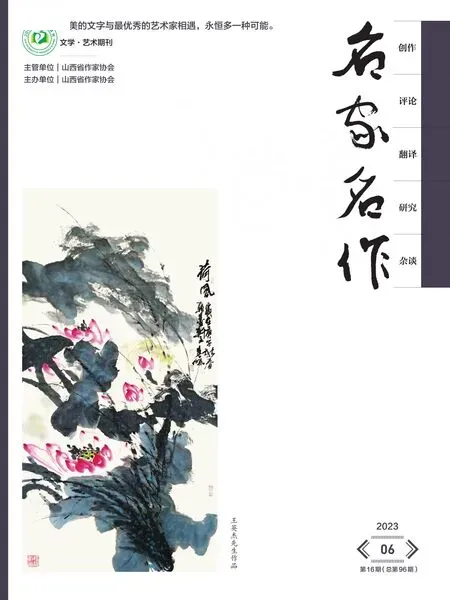麥克尤恩《黑犬》中的創傷解讀
閆 淼
一、前言
“創傷 (Trauma)”一詞來源于希臘文“Traumatize”。“創傷”最初的含義指的是因為外部力量而造成的身體上的傷害,后來才逐漸被賦予精神創傷的核心內涵。不同學者對創傷的定義有不同的看法。例如當代創傷理論家凱西·卡魯斯認為創傷是對突然發生的、災難性事件的壓倒性反應,常常以延遲的、不受控制的幻覺或其他侵入性現象的形式重復出現。而當代學者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將“創傷”定義為“一種難以掌握的體驗……在創傷體驗中,人們往往能夠想象出他們無法直接或無感情地感知的經驗,或者因為思緒太滿,甚至無法批判地、自信地表達自己的看法”。多米尼克·拉卡普拉認為創傷體驗有兩個特征——超出人們正常認識能力的不可理解性以及在事件發生之后的機械重復性。而這兩個特征與以往學者們對創傷記憶的理解達成了共識。與以往學者們將“創傷性事件”與“創傷性體驗”混用的做法不同,拉卡普拉將創傷進一步細分,將其分為“結構性創傷”與“歷史性創傷”。為了進一步解釋清楚“結構性創傷”與“歷史性創傷”,拉卡普拉借助術語“缺失”與“喪失”對其進行解釋。從字面意義來看,“喪失”指的是失去親人、身份等含義,而“缺失”指的是一種根本不存在的狀態,或者僅僅是人們希望達到的一種狀態,這種狀態直指一種完美、無憂無慮的生存境界。拉卡普拉將“喪失”與“歷史性創傷”聯系起來,將其置于歷史維度,指的是過去的事件,有明確的時間指向;而將“缺失”與“結構性創傷”聯系起來,將其置于超歷史維度,不包含過去、現在或未來。簡而言之,拉卡普拉將可追溯到具體的事件的創傷經歷稱之為“歷史性創傷”,而將因為當事人過分渴望無法實現的烏托邦世界而形成的某種難以釋懷的鄉愁形成的創傷稱之為“結構性創傷”。
伊恩·麥克尤恩是英國最具影響力的當代小說家之一,被稱為英國當代文學的 “國民作家”。小說《黑犬》出版于1992 年,由前言和四部分故事主體構成。在前言中主人公杰里米以第一人稱敘述的形式回憶了自己孩童時期不幸的成長經歷。在故事主體的四個部分,麥克尤恩分別以“威爾特郡”“柏林”“馬伊達內克”和“圣莫里斯—納瓦塞勒”為名,通過不同的敘事視角描述了發生在四個不同空間的事件,進而揭示了戰爭的記憶和人性的變化,展現了現代社會中人們精神世界里普遍的恐慌和焦慮。《黑犬》的創作與麥克尤恩的親身經歷密不可分。正如譯者郭國良在小說《黑犬》的譯后記中指出——以第一視角杰里米為主導的前言部分其實正是麥克尤恩對存在于社會中的孤獨以及對社會的無知感的戲劇性表達。無論是小說中杰里米童年缺失性創傷體驗還是岳母瓊與岳父伯納德失敗婚姻的創傷體驗,其實都是麥克尤恩自身經歷的縮影。
二、杰里米的缺失性創傷經歷
麥克尤恩小說中的家庭絕大多數展現的都是支離破碎的,父母均缺席了孩童的生長。其實麥克尤恩筆下破碎的家庭與他本人的親身經歷是密不可分的。麥克尤恩自11 歲就被迫遠離家鄉,被父母寄養在伍爾弗斯頓·霍爾的寄宿學校。在一群年紀相似且家庭破裂的工人子弟中,小麥克尤恩感到無比迷茫與孤獨。粗魯且殘暴的工人子弟給尚幼稚的麥克尤恩留下了深深的陰影,麥克尤恩回憶這段時光運用的“性地獄”詞語給他的早期作品留下了深深的痕跡。
在小說《黑犬》的前言部分,敘述者杰里米講述了不幸的成長經歷。杰里米在8 歲的時候父母因車禍去世,留下年幼的他與姐姐相依為命。失去雙親的姐弟倆不得不居住在姨媽家,生活中缺少孩童時期應享受的樂趣與玩伴。在他從童年到青少年的跨越時期也并未得到姐姐與同輩朋友的幫助,正如文中莎莉所提及的“苦難會將一個孩子置于多么孤立無援的境地”一樣,小說中的杰里米沉迷于封閉的內心世界。1959—1975 年的越南戰爭導致美國國內掀起了反戰的浪潮。那個時期的年輕人對父母不屑一顧、滋事添亂,在臟亂的公寓里瘋狂聚會并酗酒狂歡,他們試圖以這種離經叛道的方式填補內心的失落與空虛。與這些人不同,失去父母的杰里米走進朋友的家里會與他們的父母交談以減輕縈繞心頭的失落感。
另外,緊張的姐弟關系加深了杰里米的失落感與孤獨感。失去父母的瓊并沒有承擔起撫養弟弟長大的責任,相反她早早地穿上了迷你裙在姨媽家與無數不知名的男生約會。成年后便早早地踏入了暴力性成人婚姻的鬧劇,不到20 歲的她便有了女兒莎莉。瓊與自虐成性的丈夫哈珀在公寓里酗酒打架,將女兒莎莉扔給杰里米撫養并靠父母留下的遺產生活。姐姐瓊也不會關心杰里米的服飾、日常飲食與行蹤下落等,緊張的姐弟關系讓杰里米倍感孤獨與失落,于是他想通過進入大學來擺脫與姐姐生活在一個屋檐下的困境。
毫無疑問,姐弟關系的冷漠限制了家庭成員的內部交流。這種由家庭與當時大環境下帶來的結構性創傷導致杰里米在成長過程中十分渴望愛與關懷。這種愛與關懷的缺失也使他尋找各種方式來擺脫。因此杰里米最初通過與同齡人的父母交談來擺脫孤獨感,后來通過照顧侄女莎莉遠離自身的煩惱,隨后在上大學后通過與導師的交往來試圖擺脫縈繞心頭的失落感。但毫無疑問,這些嘗試最終以失敗告終。但幸運的是杰里米最終找到了方法,他通過婚姻結束了多年的鬧劇。杰里米與妻子結婚并孕育了4 個孩子,最終用愛改變了人生,救贖了自己。
三、瓊與伯納德的婚姻創傷體驗
麥克尤恩的婚姻之路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麥克尤恩在東英吉利大學認識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彭妮·艾倫。兩人婚后相敬如賓,但是由于信仰和思想觀念的沖突,二人于1998 年以痛苦的方式結束了這段婚姻。而麥克尤恩將這段婚姻經歷以及與妻子觀念的沖突帶來的創傷都投射在其小說中。
小說《黑犬》生動展現了三樁完全不同的婚姻,其中著墨最多的是杰里米的岳母瓊與岳父伯納德的婚姻。小說第一部分便講述了岳母瓊與岳父伯納德相知、相戀與相離的過程。兩人相識于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此期間共產主義思潮在西方受到人們的追捧。瓊和伯納德同時加入共產黨并希望建立一個理智、公正、沒有戰爭和階級壓迫的世界,共同的目標使兩個年輕人迅速陷入愛情之中。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兩人思想上開始出現隔閡,例如紅蜻蜓事件。事件的起因是伯納德在度蜜月途中于火車站的月臺周邊發現了一只紅蜻蜓,為了保持紅蜻蜓的美麗,伯納德決定用殺蟲瓶將它殺死并做成標本,但這一行為卻遭到了妻子瓊的反對。原因是瓊擔心殺死紅蜻蜓會對肚中的胎兒不利,而令人諷刺的是瓊最終誕下了擁有六指的女嬰。這次的爭執以瓊的妥協為結局,但卻為兩個人思想的分歧埋下了伏筆。而真正導致兩人感情破裂的卻是黑犬事件。瓊在度蜜月的途中遇到了兩條黑犬。據說這是“二戰”期間納粹遺留在此地,是戰爭余孽的化身。有孕在身的瓊,獨自與兩條黑犬對峙,最需要丈夫伯納德陪伴的時候,丈夫卻只顧關注昆蟲的動態。除此之外,伯納德在事后也只顧講述自己的觀察而無視妻子瓊的恐懼與無助。失望之余的瓊與伯納德再次發生激烈的爭吵。而正是與兩條黑犬的對峙使得瓊的理念與信仰開始發生變化,她開始相信上帝的存在。價值觀和信仰的不同導致伯納德和瓊爭吵不斷。瓊認為伯納德是典型的理性主義者,他只相信科學并只關心數據與事實,盲目地堅持“理性的社會工程能把人類從痛苦與殘忍的天性中解放出來”。而伯納德則懊惱瓊的神秘主義,他難以忍受瓊保護自我的宿命論與堅信獨角獸、樹精、天使和“我們內心的上帝”等事物的存在。兩人從此在精神上產生分歧并開始了分居生活。在小說中,麥克尤恩把理性和神秘主義的沖突轉化為岳父伯納德與岳母瓊的思想和信仰之間的競爭和沖突,而這種沖突是導致他們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這種由破裂的婚姻生活而導致的結構性創傷使得瓊希望獲得愛與關懷,因此她也不斷地尋找方式來治愈自己。幸運的是瓊從與自然的相處中得到了快樂,獲得了愛的力量。
四、戰爭陰影下的喪失性創傷
麥克尤恩關于創傷的寫作不僅與他自己的成長經歷密切相關,也與他所處的環境密切相關。麥克尤恩的父親參加過“二戰”并在敦刻爾克戰役中受傷,因此麥克尤恩的父親經常給年幼的麥克尤恩講述這段經歷。父親經常的講述使得麥克尤恩仿佛親身經歷過“二戰”并聲稱他們這一代“在二戰的陰影下成長,父母的故事占據了童年”。因此麥克尤恩將這段戰爭所導致的創傷經歷呈現在多部小說中。
小說《黑犬》的故事背景發生于1946—1989 年之間的歐洲社會。那時的歐洲正在“二戰”的傷痕中掙扎前行,整個社會動蕩不安。小說《黑犬》對多次戰爭及戰爭帶給人們的傷痛進行了描寫,例如美國侵略越南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給普通群眾帶來的影響等。其中小說中突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給猶太人帶來的創傷,其中著墨最重的便是參觀馬伊達·內克集中營這一具體事件。在結構性創傷中成長的杰里米不斷尋求各種方法來救贖自己,然而與未婚妻參觀馬伊達·內克集中營這個事件卻使主人公的創傷進一步加深。“在棚屋后的遠方,那座如一艘臟兮兮的、只有一根煙囪的不定期貨船的建筑,就是焚尸爐,正自由地在橙白色天空映襯的背景上浮動……進入一間小棚屋,看到屋內的鐵籠里塞滿了鞋子,有成千上萬只那么多……我看見一只釘有平頭釘的靴子,旁邊是一只嬰兒鞋,鞋子上溫順的小羊羔圖案仍然從塵埃中顯露出來。生命變成了廉價的貨品。”盡管敘述者語氣平靜,但是“焚尸爐”“鐵籠”“成千上萬的鞋子”等意象無一不透露出“二戰”期間納粹給猶太民族帶來的傷痛。
大屠殺事件不僅給猶太民族帶來了陰影,同樣還對沒有經歷過創傷事件的人產生了不安的影響。麥克尤恩并沒有直接描寫“二戰”帶給人們、社會乃至國家的傷痛,他借助沒有經歷過該事件的瓊與杰里米的視角委婉地指出“二戰”帶給人們的傷痛。參觀馬伊達·內克集中營這樣的事件,完全超出瓊與杰里米的理解范圍。弗里德蘭德和拉卡普拉均主張以文學虛構敘事和歷史傳記相結合的形式來表現大屠殺,這一觀點得到了麥克尤恩的贊同。在刻畫這個非同尋常的事件時,麥克尤恩將其與日常生活用品——鞋子聯系在一起以凸顯大屠殺的殘忍。這種再現不僅不會削弱大屠殺事件的獨一無二性,相反還彰顯了虛構敘事相較于傳統歷史現實主義的優勢。麥克尤恩用最簡單的圖像與直白的語言描述了“二戰”帶給人們的慘痛記憶。
這種由參觀馬伊達·內克集中營而導致的歷史性創傷使得杰里米的創傷進一步加深。幸運的是杰里米并沒有因此對生活失去希望,相反不斷地尋找方式來治愈自己。最終發現可以用真愛的力量來治愈創傷救贖自己。其實參觀集中營這一事件也表明了麥克尤恩面對戰爭時的態度:他反對戰爭,認為戰爭其實也是“黑犬”的化身,同時他也主張人們要直視歷史,超越歷史帶給人們的創傷。
五、結語
綜上所述,麥克尤恩在《黑犬》中結合自身經歷對童年缺失性體驗、失敗婚姻的經歷和當時時代背景下戰爭給人們帶來的痛苦遭遇等一系列創傷事件進行了重塑。這是麥克尤恩對個人、社會及時代背景的思考。小說中的主人公面對創傷并未失去對生活的信心,他直面創傷,積極地采取各種方式進行救贖。它也反映了麥克尤恩對創傷的思考和態度,即相信真愛可以改變和救贖人生。因此,對愛的訴求是這部作品的核心,也是麥克尤恩關于創傷寫作的核心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