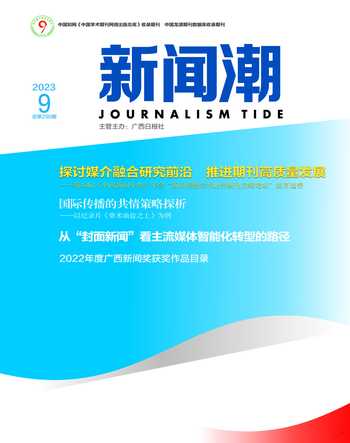鄉村籃球熱:貴州臺盤“村BA”儀式化傳播研究
郭瑜寧 范曉玲

【摘 要】2022年夏,貴州省臺江縣臺盤村一場籃球賽憑其火熱的觀賽氛圍在網絡傳播開來,網友們熱情地稱其為“村BA”。2023年“村BA”再次舉行,《人民日報》等多家主流媒體對其進行網絡直播,當地村民與網友通過現場觀賽與網絡直播共享別具一格的籃球盛宴。本文以“村BA”及相關大眾傳播實踐為研究對象,結合“儀式化傳播”的理論視角,分析“村BA”火爆背后的儀式化展演及契合鄉村振興的實現路徑。
【關鍵詞】儀式化傳播;村BA;傳統文化;鄉村振興
詹姆斯·凱瑞提出的“傳播的儀式觀”將文化研究帶入到傳播學領域。羅森布爾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儀式化傳播”這一概念,即大眾傳播活動的儀式化。“村BA”原本只是屬于當地村民的小型賽事儀式,網絡爆火后,大眾媒介及時跟進,這期間的傳播行為與互動展示出儀式化傳播的特點。
線上線下觀眾通過互動參與儀式,共享體育賽事帶來的激情與當地文化。還有一些觀眾以游客的身份到現場觀看比賽,以旅游消費等行為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村BA”展示當地傳統的民族文化與現代體育賽事文化的良好結合,兩種文化的交融展現出儀式化傳播的種種特征,帶給儀式參與者前所未有的文化體驗,當地也獲得了實打實的經濟效益。其他有共同點的鄉村,模仿當地的發展模式,借助儀式化傳播,也打造起自己的IP,助力實現鄉村振興。
一、儀式化傳播概念概述:作為儀式的傳播
從狹義上來說,儀式是發生在某種特定過程中的正式活動。這個意義受到早期的人類學家的青睞,他們普遍用儀式來指那些具有高度形式感的和非功利性目的的活動。廣義上,儀式可以指所有人類活動的表現形式。郭于華對儀式的定義是:“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所規定的一整套行為方式。它可以是特殊場合情境下莊嚴神圣的典禮,也可以是世俗功利性的禮儀、做法。”[1]儀式的本質即以象征符號為核心的人文活動。
詹姆斯·凱瑞受文化人類學、北美技術學派以及早期芝加哥學派理論影響提出“傳播的儀式觀”,將傳播分為“傳遞觀”與“儀式觀”。“儀式觀”認為傳播的本質是維系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的儀式性活動。他認為儀式觀才是傳播的起源與最高境界,這個境界就是建構并維系一個有秩序的、有意義的、能夠支配和容納人類行為的文化世界。[2]傳播的傳遞觀只關注傳播的淺層形式,而儀式觀真正體現傳播維系社會、共享意義的文化本質。
1988年,羅森布爾在《儀式傳播》中提出儀式傳播的概念。他將“儀式傳播”分為“作為傳播的儀式”和“作為儀式的傳播”。前者側重于儀式,指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社會行為;后者側重于儀式化的大眾傳播現象,即儀式化傳播。羅森布爾的“儀式傳播”中,包括“傳播的儀式觀”、日常生活中的儀式、“媒介事件”、具有儀式性的媒介使用行為、被儀式化的事件等。[3]“村BA”作為體育競賽,展現出儀式特征,在大眾媒體報道中展現儀式化傳播的特點。本文以“村BA”及相關大眾傳播活動為研究對象,以儀式傳播為視角,從儀式展演的條件、儀式展演的特點及現實意義進行分析,講述當地運用現代傳播技術結合賽事活動的方式弘揚傳統文化、構建村民精神文明世界、助力鄉村振興的過程。
二、“村BA”的儀式構建
臺盤村隸屬貴州省黔東南州臺江縣臺盤鄉,當地村民每年農忙過后會舉辦“吃新節”預祝糧食豐收,其中包括籃球賽,當地在“吃新節”舉辦籃球賽已持續幾十年。2022年夏,臺盤村籃球賽因為一條短視頻爆火,視頻中比賽盛況空前,附近的房頂上都站滿了球迷。極具鄉土氣息的賽事舉辦風格、村民們熱情的觀賽氛圍,吸引了廣泛關注,網友們熱情稱其為“村BA”,大眾媒體同時加入傳播進程中。
2023年“村BA”開始前,眾多媒體提前進行宣傳,電視關于“村BA”的一系列報道,抖音、微博等網絡平臺列出專門的詞條,受眾的點贊、留言等互動,這一系列行為都顯示出儀式化傳播的特點。受眾被大眾媒介邀請,通過媒介所傳遞的符號加入這場儀式的表演與互動。研究“村BA”的儀式展演過程,首先需確保其屬于儀式化傳播范疇。體育賽事傳播在主題、內容、類型、方式、場景等方面與大型儀式展演所需條件類似,且在儀式展演過程中有三條共性:時空性、象征性、參與性。
(一)時空性:特殊時間地點舉行
儀式有其特定的時間、地點和群體參與。籃球賽的舉辦地點設置在村子里的標準球場,比賽持續半個多月。臺盤村在“吃新節”舉辦籃球賽已有幾十年的傳統,據村民講已持續三代人。“很多儀式的產生,就是有一些很好的理由促使某些行為必須被重復,并被當成文化的或是習慣的模式傳承下去。”[4]幾十年的持續舉辦,早已讓在“吃新節”舉辦籃球賽成了儀式。媒體在報道過程中采取的策劃、宣傳,受眾的互動則構成儀式化傳播。
(二)象征性:符號貫穿整場儀式
符號即用來代表其他事物的象征物,由“能指”與“所指”構成。參賽球隊的隊名、服裝、隊標,比賽中所使用的籃球、計分板,勝者的獎品銀帽、繡片等都是一個個符號。這些符號在儀式中重復出現,且每個符號都具有象征性意義。計分板上的數字代表著哪一方接近勝利;籃球場地板中央“臺盤”兩字象征著比賽舉辦的地點,冠軍獎品苗族銀帽,制作精良、程序繁瑣,是對奪冠球隊的認可與獎勵,更彰顯了當地以苗族銀飾為代表的地方文化。比賽時,觀眾共同對儀式意義解讀,與其他人分享,經由大眾媒介的報道,符號傳播到遠方,被媒介受眾所認識并產生自己的理解。
表1可以清晰看出,比賽期間出現的各類符號及其象征意義,繡片、銀帽等獎品是當地民族文化的代表,作為獎品出現在現代體育賽事中,體現了民族文化與現代體育賽事文化的良好結合。
(三)參與性:主體共同構成儀式
不同學派由于關注點不同對儀式的意義的理解、解釋也就各不相同,但儀式首先被限定在人類的“社會行為”這一表述之上,這就意味著儀式需要主體的參與才能構成儀式。儀式舉行期間所需要的各種符號及其象征意義都是由人制作或賦予,沒有主體參與就無法構成儀式。在這期間,各村代表隊、現場觀眾、球衣的設計者與比賽的策劃者共同構成儀式的參與者。除了現場的參與者外,大眾媒介通過報道,使受眾通過媒介,也一同參與進“村BA”這一場儀式化傳播中。
三、“村BA”的儀式展演
儀式傳播研究的關注點之一是儀式傳播所展示出的特性。體育賽事向來是儀式傳播研究的關注對象,“村BA”及相關大眾傳播活動,不只是體育競賽,還有當地特色民族文化,展現出其作為儀式獨特的一面。
(一)民族符號貫穿賽事
傳播是符號和意義組成的社會傳播過程,并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維持、修改和轉化。因此,這一過程成為一種文化儀式,得以分享文化的意義。[5]比賽開場的民族服飾,繡片、苗族銀帽等獎品,每個符號都有其特定意義。奪冠球隊獲得的苗族銀帽作為勝利者的符號,背后就有其象征意義。銀帽由當地非遺技藝傳承人經復雜工序制成,重達1000克左右,銀帽上的飛禽走獸、花鳥蟲魚的圖案代表著當地的圖騰崇拜,把這當作冠軍的獎品,象征以苗族銀飾為代表的當地民族文化。
儀式化傳播過程中,象征符號占據了主要地位。這些符號不是簡單地傳遞到媒介受眾,而是經過精心的選擇、組合、排列,線上線下的觀眾都能夠接收到這些符號:“臺盤”兩字印在場地中央,介紹了比賽所在地,傳統的民族舞蹈在賽前暖場,有濃厚的當地民族文化特色,儀式化傳播過程中,這些符號被媒介受眾所接觸,通過互動認識背后的意義與文化,這些都是儀式展演過程中象征性的體現。
(二)表演展示傳遞意義
儀式是一種文化的表演,人類學家特納使用了“社會劇”以強調儀式的表演性。[6]“村BA”作為體育賽事具有很強的表演性與示范性,伴隨著儀式化傳播把這種表演帶給更多人。開賽前啦啦隊員身穿當地傳統民族服飾表演民族舞蹈,舞蹈就是當地苗族文化的一部分,通過儀式化傳播表演給了媒介受眾。比賽時球員的精彩得分、技巧動作,球隊得分反超,表演的則是籃球文化。半個多月的賽程期間,有時比賽過程中突遇降雨、地板濕滑,更增加比賽的激烈程度與不確定性。這些表演勾連了線上線下并形成了輿論熱點,吸引了籃球愛好者,獨特的民族舞蹈吸引了民俗文化愛好者、旅游愛好者前來參觀,這些互動,使得當地的形象得以呈現、文化得以分享。
(三)媒介助力促進互動
傳統賽事儀式通常需要親身經歷,并受到時空的雙重限制,但隨著技術發展,賽事可以做到線上和線下的儀式展演,個體通過互動加入儀式,交流分享賽事文化。“村BA”自2022年8月通過大眾媒介進入人們的視野,2023年3月27日,總決賽打響,人民日報新媒體、佛山看點等眾多媒體進行直播,使得更廣范圍的觀眾都可以加入儀式。
線上觀賽時,觀眾實時發送彈幕、評論等,這些內容會隨時間滾動、更新,且會被其他線上觀賽者查看、點贊、評論,以此來接近現場的“互動感”,從而完成對賽事文化的互動,加入儀式化傳播。休息環節表演民族舞蹈、展示特色獎品等,更是分享了本地的民族文化,觀眾在看籃球賽之外,還可以交流、分享對當地民族文化的認識、感受等,實現對文化的共享。
(四)情感連帶共享認知
傳統的體育賽事中,賽事愛好者更喜歡到現場看比賽,他們是儀式的眾多參與者之一,不僅因為現場可以激發更高的情感能量,他們還希望接近共同愛好這項體育賽事的人。[7]賽前宣傳、開幕式,現場外部和內部環境的儀式感讓現場觀眾有了儀式帶來的初步沖擊,現場解說、觀眾的吶喊,種種互動讓參與者的感官刺激被進一步放大。
蘭德爾·柯林斯在《儀式互動鏈》中提出“情感連帶”這一群體互動模型,認為群體的相互關注會增強群體間的情感。群體在不斷互動中,成員情感與注意力的相互連帶會讓其產生一種共享的認知體驗。[8]當比賽進行到激烈對抗階段,觀眾會感覺到激動、興奮,情緒被調動并伴隨強烈的傾訴欲望,身處其中,這種情緒會被持續放大,觀眾歡呼、吶喊與他人分享情緒。這種不斷地互動,觀眾都會把注意力更加集中在比賽上,通過對比賽中符號的認知從而共享“村BA”中所蘊含的籃球文化與民族文化。
比賽休息的環節會進行民族舞蹈的表演,其中的反排木鼓舞,已經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舞蹈動作靈巧活潑、矯健敏捷,記錄了苗族祖先不畏險阻長途遷徙、追求美好生活的故事。當線上線下觀眾達到情感連帶的狀態時,便能共享當地苗族居民這種特色舞蹈以及背后所蘊含的文化。
四、“村BA”的現實意義
(一)傳播民族文化
詹姆斯·凱瑞認為儀式不僅涉及生活準則及世界觀的融合,而且還具有互動功能,這一功能使它成為意義模式,而且還是一種社會互動的形式。[9]“村BA”通過這種互動,傳播了當地文化與籃球文化,構成自己的獨特形象。苗族銀帽、木龍舟、繡片等獎品,彰顯了當地特色,有些還使用非遺技藝制作。其中的繡片,可作為衣服的裝飾品,而且還用于擺設、收藏等,造型獨特。制作時有十幾種針法,如平繡、凸繡、辮繡、堆花等,藝術價值高。繡片以當地生產生活、傳說故事為內容,被譽為“身上的史書”和“穿著的圖騰”,有很強的表意功能。當地苗族的特色文化隨著儀式化傳播,讓更多人認識,參與儀式的籃球愛好者、對當地民族文化感興趣的人通過互動,對“村BA”以及當地的文化產生了認知、共享,當地的民族、地方文化也借此得以傳播。
(二)凝聚群體認同
對村民來說,盡管個體存在差異,但儀式傳播中的共識使得他們產生情感共鳴,使村莊在他們心中占有一席之地。[10]“村BA”舉辦時,一些村民參與比賽競技,一些村民負責組織后勤等工作,還有的到現場觀賽。大家本就生活在同一群體中,村民通過不同的方式參與比賽,強化了個體對群體身份的認同。在儀式化傳播的過程中,各個符號被傳遞給媒介受眾,但這些符號并不是簡單的意義疊加,而是在互動之中對符號進行了排列、組合,賦予其獨特意義從而構成文化的共享。
體育競賽的獎品一般是獎杯、獎牌,而“村BA”的獎品則是苗族銀帽、木龍舟、繡片。休息環節一般會進行啦啦隊表演、播出廣告,而“村BA”則是表演反排木鼓舞、苗族蘆笙、非遺古歌等。這些符號背后的文化意義,共同構成了當地對外界展示的形象。這種形象在儀式化傳播中觀眾認知、認同。當地的民族形象是中華民族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文化與現代體育賽事的結合,通過線上與線下的互動,當地村民、線上的球迷、對當地文化感興趣的人參與到儀式化傳播中,參與者的民族認同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一步增強。通過大眾傳播,群體凝聚力也從相對較小的群體擴展到更大的群體。
(三)助力鄉村振興
“村BA”已成為當地獨一無二的IP,成為知名的文化旅游名片,具有強大的符號價值。賽事儀式中,符號是承載著文化意義的“物”。儀式結束后,人會因為對儀式的認同進行相應的行動。比賽結束后,村民們不僅會在休閑時通過籃球娛樂,參與集體事務的熱情也會高漲,還有年輕人返鄉創業,從事體育與旅游行業。村集體開辦線下體驗店,銷售體現當地文化的文創產品,比如籃球印上有特色的圖騰蝴蝶、牛、魚等圖案裝飾。
2020年,臺江縣脫貧摘帽,經濟和基礎設施建設發展迅速,交通條件大為改善,還覆蓋了5G網絡。經濟發展和技術的支撐,把苗寨和外界的距離縮短,也讓“村BA”被大眾所熟知。臺盤村所在的臺江縣5年間在全縣各村寨修建了118個標準籃球場,臺盤村更是給球場安裝了照明設施,修建了看臺。早在2021年6月,“美麗鄉村”籃球聯賽作為貴州全省的賽事IP被正式推出,比賽以村為起點,再到縣、市。可以說,“村BA”的爆火并不是完全的偶然,這背后離不開當地的經濟發展與基礎設施完善。
借助“村BA”這一IP,當地政府打算把臺盤村的籃球文化和周邊村的特色產業串聯,發展好旅游產業,增加村民收入,助力鄉村振興。
五、結語
臺盤村沉淀了三代人的籃球文化,讓村民們在享受比賽的過程中,加強了村民的群體認同、情感的交流及凝聚力,增加了村民對家鄉的情感。通過儀式化傳播,讓原本參與范圍和影響范圍較小的賽事儀式成了參與范圍和影響范圍更大的“村BA”。在這個過程中,身在媒介另一端的觀眾與現場的觀眾共同參與到儀式當中,享受了比賽,了解了當地文化。還有部分觀眾選擇以游客的身份到當地現場觀賽、旅行等,帶動了當地經濟發展。其他有特色民俗活動的地區,可以參考臺盤村的發展模式,依托經濟條件與基礎建設的完善、政府的支持,借助儀式化傳播實現鄉村振興。
參考文獻
[1] 郭于華.儀式與社會變遷[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45.
[2] 陳力丹.傳播是信息的傳遞,還是一種儀式:于傳播“傳遞觀”與“儀式觀”的討論[J].國際新聞界,2008(8):44-49.
[3] 劉建明.“傳播的儀式觀”與“儀式傳播”概念再辨析:與樊水科商榷[J].國際新聞界,2013(4):168-173.
[4] 王宵冰.儀式與信仰[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45.
[5] 陳立勇.儀式觀視閾下的世界杯傳播[D].遼寧:遼寧大學,2011:13.
[6] 邵靜.媒介儀式:媒介事件的界定與儀式化表述——以我國的春節聯歡晚會為范本[J].浙江傳媒學院學報,2009(4):6-9.
[7] 高佳怡.儀式傳播視角下青年亞文化群體身份認同研究[D].西安:西北大學,2021:48.
[8] 柯林斯.互動儀式鏈[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31-36.
[9] 諶湘閩.詹姆斯.W.凱瑞傳播儀式觀研究[D].長沙:中南大學,2013:27.
[10] 楊逐原.儀式傳播中的意義生產及村落共同體的認同研究:以貴州省黔東南州占里村為例[J].貴州民族研究,2022(6):126-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