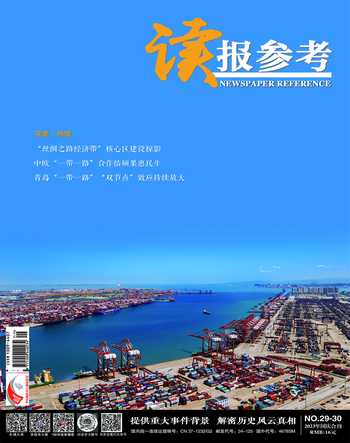逃離朋友圈,生活更好還是更壞?
盡管微信依然穩居“第一社交App”位置,但越來越多的人有了“逃離”朋友圈的想法。對待朋友圈態度之變,背后發生了什么?
朋友圈變工作圈
打開自己的朋友圈,齊整地排列著色彩相同、風格一致、標題很長的鏈接,簡潔而乏味——今年40歲的石先生,保持每周更新一條朋友圈——那是他供職企業微信公眾號更新的頻率。石先生在一家國企負責企業動態文宣,“微信公號剛開始的時候,企業各個部門都在做,但講的都是自己的工作,哪有關注度?現在干脆精簡成會議記錄和領導講話,更沒人要看了”。
點開這些鏈接,閱讀量通常只有兩位數。因為風趣幽默、能說會道才被選去負責這項工作的石先生坦言,自己在朋友圈就是個“無情的轉發機器”:“這是我的工作范疇,我自己再不轉怎么辦?”
當微信代替短信、電話成為主流的即時通訊工具后,許多人直言“朋友圈已不是朋友圈”。“從微商賣家到新接觸的客戶,陌生人見面連電話都不留了,首先就是加微信。”在上海陸家嘴一家金融機構工作的鄧蓉說,面對朋友圈中眾多工作上的聯系人甚至陌生人,她無法真正敞開心扉講自己想講的事,“轉發工作信息是最安全的”。在小紅書關于這一話題討論里,有人說“35歲以后就不要發朋友圈了”,還有人表示“不發朋友圈是成熟的標志”。
“我們的朋友圈就是工作場所。”曾在多家品牌從事銷售工作的艾德直言,正是因為騰訊財報所言“朋友圈使用時長同比大致穩定”,五六年前,艾德所在的品牌主要是讓銷售人員主動加有消費能力顧客的微信,鼓勵銷售“充分運用私域流量”。但朋友圈從此和店面一樣成了主管會查看的區域,“比如,我養了兩只貓,經常發些動態,主管覺得不錯,可以吸引客戶;但有次我回老家發了一組破舊的老屋,有人建議我刪掉,因為‘跟品牌調性不合”。如今,艾德工作的品牌要求他們用企業微信添加客戶,避免銷售跳槽帶走客戶,“這樣的朋友圈就純粹是賣貨廣告,更沒‘人味了”。
社交裂變的“修羅場”
“很多工作內容對我來說完全沒有信息量,更難受的是我看不到有個性、有血肉的‘人。”從事藝術推廣工作的姜女士曾經很喜歡看大學同學的朋友圈,“他像編輯一樣為我們選擇內容,再配以自己的觀點,往往一針見血”。不過同學考公“上岸”后,幾乎再也沒見過他在朋友圈發過這樣的內容。“偶爾深夜看他發些觀點,老朋友評論‘你終于回來了,結果早上發現他刪掉了。”
石先生很能共情這樣的行為,“你都不知道你朋友圈里藏了些什么人”。盡管微信在朋友圈也不斷推出分組、屏蔽、限時可見等功能,但“這些功能有時會帶來更大的尷尬”。石先生的同事曾使用分組功能,在朋友圈里吐槽合作方工作安排不合理、效率低下。誰知當天合作方就找到石先生,表示“不滿意可以在臺面上交流”。石先生幾經安撫打聽,才得知同事的朋友圈被截屏后傳給合作方。“現實中,我還能提醒大家不要傳話,但朋友圈里的聯系人環環相扣,只能說‘朋友圈里不盡是朋友。”
在一項相關調查里,即便還有約20%的人會在朋友圈發個人生活方面的內容,但許多“社交規則”也讓人感受到了不同。在小紅書的熱門話題里,有人吐槽朋友“跳贊”給自己帶來傷害。有網友編輯自己出游照片發布朋友圈,卻發現與自己交情頗深的老同學贊了其他人的同樣內容,卻跳過了自己發的朋友圈。
有人不喜歡被“跳贊”,就有人討厭“連贊”。有網友抱怨,自己剛發朋友圈,往往有一類人會立即點贊,這些點贊者幾乎會把朋友圈所有人發的內容都贊一遍。“我精心編輯的內容,希望得到共鳴、討論甚至是反對。這種看也不看每個人都贊一遍的人,讓我覺得自己很廉價。”
為了避免這樣的煩惱與尷尬,一些人選擇關閉朋友圈,轉向其他社交平臺。鄧蓉坦言,自己會將部分想表達的內容轉到小紅書上,“自己不發筆記,而是發在別人主題筆記的評論區里,因為數據關聯微信好友可能會在別的平臺也看到我”。即便如此,仍有人研究她朋友圈空白處的圖標,以確定自己不是被她屏蔽了。
近期經歷辭職、創業、再求職、換城市生活的影視從業者劉磊對這樣的變化很有感觸。一年半前,他關閉朋友圈,篤信“作品能說話”,然而再求職時卻發現與此前不少認識的人疏遠了。“不必把朋友圈看得那么復雜,其實就是獲取彼此信息的渠道。即便點贊之交,常常‘刷臉也是有用的。”重開朋友圈后,劉磊才知道高中同桌去年幾經艱難終于有了自己的孩子,自己卻一無所知。
在互聯網平臺研究流量動向的吳先生認為,從博客到朋友圈,人們對社交工具的需求總是從情感逐漸變為工具,“就像如今很多人懷念微博剛興起時公眾人物流露的真性情,如今似乎只剩廣告和正確的廢話。朋友圈也是這樣,當流量足夠龐大后,顯得‘無趣卻‘必要。未來會產生怎樣的社交工具,拭目以待”。
(摘自《解放日報》簡工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