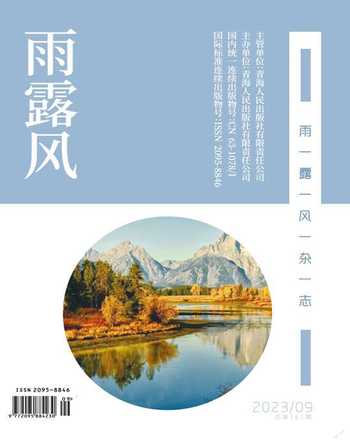論《十四行集》的成長隱喻
蔡雅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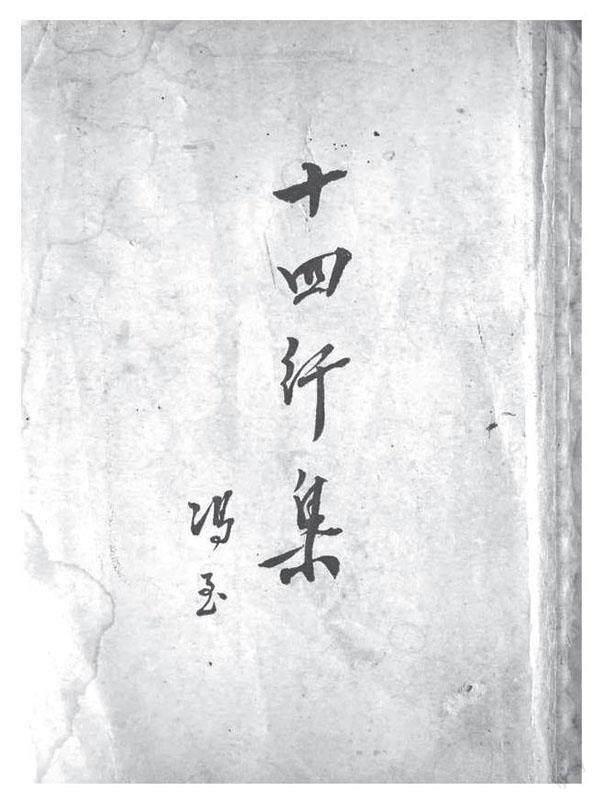
馮至(1905年—1993年)寫于20世紀40年代的《十四行集》是他自身創作歷程中的高峰。詩集展現了一個本真詩人在抗戰救亡、民族矛盾激化的現實中“借異鏡、磨己鏡”的努力,暗含著精神成長的隱喻。這種隱喻并不局限在修辭層次,而是一種認知現象,對詩人的思維方式、語言使用和作品氛圍構成主導性影響。本文將以《十四行集》為對象,探討馮至筆下“成長”之題的隱喻,從中分析詩人如何在時代動蕩中走向抒情的深化與自我身份的再確認。
一、成長命題的提出
受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年—1926年)、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年—1832年)影響,《十四行集》所做的工作是將日常可見化為不可見的奧秘,再化為可見的詩篇。而本文將重點探討從“可見”到“不可見”這一階段中詩人是如何挖掘世間秘密的。這一階段要求詩人不斷“走一條生的”(第26首)路,而走新路的前提就是追問、探索、期待、創造。1941年,馮至寫下的第一首十四行詩《一個舊日的夢想》正暗示了這種上下求索的精神。這種追問精神與這首詩中的“隕石”意象有關。作為石頭意象的一種,隕石本身帶有“堅硬、粗糙、蒼老等形而下的外形”。詩人便借隕石為舊夢賦形,完成由無形到有形的創造,讓隕石作為藝術中介物傳達夢與自我的沉默、堅硬與失落。詩人、舊夢、隕石三者合一,產生同頻震動。值得注意的是,這場交流即使在沉默孤獨中產生,也蘊含著一股新生的力量——石頭具有創世、誕生的色彩。馮至在寫成的第一首詩中提出隕石意象,顯示出靜極生動、無中生有的精神,暗示著《十四行集》是一場詩人不斷開鑿、思索與追問的精神成長之旅;也是人類不斷探索并吸收天地精華而成長的寓言:《十四行集》以“追問”重新審視自我、他人、存滅、來去、變化等困惑人類千百年的難題,接通屈原《天問》的探索傳統。例如“誰能把自己的生命把定/對著這茫茫如水的夜色”(第20首)等句。除直接的問句外,詩人還展示推演的過程,例如第15首為了提出“什么是我們的實在”這一問題,詩人從馱馬——貨物、水——泥沙、風——嘆息、鳥——天空、我們——山水等幾組關系中步步追問著。
在追問中,詩人處于從孤獨茫然狀態向自洽靜默狀態轉化的過渡階段。追問因此成為一種“儀式”。人類“成長”本身需要儀式,以此確立自己進入下一階段的身份。《十四行集》則以追問作為成長儀式,寫出人類思想、感情、智力、道德、精神等方面不斷走向成熟的各個階段,并指向無窮開放的境界;且能從一己而至于人類,《十四行集》的隱喻思維本身也帶著無限的延伸感。
二、成長寓意的深化
詩人所面臨的不同階段的歷練可簡單概括為:陣痛——頓悟——開放。
第一度成長,來源于考驗中的陣痛:詩人必須以“整個的生命”承受恐懼與別離。《十四行集》第一首即以“彗星”意象比喻個人要承擔的一切突發性事件:“我們準備深深地領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跡,在漫長的歲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現,狂風乍起(第1首)。”“彗”字的本義為“掃”,動詞,暗示了一種強烈的力量,這與馮至筆下“狂風乍起”的意境相通;而彗星在歷時性的語境中已成為災難的象征,詩人卻如“登九天兮撫彗星”(屈原《九歌·少司命》)一般,在恐懼、敬畏之中與突發事件同在。他用“承受”“深深地”等詞表示自己生命的阻滯,只為迎來“更加強烈的噴射”(康德語)。詩人就在毀滅與誕生相互轉化的辯證法中開啟了《十四行集》;故而第一首詩作為詩集序曲是言之有理的。除了“彗星”降臨的考驗,詩人還在威尼斯憂慮孤獨、在原野上聆聽啼哭、在馱馬隊伍中思慮、在狂風暴雨中的小屋驚顫;他“憂患重重”……此刻詩人處于不成熟的階段,他的問題充滿了困惑與憂煩。
第二度成長,源于生命走向澄明之前的頓悟。詩人在物(有加利樹、鼠曲草、小狗、靜物)與人(蔡元培、魯迅、杜甫、歌德、梵高)的啟迪中發問,獲得了真理體悟:宇宙萬物、自然本身有一種靜默運行著的秩序,它“好像宇宙在那兒寂寞地運行”(第13首)。在詩人看來,這種脫離語言而存在的秩序首先運行在一個凝固的時間里——瞬間化入永恒或永恒凝為一瞬。詩中小昆蟲交媾的瞬間、我們擁抱的一刻是瞬間進入永恒;無時無刻不在生長與脫落的有加利樹、沒有停息的啼哭、“只感受時序的輪替,感受不到人間規定的年齡”則是永恒化作瞬間。詩人的這種觀念與中國傳統農耕型社會安土重遷的穩定性有關。中國古代傳統抒情詩成就高于敘事詩,也是由于受到這種循環生存經驗的影響。然而,《十四行集》卻并未走向傳統的抒情詩。這是因為馮至在西方線性時間觀影響下將“時間”重新闡釋,達到過去、現在、未來的統一:“寂寞的兒童,白發的夫婦,還有些年紀輕輕的男女,還有死去的朋友,他們都給我們踏出來這些道路;我們紀念著他們的步履,不要荒蕪了這幾條小路(第17首)。”對于馮至而言,真理就存在于凝固循環與線性前進辯證統一的時間中。
在物理空間上,詩人認為真理存在于自然界之中。他呼吁“不應該把些人事摻雜在自然里面”,即人對自然應保持緘默,不妄下判斷。正如海德格爾認為要“讓存在者成其所是”。這種態度投射到詩歌創作中,即是一種“靜默”的心理動作。首先,詩人以靜制動。他面對自然時總是保持著觀察順應、禱告祝福的沉潛姿態而非無限的擴張、解放。不管是“我們安排我們/在自然里,像蛻化的蟬蛾”(第2首),還是在阡陌縱橫的田野上,視有加利樹為引導、向鼠曲草祈禱,人勞碌著的占有意志都得到暫時休息。其次,詩人還能以靜促動——以靜默之力促進自然呼吸之律動。例如“我們聽著狂風里的暴雨,我們在燈光下這樣孤單”(第21首)、“深夜又是深山,聽著夜雨沉沉”(第22首)表示自然間一切都在沉淀、醞釀,到了頂點才開始釋放,“一天雨云忽然散開,太陽光照滿了墻壁”(第23首)“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語聲/在我們夢里是這般真切……是我自己的生命的分裂,可是融合了許多生命,在融合后開了花,結了果?”(第20首)。也寫出積聚后的分裂,還有不斷向上生長的有加利樹和不斷向下沉埋的死者,自然就處在這積聚與釋放、擴張與收縮的永續循環中。一虛一實,有無相生,萬物由此而來。如《逍遙游》里所說“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人也在自然浩大的吞吐之間獲得生命——“我們的生長、我們的憂愁/是某某山坡的一顆松樹/是某某城上的一片濃霧”。最后,自然通過呼吸與眾生進行訊息交換。例如自然將光明信息帶給初生小狗;吸進的氣體“在身內游戲”(第25首);但我們的生長與憂愁也在呼吸間傳給自然,“隨著風吹,隨著水流,化成平原上交錯的蹊徑”(第16首)。由此讀者可以想象,《十四行集》背后蘊藏著一股由出納、隱現、聚散等變化形成的恢弘氣勢與吞吐力量。
三、未完的成長歷程
那么,這種存在于時、空中的秩序是什么?正如許多學者指出的,是脫落與生長同在;是通過否定重塑自我;是與宇宙萬物聯結、溝通;是在蛻變中進入永恒……這些秩序有什么意義?1942年,馮至在《昆明日記》中寫道:
“戰爭把世界分割成這么多塊彼此不通聞問的地方。兩三年來,到過這山上來的朋友們其中已經有一些不能通音訊,而且有的已經死亡。對著和風麗日,尤其是對風中日光中閃爍著的樹葉,使人感到一個人面對著一個宇宙。”
可以說,秩序的意義正在于聯結孤獨的個人和曠遠的宇宙。實際上,個人也是一個小宇宙。《十四行集》則進一步展現大宇宙對小宇宙的吸引力——“我們不知已經有多少回//被映在一個遼遠的天空”(第20首)。故而詩人喊出“給我狹窄的心/一個大宇宙”(第22首);并時常回憶起來自宇宙母體的原始記憶“海鹽在血里游戲——睡夢里好像聽得到/天和海向我們呼叫”(第25首);有加利樹插入晴空、永向蒼穹才能“升華了全城市的喧嘩”(第3首)。詩人還以“彗星”“星辰”“星秩序”“隕石”等天文意象,展現對于宇宙精神、宇宙運行規則的向往;又以“長庚”“啟明”隱喻蔡元培、以斷線“紙鳶”形容戰士。從表面而言,戰士凋落了;但實際上, 詩人指出墮落的人們已不能“維系住你的向上,你的曠遠”(第9首)。在《辭源》中,鳶為古代一種猛禽之名。“不能維系”與猛禽的內涵相通,傳達出掙脫束縛、向大宇宙而飛的渴望與人的遼闊天性。這種永遠向上的姿態才是成長的第三階段。總之,當詩人一個人對著一個大宇宙,其背后的精神狀態并不會永遠停留在孤獨茫然上,而是永恒的眺望與向往。最后一首十四行詩中的“奔向遠方”“但愿”等語正暗示了這種動態開放的神圣之旅。
同時,從整體解讀《十四行集》,會發現這三度成長在詩集中并不是線性鋪開而是糾纏難分、反反復復的——成長之路向來迷途遍布。例如,在第6首詩中,詩人將啼哭、絕望作為負面因素納入敘述,顯示心靈的掙扎與愁慮;但在第3首詩中,詩人通過有加利樹又看到了脫落衰敗與成長壯闊的對立統一。它的生長越過單純的時空,邁入廣闊的宇宙——向四周敞開,又把有關聯的一切聚攏于自身,構成了一個整體。在這個整體中,有誕生和死亡、災難和祝福、勝利和恥辱、堅韌和衰退……有加利樹由此成為宇宙萬物命運的象征與撫慰人心的力量。在第21首詩中,暴雨又“把一切又淋入泥土/只剩下這點微弱的燈紅/在證實我們生命的暫住”。詩人便試圖從微渺的命運中走出,在愛情、親密、夜晚三維構成的時空中,認識到自己暫時的生命中也“藏著忘卻的過去、隱約的將來”(第18首)。正是這種能力給了詩人一種前所未有的自信和驕傲,堅信能“在深夜吠出光明”(第23首)。總之,“奔向遠方”的渴望與反復曲折的磨練激發出詩人向死而歌的勇氣,也提示著成長永續、未完的狀態。生存真諦最終在這種精神化時間、空間中翻騰延續。可見,在《十四行集》中,詩人是以對生命“內在的信心”對抗焦慮孤獨的生存體驗,使之不流于過分的感傷虛無或矯揉造作;另一方面,又以衰敗、寂寞、死亡作為人生的底色,使樂觀的信念不過于浮淺。這讓詩集既沉痛又曠遠,既灑脫又執著,既苦澀又明凈,既日常又玄妙,展現出馮至不同于王國維、郭沫若、李金發、穆旦、海子等人的精神氣質。
四、結語
《十四行集》在追問中成長,并以開放性的姿態指向一個盤旋蜿蜒不斷向上的詩國,擺脫了早期現代漢語詩歌抒情泛濫、流于感傷或說教的傾向,走向沉穩而有節制的深度抒情。有學者指出,馮至“建立了另一片形而上詩國:積極、溫馨、寧靜,對生命持有內在的信心,對世界懷有廣大的同情,他的形而上觀念呈現一種積極的建設姿態”。而本文認為,這種積極的建設姿態正來自于《十四行集》由隕石意象、追問姿態而延伸出的成長主題。鄭敏師承馮至,她的詩歌也傾訴成長的渴望:“一個靈魂怎樣緊緊把自己閉鎖/而后才向世界展開,她苦苦地默思和聚煉自己/為了就將向一片充滿了取予的愛的天地走去。”從馮至到鄭敏,追問、沉思、掙扎、成長相互融合,讓中國現代詩歌中形而上的訴求不至于過分流連虛無、陰暗與懷疑,而多了幾分向死而生的勇氣。
在朝不保夕的戰爭年月,死亡成為更加突出的問題。但馮至“向上”成長的姿態并非遠離時代、固守在西南聯大的象牙塔中,反而是為了“向下”潛入時代深處,走出早期的浪漫,避開浮淺的叫喊,在詩歌內部挖掘與時代崇高相呼應的質素、與時代卑污相抗衡的力量。詩人就在與時代的疏離與緊貼中完成自我身份的確立:他和他的時代是共生與對抗的。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和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都曾有過類似的觀點:同時代就是不合時宜。這種反叛者的身份也貫穿著馮至的一生。在馮至1991年寫的詩歌體自傳中,“自我否定”是一個關鍵詞。如上文所述,詩人是一塊隕石,開鑿的力量正來自內部的否定。由此撬開的身心裂縫是促成馮至吸納外部訊息、自我成長的重要力量。“他一生都在省審,都在尋求精神的故鄉,都在與自己身上的孤獨、怯懦作斗爭。不斷克服,使他總是從人生的一個境界達到另一個境界,正像他自己講的在停留中有堅持,在隕落中有克服。盡管有時這些克服仍為后來的克服所否定,但整體的過程卻顯示了一個現代知識者獨特的精神軌跡,創造了生命的內在價值和意義”。從《十四行集》到馮至“未完成的自我”,都向讀者昭示:人類永遠踏在一條開放性的完善之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