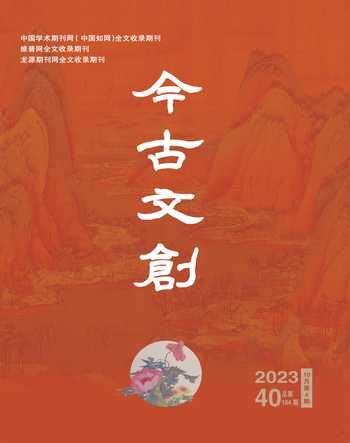《墨子·尚同》中“尚”字的英譯探究
唐楊

【摘要】在《墨子》英譯中,由于原文本保存不善和語言晦澀,英譯者往往需要借助校勘本來完成翻譯,然而不同校勘者的訓詁也可能會指向對文本的不同理解。本文以《墨子·尚同》三元組標題中的“尚”為例,考察了7個《墨子》英譯本中的處理差異,并結合校勘本選取和翻譯結果來探討典籍翻譯中校勘本和譯者的關系。
【關鍵詞】《墨子》;典籍英譯;校勘本;尚同
【中圖分類號】H059?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40-011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0.035
墨家十論又稱墨家十大主張,在先秦時期是墨子思想體系中的專屬詞匯。它們也是《墨子》十個核心章節的標題,往往一個詞就涵蓋了《墨子》中一個三元組的要點,是對墨家思想一個論點的整體歸納。其翻譯既以小見大地反映了譯者本人對于《墨子》篇章的理解,也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英文讀者對于墨家主要思想的把握。研究墨家十論的翻譯,有助于探究譯者對于《墨子》思想的理解,也有助于探討《墨子》英譯中面臨的問題,進而促進墨子思想在海外的準確傳播。本研究將以《墨子·尚同》的標題為例,呈現現有7個《墨子》英譯本中對“尚同”中“尚”的翻譯,從校勘本和譯者的關系來探究不同譯本間差異產生的原因,并據此為將來的《墨子》譯者提出借鑒和參考。
一、七個《墨子》譯本介紹
迄今為止,包含墨家十個核心章節的《墨子》英譯本共9本,綜合各譯本的代表性和其中“尚同”翻譯的差異性,本文選擇了7個《墨子》譯本作為考察范圍,它們的譯者分別為:梅貽寶,華茲生(Burton Watson),汪榕培和王宏(下文簡稱WRP&WH),李紹崑(Cyrus Lee),艾喬恩(Ian Johnson),諾博諾克和王安國(John Knoblock& Jeffrey Riegel,下文簡稱JK&JR)以及方克濤(Chris Fraser)。
1929年,在海外留學的中國留學生梅貽寶在《墨子的倫理和政治學說》(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Works of Motse)中節譯了《墨子》現存53篇中的36篇,其語言保留了原文的典雅和嚴謹。1963年,著名美國漢學家華茲生(Burton Watson)的《墨子》節譯本Mo Tzu: Basic Writings出版,其作品主要節譯了《墨子》中表現政治和倫理的部分,且對原文章節多有刪減。2006年,中國譯者汪榕培和王宏合譯的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Mozi面世,這是全世界第一本《墨子》全譯本;2009年,美籍華裔學者李紹崑(Cyrus Lee)完成了《墨子》的全譯本The Complete Works of MoZi in English。2010年,艾喬恩的《墨子》全譯本The Mozi: A Complete Translation出版,艾喬恩作為一名學者,對先秦思想頗有研究,其譯本引起了海外研墨學界的高度關注,著名墨學家紛紛為之作評。同年,漢學家約翰諾博諾克和王安國(JK&JR)合譯的《墨子》節譯本接踵而至,諾博諾克對先秦文學頗有研究,此譯本也是其墨學研究的一個總結性產物,漢學家戴卡琳在其書評中稱贊此書很好地融合了當時墨子研究的新成果。2020年,西方哲學家方克濤為了向廣大學生和哲學家們推廣墨子哲學思想,出版了《墨子》節譯本The Essential Mòzǐ: Ethical, Political, and Dialectical Writings Mo Zi,在該譯本中他以墨家哲學思想為主線對原文進行了刪減,該譯本融合了作者近幾十年的墨學研究結果。
在上述7個譯本中,既有年代較為久遠的譯本,又涵蓋了最新的譯本,既包含海外譯者的譯本,又包含中國譯者的譯本,還有西方譯者和國內機構合作的譯本,這使得本文的翻譯考察范圍不僅在時間上跨度較大,在譯者的文化身份層面也較為豐富,這有助于呈現《墨子》譯本的多樣性。
二、《墨子》譯本中有關“尚”與“上”的爭議
“尚同”是墨家十論中的第二個主張,也是《墨子》核心章節中一個三元組的標題,書中分上中下三章對這一主張展開論述,三章均保存完好。
盡管林清源曾提到:“戰國時期思想類文獻罕見書寫標題語,且其標題格式似乎尚未形成嚴格規律。”[1]并據此懷疑《墨子》一書中標題的合理性,但多數學者仍認為,墨家十論足以概括墨子的基礎思想。加上“尚同”這一表達本身在《墨子·尚同》的正文部分出現頻次較高,出現了28次之多,因而“尚同”一詞在墨子思想中的重要性幾乎毋庸置疑。在《墨子·尚同》三元組中,作者先論述了天下的混亂起于“人異義”,認為結束混亂的方式就是使人“尚同一義”,并從鄉、國、天下等維度層層論證“尚同一義”的重要性。從本三元組講述的內容來看,“尚同”這一標題在這三章也確實具備提綱挈領的地位。綜上所述,“尚同”這一標題能較為準確地傳達《墨子·尚同》篇的思想,作為墨家十論之一,其翻譯對于墨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也至關重要。本研究收集了上述《墨子》7個譯本中對于《墨子·尚同》這一三元組的標題翻譯,分別得出了以下7種結果:
從“尚同”一詞的最終翻譯結果來看,七位譯者對于“尚同”中“尚”的理解存在著差異,即“尚同”中的“尚”究竟是指“尚”,還是指“上” ?其次,如果此處的“尚”是指“上”,那么進一步而言,“上”是指方位詞“上”,還是指代名詞“上位者” ?
針對第一個問題,譯者們的回答分為了兩類。第一類譯者,諸如梅貽寶、華茲生、WRP&WH以及方克濤都將“尚”理解為“上”。不同的是,方克濤將“上”理解為方位詞“上”,并將其譯為“upward”;而余下三位譯者則將“上”理解為“上位者”這一名詞的指代,并同時使用了“superior”一詞。在這之中,三位譯者對于“上位者”的理解又存在著細微的差別,即華茲生所言“上位者”是每個人自己的上位者(One’s Superior),而余下兩位所指似是一位唯一且眾所周知的上位者(the Superior)。因而前者的“One’s Superior”可以指向低層級的上位者,如原文中提到的“鄉長”“國君”,而后者所言“the Superior”卻只能限定于“天子”甚至“天”這樣的唯一存在。第二類譯者,也即李紹崑、艾喬恩以及JK&JR,他們的譯本都將“尚”闡釋為“崇尚”,“同”理解為名詞。李紹崑將“尚同”譯為“Esteem of the Identified”,根據牛津字典和柯林斯字典,esteem意為“尊重、推崇”(great respect and admiration);艾喬恩和諾王都選擇了“exalt”一詞翻譯“尚”,含有“高度評價某物”(to praise something highly)之義。
由此可見,一個“尚”字激起了譯者們的種種考量。一些譯者在其譯本中明確表達了自己對“尚同”含義的疑惑和分析。梅貽寶在其譯本中提到:“校勘者們都認可將其闡釋為‘上同’(Identification with the Superior)。但從文章的內容來看,或許兩種解釋都可行”。[2]JK&JR的譯本中也提及了這一點:“原文中‘上同而不下比者’這樣的表述似乎表明,‘尚同’應該被理解為‘上同’(conformity with superiors或upward conformity)。但當‘尚同’單獨使用,作為一個主張的名字;或當它與‘一義’(unify standards)并列,用來指兩個互補的學說時;以及當它作為三章的標題時(顯然是基于上述用法),此時它應理解為‘尚同’(exalt conformity)。”[3]
綜上所述,在翻譯“尚同”這一標題時,譯者們參考了已有校勘本的意見,以及該表達在文本中的使用情況等因素來確定“尚同”的譯法。接下來,本研究將基于對以往《墨子》校勘本的考察和對《墨子》原文本的分析來解讀“尚同”的內涵。
三、校勘本中對于“尚”與“上”的探討
由于《墨子》在流傳過程中破損嚴重,如今譯者們在翻譯《墨子》時多據某一個或幾個《墨子》校勘本。學者聶韜早已注意到《墨子》英譯中校勘本對譯本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其研究對現有《墨子》英譯中大部分譯本所選取的校勘本進行了考據。[4] 據其考證,梅貽寶與華茲生的《墨子》英譯本都以孫詒讓的《墨子間詁》為標準底本;WRP&WH的英譯本中以周才珠和齊瑞端的《墨子全譯》為中文對照;李紹崑在參考文獻中列出了自清以來《墨子》的主要校勘本,并未指出所據核心底本;艾喬恩以吳毓江的《墨子校注》為主要參考對象;JK&JR以《墨子間詁》和王煥鑣的《墨子校釋》為主要底本;方克濤則主要參考了《墨子間詁》和《墨子校注》兩個版本[5]。因而,本研究也主要考察了上述校勘本中對于“尚同”這一標題的探討,此外還考察了這些校勘本中“尚同”與“上同”的用法。
據考察,《墨子間詁》[6]與《墨子校注》[7]在《墨子·尚同上》中均引用了《漢書·藝文志》、畢沅等人的說法,認為標題中的“尚”通“上”。然而收錄于《墨子大全》中的《墨子校釋》和《墨子全譯》并未沿用這一說法。首先,這兩個校勘并未引用此前校勘本中“‘尚’同于‘上’”的說法。其次,二者均在篇首對“尚同”思想進行了解讀,前者對“尚同”與“上同”的使用進行了區分,分別用于“尚同說”和“上同于(某人/某物)”這兩種搭配[8];而后者則強調,“尚同”不是“上面”或“長官”的一言堂,而要逐級向上統一,直到統一于“天”,而此鏈條上除“天”以外的上位者都不能隨心所欲[9]。這些校勘本中均保留了“尚同”與“上同”兩種表達在正文中并存的格局,且四個校勘本中二者的用法和出現頻次無異。
由上可知,前兩個校勘本都認可將標題中的“尚同”解讀為“上同”,而后兩個校勘本至少沒有明確支持這一解讀。從譯本與校勘本的對照來看,以前兩個校勘本為主要藍本的梅貽寶、華茲生、方克濤都選擇了將此處的“尚”解讀為“上”。而參照多個校勘本的李紹崑、艾喬恩以及JK&JR則保留了“尚同”的字面含義。WRP&WH版的《墨子》英譯本在這一點上并未認同其所附的校勘本。接下來,對于《墨子校釋》中對于“尚同”和“上同”的用法區分,本文將回置到《墨子》原文本語境,尋找根源。
四、基于《墨子》原文本的“尚”和“上”的考察
在該三元組中,“尚同”在正文中共出現了28次,其中“尚同其上”“尚同乎/于(上位者)”出現了11次,“尚同一義”出現了5次,“尚同為政”出現了5次,“尚同之(為)說”2次,余下還有“尚同之功”“尚同者”等形式。文中“上同”共出現了8次,其中有4處在與“下比”相對照,4處為“上同乎/于(上位者)”的形式。由于文中存在“尚同其上”中“尚”與“上”連用,且在與“下比”相對照時,文中從未通假為“尚同”,可以推測,原文對于“尚”與“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意義區分,且在明確與“下”相對時,只用“上”。盡管在“尚同乎/于(上位者)”和“上同乎/于(上位者)”中,“尚”和“上”存在約通共用的可能性,但“尚同”作為為政之策,為政之說時,從未與“上同”互換,再次證實了“尚同”與“上同”并不等同。這一現象與《墨子校釋》中對兩種表達用法的區分相符。
要理解《墨子》中“尚同”的含義,還需要明白墨子所謂“同”的對象。在三元組開端,作者就提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曰「人異義」 ……天下之亂,若禽獸然。”作者認為,天下之亂起于“人異義”。因此要解決天下亂象,就要改變“人異義”的現狀。接下來的數段中,作者討論了鄉、國、天下三個維度的治理,每段皆以“察鄉(國/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壹同鄉(國/天下)之義,是以鄉(國/天下)治也”作結。在作者看來,治理地區亂象的根本在于要“一同地區之義”。在《尚同下》,作者又分家、國、天下三個維度分別討論了治亂之術,三次討論均以“然計若鄉(國/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為政故也。”由此可見,作者最終強調的并非“上位者”的存在,而在于“尚同一義”。對此,吳根友和丁銘也有所闡述,他們認為“‘上同于天’的命題,其實質還是‘上同于義’”[10] ,這一論斷與《墨子全譯》中的理解相互印證。
綜合上述討論,盡管眾多校勘者和譯者認為本章“上”和“尚”是意義相同的通假字,經過對二者出現頻次和語境的詳細考察,卻能看出原文對二字的用法確有區分。在“尚同”這一主張中,作者所強調的“同”的最終指向并非上位者,而是“義”。世人最終要達到的是“尚同一義”即“與天同義”,而每個階層內部和之間的“上同”更像是通往最終目的“同一義”的過程。另外,“同”這一概念也出現在了儒家學說中。《論語》中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知,儒家學派對“同”這一概念頗有微詞,認為“和”比“同”更接近君子品質。此處的“尚同”或許也能如“非樂”“節葬”般,看作墨子站在自己的視角對儒家觀點提出的又一種反駁。
在上一節的校勘本考察中,《墨子校釋》否認了將“尚”解讀為“上面”和“上位者”的說法;《墨子全譯》肯定了“尚同”與“上同”用法的差異。本節基于原文本的考察也證實了這兩個校勘本中的主張。結合原文本、校勘本以及譯者的意見,筆者更傾向于將標題中的“尚同”中的“尚”理解為其本意,而非“上”的通假字。
五、結論
本文首先注意到了7個《墨子》譯本對于“尚同”標題翻譯的差異,進而回到了譯者們所依據的校勘本和《墨子》的原文本中尋找分歧的根源。在考察校勘本的過程中,本文發現,“尚”與“上”的討論在校勘本中就已存在,而從譯本與校勘本之間的對應關系來看,校勘本的選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譯者的理解和判斷。因而對于《墨子》這樣內容解讀存在爭議的文本,選擇更為全面的校勘本或多個校勘本對照閱讀,將有助于譯者準確理解原文并給出合適的譯文。此外,校勘本雖然是歷代學者的心血之作,但仍只是一種可能的解讀,攜帶著校勘者自身的時代和認知局限。在“尚同”英譯一例中,梅貽寶和JK&JR都在遵循校勘本的同時,還留下了自身對于原文本的理解和思考,這一舉動使得其譯本有了超越校勘本的局限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1]林清源.簡牘帛書標題格式研究[M].臺北:藝文印書館,2004.
[2]梅貽寶.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Works of Motse[M].London:Arthur Probsthain,1973.
[3]Knoblock,J.and Riegel,J.Mozi: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of 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Writing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13.
[4]聶韜,陳璐.有意即取舍,無意為誤釋—— 《墨子》校勘本的差異性對譯者的影響[J].中國翻譯,2021,42(04):124-132.
[5]Fraser,C.The Essential Mòzǐ:Ethical, Political,and Dialectical Writing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
[6]孫詒讓.墨子間詁[M].北京:中華書局,2021.
[7]吳毓江.墨子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3.
[8]王煥鑣.墨子校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9]周才珠,齊瑞端譯注.墨子全譯[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
[10]吳根友,丁銘.“共同善”視角下墨子“尚同”思想新解[J].哲學動態,2022,(03):45-54+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