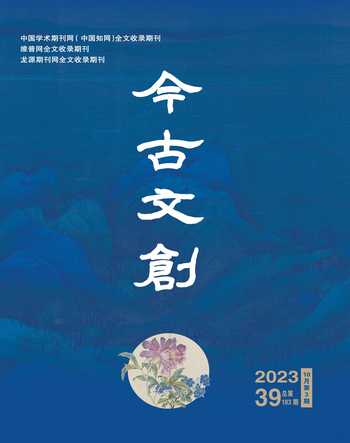論邵麗“ 掛職系列 ”小說的非虛構特征
【摘要】邵麗的“掛職系列”小說,是指邵麗在掛職期間及其以后創作的以反映人民生活和書寫時代憂思為主要內容的系列作品,在非虛構寫作風靡文壇的當下回望該系列小說,可以發現該類小說中作家多擔任行動者的身份、小說敘事視角多為第一人稱敘事,主題思想則自覺反映時代憂思,小說顯示出頗具特色的非虛構寫作特征。
【關鍵詞】邵麗;非虛構特征;“掛職系列”小說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39-004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9.014
20世紀80年代,隨著董鼎山教授將非虛構一詞引進中國,“非虛構”文學開始在中國落地生根,2010年伴隨著《人民文學》建立了“非虛構”專欄,非虛構文學正式受到廣泛關注,并由此形成了創作熱潮。人民日報將非虛構寫作計劃命名為“人民大地·行動者”,計劃的宗旨是“以‘吾土吾民’的情懷,以各種非虛構的體裁和方式,深度表現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層面,表現中國人在此時代豐富多樣的經驗。” ①該計劃特別指出,“不僅要求作者對真實的忠誠,要求作品具有較高的文學品質。還特別注重作者的‘行動’和‘在場’,鼓勵對特定現象、事件的深入考察和體驗。” ②而目前學界針對“非虛構”的學術性定義仍在討論中,但整體上分為兩類:一是以王暉等人為代表,認為“‘非虛構’是相對于‘虛構’而言,不僅僅是一種具體文體的寫作,而是一種文體類型的集合” ③;二是以張文東等人為代表,認為“非虛構”是一種創新的敘事策略或模式。
學界針對“非虛構寫作”的定義仍處于討論與爭辯中,但隨著大量“非虛構寫作”的典型文本的出現,其特征已較為確切,即以“作家的行動和在場性”“第一人稱敘事視角的下移性”以及“走向吾土吾民,深入考查和體驗特定現象和事件的為人民的屬性”為主要特征。邵麗的“掛職系列”小說是作家邵麗深入基層后的創作——主要指的是邵麗在掛職期間及以后,發表的十幾篇既反映官場生活,又揭示底層生活的作品。其中的中篇小說《劉萬福案件》(2011年)、《第四十圈》(2014年)和短篇小說《村北的王庭柱》(2010年)、《掛職筆記》(2011年)、《老革命周春江》(2011年)五個篇目的非虛構特征尤為明顯。
本文針對邵麗掛職系列小說中的非虛構特征的研究主要以張文東等人關于非虛構寫作的觀點為基礎,并以《人民文學》針對“非虛構寫作計劃”的命名為關鍵詞展開研究,試圖從敘事策略角度分析邵麗掛職系列小說中的非虛構特征,并理解作者在“掛職系列”小說中的求真理想。
一、“行動者”——書寫掛職生活體驗
2005年至2007年邵麗以副縣長的身份在河南省汝南縣進行了掛職鍛煉,這段工作經歷直接促使了作家寫作動機的生成,并對邵麗的創作風格產生了重要影響。邵麗曾說:“如果你專門去體驗生活,實際上那不是你的生活,而是你生活之外的生活。” ④她在《掛職筆記》中提道:“作為一個小說家,當我被派往一個百多萬人的大縣掛職副縣長體驗生活時……那時候我顯然以為,掛職的意義不在于職,而在于掛。我是確確實實被掛在生活之外了。” ⑤而即使是“掛在生活之外”的體驗,依然賦予了邵麗“行動者”與“在場者”的身份來觀察基層官場與人民生活——邵麗因此能夠站在更為客觀的立場來觀察她周圍群體的真實生活狀態,這段經歷成為她實現非虛構表達的基礎。在非虛構寫作中,有作家認為“誰來寫比寫什么更重要。” ⑥這不僅是對非虛構寫作中寫作主體“行動者”和“在場者”身份的強調,更是對寫作主體自身素養的要求。近年來伴隨著“非虛構寫作計劃”的出現,以梁鴻等作家為代表性創作出典型的底層非虛構作品的熱潮,眾多文學愛好者進入了非虛構寫作的隊伍中,與此同時非虛構文本的文學性也逐漸受到熱議,而邵麗的“掛職系列”小說的產生前提是寫作主體以作家身份來體驗掛職生活,其“在場者”和“行動者”的身份使其占有了第一手寫作資源的同時產生了寫作動機,因此其“掛職系列”小說實現了“在場者”的非虛構表達。
二、“大地”——第一人稱敘事視角的下移
第一人稱敘事與非虛構小說并不存在直接關聯性,但于非虛構寫作的作家而言,以第一人稱敘述能夠更好證實其“在場者”和“親歷者”的身份,第一人稱視角的敘事增加了事件本身的真實感與作家表達的真誠感。在《村北的王庭柱》《掛職筆記》《老革命周春江》《劉萬福案件》《第四十圈》5篇掛職小說中,作者選擇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直接講述自己在掛職期間體驗到的基層生活的不同側面,小說開篇就選擇直接暴露作者的真實身份,《掛職筆記》《劉萬福案件》《第四十圈》中邵麗都選擇于第三段說明了自己下派到縣里掛職當副縣長的身份并借此身份開始講述自己于基層的所見所聞。《村北的王庭柱》《老革命周春江》則是在開端就交代了自己身為作家的身份,并以此身份講述有關小說人物主體的內容,“掛職系列”小說中邵麗多借助“掛職作家”的真實身份進行“第一人稱敘事視角”的真實言說。
并且在“掛職”系列小說中,以“第一人稱”進行敘事時“我”的目光始終是與所生活的大地齊平的,“我”站在“基層官員”與“小人物”的立場上,敘述官場生活而規避官場黑幕的書寫,擺脫傳統官場書寫模式的范式轉而還原官員的日常生活;寫底層群眾而不單苦吟誦苦難,力求真實再現“小人物”的內心的困頓與掙扎。《掛職筆記》一文中,祁副縣長身為縣長也有著自己的難處,他雖管計劃生育但也面臨著超生的問題,暴露出官員和普通人一樣——想要通過綿延子嗣來傳宗接代的傳統思想。而“我”在掛職結束的宴會上與和我工作背景相似的縣委書記談心時的對話,更是真實反映了基層官員工作的難言之隱,“每任縣委書記來的時候都豪氣干云,想改變這里的一切,到最后什么都不能改變,如果有所改變的話,只能是縣委書記變了,這里的一塊磚你也變不了。” ⑦“我”大為詫異,“下來之前就常常聽說縣委書記是土皇帝,一言九鼎,真實的情況怎么會是如此?” ⑧縣委書記卻說:“說起來這個縣有一百多萬人,光四大班子領導就有五六十人,可真正操心管事的,就縣委書記一個,最后所有的矛盾都堆在你這里……” ⑨邵麗選擇下移敘事視角,把官場看作普通現實生活的一部分,立足日常生活,反映官員于樸實工作中的所思所想所為。
“掛職系列”小說中的《第四十圈》里展現了齊光祿從一個良民到謀殺者有跡可循的路徑,他無論是從物質上還是精神來說,生存條件一直被搶奪且受到連續性的不公待遇。《劉萬福案件》中劉萬福面對不公從隱忍、無奈到產生違法亂紀的行為則是一個量變引起質變的過程,民眾深陷自身生存的困境無法逃脫從而走上極端的犯罪道路。此篇目中的細節性事件十分值得關注,身為“趙縣長”的“我”在寒假期間去走訪慰問貧困戶,并在其女兒的建議下決定舉辦大型公益節目,讓貧困戶通過上電視的方式得到幫助。但那個“爺爺領著五個孩子的家庭”始終沒有露面。其中的一個女孩面對我們問道:“為什么只有到春節才能看到你們的笑臉,摸到你們溫暖的手?……當你們在電視上拉著我們手笑的時候,我和妹妹卻在底下看著你們哭。你們從來沒想過,把我們一家人的痛苦拿去展覽我們會是什么心情?” ⑩這位十六七歲的孩子道出了部分受助者民眾的真實心聲——老百姓的苦難不應該成為某個節假日中相關部門的表演道具,更不應不考慮他們的尊嚴將幫扶形式化,老百姓渴望的并不是沒有尊嚴的憐憫,而是可以解決燃眉之急的實實在在的幫助。邵麗在“掛職系列”的小說中聚焦于時代洪流中這片土地上的平民,他們甚至有的會因跟不上時代前進的步伐而身陷生存困境之中,即使寫官員也規避了宏大敘事,將他們看作是歷史前進歷程中的普通人,“她的創作即便寫官場和官人,也不僅僅著眼于人的日常生活和自然屬性或動物本能,而是同時也有,或更多的是人的社會存在和文化傳承。” ?她的目光始終關切著這片熱土上的形色人物,意在以下移的敘事視角實現和小說中人物的平等對話,并在微觀敘事中展現社會風貌,這種由下至上的敘述方法與非虛構寫作的路徑是一致的。
三、“人民”性——喚起時代憂思
邵麗在掛職筆記中,對現實生活與社會轉型期的城鄉精神世界給予了深切關注,在作家的問題意識下表達著城鄉困惑與人性的光輝。書寫時代憂思的意圖與非虛構寫作不謀而合。但值得注意的是,邵麗的非虛構寫作對人民的生活并非只是簡單的復制,非虛構小說不能也不該成為傳統的歷史記錄,陳鐸指出:“非虛構對‘生活真實’的恪守,更多指向文學的社會學層面,而小說借由對真實事件的虛構傳達出作家對混沌經驗的多重理解,它試圖抵達的則是人性和人的精神層面的真實。” ?這也是非虛構寫作的文學性所在。邵麗的非虛構表達意在喚起時代憂思,她在實現為人民發聲的寫作意圖中呈現的非虛構表達仍然兼顧作品的藝術性,因此作品呈現出的特點不同于某些虛構小說浮于表面的自足性,也區別于傳統紀實性小說的嚴肅性,總體上的特點是處于上述兩種特點之間的非虛構性。
為了實現為人民的書寫,“掛職系列”小說中邵麗為建立作者、讀者和小說人物的“情感共同體” ?,展現真實而復雜的風土人情,從而更大程度喚起時代憂思,所做的努力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首先,邵麗選擇在自身的道德立場中重構自我認知與情感,體現作家強烈的人文關懷意識。作者在《劉萬福案件》這一小說中敘述故事的同時,不斷向讀者揭露重構的心路歷程:小說故事概況源于生活,但正如作者在小說開頭所言“我被這個故事俘虜了,我體會了和他的悲哀同樣的悲哀” ?,在這種寫作動機的驅使下,作者以劉萬福真實的經歷為基礎重構寫作元素,營造了“三生三死”的記憶點,力圖具象地再現其遭遇礦難、車禍再到尊嚴受損這一困苦歷程,還原底層民眾此時內心真實的困頓與掙扎,同時也詮釋了以劉萬福為代表的底層民眾在精神負重不斷加碼的過程中,仇恨情緒的爆發并非意料之外的結果。
洪治綱指出在非虛構寫作中,“作家,當事人,讀者之間呈現出情感與觀念的同步共振的狀態……其中,作家的平視姿態,以與當事人形成的信任同盟,是非常重要的前提,也是主體間性得以建構的基礎。有平等才有信任,有信任才有默契,有默契才能道出真相,并確保所敘述之事的真實。” ?邵麗在建立這種平等的信任同盟過程中的方法則是選擇隱匿自我主觀立場,作家帶著問題意識探索事件的真相,但并不直接判斷事件或人物的好壞,于是多個人物主體在與作家平等的關系中表達自己的聲音,文本從多個側面來為讀者呈現事件的真相。在“掛職系列小說”中,邵麗隱匿個人主觀立場下呈現出來的官員與百姓都不是非好即壞的人物典型,有利于讀者最大限度地觀照現實進而去審視人性的復雜。《第四十圈》中,作品從官員視角和百姓視角分別陳述對齊光祿的評價——周友邦以官員視角認為他家風很差而偏向對去世的公職人員充滿惋惜,而百姓視角則認為雖然齊光祿出手太重,但還是堅決認為老百姓鬧事的原因在于涉事的官員對案件處理得不合適。在意見相左的陳述中,身為敘述人的“掛職縣長”講述這些故事時,主動隱匿自我立場后留給讀者思考,從而展現更加客觀真實的基層生活。
邵麗在寫作中不自覺采用非虛構策略進行創作來探索周遭的境遇,展現真實的社會。為實現這種表達的需要,她不僅對自我情感與自我認知進行了重構,同時自覺懸置了自我的主觀立場,小說文本形成多維度展現人民真實生活圖景的結構。非虛構寫作處理下,讀者進行閱讀時不需對人物作太多的預判,只需跟隨敘述人的講述便可擁有較為清晰且純粹的視野觀察小說中的人物,能夠在作者波瀾不驚的理性敘述中探索事件真相,不局限于作家個人的逼仄情感,體悟城鄉背景下官與民的真實內心歷程。邵麗的“掛職系列”小說站在人民立場上關注著時代變動中人民的主體地位,書寫著涵蓋了不同階層的時代憂思。
四、結論
邵麗的“掛職系列”寫作以個人真實掛職經歷為基礎,以第一人稱展開的敘事內容,兼具“在場者”的“真實性”與“重構與懸置”的“自覺性”,且兩方面于互補互動中顯示出作者以現實主義為基調的問題意識。而對其非虛構的特征形成的敘事效果的研究不應單純是針對形式上的談論,邵麗的“掛職系列”寫作因其鮮明的非虛構寫作特征,于“求真”的同時兼具對自身經歷的深刻體悟與反思,試圖用自身經驗書寫人性和精神層面的真實,為當代文學長廊中增添了緊貼大地的實實在在的官與民的形象,在時代變動中表現出當代作家的文學敏銳感與社會承擔意識。
注釋:
①《“人民大地·行動者”非虛構寫作計劃啟事》,《人民文學》2010年第11期,第208頁。
②《“人民大地·行動者”非虛構寫作計劃啟事》,《人民文學》2010年第11期,第208頁。
③王暉:《“非虛構”的內涵和意義》,《文藝報》2011年03月21日,第五版。
④邵麗:《寂寞的湯丹》,春風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86-87頁。
⑤邵麗:《寂寞的湯丹》,春風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頁。
⑥沈閃、黃燈:《黃燈:我怎樣寫作〈大地上的親人〉》,《關東學刊》2019年第3期,第154-161頁。
⑦邵麗:《掛職筆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頁。
⑧邵麗:《掛職筆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18-19頁。
⑨邵麗:《掛職筆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頁。
⑩邵麗:《掛職筆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頁。
?於可訓:《主持人的話》,《小說評論》2015年第1期,第128-129頁。
?陳鐸:《現實性、日常性與審美性:論邵麗“掛職系列”中的官場書寫》,《寫作》2019年第5期,第42-49頁。
?洪治綱:《論非虛構寫作中的主體情感與觀念》,《文學評論》2022年第5期,第112-120頁。
?邵麗:《掛職筆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頁。
?洪治綱:《論非虛構寫作中的主體情感與觀念》,《文學評論》2022年第5期,第112-120頁。
參考文獻:
[1]張延文.邵麗藝術風格論[J].小說評論,2015,(01): 137-142.
[2]張文東.“非虛構”寫作:新的文學可能性?——從《人民文學》的“非虛構”說起[J].文藝爭鳴,2011,(03):43-47.
[3]洪子誠.當代中國文學的藝術問題[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294.
作者簡介:
楊兆昕,女,河南鶴壁人,長春理工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