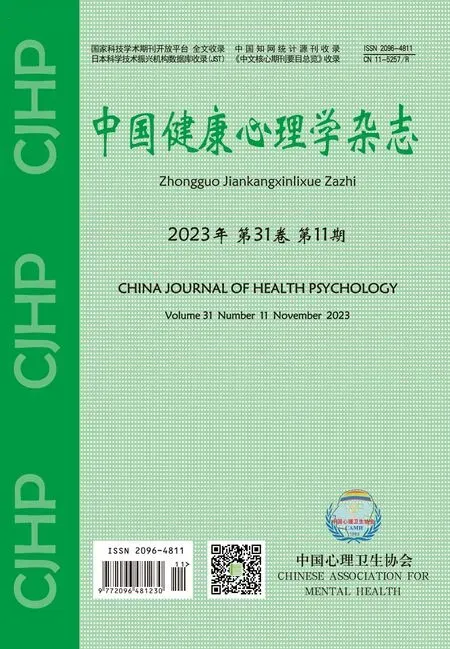初中生良好同伴關系對其積極干預欺凌行為的影響: 有調節的中介模型*
石常秀 代晨輝 辛 宇 趙小軍
河北大學教育學院 071002 △通信作者 E-mail:psy790821@aliyun.com
校園欺凌是學校背景下的一種特殊形式的攻擊性行為,目的是對他人造成傷害或者引起不適[1]。欺凌現象所造成的影響是非常嚴重、深遠的,被欺凌者在經歷過欺凌事件后往往會表現出抑郁等內化問題[2]。以往的學者著重于欺凌雙方,較少關注旁觀者,然而在現實欺凌場景中,旁觀者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積極的旁觀者干預行為會給予被欺凌者情感上的支持或保護[3],能夠有效減緩欺凌帶來的負面影響[4],因此探索旁觀者積極干預欺凌行為的影響因素,從而促進旁觀者積極介入是校園欺凌防治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校園欺凌場景中,幫助被欺凌者需要直面巨大的壓力[5],能否克服壓力去保護被欺凌者,一方面受到特質焦慮、道德推脫等自身特質及認知因素的影響[6],另一方面個體的同伴關系質量也會影響其制止欺凌行為的意愿[4]。同伴關系是指年齡相當或者心理發展水平差不多的個體間通過溝通、合作等社會交往所建立的較為穩定的社會聯結關系,對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發展及人格完善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力[7]。研究發現具有良好同伴關系的個體在所屬群體中受歡迎程度較高[8],這會使其感知到較高水平的社會支持[9],從而作為一種保護性因素減少抑郁、焦慮和自殺意念等問題的風險[10]。因此在校園欺凌中,良好的同伴關系可以使個體更有底氣去制止欺凌行為,而不必擔心由于幫助被欺凌者而面臨孤立、排擠等風險。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H1:旁觀者良好的同伴關系能夠正向預測其面臨欺凌時采取的積極干預行為。
基于青少年旁觀者行為的情境-認知模型(The Situational-Cognitive Model of Adolescent Bystander Behavior)可知,旁觀者在面臨欺凌事件時,會對事件的嚴重程度進行評估,同時對欺凌者/被欺凌者個體因素以及群體社會關系(或地位)進行考慮,之后觸發與干預欺凌相關的態度、自我效能信念等,最終決定是否采取干預措施[11],也有研究發現那些認為自己有能力成功制止欺凌行為的青少年往往會做出更多的積極介入行為[12]。此外自我效能感的發展會受到重要他人(如父母、教師、同伴等)的影響,尤其在青少年時期,同伴接納和人際關系對于自我效能感的發展非常重要[13]。自我效能感作為個體對自身能否有能力完成某一目標或者行為的主觀推斷,是其做出行為決策的重要內驅力。當目睹欺凌行為時,自我效能感是決定個體選擇“置身事外”還是選擇“挺身而出”的重要影響因素,即當擁有較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時,個體越相信自己能夠成功制止欺凌行為,由此更有可能做出積極的干預行為[14],據此提出本研究的H2假設:自我效能感在同伴關系和旁觀者積極干預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
Casey等人的情景-認知模型[11]認為,個體對欺凌情景進行評估后會激活與欺凌相關的認知因素即干預欺凌的責任感、對欺凌行為的態度、社會規范感知以及自我效能,這些認知因素不僅能夠直接影響個體是否做出干預欺凌的行為決策,而且不同認知因素的作用也存在相互影響。班級欺凌頻率感知是個體對自身所處班級欺凌行為發生頻率的主觀判斷,也被認為是班級欺凌規范水平的一個評估標準[15],感知到欺凌行為頻率越頻繁,來自班級的社會規范壓力也就越大,這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導致旁觀者做出置身事外甚至協助欺凌行為[16],因此自我效能感對于旁觀者積極干預行為的作用可能會受到班級欺凌頻率感知水平的影響,據此提出假設H3假設:班級欺凌頻率感知能夠調節自我效能感和旁觀者積極干預行為的關系。
綜上所述,本研究建立如圖1所示模型,當目睹欺凌行為時,旁觀者的同伴關系能夠預測其積極干預行為,自我效能感在二者間起中介作用,此外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可能受到個體對自身所處班級欺凌行為發生頻率感知的調節。

圖1 同伴關系對旁觀者積極干預行為的作用機制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采用整群抽樣的方式從河北省選取初中生被試,回收數據436份,經篩選后得有效數據416份(95.4%),被試來源于10個班級,平均年齡為13.67±0.87歲,其中初一學生78名,初二學生157名,初三學生181名;男生225人,女生190人(有一人未填寫性別信息);家庭所在地城鎮的學生有364名,農村學生47名(有5人未填寫家庭所在地信息);有122名學生為班干部,289名學生未擔任班干部(有5人未填寫該信息)。
1.2 方法
1.2.1 同伴關系的測量 采用鄒泓編制的同伴關系量表[9],4點計分,共30道題,分為同伴接受和交往恐懼自卑兩個維度,為了使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時因子載荷方向保持一致,本研究參考王凱和張野的處理方式[17],將交往恐懼自卑維度反向計分,總分=交往恐懼自卑分維度得分(反向計分后)+同伴接受分維度得分,總分越高表明個體的同伴關系越好。本研究中兩個分量表的α系數分別為0.91、0.88,總量表α系數為0.93。
1.2.2 自我效能感的測量 采用王才康等人修訂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18],4點計分,共10題,得分越高代表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α系數為0.80。
1.2.3 班級欺凌頻率感知的測量 采用曾欣然等人修訂的個體感知到的班級欺凌行為頻率分量表[15],共3道題,5點計分,得分越高表明個體感知到的班級欺凌行為的發生越頻繁,本研究中該量表的α系數為0.78。
1.2.4 旁觀者積極干預行為的測量 采用游志麒等人修訂的校園欺凌旁觀者干預量表的干預分量表[19],該分量表共4道題,5點計分,得分越高代表個體更傾向于干預欺凌行為,從而保護被欺凌者,本研究中該分量表的α系數分別為0.77。
1.3 統計處理
采用SPSS 25.0和Amos 24.0進行統計分析,為避免多重共線性對研究的影響,在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之前將變量進行中心化處理。
2 結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對研究結果的干擾,本研究采用Harman單因子法的驗證性因子分析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20],使用Amos軟件構建驗證性因子模型,模型擬合分析結果如下:χ2/df=4.49、GFI=0.58、CFI=0.54、TLI=0.52、RMSEA=0.09,即模型擬合較差,因此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2.2 描述統計及相關分析
表1所示,同伴關系、自我效能感、旁觀者積極干預行為三者之間呈兩兩顯著正相關,個體感知到的班級欺凌頻率與同伴關系、自我效能感及旁觀者積極干預行為均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

表1 各變量描述統計及相關分析(r)
2.3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應
自我效能感為單維結構,滿足打包的要求,因此本研究采用因子載荷平衡法將其進行項目打包[21],之后構建結構方程模型。模型擬合分析結果顯示如下:χ2/df=2.50、GFI=0.97、CFI=0.97、TLI=0.95、RMSEA=0.06,各擬合指標基本處于可接受的范圍。路徑分析如圖2所示(圖中為標準化路徑系數),同伴關系能夠正向預測自我效能感,當同伴關系和自我效能感同時預測旁觀者的積極干預行為時,二者的正向預測作用也均是顯著的。

圖2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2.4 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
研究采用方杰等人的觀點[22],通過用無約束方法構建無均值結構的潛調節效應模型的方式分析班級欺凌頻率感知的調節作用,即在中介模型的基礎上加入班級欺凌頻率感知作為調節變量,根據自我效能感和班級欺凌頻率感知指標的因子載荷按照配對乘積法“大配大,小配小”的要求構建“自我效能感×班級欺凌頻率感知”潛交互項的指標:交互1、交互2和交互3。結構方程模型擬合分析顯示,各擬合指標均屬于可接受范圍:χ2/df=2.67、GFI=0.93、CFI=0.92、TLI=0.90、RMSEA=0.06。路徑分析具體結果如圖3所示(圖中為標準化路徑系數),自我效能感和班級欺凌頻率感知的交互項能負向預測旁觀者積極干預行為,即班級欺凌頻率感知的調節作用顯著,能夠調節自我效能感和旁觀者積極干預行為的關系。

圖3 有調節的中介模型


圖4 簡單斜率分析
3 討 論
3.1 旁觀者同伴關系對其積極干預行為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旁觀者良好的同伴關系能夠正向預測其積極干預行為,即擁有良好同伴關系的個體在目睹欺凌事件后更傾向采取一些措施去制止欺凌行為,這與以往的研究相符合。同伴關系作為青少年階段最重要的人際關系之一,在其身心發展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7]。“擔心成為下一個欺凌受害者”是個體選擇“置身事外”不愿意制止欺凌行為的心理障礙之一,幫助被欺凌者可能會導致自身陷入不安全的境地,這也是很多目睹欺凌事件的個體會認知失調的重要原因[3]。明知道欺凌行為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應當去阻止,但由于自身安全的脆弱性,害怕去干預,而良好的同伴關系恰好能作為一種資源性因素,緩解個體干預欺凌時面臨的壓力,減少對于結果的擔憂,即使自己出面制止欺凌行為,由于也不用擔心會遭到報復,成為下一個受害者,因此具有良好同伴關系的個體在面對欺凌行為更容易克服壓力去制止欺凌行為。
3.2 自我效能感在旁觀者同伴關系和積極干預行為間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發現自我效能感在旁觀者同伴關系和積極干預行為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具備良好同伴關系的個體由于在社會互動的過程中接受到來自同伴的積極反饋,更容易建立較高程度的自我效能感從而促使其積極制止校園欺凌行為。一方面個體如果得到同伴群體的認可、接納及尊重,那么他可能會對自身價值有著更高的認可度[23],其自尊、自我效能感等自我概念也會隨著提高;另一方面同伴關系較好的個體往往在所屬團體中也具備更高的受歡迎程度[8],這種社交互動上的成功經驗極大程度上會促進個體的自我效能的發展。基于成本-效益的角度出發,個體在做出干預欺凌行為的決策時會充分權衡利弊,分析干預行為的成本和收益[24],因此自我效能感較高的個體,即相信自己能夠成功制止欺凌行為時,才會更有可能去采取相關干預措施。
3.3 班級欺凌頻率感知在自我效能感和積極干預行為間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還發現班級欺凌頻率感知能夠調節自我效能感和積極干預行為的關系,即只有當個體感知到較低頻率的班級欺凌行為時,自我效能感才能預測其積極干預行為。以往研究發現大多數人的觀點都認為自己應該制止欺凌行為,然而實際上卻只有少數人會挺身而出保護被欺凌者[25],這種態度和行為存在沖突的原因可能是個體受到同伴群體環境的影響[26]。情境-認知模型認為當目睹欺凌行為時,個體首先會綜合各方面的環境信息評估欺凌行為的嚴重程度[11],當班級欺凌行為發生頻率較高時,這會“扭曲”班級成員對于欺凌行為嚴重程度的評估,更傾向將欺凌行為識別為一種“司空見慣的小事”,從而影響自我效能感對于積極干預行為的作用,也就是說即使個體認為自己有能力制止欺凌行為,也會由于避免“多管閑事”而拒絕制止欺凌行為,這也是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只有當個體感知到班級欺凌行為發生較少時才成立的原因。
3.4 研究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基于旁觀者情景-認知模型,探討了旁觀者同伴關系的好壞與其是否選擇積極干預行為的關系,以及自我效能感和班級欺凌頻率感知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一定程度上驗證并擴展了該模型在國內背景下的應用。然而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本研究采取橫斷研究設計,并不能得出確切的因果關系,未來可以采取縱向研究設計或者實驗法的方式進一步明確因果關系。其次本研究主要探討了自我效能感和班級欺凌頻率感知的作用,而以往的研究發現個體對于欺凌的態度、責任感等認知因素在做出欺凌干預決策過程時也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未來的研究可以綜合欺凌相關的認知因素,并將其與學校氛圍,欺凌者-被欺凌者的個人特征等外部信息相結合進一步探索個體積極制止欺凌行為的產生機制,并促使那些“置身事外”的局外人轉換為“挺身而出”的保護者,從而改善校園欺凌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