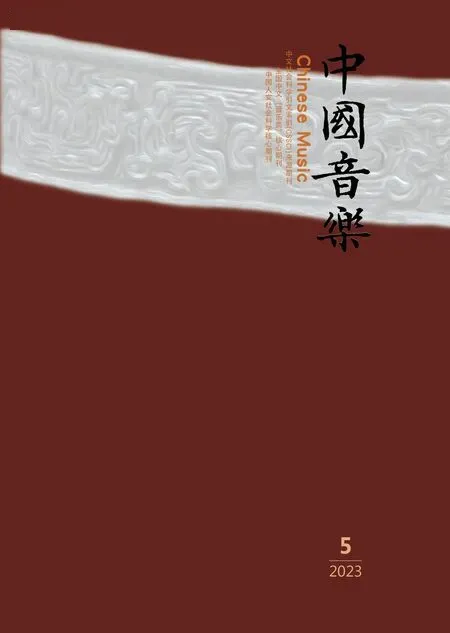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的音樂結構研究
——基于圈層傳播的視角
○張麗
環洱海區域①環洱海區域地處環洱海區域中部,其地理單元與大理市的空間范圍基本一致,與洱源、巍山、彌渡、賓川、祥云等縣相連。轄區包括喜洲、雙廊、下關、大理等十個鄉鎮,一百多個村委會。是以白族為主體的多民族聚居區,自秦開“五尺道”以來一直與中原聯系密切,文化互動頻繁,形成了獨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并兼具向周圍擴展活力的“大理文化圈”。在上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各種文化在環洱海區域不斷并列發展、立體層疊、交互融合,為鼓吹樂的傳入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鼓吹樂作為全國性意義的樂種存在,經各類傳播模式傳入環洱海區域并繁榮發展,在時空性的傳播過程中形成以洱海為中心,圈層式向周邊地區輻射的發展樣態。
環洱海區域存見的鼓吹樂及其曲牌自生發之日起,經歷了產生、傳播、接受、融合的過程,而傳播則是該過程中的核心環節。通過田野考察和文案梳理的互補互證發現,環洱海區域鼓吹樂的物質結構和曲牌類型均體現出“二元共在”的典型特征,即主奏樂器有“兩類形制”,曲牌包括“兩種類型”的特點。從歷史溯源、現實樣態、音樂形態等方面研究表明,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的整體形態與邊疆民族地區自身的社會發展、歷代中央王朝與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互動、傳統音樂體系的形成與傳播等因素密切相關。因此,從圈層傳播的角度立足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勾勒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傳播的歷史圖景,追問其傳播的歷史動因,以“禮”“器”“曲”三方面考察其類型結構、音響結構、曲體結構之間的多層關系及音樂思維便是本研究的邏輯起點。
一、圈層傳播之內涵闡釋
傳播的價值在于啟發再創造,同時賦予民族內涵和文化價值。文化的創造則體現為符號的創造和運用符號進行的創造,而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則是在“禮”“器”“曲”三類符號意象中的文化再造。此三項在歷時性的國家制度推動下,受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等因素的影響,使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呈現出圈層式傳播的特征。
“圈層”一詞來源于人文地理學科的“圈層結構理論”,該理論主要指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城市為中心,呈圈層化向外發展至其他城市及周圍地區,由內到外可以分為內圈層、中圈層和外圈層。圈層的概念目前在學界沒有形成統一的共識,有學者認為“具備一定的境域以及多民族國家這兩個要素,是圈層結構產生的必要條件”②郭聲波:《從圈層結構理論看歷代政治實體的性質》,《云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第86頁。。中國傳統社會關系網是以血緣、業緣和地緣為核心層層推進而構建的,關系網最基礎的因子是“一個個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每一個私人關系網如一塊石頭落入水面激起的一圈圈波紋”③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41頁。,這一圈圈波紋就好似各圈層的社會關系。因此,圈層作為一個動態的場域,其典型特征是層級化,首先是圈層內部的內層關系構建,在此基礎上內層關系不斷向外延展、突破,同時又有外部力量向內部滲透,總體為多向度傳播形式。基于以上理論,地處西南邊地且有著豐富民族群體結構的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便具備了圈層結構的生成條件。在人類學意義層面,環洱海區域的圈層結構包括域內各民族之間的關系,以及各民族與外部(境內和境外)民族之間的互動關系。在音樂學理論層面,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的圈層結構為域內各地區各民族群體中鼓吹樂曲牌的內在流傳(內圈層),向他地域、他族群的外散傳播(中圈層),以及國內其他地區的曲牌音樂對環洱海區域的內聚輸送(外圈層)。通過對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的梳理與分析發現,其在三個層次結構中的傳播與接受在內圈層和外圈層中最具活力。其中,內圈層體現的是一種對環洱海區域傳統音樂文化的傳承與堅守,外圈層體現的是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對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吸納與融合。
二、“禮”——類型結構之文化基因
環洱海區域鼓吹樂及其曲牌是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中通過音樂文化信息傳播而生發的。在各朝代中央集權有意識的影響過程中,該區域人民在無意識狀態下承繼的禮樂制度,為鼓吹樂的生根發芽提供了文化土壤,同時也成為曲牌類型劃分的重要文化基因。
(一)禮樂制度:文化空間構建之循禮典制
禮樂制度與儒學有著天然的聯系,并隨著儒學的普世而得到弘揚。儒學作為漢文化的精神內核在秦漢時期隨“五尺道”“西夷道”“南夷道”出入云南,唐宋時期“南詔”和“段氏”兩個地方政權加強與中原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聯系,使儒學在云南的傳播達到了頂峰。南詔時期的儒學盛行于統治階級,大理段氏時期開始流入民間,到元明清時期已普及廣大民眾,地理范圍從城鎮發展至鄉村,族群結構從漢族向少數民族延伸。學校是儒學傳播的主要陣地,至明代中期,中央政府在云南凡設府、州、縣以及衛所的地區都設立學校。據史書記載,云南共有學宮(廟學)70所,桂林書院(大理)、秀峰書院(騰沖)、正學書院(保山)等④曾相:《儒學在云南的傳播與發展》,載:《孔學研究》第一輯,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28頁。均位于環洱海區域及外圍地區,環洱海區域以大理為中心波及周圍形成的文化圈是歷史必然。儒學的興起使中原文化源源不斷的被環洱海區域民眾理解并接受,這就為鼓吹樂在該區域的流傳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礎。鼓吹樂自古具有禮樂屬性,環洱海區域少數民族學習禮樂文化的同時,結合本民族傳統文化逐漸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民俗儀禮,并將鼓吹樂用于各類民俗活動中,繼承中原古老曲牌的同時又創生了本地區本民族的傳統曲牌,最終形成地域特征鮮明、民族特色濃郁的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系統。
鼓吹樂在千年的歷史變革中逐漸由軍樂、官樂向民間禮俗用樂轉變,呈“文化下移”的發展態勢。禮樂制度規定了不同階級的用樂形式和內容,在“趨中心化”的心態指引下,民間社會對禮制學習并將其變異傳承,在環洱海區域便有了當下展現的喜慶類儀式(吉禮)和喪事類禮儀(兇禮)。鼓吹樂在儀式中的貫通性使其被民眾學習、接受并使用。禮制讓環洱海區域各族人民制定本民族儀式流程有據可依,樂制讓中國古代傳統的“制樂”行為在不同族群和文化空間中得以發揚,所以在禮樂制度的影響下,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與民間各類民俗儀式活動相依共存,協調發展。禮樂制度的傳播,讓“親死則火之,不為喪祭”的原生習俗改變為“歲時之禮,往來之儀,一本中原”的規范禮儀,最終呈現出具有儀式規范化、儀軌程序化的民俗活動,為環洱海區域鼓吹樂及其曲牌繁榮發展營造了重要的文化空間。
(二)文化選擇:曲牌類型形成之審美傾向
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以各類民俗儀式為依托,在傳播過程中不斷變化發展,衍生出大量的變體或“又一體”。環洱海區域人民在文化的傳播和交融過程中,無意識地選擇并習得了鼓吹樂文化,在傳承過程中受審美傾向的影響卻有意識地將本土民族音樂嫁接其中,經長期發展傳衍,形成了大量的同名異曲或同名異宗曲牌,從文化源流層面可將其分為外來曲牌和本土曲牌兩類。外來曲牌指隨漢文化、漢族移民或中原樂工一道傳入環洱海區域的古老曲牌;本土曲牌是環洱海區域民眾在學習、接納漢文化的同時將其與本民族音樂融合而創生的曲牌,兩種曲牌類型是文化接觸、交流、融合與創造的結果。
1.外來曲牌
曲牌在傳播過程中通常會因為傳播渠道、地緣結構、受眾群體等關系的變化而變化,當曲牌傳播到他地后,往往受異地音樂文化的影響而產生新的變體。但無論曲牌在傳播中如何變化,其音樂性卻不會變。一支曲牌受各方因素影響發生變化時,該曲牌不會消失,會以另一種音樂形態流傳于民間,那么,曲牌與曲牌之間交融而形成的曲牌變體與原曲牌一道被民間儲藏并不斷傳衍,這是環洱海區域擁有大量“同名異曲”或“同名異宗”曲牌的原因。
在田野中發現,樂班負責人常發出“奏【將軍令】”“奏【大開門】”“奏【小開門】”等指令,這些都是中原古老曲牌。于是筆者隨即對《中國民間歌曲集成·云南卷》《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云南卷》《中國戲曲音樂集成·云南卷》以及各地方器樂曲集進行梳理,發現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中保留著古老曲牌名的曲牌有很多,如【小桃紅】【將軍令】【朝天子】【南清宮】【下山虎】【銀紐絲】【金紐絲】【一封書】【節節高】【山茶花】【大桃紅】【虞美人】【山坡羊】【普天樂】【傍妝臺】【滿堂紅】【大開門】【小開門】【南正宮】【小鷓鴣】【滴滴金】【蓮花落】【浪淘沙】【海棠花】【石榴花】【哭皇天】【泣顏回】【錦上花】【柳青娘】等,其中曲牌【泣顏回】【錦上花】【柳青娘】主要用于滇劇器樂部分,其他曲牌都以鼓吹樂形式存在。以上均為古代中原地區較為流行的曲牌,在古代時期就在不斷的傳播和運用中派生出多支變體,旋律形態各異,經多渠道流入環洱海區域后,在不同地域空間和民族群體中傳承至今。
禮樂制度讓環洱海區域各族人民依據本族文化建立了一套民俗禮儀,各類民俗活動便是鼓吹樂曲牌的表演場域。同時,不容忽視歷代漢民入滇對區域文化結構的影響,因為人是禮樂文化和音樂文化傳播的主體。據多位學者考證,入滇漢民主要來自“北八省、南七省”,即江蘇、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河北、山西等各地⑤郝正治編著:《漢族移民入滇史話》,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91-95頁。。從人口學理論出發,就可將環洱海區域與以上各地的同名曲牌進行形態比較,進而窺探其曲牌流變的規律。首先將以上各省的的鼓吹樂曲牌⑥各省區曲牌以《中國民族民間器樂集成》為參考文本。名錄和《新定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⑦〔清〕周詳鈺等:《新定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乾隆十一年。(下文統稱《九宮大成》)曲牌名錄進行對比,列出同名曲牌;再從諸多曲牌中找出環洱海區域與各省區的同名曲牌進行形態比較研究。通過梳理發現,環洱海區域鼓吹樂與《九宮大成》比對共有15支同名曲牌⑧文中所列曲牌主要分布在大理市各縣區,楚雄州存有一支曲牌【山坡羊】。,與入滇漢民發源地省份的鼓吹樂中有10支同名曲牌。其中,【大開門】【小開門】【將軍令】【山坡羊】重疊次數最多,其次是【水龍吟】【柳青娘】【滿堂紅】【小桃紅】,【下山虎】和【南清宮】分別與江西省和湖北省重疊。筆者將環洱海區域、省外以及《九宮大成》重疊次數較多的8支曲牌之形態進行三角式交叉研究發現,這些曲牌僅有曲名相同,其旋律、曲體、調式調性等均形態各異,屬同名異宗曲牌(見圖1)。可見,中原古老曲牌隨著鼓吹樂文化傳入環洱海區域被廣大人民接受、運用,但在具體藝術實踐中環洱海區域各族人民卻在音樂資料選擇上有所偏離,更多是發展本土民族音樂并將其嫁接到鼓吹樂文化中,形成民族性和地域性較強的地方性樂種,在長期的表演過程中,將多元文化進行疊加而衍生出大量的本土曲牌。

圖1 同名曲牌對比研究圖
2.本土曲牌
在環洱海區域各地流傳的鼓吹樂曲牌數量多至無計,其曲目之豐富就如同民間藝人所說“我們的曲子可以吹幾天幾夜不重樣”,各地區有一套功能曲牌體系。在對鼓吹樂曲牌的用樂形式進行考察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環洱海區域不同地區不同族群中流傳著大量的同名曲牌,這些曲牌功能意義一致但旋律形態各異,從語言學的層面審視,這是“名稱借貸”現象在音樂文化中的呈現。
名稱借貸是指不同地區、不同族群在同一類型民俗儀式中使用的曲牌名稱相同,而這種“同”是區域間和族際間的文化、語言在多向度的“接觸”過程中最終形成的一種名稱借用和實踐運用。借貸一詞源于經濟學,金錢的借貸要由實際交付來達成,而本文曲牌名稱的借貸則強調對曲牌名稱借用并在文化空間中有實際運用,因重“實踐”因素故用“借貸”一詞。環洱海區域各民族使用的曲牌名稱基本都是漢語稱謂,且同一儀軌使用的同名曲牌的情況甚多,如儀式開始時的【大開門】【小開門】,婚儀中的【迎親調】【拜堂調】,宴席中的【敬酒調】【上菜調】【坐席調】,喪儀中的【哭喪調】【起棺調】【下葬調】,婚喪儀式中均有的【過山調】【過村調】,此類名稱相同但曲調各異的現象,究其原因是文化接觸過程中所引起的語言接觸、文化接觸、音樂接觸,在多向而漫長的接觸過程中曲牌名稱使用的空間相對應、民間藝人和民眾的審美追求相對應,故形成了曲牌名稱借貸的用樂特點(見圖2)。這一特點的深層根源是歷史上的移民促成了族際間和文化間的接觸,漢族、漢文化、漢語作為強勢的一方,至環洱海區域對各族群起到了較強的影響作用,從文化、語言、習俗等諸多方面對原本土文化形成干擾,在鼓吹樂文化中形成語言同一性(漢語)的名稱借貸特點。

圖2 “名稱借貸”的衍化過程
環洱海區域民間的諸多同名曲牌非同宗,其意義更多體現在曲牌功能和文化習俗方面,文化是無界的,曲牌名稱的借貸也是無界的,區域內的互借,區域外的影響,族群間的共時干擾和歷時傳承,讓我們看到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體系中既有中原古老曲牌的影子,也有本地流傳上百年的民族曲牌,也正是以上諸多因素的交織,同構了環洱海區域鼓吹樂的文化多樣性以及曲牌豐富性。
三、“器”——音響結構之物質載體
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是由嗩吶主奏配合以鑼、鼓、镲、鈸打擊樂器的器樂合奏形式,其儀禮文化及物質結構傳播至環洱海區域被當地人民理解和接受,在傳播過程中,多種文化接觸、交流和融合,最終形成了主奏樂器之“兩種形制”和樂隊配置漸縮性發展的主要特點。
(一)兩種形制
環洱海區域鼓吹樂之“兩種形制”是指主奏樂器嗩吶有七孔嗩吶(無背孔)和八孔嗩吶,八孔嗩吶其形制同于中原漢族嗩吶。七孔嗩吶的使用主體為白族,在與白族混居或相鄰的彝族村落也有使用,因而民間習慣將七孔嗩吶稱為白族嗩吶,本文采用此稱謂并將八孔嗩吶稱為“漢族嗩吶”來進行討論。白族嗩吶由音管、碗口、芯子(過氣)、氣盤、哨子組成,其形狀和構造與漢族嗩吶相近。管身木制長約30厘米,各地區管身長度有1厘米至3厘米的差異,管身正面依次設七個音孔(非勻孔間距),無背孔。白族嗩吶流行區域以外的地區均使用漢族嗩吶,二者構造基本相同(見圖3)。漢族嗩吶開八個音孔(前七后一),音域達十七度,比白族嗩吶的十五度音域寬兩度,但在實際表演中,藝人常用的音域多在十度至十二度以內。據不完全統計,白族嗩吶主要流行于大理市洱海西部(海西)的喜洲鎮等地、洱海東部(海東)挖色鄉等地,永平縣北斗鄉、洱源縣茈碧湖鎮等地的白族、彝族聚居區,總體呈“中心聚集、外圍散存”的分布形態,即以洱海中心聚集,在南澗縣、永平縣一些鄉鎮零星散布。盡管兩種形制的嗩吶有大致的區域分布,但分布較為模糊,整體呈現大聚集、小分散的特點。

圖3 白族嗩吶(左,大理市)和漢族嗩吶(右,永平縣)形制圖(單位:毫米;繪圖:張麗、陳海鳳)
筆者在跟隨民間藝人學習白族嗩吶的過程中發現,通過氣息力度和取音孔位的不同可以發出不同音高,實現了“一孔雙音”“一孔三音”的可能,且在實際演奏中經常得以運用,這是對楊育民提出的白族嗩吶之“多筒音”⑨楊育民:《白族吹打:大理傳統音樂研究》,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6年,第14-21頁。現象的佐證(見譜例1)。白族嗩吶多筒音特點致使筒音與第一音孔構成了多種音程關系,從而形成了白族嗩吶演奏的曲牌調式調性多變的特點。白族嗩吶第一孔與第六孔和第七孔分別相距七度和八度,因易于演奏故七度、八度音程跳進被白族嗩吶藝人經常使用,久而久之,大的音程跳進就成為白族人民的審美習慣,有的樂曲甚至出現十五度、十六度的大跨度跳進,使得樂曲旋律跌宕起伏、意味深遠。

譜例1 白族嗩吶“多筒音”現象
(二)樂隊編制
環洱海區域鼓吹樂的打擊樂器主要有鑼、鼓、镲、鈸,俗稱“四大件”。據當地藝人介紹,較早時期的鼓吹樂隊有四人至十人不等的四種編制。樂器種類相對較多,有長號、大筒、海螺、竹笛、小直簫、云鑼等。長號和大筒目前在山區、半山區的村落還有使用,云鑼和海螺便較少存見。隨著歷史的發展,環洱海區域鼓吹樂的樂隊編制逐步被簡化,以洱海為中心向外呈漸縮性的配置形式。洱海周邊平壩區的民間樂隊編制根據場合及應事需要主要有雙吹四打、單吹三打、只吹不打幾種。雙吹四打由六人演奏,樂器有兩支嗩吶、鼓、镲、大鑼、小鑼、鈸各一。單吹三打由四人演奏,一支嗩吶、鼓、镲、大鑼、鈸各一。只吹不打即兩人配置,樂器為兩支嗩吶和兩支長號,演奏的曲牌、曲目以及儀式流程與其他樂隊配置的一樣。而在更外圈的山區、半山區則多為一支嗩吶配一個小镲的演奏形式,據當地人陳述,樂隊人數多,經濟開支就大,受經濟所限,逐漸形成了較為單一的編制模式。
從地理文化空間來看,文化傳播由文化中心區向四周擴散,傳播過程中存在信息遞減的基本規律,即離文化中心區越遠文化傳播的影響力便越弱。因此,鼓吹樂的樂隊配置在傳播的過程中呈現出層級性、階序性的減縮現象。首先,之于全國范圍的大圈層來看,環洱海地區鼓吹樂減少了大部分地區鼓吹樂必用的打擊樂器種類,如,管子、笙、笛等;從環洱海地區的小圈層來看,以“大理文化圈”的鼓、鑼、镲、鈸“四大件”打擊樂器構成為圓心,向外遞次減縮為兩件、一件打擊樂器配置的情況。如果說漢族嗩吶是環洱海區域人民對中原文化的“接受與傳承”,那么白族嗩吶便是對鼓吹樂物質構成的“接受、再造與傳承”。
四、“曲”——曲體結構之思維傳承
基于曲牌之“同名異宗”的特點,本文將從本土曲牌的曲體結構進一步分析其音樂特征和音樂思維。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的結構遵循著中國傳統音樂思維,在發展過程中秉承著中國傳統音樂組織音樂的深層結構邏輯,其曲體結構大體可分為單牌體、復牌體、聯曲體和類集曲體。在曲牌的傳承過程中,必有“變”的因素,因此在上述四類曲體結構中,兼具整體一致性和局部差異性的特點。
(一)單牌體
單牌體是中國傳統音樂中最基本的結構形式,也是最短小的尚未經過再發展的器樂曲結構。此類結構在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中占有較大比重。在實際演奏中,單牌體可以單獨演奏,也可以作為套曲的組成部分。單牌體曲牌包括方整性結構和非方整性結構兩種。方整性結構的單牌體大多吸取或模仿民間歌曲、時令小調的結構形式,由上下句對稱或用“起承轉合”的原則構成,因此單牌體結構的曲牌富于歌唱性特點。非方整性結構的曲牌由若干個動機和樂節連續發展或匯聚而成,旋律內部的樂句為長短句或不易分句。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中產生非方整性旋律結構的原因有二:一是旋律衍生手法促成的樂句不均衡,民間通常以一個短小的樂匯不斷發展成較長的樂句甚至樂段,因此在旋律中常有較短小的音樂材料獨立成句;二是鼓吹樂人演奏的即興性旋律形態帶來的不規整樂句結構,雖然即興是建立在一定程式基礎上的,但即興表演仍然會打破程式,呈現出不同的結構特征。環洱海區域鼓吹樂中的單牌體曲牌從數量上看,非方整性結構所占的比例較大;從結構上看,有單句、兩句、三句、多句等不同的曲體結構形式。
(二)復牌體
復牌體是在單牌體曲牌的基礎上進行一定的發展,從樂句的運動方式來看,復牌體可分為并置復牌體、再現復牌體和循環復牌體。并置復牌體由兩個樂段并列構成,兩個樂段之間的音樂材料不盡相同,處于并置狀態,材料既可重復也可對比。再現復牌體是在并置復牌體的基礎上帶再現部的三段式曲牌結構。循環復牌體指以循環結構原則的音樂結構,具體指在曲牌旋律中,部分樂段不斷循環穿插出現的曲體結構。三種結構體式在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中較為多見,整體上看,單一屬性曲體結構的曲牌較多,最有特點的是多種曲體結構共存的曲牌。2018年10月,筆者在大理市喜洲鎮周城村采錄到的曲牌【美女梳妝】(篇幅所限,譜例略)就是再現復牌體和循環復牌體的綜合。【美女梳妝】引子、身部、尾聲構成,引子是自由的散板,身部由三個樂段構成,其中第三樂段是第一樂段的變化再現,尾聲為鑼鼓樂。引子和尾聲固定在頭尾沒有循環,穩定全曲。循環體均在“身”部,其中第一樂段循環演奏五次,第二樂段中每個部分與第一樂段相接循環兩次,第三樂段抽取第一樂段的部分材料進行變化再現,沒有循環。第一樂段和第二樂段不斷地循環穿插出現,最后由第三樂段銜接發展至尾部結束全曲,形成了典型的循環復牌體結構(見圖4),僅出現一次的A1樂段是對A樂段的變化再現,如此便使該曲牌在結構上有了雙重屬性,既是再現復牌體,又是循環復牌體,成為較典型的曲體結構范例。

圖4 【美女梳妝】“身部”曲式發展流程圖
(三)套曲體
套曲體是由兩首或兩首以上曲牌聯綴而成的曲體結構,聯綴的曲牌在一定基礎上形成對比。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屬于牌套,且是牌套中的散套形式。根據曲牌功能與用樂機制,將環洱海區域鼓吹樂中的套曲體分為儀式性曲牌聯套和同宮系統曲牌聯綴兩類。其中,儀式性曲牌聯套又有“異名異曲套曲”和“同名異曲套曲”之分。
1.儀式性曲牌聯套
“異名異曲套曲”是指在不同的民俗儀式中,根據儀軌的發展嚴格演繹與儀軌內容相適應的鼓吹樂曲牌之聯套,曲牌數量與儀程的繁簡度成正比。套曲的規模和內容依附于民俗儀式的儀程和儀軌而定。在環洱海區域,民間習慣將一個儀式中從頭至尾演奏的曲牌稱為“一套”,主要有婚儀套曲和喪儀套曲,且具有規定性和靈活性特點。規定性表現為儀式中的曲牌用樂與儀軌是相應的,專牌專用較為常見;靈活性則體現在任何一個儀式中都會因為儀式東家的需求對儀式的流程和儀軌進行調整,用樂曲牌也就隨之變化。無論婚儀還是喪儀,樂班都按照規約用特定曲牌開始儀式和結束儀式,儀式進程中的曲牌則相對靈活,呈現出“兩頭固定,中間自由”的曲牌用樂形式。
“同名異曲套曲”是指在不同的儀程中根據儀程的性質、內容、目的等將多首同名異曲曲牌在同一環節間斷性演奏,具有擴展儀式的意義。環洱海區域有很多內容、功能、性質和情緒都極為相似的同名鼓吹樂曲牌,此類曲牌被用于民俗儀式的某一個儀程中,通過不同旋律的同功能曲牌來強化儀式的目的性、增強儀式的感染力。因此在環洱海區域各地產生了較多的廣義性的套曲,如【一杯酒】【上菜調】【坐席調】【鬧房調】【迎親調】【祭奠調】【孝堂調】【下葬調】等。以宴客儀程為例,在不同的環節演奏一套與儀式內容相應同名曲牌(見表1)。

表1 宴客儀程中的同名異曲類套曲(部分)
表1的曲牌用樂形式是環洱海區域各類民俗儀式中的典型特征,套曲中曲牌的功能、情緒相同,但旋律結構、曲調長短、節拍速度、調式調性等卻不同,從而在同一曲調情緒中形成了一定的對比。整體上看,以儀式功能為主要演奏目的的套曲體具有曲數靈活性和演奏間歇性的特征。
2.同宮系統曲牌聯綴
同宮系統內不同曲牌聯綴構成的套曲體在環洱海區域并不多見。在洱源地區用【龍上天】【栽秧調】聯綴,鶴慶地區用【過江調】和【過山調】聯綴等。根據調查發現,將曲牌進行聯綴使用是近代才有的藝術實踐。洱源縣原文化館館長楊光輝就曲牌聯綴的使用情況向筆者進行介紹:“在(大理)民間通常沒有聯綴體,把【龍上天】和【栽秧調】聯綴是因為表演的需要。洱源是嗩吶之鄉,洱源縣慶時導演要求出一個百人嗩吶隊的節目,但民間曲牌大都比較短小,就需要增加演奏時長。反復演一支曲牌比較單調,所以我就把【龍上天】和【栽秧調】聯綴起來表演,因為這兩支曲牌都是羽調式……”在鶴慶地區,通常在喪禮儀式的送葬過程中將【過江調】和【過山調】聯綴演奏。據鶴慶縣民族宗教事務局絞雄才介紹,婚禮儀式中曲牌大多為單牌單用。通過相關文化工作者的描述,筆者認為洱源縣的曲牌聯綴是有意識的,而鶴慶縣白依人⑩注:白依人是彝族的一個支系,因傳統民族服飾火草衣為白色而被稱為“白依人”或“白衣人”。主要居住在大理白族自治州鶴慶縣六合鄉。對曲牌聯綴使用則是無意識的,二者的共同點是曲牌聯綴的前提均為同宮系統使然,民間稱“調子一樣”,即為宮調系統一致。
由此,曲牌聯綴體在環洱海區域民間的使用具有兩個特點:一是曲牌聯綴體在環洱海區域使用不廣泛,二是曲牌聯綴的前提是同宮系統,而該特點就是中國傳統音樂套曲體的重要特征。因此,盡管洱源縣的案例屬于近代的“創作”,但目前很難斷定環洱海區域鼓吹樂套曲體是古代流傳至今,還是在近代以來一些音樂人進入田野之后的再創作。但無論哪種形式都是中國傳統音樂套曲音樂思維在環洱海區域鼓吹樂中的具體實踐。
(四)類集曲體
類集曲體是指運用集曲思維創制的結構體式。
集曲是對原有曲牌進行“摘句組合”的一種制曲手法,其最為明顯的特征是在同一宮調或異宮系統中從不同曲牌摘取曲調的一節或一段,按一定的樂學理論重組為一個新的曲牌。集曲均另立新名,而所集的曲牌均在集曲名上體現,所以從集曲名能尋到參與組合的曲牌,從而探究其組合規律和思維邏輯。筆者在楊育民《白族吹打》一書見到由多個曲調片段組成的曲牌【龍上天】?同注⑨,第160頁。(見譜例2),隨后便在田野中重點關注采錄了曲牌【耍龍調】【耍虎調】【栽秧調】【過山箐】,通過對其記譜與分析,認為這就是運用集曲思維即摘句組合手法構成的曲牌。

譜例2 【龍上天】
譜例2從宏觀上看,【耍虎調】的開頭音組和【耍龍調】的結尾音組音材料完全相同,后者音區移高了八度,形成了交錯音區的連環扣,讓兩支曲牌的銜接十分自然。【栽秧調】和【耍虎調】的首尾音組以“B”音為骨干由“E”音形成上下圍繞,形成材料倒影的銜接。【過山箐】的銜接則以【栽秧調】最后一小節的板位音高開始,與上一曲牌的銜接形成隔眼魚咬尾。【過山箐】與【栽秧調】的組合以“B”音為主音用功能圍繞的方式將兩支曲牌緊密連在一起。每一支曲牌中所摘之句的組合方式均使用了中國傳統音樂的不同旋律發展手法,所集曲牌均在一個宮調系統內。其創曲的方式和手法就是中國傳統的集曲手法,但組合而成的曲牌名則沒有使用集曲通常取原曲牌名中的一至二字合為曲名的方式,而是運用了民間常用的曲牌名【龍上天】來稱之。此處的【龍上天】只是名稱借用,其旋律與上文聯綴體中的【龍上天】沒有關聯。
從微觀上看該曲牌所摘取與運用的四支曲牌樂句之形式與手法可知,該類集曲體摘句重組的手法具有靈活性與創新性的特征(見譜例3)。首先,所集第一支曲牌【耍龍調】中摘取的樂句為原曲牌第一樂句的前六小節,旋律和調式不變,僅將最后一個音符作下移小二度的處理,以便接續下支曲牌的旋律,因此可將其視為原樣摘取。所集第二支曲牌【耍虎調】則是摘取中段樂句并進行較大的變化發展而加以運用,所摘樂句在原曲牌為G宮系統,樂句首尾音樂材料與原曲牌音樂材料相同,其余材料進行了大幅度的展衍變化,在新曲牌中將調高下移五度至C宮系統,從聽感上有新的主體樂思,但因為樂句較短沒有形成較大的偏離感。所集第三支曲牌【栽秧調】首先摘取了第一樂句的部分音樂材料通過音區改變、音符上移或下移來進行變化發展,之后又摘取第二樂句開頭的音樂材料和第三樂句結尾的音樂材料糅和發展為一個樂句。最后原樣運用第一樂句的第一小節進行同音反復,后接一個梯度下行的樂匯連接下一支曲牌。所集第四支曲牌【過山箐】為單段體,由引子、四個樂句和一個尾聲構成,其中第四樂句是將第一樂句通過“換頭”的形式發展而來。結尾部分摘取的是【過山箐】的引子和第一樂句,在旋律發展上通過添眼加花的形式進行細微的變化。最后五個小節在【過山箐】中反復出現,是為主題旋律,因而該樂句的類集曲體中的具有較強的辨識度。

譜例3 類集曲體所摘曲牌樂句片段;董世雄演奏;張麗記譜
從以上分析得知,大理市白族民間流傳的【龍上天】在集各支曲牌時,總體為首尾樂句原樣運用,中部旋律變化發展的組合手法,而該手法在局部樂句的摘取運用中也有體現。此外,大理市有的【耍虎調】是從【耍龍調】【龍擺尾】和原曲牌【耍虎調】中摘句組合而成。洱源縣有的【栽秧調】則從【耍龍調】【過山箐】【跳彩】中摘取部分材料重新組合而成。這些通過摘句重組的曲牌在樂句的摘取和使用的手法是否與【龍上天】一致還有待進一步深究。在環洱海區域民間還有很多類似這樣使用集曲思維來進行創曲的形式。由于該曲式在環洱海區域鼓吹樂中不具規模性,集曲之手法沒有形成一套規范性體系,故本文暫且將此種形式稱為“類集曲體”。
結語
在上述討論中不難看出,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是中原文化與邊疆少數民族文化交流互融的活態樣本,其形成和發展體現的是一種整體性、包容性的學習方式和接納模式,從而保持了本有的自由度和靈活性。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在歷時與共時的發展過程中,體現了文化相通性、思維延續性和音樂共享性,因此,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具備了中國傳統曲牌音樂的文化公認與共性因素,這種構成性對中國傳統曲牌和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而言都具有雙重意味。一方面,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繼承了中國傳統曲牌音樂文化的精神價值沉淀,這是在二者(個體與整體)共生共存的基礎上累積而成的具有超越延續性的地域化音樂形式,是中國傳統音樂及曲牌之內涵的重要組成;另一方面,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與中國傳統曲牌的音樂形式、曲牌成分、曲牌思維、曲牌功能等要素彼此貫通,具有同一性特征進而成為一個有機整體,是“大一統”文化觀框架下的多元音樂呈現。環洱海區域鼓吹樂曲牌通過差異的填充和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的文化共同體,其文化根脈是中華傳統文化,文化身份是中國傳統音樂,是“一體多元”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表演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