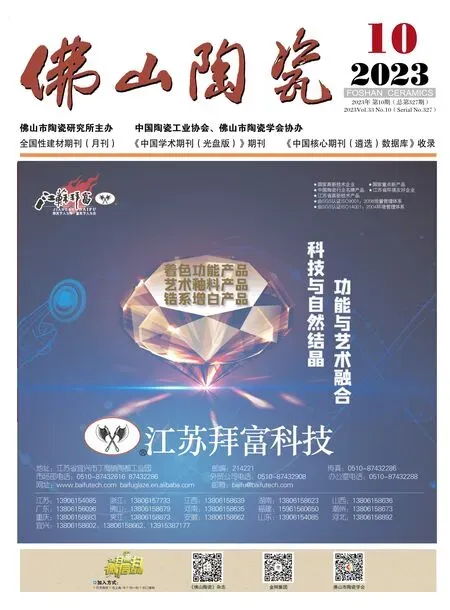論“珠山八友”瓷繪藝術中審美趣味
黃鑫,郭婷
(1 湖北美術學院,武漢 430000;2 武漢小藍書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武漢 430000)
1 珠山八友瓷繪技藝的傳承
1.1 傳統陶瓷的衰微
清末成為封建王朝最后絕唱,且太平天國占領景德鎮長達七年,皇室力量的衰微導致景德鎮御窯廠搖搖欲墜,難以維系。工人們不得不另謀生計,一生畫瓷的匠人們在戰火平息后,重操舊業,以畫瓷謀生。此時,多以“淺絳彩”為主,依靠畫工打開市場的大門,這也對晚清景德鎮陶瓷產生重大影響。在劉新園先生《景德鎮近代陶人錄》中寫道兩點重要影響:“1.自淺絳彩風行后,景德鎮無論從事釉上或釉下彩的藝人都大量使用宋元以來的紙絹繪畫為粉本,使統治彩瓷許多世紀的官窯紋樣變得古老而又陳舊。2.繼淺絳藝人之后,景德鎮的藝人都要在瓷器上寫下自己的姓名和雅號,題上詩詞和紀年,促進藝人對書法和文學的理解,毫不夸張的說,晚清淺絳彩藝人是景德鎮近現代彩瓷風格的開創者。”正是以上影響,景德鎮陶瓷藝人對于書畫的認識進一步加深,雖然其藝人文化程度低,但僅專工一種題材,這就使得在晚清之際,這批文人瓷畫師倡導的淺絳彩瓷幾乎取代古粉彩瓷的地位,成為當時的主流。
1.2 其他繪畫技法的影響
“珠山八友”的形成,據《景德鎮陶瓷史稿》記載,“珠山八友”形成的時代是在“清末民初”,但根據吳海云先生的考證并推斷“珠山八友”的形成是在“民國十五年以后”。“珠山八友”皆作宣紙畫,并以詩書畫入瓷以美化瓷器,吸收各家所長,更是形成了一個新的潮流。民國時期,以“珠山八友”為首的新粉彩瓷藝家們吸收了“淺絳彩”、傳統“粉彩”的表現形式和繪畫技巧,并在此基礎上不斷進行實踐,力圖解決釉料緊密性不強的缺陷,并不斷加入新的技法,將傳統的文人畫風格和創新意識緊密結合到陶瓷藝術中。這使得以“珠山八友”為首的瓷藝家們的藝術形成繼承了中國傳統繪畫藝術,對傳統粉彩進行了改革,更是形成了開放創新的近現代景德鎮陶瓷風格。除此之外,“珠山八友”還受到了新安畫派的影響,新安畫派以徽籍畫家頗多,而在當時“淺絳彩”瓷藝家金品卿、程門等人皆出自于此,自幼耳濡目染頗受影響,新安畫派潛移默化的影響著這批“淺絳彩”藝術家,進而影響到了“珠山八友”并將其繪畫技法吸收,產生一定影響。而對于“珠山八友”影響最為深刻的應為“揚州八怪”,其中王琦是“揚州八怪”中黃慎的師承者,更是在瓷板畫《麻姑獻壽圖》題記中標明“仿黃慎之筆意”繪制而成,除此之外,兩者皆在創作上不受約束,不同于時俗,強調“師古而不泥古”,“珠山八友”更是有人效仿“揚州八怪”進行作畫,“揚州八怪”對于“珠山八友”的影響顯而易見。
1.3 創新求變,以變為生
以“珠山八友”為首的瓷繪家因注重詩詞、書法等各方面造詣和修養,并且秉持“師古而不泥古”,這也導致他們的藝術作品呈現百花齊放,各具特色。其藝術作品頗具感染力和表現力,主題思想和個性展現的淋漓盡致。如汪野亭將西方明暗透視的方法帶入瓷繪中,使得畫面更加生動,顏色更加艷麗,又如王琦將西洋畫陰陽彩瓷技法引入他的人物畫創作中,對人物的外在構造,面部輪廓注重明暗面的體現。創新求變的精神使得“珠山八友”的作品在民國時期的景德鎮異軍突起,形成自身獨特的風格。
當“淺絳彩”逐漸為世人所膩,缺陷日益顯現,“珠山八友”為首的瓷藝家們主動求變,重新回到粉彩的藝術表現形式,擺脫清代官窯繁密紋飾和濃烈的宮廷皇家趣味,將注入了文人畫風的“淺絳彩”和“師古而不泥古”的揚州八怪的影響融匯到新新彩之中,打造出豐富華麗帶有文人氣息,雅俗共賞的新風格。
他們從傳統的“紅店”藝人的模式下走出來,將這些文化營養運用于新粉彩的創作之中,開拓了陶瓷藝術作品繪畫與文化融為一體的藝術領域,并給后人留下了一個新的理念:“瓷藝應與時俱進,融入時興畫技。”珠山八友瓷繪將文人畫的繪畫思想及文人情懷帶入陶瓷繪畫中。畫瓷器易,畫修養難,珠山八友吸取前人教訓,為景德鎮近現代陶瓷開啟了一個新的平臺。正如鄒文光先生所說;他們完成了從陶瓷工匠到陶瓷的文人的轉變。
2 珠山八友瓷繪中的審美意識
“珠山八友”所產生的時代背景可以看出,他們正處于社會變革的時期,“珠山八友”以創新求變,充分吸收了中國傳統藝術的影響,并結合西方近現代文化思潮所產生的影響,形成集文人畫、世俗化、現代化為一體的雅俗共賞的審美意識。
2.1 獨特的創作理念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前半期的景德鎮,除了晚晴御廠生產的宮廷用瓷之外,其彩瓷可粗分為如下三類:(1)以前代之青花、古彩(或稱硬彩)、粉彩為模式而生產的仿古瓷;(2)質地較粗之青花、古彩、粉彩瓷;(3)吸取文人畫的某些技法而產生的一批淺絳、粉彩和青花細瓷。此時的第三類,多為官僚、地主富商們家中裝飾所用。如此背景之下,出現了金品卿、王少維等近代陶瓷美術的開拓者。而這批淺絳彩入民國后逐漸失傳,據景德鎮陶瓷史稿載:“……原因是自清末洋彩(新彩)傳入后,其顏色之鮮艷,和手續之簡單,就取淺絳而代之。”而此時,繪瓷著者頗多,如王曉婷,擅仕女、周小松,擅神佛、許尚禮、擅花卉,稍晚則有所謂“珠山八友”,各有所長。
而大量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形成對沖的時期,“珠山八友”以上述繪瓷技藝脫穎而出顯然不足。他們在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也吸收西方畫法,風格上各有所長,皆不落于俗套,在受到海派繪畫藝術、西洋藝術、中國傳統山水畫藝術等多種藝術流派的影響,形成自身獨特、雅俗共賞的風格。誠如,劉雨岑先生、程意亭先生為代表:前者獨創“水點桃花”、黑葉描金“牡丹”與“繡球”,候著此時在顏料的制作上多有經驗,打造出設色秀麗,兼具柔美與豪情的格調。更有“珠山八友”中擅魚者——鄧碧珊,傳世之作多為粉彩魚藻圖,開瓷藝魚藻文人畫之先河,此前瓷上畫魚多為裝飾之類,鄧碧珊在魚鱗繪制上獨運功力。

圖1 左粉彩魚藻圖瓷板民國鄧碧珊景德鎮中國陶瓷博物館藏

圖2 右粉彩魚躍生趣圖瓷板民國鄧碧珊景德鎮中國陶瓷博物館藏
所繪魚生動傳神,魚的細節寫實逼真,構圖簡單大方,獨具簡約秀美之風,雅俗共賞。顯然在傳統的中國畫筆墨趣味之上,融入了日本東洋繪畫技法,可見“珠山八友”創新之風已然顯現,更有如汪野亭將西方明暗透視的方法帶入瓷繪中,使得畫面更加生動,顏色更加艷麗,又如王琦將西洋畫陰陽彩瓷技法引入他的人物畫創作中,對人物的外在構造,面部輪廓注重明暗面的體現。
“珠山八友”有著兼收并蓄的思想、注重個人技法提升與創新,更是因為他們有著一個共同的創作理念,促使他們成為了新一代的領軍人物。畫瓷器易,畫修養難,傳統紅店藝人十分注重圖樣,這些圖樣往往代代相傳,久而久之,就成為了缺乏生命活力的樣板。而“珠山八友”不斷創新的獨特創作理念打破了傳統的作風,與諸多“紅店模式”工作下的傳統匠人不同。他們打破了傳統的模式,將整個理念從傳統的“紅店模式”中分割出來,開拓了陶瓷藝術作品繪畫與文化融為一體的藝術領域,并給后人留下了一個新的理念:“瓷藝應與時俱進,融入時興畫技。”“珠山八友”完成了從借鑒、繼承到創新的整個過程,并秉持著新的創作理念,促使著陶瓷匠人們向陶瓷藝術家的身份發生轉變。可以說,“珠山八友”這批建國初期的新粉彩藝術家將其技藝傳授于其后輩及其他有志于新粉彩創作者,從而形成了蔚為壯觀的新粉彩創作群體。
2.2 獨特的文人思想
文人畫是中國繪畫中特有風格,初現于宋,歷經宋、元,盛于明、清。元代,文人畫成為中國古代繪畫中最為重要的繪畫體系,至于明清文人畫更是盛行一時,相關理論著作頗多。文人畫創作上以求詩、書、畫、印結合,表現個性。在《景德鎮陶瓷史稿》中記載:“瓷器題字是當時一種風氣,造瓷一方面要遷就這種風氣,以便使瓷器易于銷行;一方面又要顧到裝飾簡便,減少裝飾時間,降低成本。所以他們就利用最簡單的筆畫和簡單的詞句,以趨時尚,而又要不使有文不對題的弊病,如‘仿元人法’。‘八大山人’等句……”通過記述可以看出,在民國這種題詞已然成為一種時尚,這種時尚就要求當時的陶瓷藝人對于詩詞有一定的了解和認識。“珠山八友”也深受影響,他們對將中國文人思想與瓷器結合,王大凡先生曾畫《珠山八友雅聚圖》,并附題詩:“道義相交信有因,珠山結社志圖新;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蟲魚獸與人;畫法惟宗南北派,作風不讓東西鄰;聊將此幅留鴻爪,只當吾擠自寫真。”可謂是對“珠山八友”瓷繪較為高度的概括。誠然,“珠山八友”所創作的風格各異,各有所長,有善“工筆”,有善“寫意”,亦有“兼工帶寫”,但無一不對中國傳統繪畫有著一定的繼承。例如,王大凡所創“落地粉彩”的技法,既是采用如國畫中工筆畫的“分染”的辦法,配以特殊手法燒制,色彩自然,貼近生活之效;又如《粉彩柳毅傳書紋瓶》選取秀才劉毅赴京應試遇一位女子在冰天雪地下牧羊的民間愛情故事,選材貼近生活,表達民間對于自由愛情的向往。所繪人物兼工帶寫,用筆流暢,所繪馬、羊神色輕松,線條動感飄逸。

圖3 粉彩大富貴亦壽考圖瓷板王大凡藏景德鎮中國國家博物館

圖4 粉彩柳毅傳書紋瓶王大凡民國藏景德鎮中國國家博物館
而作為瓷業美術社的副社長王琦,在瓷繪的人物形象上更有獨到見解。其一生都與人像相關,17 歲以捏面人謀生,后學畫瓷版畫像。所畫人物用筆剛勁、衣紋繁而不亂,整而不散,人物臉部刻畫更是細致,加以草書題畫,風格在“珠山八友”之中頗為突出。如圖5、圖6。圖5、6 中老翁與鐘馗形象刻畫細致,衣紋褶皺繁復,準確凝練,極具王琦個人風格。這種奔放的畫風和流暢的筆法,皆因其對于“揚州八怪”的黃慎的推崇與學習。而圖5《粉彩鐘馗除邪降福圖瓷板》因其體積感而讓王琦被稱為“西法頭子”。彼時的王琦已經開始脫離“揚州八怪”的影響以及對西畫認知,形成獨具一格的畫風和藝術特征。《珠山八友藏品鑒賞》一書之中將之王琦的人物畫稱之為“介乎于中國傳統減筆描與枯柴描之間”《珠山八友》書中則如此形容他的藝術特征“線條放達而又疏松,尤其中鋒用筆比黃慎的衣紋線條更有力度和厚度,也更為概括。”而其他幾位各有所長不一一贅述。值得一提的是“珠山八友”所處的時期是“國破家亡,匹夫有責”的動蕩時代,此時的景德鎮瓷器,也處于變革時期,官窯衰微,據載“民國以來,景德鎮的瓷器,還是繼承著清末作風。日用瓷與美術瓷在質量上都有愈趨愈下之勢。”而“珠山八友”的瓷繪融多家之長,打破了清末傳統的作風。

圖6 粉彩漁翁圖瓷板(右)民國藏景德鎮中國陶瓷博物館
陳師曾指出“文人畫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學問,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珠山八友”積極創新,不落于俗套,此為思想,動蕩不安的社會之下,仍積極發揚陶瓷文化,此為才情。而在鐘連生的王琦小傳中載“王琦為人仗義大方,他在景德鎮東門頭自建了300 多平方米的住房和畫室,其中數間專供畫友作畫、住宿。”可見,以王琦為首的“珠山八友”人品正直。關于學問,“珠山八友”各有所精,他們大多來自“紅店”,這也是他們的缺陷,以王琦為例,從捏面人到彩繪瓷像,王琦經歷了不斷的學習,拜師鄧碧珊后更是不斷練習書法學習詩文。每一位“珠山八友”的成員們都經歷了不斷的學習終為一方專精大家。“珠山八友”可謂因道相交,追求創新,兼收南北風,自創一派。在社會動蕩的時期,他們將挽救陶瓷藝術為己任,不斷創新。
“蓋藝術之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應者也。”他們的藝術作品以世俗生活為源泉,以兼收并蓄不斷創新的思想為發展,已然形成極具特色的文人思想。以“珠山八友”為核心的新粉彩,在融入傳統山水畫藝術,加以文人思想入瓷后。陶瓷工人、匠人就開始向陶瓷藝術家發生轉變。這無形之中提高了陶瓷制作者對于審美、文化素養上的要求。藝術家們更多的是在追求以繪畫為主的純藝術,而不只單純是追求工藝,以“意境”為重的文人思想深刻影響著陶瓷繪畫。在瓷器上繪畫,可以充分發揮工藝和文化的潛力,讓大眾從欣賞陶瓷工藝轉變成欣賞陶瓷繪畫內容,這是陶瓷文人繪畫審美的拓展與變遷。也是陶瓷匠人向藝術家發生轉變。
3 結語
陶瓷藝術,早在商代就登上歷史舞臺,經歷數千年的陶瓷繪畫為中國文化的一大代言詞。19 至20 世紀是中國面臨巨大變革的時代,陶瓷藝術的審美趣味在這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珠山八友”作為清末民國的陶瓷大家,他們的工藝審美的轉變承載著許多因素,如中國的文人品格,西方各種藝術流派的流入等等因素。而這些思想的融入,也讓粉彩在民國時期煥然一新。新粉彩帶來的革新,開啟了現代陶瓷藝術的先河,打破傳統的“紅店模式”,告訴后人創新乃器物新盛之源。陶瓷藝術是中國藝術史上博大精深的文化,其精美的制作,絢麗的工藝正是陶瓷藝術經久不衰的秘訣。當代中國陶瓷藝術家們更應該肩負起中國陶瓷燦爛文化的重擔,緊跟時代努力創新,讓中國陶瓷藝術在世界中綻放更加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