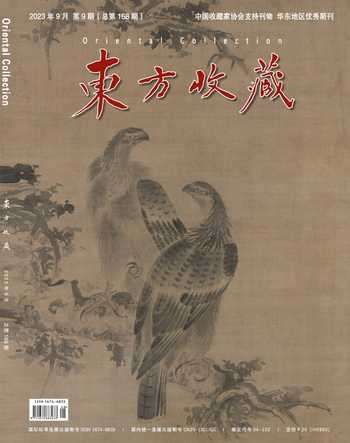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數字化展示探析

摘要:當前博物館數字化展示形態日新月異,元宇宙概念及其應用場景的出現,搭建真實的文物生態系統,實現博物館的虛擬在線體驗,讓觀眾突破時空界限,成為歷史文化的親身參與者,這無疑是未來博物館數字化建設的重要出路。文章以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為例,橫向研究對比國內外博物館數字項目的優秀案例,縱向分析國內博物館數字化建設的特點以及元宇宙博物館的特點,進而探索未來元宇宙博物館的建設思路,為現代博物館數字化展示與傳播提供有價值的設計思考。
關鍵詞: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數字化展示;元宇宙
2022年3月,國內60多位博物館館長、學者聯名發起《關于博物館積極參與建構元宇宙的倡議》,提出博物館應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方向,積極主動參與建構元宇宙,在相關主題的國際對話中發出中國聲音。[1]美國博物館協會 AMM 主席Laura Lott提出:“數字化技術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巨大的機會,讓世界各地的人即便沒有親自來博物館也能獲得我們的藏品,數字化是對現實文物的一種增強。”元宇宙結合虛擬沉浸等多元手段,使傳統文化以更年輕的方式促進博物館展示形式豐富起來,這是未來博物館展示互動的重要途徑,博物館與元宇宙的碰撞也令人期待。因此可以說,元宇宙博物館的數字化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博物館數字化展示現狀
(一)國外博物館數字化展示
國外博物館的數字化探索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從圖書館的數字化采集開始,伴隨計算機技術的發展,逐漸邁向博物館數字化建設,開展館藏文物的數字化保護工作。1995年,IBM東京研究所與日本民族學博物館合作實施側重博物館教育的“全球數字博物館(Global Digital Museum)計劃”,為公眾提供藏品資料檢索、網上瀏覽和編輯等,這是亞洲地區最早開展博物館數字化展示工作的項目之一。進入21世紀,國外博物館數字化已基本實現館藏資源數據共享。2017年,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開放“資源獲取”項目,在線上公開其館藏的 37.5萬余件文物和藝術品的高清圖片,供公眾免費下載使用。除此之外,國外博物館更加注重展示手段的交互性和娛樂性,近年來更是融入元宇宙概念進行積極探索。例如盧浮宮第一個虛擬現實項目“蒙娜麗莎·玻璃之外”,用8分鐘的VR體驗向觀眾展示了世界名畫《蒙娜麗莎》的背后故事;巴黎博物館利用增強現實技術“復活”已滅絕物種,設置虛擬向導、沉浸式體驗和虛擬互動,增強參觀的趣味性。
(二)國內博物館的數字化展示
隨著政策支持力度和民族文化自信的加強,國內博物館數字化建設正迅速發展,數字化探索持續向縱深方向發展,在元宇宙方面已經具備以下幾個特點:
1.“空間虛擬仿真”線上展覽
VR 展廳是國內較為成熟的線上展覽模式,即用全景攝影、虛擬現實技術等復原實體展覽,并支持VR瀏覽,如北京故宮博物院全景游覽、敦煌研究院數字洞窟等,以及龍門石窟“云上龍門”小程序圍繞景區游覽環線制成VR虛擬漫游,720 °暢游龍門實景。
2.數字藏品火熱“群像”
自2021年起,國內博物館如火如荼地開展館藏文物的數字藏品開發。截至2022年9月,包括廣東省博物館在內的20余家國內博物館總計發售數字藏品300余件,且一經發售便銷售一空,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形成火熱“群像”。筆者調研近兩年國內博物館發行數字藏品的情況并進行梳理(見表格),可以發現,目前發售平臺相對集中但沒有形成統一性,部分藏品還存在重復發售的現象。
數字藏品與普通三維模型的區別在于能夠使用區塊鏈技術生成一個唯一的數字憑證,保護數字版權并進行發售、購買、收藏和使用。用戶可在手機端進行 AR 體驗,實現360 °鑒賞,這也是元宇宙博物館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內元宇宙博物館的建設擁有豐厚的土壤,70多萬處不可移動文物和1億件/套國有可移動文物,星散在廣闊的中華大地上,綿延在歲月長河里,構成元宇宙博物館的基礎架構。但是,文物數字化比例仍較低,資料顯示,“全國調查的文物數字化比例約為44.11%,其中珍貴文物藏品數字化比例為67.82%。而在國外,法國盧浮宮數字化程度高達75%,大英博物館文物的數字化比例也近50%”[2]。這就導致大部分文物的三維模型和高清圖片等數字資源完整性不足,質量參差不齊,缺乏統一標準。未來元宇宙博物館的建設任重而道遠。
(三)智慧化是博物館數字化展示的有效變革
所謂智慧博物館,是以數字化為基礎、智能化為手段、智慧化決策為標志的博物館新業態。[3] 從數字博物館到智慧博物館,充分利用信息技術成果,處理收集關鍵信息,衍生云游博物館、AI 智能導覽等展示方式,提升公眾服務水平,增強互動體驗。可以說,智慧博物館是博物館數字化展示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引導技術應用的一種有效變革。
二、博物館的元宇宙化
(一)元宇宙概念
網絡科技發展到當下,已經進入最新臨界點。現在的互聯網通過電子屏幕傳導信息,存在一定的信息壁壘。[4]元宇宙則打破這層信息媒介,使信息從被動接收轉為主動選擇和獲取,并能夠讓人在沉浸的、立體的、可感知、與主體融合一體的實體互聯網形態中社交和工作。
元宇宙是整合多種技術而產生的虛實相融的互聯網應用和社會形態[5],即“沉浸式互聯網”。當下的一些網絡游戲,在社交屬性上就具備元宇宙的互動特征。例如《堡壘之夜》(Fortnite)與美國饒舌歌手特拉維斯·斯科特(Travis Scott)在游戲中展開跨界合作,舉辦 “ASTRONOMICAL”虛擬演唱會,據官方統計,吸引超過1200萬名橫跨美國、歐洲、亞洲、大洋洲等服務器的玩家同時在線參與。
(二)元宇宙博物館
元宇宙博物館具有兩項技術特征:一是虛擬現實技術(VR)。VR能夠實現博物館虛擬化、參觀體驗的沉浸感,將博物館文物及周邊環境直觀鮮活地呈現在觀眾面前;二是區塊鏈技術。區塊鏈技術以非同質化代幣NFT(NonFungible Token)加持下的虛擬貨幣為特征,為元宇宙里的虛擬文物賦予所有權和價值,不可隨意復制和轉發。正如前述,各大博物館發行的數字藏品均包含相對應的區塊鏈證。除此之外,由于數據全部保存在服務器中,元宇宙博物館可以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進行文物展示,沒有被毀壞、偷竊的危險。[6]
實現元宇宙博物館的完整生態系統,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先從淺層文物展示過渡到深度內容開發,再從“場景復原”到“沉浸參與”,打造沉浸感。當前一些博物館將建筑和藏品放置在VR虛擬空間里,游客通過“云端訪問”或佩戴VR設備進入體驗,就是元宇宙博物館基本的訪問形態,但受限于VR硬件佩戴舒適度、時長及三維場景所帶來的眩暈感等因素影響,多數觀眾無法適應長時間的體驗,VR觀展的全民普及還有一定距離。
總的來說,當前國內外博物館的元宇宙化仍處在概念和基礎研發階段,但讓觀眾突破時空限制,成為歷史的親身參與者,無疑是將來智慧博物館發展的重要方向。未來元宇宙博物館將延續博物館承載歷史、溝通古今的橋梁作用,利用更先進的技術,將傳統文化以可視化、可體驗的形式永久留存下去。[7]
三、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元宇宙博物館的建設思路
(一)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的數字化展示實踐
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以下簡稱夏博)毗鄰二里頭遺址而建,以二里頭文化為核心,系統展示夏代歷史文化、二里頭遺址考古歷程以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相關研究成果。夏博如今已先后完成智慧化信息平臺、數字館、多人互動展示墻、熱力導覽小程序等的建設;開發“我為夏都造園林”夏代工程建造互動游戲。此外,為滿足無法到場游客,夏博官網、官方公眾號也上線“中華牙璋展”等虛擬展覽。
1.夏博數字館
夏博數字館以“‘最早中國’探尋之旅”為主題,利用沉浸式投影空間、半造景三維數字劇場、雷達感應投影互動等數字技術復原二里頭遺址的整體面貌。展館由序廳、A區、B區三個區塊組成,設立五大主題展示區,再現夏代都城規模和形制、政治禮制、官營手工作坊、國家級祭祀儀式等場景,讓觀眾身臨其境地感受夏代先民生活和最早王朝的國家氣度(圖 1)。
2.藏品數字化
夏博藏品類型涵蓋青銅器、陶器、玉器、綠松石器、骨角牙器等,在數量和質量上均形成規模和體系。通過對文物進行高精度三維建模、高清拍攝,完整記錄文物的細節和全貌,并經后期處理,在多媒體平臺進行三維展示,為后期三維打印、制作數字復制品、實現無實物數字展出等諸多數字項目提供數據支撐。
3.虛擬展廳
夏博官網、官方微信公眾號針對基本陳列和臨時展覽,均上線虛擬展廳,能夠最大限度地完整保存已經撤展的文物和文字信息,從而形成系統化的文化研究體系。但目前虛擬展廳仍以最簡單的靜態展示模式為主,館內藏品的呈現內容和數量還相對有限,游客點擊鼠標瀏覽全景展廳的過程也不流暢,使這種云端訪問方式頗為受限。
4.二里頭考古遺址公園VR全景漫游
該項目復原二里頭時期夏代先民的生產生活場景,以VR虛擬漫游形式實現二里頭遺址虛擬重建。游客佩戴 VR 眼鏡穿越回到3800年前的夏代,720 °探索二里頭考古遺址公園,體驗二里頭先民生活,發現更多遺跡信息(圖 2)。
(二)元宇宙沉浸式展館
瑞士日內瓦大學團隊復原龐貝古城遺址,利用AR將數字內容疊加在現場遺跡環境中,使游客能在龐貝古城遺址上體驗歷史情境。2022年3月,河南智慧旅游大會線上會議在網易瑤臺召開,會議基本搭建起一個較為完整的虛擬場景,提供實時參與互動,古典與現代場景的融合也增強了用戶的臨場體驗。
二里頭遺址是夏博建設的重要依托,作為夏王朝中晚期都城,二里頭遺址被譽為“最早的中國”。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文化,是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對研究華夏文明的淵源、國家的興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設、王宮定制等重大問題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有廣闊的元宇宙數字創作空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遺址是一號宮殿,這是我國院落式建筑群組合的最早起源,由主殿、廊廡、大門和庭院組成,其中主殿坐北朝南,面前是空曠寬闊的庭院。[8] 諸如此類,通過復原二里頭遺址區一號宮殿遺址,以小型元宇宙的沉浸式展館拓寬夏博的展覽空間,增強臨場體驗,這個過程類似于搭建三維游戲場景,涵蓋生態環境、房屋建筑和人物活動等因素。
(三)全真虛擬角色
元宇宙博物館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創建全真虛擬角色尤為重要。2022年6月,敦煌研究院發布敦煌莫高窟官方虛擬人“伽瑤”,作為數字敦煌文化大使,參與多種文化傳播新模式;中國國家博物館推出兩名虛擬數智人,作為智慧博物館的形象代表。而夏博創作研發的IP“小夏”,是一位來自3800年前的夏代貴族形象,目前已運用于數字館、研學課堂的講解等工作。作為今后夏博智慧傳播的“窗口”,“小夏”的虛擬角色開發還有很大的空間。融入AI技術,讓“小夏”儲備豐富的二里頭文化知識,勝任數字講解員角色,和游客進行游戲互動;同時,參與虛擬直播、二里頭文化科普、IP創新跨界合作等多種文化創新模式;未來作為一部分接入元宇宙博物館中,擔任講解等工作。
用戶通過創建自己的虛擬化身進入元宇宙,與他人交流,和虛擬場景發生交互。針對夏博的虛擬角色設計,可以從擬人化與風格化的角度出發,與夏代古樸稚拙的風格形成統一,與先民崇尚自然、辛勤勞作的理念相契合。與此同時,注意虛擬角色可操作性和流暢性,加之氣氛渲染,使得用戶能夠真正融入虛擬環境,從而產生強烈的代入感。
(四)新的文物呈現形式
元宇宙博物館的展示主體還是文物,在現實博物館當中,設計師根據場地大小、文物類型和歷史脈絡等因素劃分展覽區域、定制玻璃展柜,將不同的文物陳列在展館當中,這在保證文物安全的同時隔開了文物和觀眾之間的距離,但是元宇宙博物館可以突破場地、展柜的限制,以“超現實主義”的方式展現在人們眼前。元宇宙博物館周圍可以出現任何能夠想象到的場景,例如置身于宇宙中的一座博物館或在海底的遺跡博物館等;文物的呈現方式也更加多元,例如讓文物“動起來”,或者通過一件夏代青銅器,人們可以走進3800年前的鑄銅作坊,體驗青銅器的制作流程;同時還能實現多人在線參與,交流互動,挖掘文物自身內容,了解文物背后所蘊含的歷史信息。
(五)隱私安全保護
元宇宙作為實體互聯網的產物,從用戶中獲取的數據信息會更加全面,但這些龐大且涉及用戶個人隱私的數據一旦遭到泄露,影響可能會更大,因此對元宇宙博物館的隱私保護必不可少。要建立起針對文博系統的元宇宙博物館的法律法規體系,為用戶在元宇宙博物館中游覽、體驗提供約束和保障。此外,正確的輿論宣傳引導有助于普通民眾減少抵觸心理,進一步了解元宇宙博物館并親身體驗。
目前,夏博依托二里頭遺址,已經樹立起“最早中國”的文化定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游客和研學機構紛紛慕名而來。基于夏博的元宇宙博物館建設,能夠進一步加深觀眾對夏博的印象,增強以二里頭文化為起點的中原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形成更為廣泛而深遠的文化影響力和傳播力。
四、結語
元宇宙博物館是未來智慧博物館發展的重要方向,它通過創新的方法繼承、發展傳統文化,延續了博物館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橋梁作用,拓寬了文物展陳方式。其通過易于理解、互動參與強、趣味性濃厚的虛擬沉浸式體驗和實時交互,拉近文物與觀眾間的距離,搭建起一個真實的文物生態系統,將文物背后的歷史信息真實還原,讓用戶更好地了解沉淀千年的文物和二里頭文化,真正實現博物館的虛擬在線體驗。
參考文獻:
[1]中國新聞網.六十位館長、學者聯名倡議博物館積極參與建構元宇宙[EB/OL].[2022-03-2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8354428684431501&wfr=spider&for=pc.
[2][3]錢曉鳴,劉凡,謝清青,嚴金林.2022 年中國移動互聯網背景下的智慧博物館建設[A]//唐維紅,唐勝宏,劉志華.移動互聯網藍皮書:中國移動互聯網發展報告(2022)[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263-277.
[4]曹秀蓮.元宇宙發展現狀調研與安全風險研究[J].中國信息安全,2022(06):90-93.
[5]]簡圣宇.“元宇宙”:處于基礎技術階段的未來概念[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39(02):1-16.
[6]李紅霞,蔣麗麗.當前基于Web3D虛擬現實技術的公共博物館構建探索[J].藝術百家,2014,30(S1):318-320.
[7]鐘國文,張婧樂.我國智慧博物館研究綜述[J].科學教育與博物館,2020,6(05):347-354.
[8]杜金鵬.二里頭遺址宮殿建筑基址初步研究[J].考古學集刊,2006(00):178-236.
作者簡介:
郭兆瑋(1994—),女,漢族,河南三門峽人。碩士研究生,文博助理館員,研究方向:博物館數字化展示與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