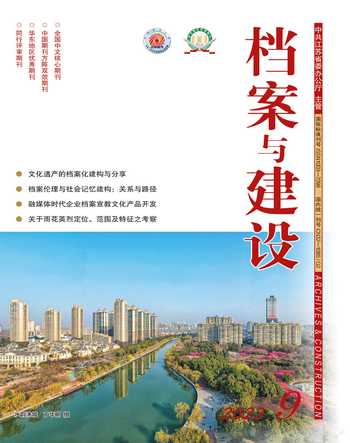檔案參與國家敘事:邏輯、維度與策略
向曉旭
摘 要:檔案形成于國家各項實踐活動中,是一項參與國家敘事的重要資源。文章首先對檔案參與國家敘事的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進行了分析,并從敘事內容、方式和情境三個層面探討了檔案參與國家敘事的維度結構。基于以上維度和國家敘事面臨的實踐困境,針對性地提出多維復合與議題貫通、場景建構與共情表達、平民視角與多元共構的推進策略,以期促進檔案參與國家敘事質量與效果的提升。
關鍵詞:國家敘事;檔案資源;敘事表達
分類號:G273.5
Participation of Archives in National Narratives: Logic, Dimensions and Strategy
Xiang Xiaoxu
(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
Abstract: Archives were formed in the national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they are important resources to participate in national narratives.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of archives’ participation in national narratives, and probes into the 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archives’ particip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narrative content, mode and situation. Based on the above dimensions and practical dilemma of national narratives, the strategies of multidimensional combination and topic integration, scene construction and empathy expression, civilian perspective and integrated diverse development a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archives’ participation in national narratives.
Keywords: National Narrative; Archival Resources; Narrative Expression
國家敘事即一個國家以何種方式呈現和傳播自身的文化底蘊、發展歷程和價值理念,以達成對內建立國家認同、增強民族凝聚力,對外展現國家形象、提升國際話語權的目的。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1],對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國家敘事體系提出了要求。檔案作為承載記憶的原始記錄,具備參與國家敘事的潛力與價值。對內,檔案信息記錄性、管理工具性等特性與國家認同的內在邏輯相契合[2],可提供國家認同的信息資源[3];對外,檔案的真實性和歷史性使其具備建設國家形象、開展國際傳播的天然優勢。[4]基于檔案的敘事活動,可將檔案同多元視域結合,在促進檔案資源開發效能和敘事能力提升[5]的同時,助推對歷史文化和國家精神的解讀。[6]
現有研究已認識到檔案在建立國家認同中的作用及敘事價值。然而,在分析檔案的敘事實踐時,現有研究多面向某類具體的實踐活動,未立足于國家敘事實踐的整體視域,全面梳理檔案參與國家敘事的相關問題,對國家敘事面臨的實踐困境亦缺少深入關注。鑒于此,本文立足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進程與國家敘事的現實問題,從邏輯、維度和策略三方面,系統探討檔案為何要參與、可參與哪些方面以及如何更好地參與國家敘事的問題,以期充分發揮檔案的敘事潛力,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提供實證支撐與精神力量。
1 檔案參與國家敘事的邏輯理路
1.1 理論邏輯
理論層面,檔案學與敘事學具備融合共通之處。敘事學視域下,一方面,敘事本身即講述故事的過程及其成果的綜合,以敘事文本為依托。檔案是社會實踐的原始記錄,其內容的清晰確定性與形成過程的社會性契合了敘事文本的基本要求,可成為敘事學分析研究的對象。另一方面,敘事學日益呈現出的跨學科趨向[7]為其同檔案學研究結合提供了空間,二者在歷史建構、文化隱喻和話語形塑等方面有著共通的研究取向,同檔案學的融會貫通也可促進敘事學研究的豐富拓展。例如,敘事作為一種認知和解讀社會生活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參與國家記憶的建構,推動著歷史闡釋與身份認同的研究。在此方面,檔案的介入可為敘事學研究提供更為真實完整的資源支撐和新的研究方向。
檔案學視域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出現的“敘事轉向”思潮推動著檔案學研究與敘事問題的結合。一方面,后現代主義的“敘事轉向”思潮促使檔案學研究重新思考檔案中的敘事[8],研究敘事的社會情境和其后的權力話語問題,推動檔案學“拓展社會情境的寬度和解釋的意義”[9];另一方面,檔案資源體系的公共轉向將檔案的外延擴展到了廣泛的社會群體的活動記錄[10],使社會各類群體皆可成為國家實踐見證、建構與敘述的主體,推動多元主體參與國家敘事的探索與研究。
1.2 實踐邏輯
實踐層面,檔案與國家敘事的實踐需求相契合。一方面,檔案形成于國家的社會實踐中,其原始記錄性、真實性、社會性等特性使其能較為清晰地展現國家的歷史文化和發展風貌,為國家記憶建構提供資源基礎,有力反擊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同時,檔案展現的文化內涵和發展變革,充分表明了中國式現代化是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上、彰顯黨的執政理念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現代化。檔案是中國式現代化得以在中國大地“行穩致遠”的有力實證,亦可為全人類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中國方案。
另一方面,檔案具有跨領域、跨媒介、多模態的特性,并貫穿于中國式現代化歷史進程的始終。其既可同社會治理、文化傳承等場域相融合,在記憶建構、思想教育等實踐層面發揮重要作用;又可依托信息技術轉化為數字態的公共資源,全方位參與到國家敘事的各個情景之中,提供多維的資源支撐和路徑參考。
2 檔案參與國家敘事的維度結構
敘事是講述故事的過程與結果的綜合,既涉及故事內容本身,又囊括了講故事的方式和將故事傳播出去的過程。鑒于此,本文將檔案參與國家敘事的維度劃分為敘事內容、敘事方式和敘事情境三方面,從檔案可參與講述哪些國家故事、以何種方式講述、在何種情形下實現講述和傳播的角度,系統探析檔案在國家敘事中的參與內容。
2.1 敘事內容
國家敘事以“中國故事”為底本。中國故事植根于中華文明土壤,反映了中華文明的復興、轉型和創新,彰顯了傳統中國、現代中國和全球中國的發展歷程。[11]檔案參與國家敘事的內容,可依此劃分為反映傳統文化和革命征程的歷史文化敘事、反映國家發展面貌的現代發展敘事,以及反映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活動、傳遞中國智慧的全球治理敘事。
(1)歷史文化敘事
對檔案中歷史文化的發掘與講述,可促成中華文化語境的跨時空聯結,進而喚醒文化基因,基于共有的認知價值與實踐經驗構建民族、文化認同。宏觀層面,記錄國家歷史文化的檔案反映了國家文化特色,推動了國家文化形象輸出和認同。如以中國傳統音樂錄音檔案、清代內閣秘本檔等為代表的檔案文獻入選世界記憶名錄,為世界文化記憶建構增添了中國底色。[12]微觀層面,反映國家歷史文化的檔案是由具備不同文化信仰的各族人民在實踐活動中共同形成的,數量龐大、類型豐富、特色鮮明,構成了民族認同和身份認同的資源基礎。如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形成的革命烈士檔案、紅色家書檔案可對內建構國民記憶、形塑民族凝聚與道路認同,對外講述中國革命故事、展現革命文化和民族精神。
(2)現代發展敘事
生成于變化、革新時代語境下的檔案,是中國發展成就的表征,賦予了中國式現代化廣闊的闡釋空間和象征意義,可推動國家發展理念的傳播與認同。如經濟建設領域,科技檔案、城建檔案等反映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社會的巨大變遷;民主政治領域,機關檔案、司法檔案等是國家治理能力不斷完善的寫照;民生建設領域,扶貧檔案見證了脫貧攻堅這一豐碑式的民生治理成就,疫情防控檔案記載了我國在突發公共事件應對上的制度優勢和治理智慧。這些檔案可向世界直觀展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強大生命力,在促進國民的國家認同與道路自信、傳播中國的價值理念與治理智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3)全球治理敘事
中國積極參加全球性治理活動,形成了諸多檔案。這些檔案折射出中國在當今國際格局中的話語實踐,是構建國家話語體系的重要底本。不同主體所形成的檔案,敘述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不同維度。如我國與俄羅斯、塔吉克斯坦等國簽署的“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等檔案的展出[13],是我國開展多邊合作的寫照;記錄援非組織、維和部隊等機構實踐活動的檔案,彰顯了中國在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上的實際行動。此外,圍繞檔案開展的國際性交流活動中的中國身影,亦是我國依托檔案參與全球治理的體現。如歷屆國際檔案大會中,中國通過參與討論、主題報告等形式同國際社會共同探討檔案議題,在全球性的檔案問題交流中講述中國方案。
2.2 敘事方式
依托不同的敘事方式,中國故事得以在不同的場域、情景中呈現和傳播。基于檔案真實性、跨領域和多模態的特點,檔案參與國家敘事的方式可分為故事化敘事、情景化敘事和數字化敘事。
(1)歷史重現:故事化敘事
故事化敘事涉及對檔案文本的分析和對關聯敘事材料的邏輯聯結,體現了情感交互的敘事規則。將相對分散的檔案內容以故事化形式組織和演繹,實現檔案由呈現國家資源到講述國家故事的意義傳遞,深入展現檔案中的文化內涵和國家精神。在具體實踐中,故事化敘事借助多種形式,深度挖掘檔案內容,重現歷史細節。紀錄片是故事化敘事的典型代表。例如,由江蘇省檔案館組織拍攝的《光耀史冊——中國共產黨在江蘇》百集紅色珍檔微紀錄片,基于記錄具體節點事件的檔案展開敘事,再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江蘇大地的革命歷程。[14]此外,檔案微電影、專題展覽等形式亦可將檔案中的史實、情感與人文色彩以故事化的形式鋪陳,潛移默化地傳達民族的價值理念和文化底蘊。
(2)場域融合:情景化敘事
敘事的開展源于人們在各種情景中的“記憶”需求[15],國家敘事亦是對不同實踐情景中的事件予以解釋和建構。檔案誕生于國家社會實踐中,與各實踐場域融會貫通,為情景化敘事提供資源支撐。面向不同實踐場域的敘事需求,檔案以文字、數據、影像等多元形態與敘事情景巧妙聯結,在提升情景表達效果的同時,可進一步拓展國家故事的闡釋寬度,促進國家精神的深入傳達。例如,在課堂思政教育上,將檔案資料與生動的講述技巧相結合營造敘事情景,通過直觀的數據與史實達到震撼人心的效果。
(3)交互共建:數字化敘事
檔案跨領域、多模態的特性使其可同數字技術充分結合,推動國家故事的開放、多元、交互式講述與建構。一方面,檔案能轉化為多元形態的敘事資源,開展跨媒介敘事,豐富國家故事的表現維度。或與新興技術結合,打造交互式的敘事空間,使公眾在沉浸體驗、互動活動中實現對檔案背后國家精神的理解。另一方面,數字檔案資源的整合與開發為公眾參與國家敘事實踐提供資源支撐。依托檔案館的數字檔案資源,公眾得以參與到國家的資源存儲、記憶建構和文化闡釋等實踐中,推動國家故事在多元闡釋與建構中生成新的意義。[16]例如,近年來興起的少數群體數字建檔實踐、面向公眾開展的數字檔案征集、著錄、數字化編研等工作,便是引導公眾參與國家敘事實踐的有益探索。
2.3 敘事情境
國家敘事需在一定的敘事情境下開展。敘事情境主要涉及敘事者以何種身份、視角展開敘事,以及參與故事的程度等要素。[17]基于敘事主體的差異,本文將檔案參與國家敘事的情境分為官方和民間兩種敘事情境。
(1)官方敘事情境
檔案的形成和敘事的開展皆與權力因素關聯。官方敘事情境下,檔案材料的選擇、敘事和傳播方式的選取,關系到國家歷史的建構和話語的形塑。[18]國家故事和集體記憶的生成,一定程度上亦是官方意志主導的選擇性建構過程。官方敘事情境中的敘事主體主要為具備一定符號、社會資本的公共組織機構;敘事內容往往發掘于具備公共性質、反映宏大主題的檔案;敘事方式傾向于通過官方渠道進行宏大的宣傳式表達。例如,基于檔案資源的黨史宣傳教育實踐、國際檔案日宣傳活動、重大公共事件所形成的檔案征集與開發活動,皆是官方敘事情境下檔案參與國家敘事的典型探索。
(2)民間敘事情境
民間敘事情境下,檔案的敘事方向從宏大的國家意志轉向微觀視野,側重反映民間各類群體乃至個人的價值觀念和生活風貌,完善了國家敘事的闡釋內容。一方面,在敘事意義不斷延展的背景下,民間主體所形成的、有敘事價值的檔案,成為其自我建構和群體闡釋的工具,不斷豐沛著國家故事的構成;另一方面,國家故事在多元闡釋主體和表達方式影響下持續生成不同意義,豐富了國家歷史記憶的建構層次。此種情境下的敘事主體主要指非官方性質的民間組織機構和公眾;敘事素材擴充到公眾群體在社會實踐活動中形成的具有保存價值的檔案;敘事方式呈現多元、動態、去中心化的特性。如少數民族、特殊群體所形成的具有獨特文化價值或象征意涵的檔案,便可視為故事來源,為國家故事增添民間聲音。
3 檔案參與國家敘事的推進策略
當前,國家敘事的實踐進程穩步推進,但同時也面臨著一些困境。一方面,在對內傳播中,如何整合龐雜的敘事資源,使其深入反映國家民族風貌,尚值得深入探究;在對外傳播中,不同的文化語境使國家敘事面臨著文化異質性的挑戰。另一方面,在官方敘事情境主導下,國家敘事在表達和傳播中體現出政治性、嚴肅性,并以較為宏大的敘事策略為主,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敘事受眾的范圍擴大和情感共鳴。針對以上實踐困境,本文圍繞敘事內容、敘事方式和敘事情境三個參與維度,深入探討檔案參與國家敘事的推進策略。
3.1 敘事內容:多維復合與議題貫通
面對國家故事龐雜多樣的現狀,從檔案中選取適宜的敘事題材,使其映襯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是發掘檔案敘事價值的題中之義。為此,可通過多維復合,架構起基于檔案的敘事邏輯。其一,資源復合。應進一步擴大檔案征集范圍,使館藏內容盡可能覆蓋國家社會發展的多個層面。在此基礎上,主動參與國家大型記憶工程、文化遺產申報等記憶建構活動,積極融入國家敘事進程。其二,故事復合。檔案中不同的敘事內容在本質上存在共通之處,即均與中國式現代化的理念內核相契合。可優先發掘有多層故事線索的檔案資源,并聯過去與現在、歷史與時代的深層故事邏輯,實現文化情感跨時空交互。其三,呈現邏輯復合。可基于檔案特性引入知識組織體系,以關聯化的邏輯整合檔案故事內容,將小的故事細節層層復合,有序引申至宏大的歷史事件,由點到面建立起系統的國家故事體系。
在復合資源之余,于檔案中挖掘共通敘事議題,是消解國家敘事對外傳播困境的有效途徑。應將反映中國發展理念的檔案內容同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話題相關聯,探尋國際共性問題中的中國智慧,使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之道為更多海外受眾所理解。例如,如何對扶貧檔案進行管理、治理等問題已得到關注,然而對扶貧檔案向外傳播的研究仍顯不足。對此,可將扶貧檔案對接國際“減貧”議題[19],發掘其在減少貧困現象中留存的國家經驗與集體記憶,將傳播話題聚焦于“減貧”上,淡化“脫貧攻堅”對外傳播的政治色彩。此外,本身便具備議題貫通性的檔案資源亦值得關注。如我國在沙特和伊朗建交活動中形成的外交檔案,既反映了中國積極探索民族、宗教矛盾等國際問題的和平化解路徑,亦體現了以和為貴、包容共濟的中華文化,是中國式現代化之“道”的生動體現,可成為講述外交故事的典型材料。
3.2 敘事方式:場景建構與共情表達
首先,建構“物理場景”,將檔案元素融入檔案館、紀念館等實體建筑中,并通過空間布局架構、視角轉換等技巧促成檔案與敘事空間的巧妙融合。如北京市檔案館與首都博物館合作推出的“胡同四合院歷史文化展”,展線的延伸伴隨著移步換景、光影色彩、形態語言等空間敘事的變化,強化了沉浸體驗。[20]
其次,搭建“精神之場”與“記憶空間”,使群體與個人的檔案記憶融入國家記憶場域中,打造身份認同與國家認同。精神場景的建構即通過探索檔案“隱喻”的敘事方法和符號化、儀式化的塑造,于受敘者腦海中架構起對應的情形或認知。一方面,以受眾體驗為導向,在物質載體與實踐活動中融入敘事巧思,隱喻故事文化,如中國絲綢檔案館推出的“第七檔案室”項目使絲綢文化于解謎實踐中無形傳播。[21]還可立足公眾交互視角,通過搭建檔案數字敘事平臺、開放檔案文創公眾設計渠道等方式,為公眾打造體悟檔案故事文化的空間。另一方面,探索建構國家敘事場景中的“檔案儀式”,強化檔案的隱喻表達與符號意義。如譜牒的興修編纂,便是維系族群身份認同的重要儀式。檔案作為國家故事的物質承載,本身便具備一定的象征意義,可通過儀式化的表達將檔案資源融入國家敘事體系,引導公眾自覺消化檔案所傳達的精神內涵。
最后,探索共情的表達方式,提升國家敘事共鳴度。一方面,國家故事由公眾共同構筑,共有的價值、身份和經驗皆可成為情感共鳴的依據。因此,檔案的敘事表達應與公眾的情感認同一致,為其創造從故事中自我觀照與投射的契機,促進其對國家精神的理解。另一方面,共情的表達應注重敘事修辭的運用,可基于檔案多模態的特性,靈活應用圖像、文本敘事與融媒體手段呈現檔案資源,調動受敘者的視聽感官,強化其情感體驗。例如,黃文秀《扶貧日記》本屬于脫貧攻堅這一宏大國家實踐的產物,但文本配音、H5作品制作和音樂渲染等方式營造了如臨其境的情感氛圍,利于促進公眾對扶貧精神的深入共情。[22]
3.3 敘事情境:平民視角與多元共構
立足平民視角,將敘事權力下放于更為廣泛的社會公眾,使中國故事由宏大“獨白”轉化為多元聲音“同頻共振”,促進國家精神為更多人理解。官方敘事情境下,平民視角的轉向可著眼于對反映公眾生活的檔案內容的發掘。在資源建設上,可將不同群體所形成的有敘事價值、代表性強的檔案納入國家公共檔案資源體系中。如梅州市華僑檔案館便將反映華僑歷史演進、留存僑眷記憶的社群檔案納入區域記憶建構規劃,推動華僑群體的記憶留存。[23]在內容表達上,可建立起社交媒體檔案數據采集平臺,收集并分析公眾形成的信息動態,掌握其關注的社會議題。在此基礎上,聚焦公眾的生活與情感變遷,以細水長流的生活化講述替代“神話”式的精神宣講。
民間敘事情境下,平民視角的轉向可著眼于官方敘事主體主動引導民間聲音參與國家敘事。民間敘事一定程度上可與官方敘事共同構筑歷史情節、講述國家故事真相。資源層面,記錄公眾生活實踐的原始記錄,從紙質檔案到數字態記錄,皆可予以關注和發掘;主體層面,各類社會組織、民間機構及公眾于國內外實踐場域中形成的、同本國相關聯的檔案,皆是民間故事素材。
此外,實踐活動同中國發展相關聯的外國機構、組織和公眾等“他者”亦是國家敘事不可缺失的力量。官方與民間情境下的敘事活動,歸根到底屬于國家故事的“自我講述”。他者力量的介入,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西方話語霸權與思想藩籬,消減文化異質性沖突。資源建設上,由域外主體持有的同中國有關的檔案資源,可與國內檔案一同補充印證、實現記憶互通。如存留于朝鮮境內的抗美援朝戰爭遺跡遺址,便可同國內的志愿軍檔案共同闡述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偉大精神。此外,由外國機構與公民在中國境內形成的反映中國社會發展變遷的圖像、視頻與文字記錄等,同樣可作為檔案素材。對此類獨特視角檔案的挖掘與發現,有利于拓寬國家故事的敘述視野。
在多元主體參與的情景下,將官方情境與民間情境、國內場域與海外場域相結合,可形成以檔案為依托的國家敘事共同體,打造文化、記憶和知識共建共享的公共敘事空間。值得強調的是,官方敘事情境始終是國家敘事的主導情境。應建立起以官方敘事為主導、民間多元主體參與的國家敘事格局,立足于國家利益和公共導向,堅持宏大主題與微觀視野、自我建構與他者講述的有機結合,避免微觀、片面的敘事對國家精神的消解。
4 結 語
檔案可參與到國家敘事中,在不同敘事情境下實現多樣化的敘事表達,傳達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圖景和理念內涵。在今后的研究中,如何深入發掘檔案在國家敘事實踐中的價值,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值得進一步展開探討。
注釋與參考文獻
[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EB/OL].[2023-08-01].http:// 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2]高勝楠,吳建華.檔案與國家認同:理論基礎、作用維度與現實路徑[J].檔案學研究,2021(6):35-40.
[3]鄭婷,陸陽.基于強化國家認同的檔案信息資源開發探析[J].北京檔案,2019(3):14-17.
[4]王玉玨,吳一諾,許佳欣.《“十四五”全國檔案事業發展規劃》解讀:檔案服務國際傳播能力建設[J].山西檔案,2021(4):78-87.
[5]周林興,姜璐.紅色檔案資源開發中的敘事表達研究[J].檔案學研究,2022(4):4-9.
[6]龍家慶.敘事表達在檔案宣傳中的運用與優化策略[J].浙江檔案,2020(1):30-32.
[7]胡全生.敘事學發展的軌跡及其帶來的思考[J].復旦外國語言文學論叢,2008(1):20-32.
[8]KETELAAR E.Tacit Narratives:The Meanings of Archives[J].Archives & Museum Informatics,2001,1(2):131-141.
[9][18]張斌,王露露.檔案參與歷史記憶構建的空間敘事研究[J].檔案與建設,2019(8):11-15,40.
[10]李孟秋.批判與建構:后現代語境下的檔案敘事[J].檔案學通訊,2022(5):10-18.
[11]王義桅.中國故事的傳播之道[J].對外傳播,2015(3):51-53.
[12]中國國家委員會世界記憶項目.世界記憶名錄(國際名錄)[EB/OL].[2023-08-01].https://www.saac.gov.cn/mowcn/ cn/c100393/gjjyml.shtml.
[13]廖倩文.檔案在文化軟權力建構中的角色分析與實現[J].檔案天地,2018(12):32-35.
[14]范小燕.江蘇省檔案館推出《光耀史冊——中國共產黨在江蘇》百集微紀錄片[J].檔案與建設,2021(8):2.
[15]龍迪勇.敘事學研究的空間轉向[J].江西社會科學,2006(10):61-72.
[16]付雅明,張永娟,劉煒,等.數字敘事作為數字人文方法:現狀與可能[J].圖書情報工作,2022(14):10-19.
[17]趙炎秋.敘事情境中的人稱、視角、表述及三者關系[J].文學評論,2002(6):126-130.
[19]欒軼玫.新時代中國國家敘事脫貧攻堅的對外傳播[J].編輯之友,2020(9):5-14.
[20]宋鑫娜.展覽中的空間敘事和語言敘事[J].中國檔案,2017(5):24-25.
[21]陳鑫,楊韞,謝靜,等.檔案文化“破圈”傳播實踐路徑——以中國絲綢檔案館“第七檔案室”項目為例[J].檔案與建設,2022(2):51-54.
[22]龍思婷.融媒背景下一個“時代楷模”的傳播——黃文秀事跡新聞生產的共情表達[D].南寧:廣西大學,2022.
[23]陳明,劉迎紅.從拒斥、選擇融入到融合:社群檔案建構城鄉記憶的路徑博弈[J].檔案與建設,2019(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