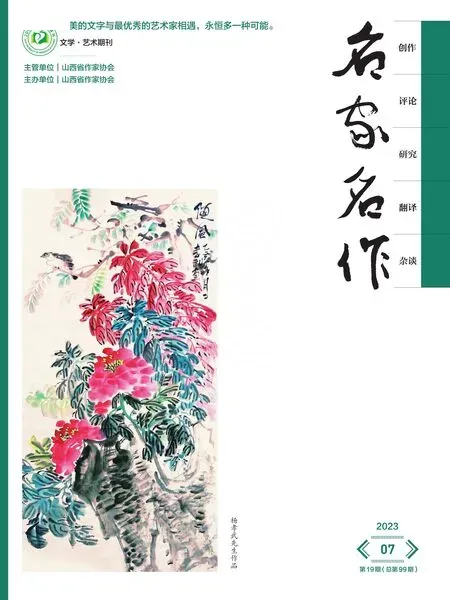論魯迅與余華小說中看客的“異化”
王 雪
近現代以來,看客作為一個人物形象而出現在魯迅的《〈吶喊〉·自序》中:“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1]417看客不僅作為人物形象而存在,更是作為一種有著頑強生命力的社會文化而存在。在現當代文學中,看客形象自魯迅開創之后就一直生生不息,其中現當代作家筆下的看客形象都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延續與繼承了魯迅筆下看客形象的內蘊。其中最能表現魯迅風格的當屬當代作家余華,因為兩位作家筆下的看客都是在特殊時代下產生和發展的,他們小說中的看客形象都呈現出人格缺失的“異化”。
一、外在行為的“異化”
看客賴以生存的方式只有一個,那就是“看”。無論是魯迅筆下無知地“看”,像魯迅說,“假使有一個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著,不久準可以圍滿一堆人;假使有一個人,無端大叫一聲,拔步便跑,同時準可以大家都逃散”[2];還是余華小說中有意識有目的地“看”,其“看”的行為和所看之事都不約而同地打上了其所在時代的烙印,呈現出異樣的生存狀態。
(一)魯迅筆下的看客:麻木愚昧的灰色群體
通覽魯迅的作品,不難發現他筆下的看客幾乎貫穿他全部文體的創作之中,除了專門描述看客的《示眾》《復仇》外,魯迅對看客的描寫都是寥寥數筆,或以主要事件的環境、或以中心人物的背景而存在。因此魯迅筆下的看客形象是群眾性的邊緣化的符號形象。最典型的就是《示眾》這篇小說,一群各行各業不同年齡的人你推我擠地爭著搶著看馬路邊被“示眾”的“白背心”,作者有意識地放大這群無名、無姓、無思想、無主見的看客“看犯人”的行為,將看客那種湊熱鬧找樂子打發無聊的精神面貌展現得淋漓盡致。還有《阿Q 正傳》中阿Q 殺頭的名場面,殺頭這種血腥恐怖的大事,在看客的眼里就像演了一出大戲,“兩旁都是許多張著嘴的看客”[1]525,臨近高潮之時,還興奮地“發出豺狼嗥叫一般的聲音來”[1]526,邊看邊點評——認為“槍斃無殺頭這般好看”[1]527。作者魯迅以白描的手法戲謔地描摹出看客那冷漠的死一般的無可救藥的麻木。
魯迅筆下的看客是一種不可忽視的有著無形力量的群體,他們常常能夠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并助力中心人物悲劇命運的走向,成為封建統治勢力的“幫兇”。例如《狂人日記》中想方設法要吃掉“狂人”的看客們,正是“‘狂人’的清醒成了對他存在的詛咒,注定他要處于一種被疏遠的狀態”[3],注定被秉持著所謂正統理念的看客所拒絕,他們無時無刻無所不在地監視著狂人,并構建起強大的輿論力量,逐漸將“狂人”抹殺。還有《祝福》里的祥林嫂,導致這個充滿悲劇性的中國傳統婦女最終死亡的原因除了封建專制“三權”的奴役外,還有魯鎮的鎮民和“我”這一群看客的推波助瀾。所以魯迅筆下的看客就是“幾乎無事的悲劇”[4]的制造者。
(二)余華小說中的看客:兇殘惡毒的黑色個體
余華繼承魯迅的國民批判性,在小說中也塑造了一批麻木的看客。《一九八六年》里的看客要捆綁一次次用古代刑法自殘的瘋子,只是為了不再去聽瘋子那毛骨悚然的嚎叫聲,與魯迅的小說《長明燈》里的村民為了制止瘋子熄滅長明燈而想辦法將瘋子送上絕路,這兩篇小說中對看客行為的描寫較為相似。還有《現實一種》中的山崗在臨刑前看到的場面,不禁聯想到魯迅《示眾》中那些爭先恐后看犯人的看客們。《兄弟》中一些關于看客冷血漠視的細節,例如當李光頭因偷看美女屁股而被抓住游行時;當孫偉母親變瘋而裸奔時;當宋凡平為迎接自己的妻子在車站被活活打死時,這些時刻發生的驚人事件,看客每每都在第一現場“看戲”,或哈哈大笑,或全程靜默。在他們眼里,無所謂悲喜,不過都是一場滑稽的戲劇罷了。恰如魯迅激憤的表達,“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1]163。
余華在繼承魯迅的同時又超越了魯迅。余華小說中的個體看客,是有著鮮明的個性、偏執的思想、自我意識和個人目的的。除了魯迅筆下愛“看戲”的特點,看客還給自己“加戲”,即創造機會使自己參與到“戲”中,使自己觀看他人的同時也被其他觀眾賞鑒。《朋友》中作者設置了一個獨特的看客視角——一個十一歲的男孩,從這個孩子的視角出發,旁觀那充滿暴力、欲望與交易的成人世界,從而更深刻地反襯出看客行為的“異化”。《難逃劫數》中的看客在看了彩蝶變美失敗的表演之后,還密切關注著彩蝶接下來的舉動,甚至在幸災樂禍的等待中還發揮藝術想象,創造出彩蝶尋死覓活的“好戲”。在余華的小說創作中,看客的“看”更是表現出一種戲劇性的荒誕和滑稽,特別是一種類似于丑角人物的出現。“以《 在細雨中呼喊 》為分界點,‘看客’所指的重點發生了悄然變化——不再是國民劣根性的表現——余華將它演化為一種狂歡節氣氛中‘觀眾’與‘小丑’(巴赫金語)之間看與被看的模式”[5]。之后“三部曲”中的《兄弟》,在宋凡平與李蘭的婚宴上,賓客們竟“東找西找拿出來了兩只白瓷杯蓋,讓李光頭和宋鋼叼住杯蓋上像奶頭一樣的圓鈕”,“在他們看來就像叼著李蘭的兩個奶頭”[6]49,看客這種自己組織戲本,還要求中心人物表演,以此滿足他們內心壓抑的性欲望。“三部曲”中的《許三觀賣血記》,林芬芳的丈夫大肆向許三觀的鄰居們宣揚許三觀在強奸自己的妻子之后給妻子買補品,作者有目的地給林芬芳的丈夫充分的表演空間,使這個個體看客在自己看的同時還呼喚其他觀眾一起欣賞點評,以彰顯這個本是邊緣化個體的存在感,傳達了生存環境造成的人的異化。
余華小說中的看客的旁觀行為還充斥著兇殘嗜血暴力般的狠毒。《十八歲出門遠行》中的“我”出門遠行,熱心幫助汽車司機的蘋果被偷事件,反觀汽車司機回饋給“我”的是冷漠的旁觀和忘恩負義地偷竊,將剛涉世懷著美好理想的“我”瞬間打入黑暗的谷底。還有《兄弟》中窺視他人隱私或個人私密的看客,就是哲學家薩特所說的“他人就是地獄”[7]的表現。像劉鎮上的男性都意圖偷看鎮花林紅的屁股,以昂貴鮮美的“三鮮面”來比喻林紅的屁股,以此達到邪惡的意淫。在偷看異性肉體的基礎上,還參與觀看他人的思想意志。小說立足于時代背景,展現了人物的一切——從身到心,從家庭到周邊,所有相關的人和事都被拿到太陽下揭露。由于宋凡平出身地主,總被要求交代自己的罪行。從私自抄家到歪曲話語再到強加思想,這一系列看客參與和制造的行為都以強大的力量虐殺著中心人物的肉體和靈魂。毫不夸張地說,宋凡平最后的慘死與看客的兇殘惡毒脫不了干系,甚至是直接兇手。
二、內在心理的“異化”
無論是魯迅筆下灰色符號般的看客,還是余華小說中黑色利器般的看客,其看的行為都自覺或不自覺地“異化”。根據心理學原理,沒有無緣無故的作為,背后必定有相應的心靈驅使。魯迅和余華小說中看客的外在行為的“異化”表明其內在心理也一定是病態的。
(一)魯迅筆下的看客:可悲的空虛
魯迅筆下的看客在喜歡看戲起哄的非正常的行為之下,表現出看客內在心理的極度不正常。《藥》里茶客看夏瑜被殺時的狀態——“頸項都伸得很長,仿佛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著”[1]440;《祝福》中的祥林嫂變成了魯鎮看客們閑來聊天打趣嘲諷的“玩物”,“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經大家咀嚼鑒賞了許多天,早已成為渣滓,只值得煩厭和唾棄”[8]18;《風波》里七斤的剪辮子風波,村民們迎合著趙七爺的恐嚇威脅,等待著七斤犯法被殺頭等一系列看的行為、看的狀態,除了表現出看客無情冷漠的心靈和麻木不仁的精神,其真正驅使的是他們那煩悶空虛的只剩一副軀殼的內部靈魂。在經歷了長期的儒家思想的教化之后,在日復一日的機械的日常生活中,他們早已對生活沒了熱情。所以當有人因奇怪的言論被殺頭,有人生活困苦磨難重重,有人要犯事時,但凡是有點新奇的聞所未聞的人和事,都能激起看客強烈的興趣,以此在這無比寂靜的一洼死水中激起一點求之不得的漣漪。魯迅正是憤怒于看客這可悲的空虛,對其復仇,在散文詩《復仇》中“路人們從四面奔來,密密層層地”[8]172來看一男一女或殺戮或相愛,為報復看客的好奇心理,始終沒有下一步的動作,使他們無聊空虛至死。
(二)余華小說中的看客:可恨的反叛
余華小說中的看客如此邪惡的行為表征彰顯出了其內心的扭曲和極端,是一種變相的掙扎,是一種壓抑的發泄,是一種絕望的呼喊。《黃昏里的男孩》中的小販撞上男孩偷蘋果,借此機會殘忍地痛打處罰,通過對別人施虐來發泄自己生活的不如意。《兄弟》中對欲望放縱的放大描寫,例如劉鎮上從一個少年李光頭偷窺女性上廁所發展到全鎮的男性都去間接偷窺,其看客群體分布廣泛:李光頭、劉作家、趙詩人、民警、其他劉鎮男人,這種荒唐可笑的行為,各個階層的參與和偷看,都深刻地諷刺了那個時代的人們因性壓抑而以這種另類的方式來獲得短暫的性滿足。還有全鎮的人對于性的敏銳關注和聯想,當大汗淋漓的宋凡平在籃球場上抱著心愛的李蘭時,看客們發出各種各樣的笑聲,“大笑、微笑、尖笑、細笑、淫笑、奸笑、傻笑、干笑、濕笑和皮笑肉不笑”[6]43。對于性的幻想性的滿足,在《細雨中呼喊》也有涉及。在曹麗和音樂老師之間的戀情信件被要求上交之后,學校里的老師們爭相傳看,還大肆討論,一時間這一盛事成為大家百無聊賴閑暇時的談資。余華小說中的看客對于身邊一切有關男女之間的事總是有著高度的熱情和好奇,無論男女老少,無論哪行哪業,都急迫地想旁觀想談論,作者以這種戲謔、荒誕的筆法傳達出所處時期的看客既可恨又可悲的掙扎、叛逆、變態的心理動態。
三、看客“異化”的時代原因
魯迅筆下的看客和余華小說中看客形象的行為與心理的“異化”,表明了看客的精神與思想的非理性釋放,尤其是“在極端狀態下人的獸性展露無遺”,而造成這種“異化”的原因歸根結底在于作家記憶深處的那個極端時代。
(一)魯迅所處時代的“失語”
魯迅作品中展現的是百年未有之的皇權崩塌、軍閥割據、民不聊生的大變革之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混亂時代。歷經辛亥革命和兩次復辟等接二連三的變局,在這個時期的中國,國民物質貧困、精神困苦,甚至可以說人的生命連牲畜都不如。就是這樣國將不國的年代,整個民族乃至全體國民就是魯迅所指的鐵屋子里尚在呼吸的死人。人民群眾在幾千年傳統封建的統治下被摧殘、壓榨、奴役,成為沒有個體靈魂、沒有自我生命的“空心人”。這個時代下的國民“活著便只是一種形式,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逆來順受、任由社會以及生活將靈魂從身體中抽離出去,只剩下一個空殼”[10]。所以他們無比的空虛寂寞,滋生了看客文化。同樣因為他們的空虛,而盲目從眾地旁觀,導致抹殺個體的判斷和話語表達。魯迅筆下的看客完全喪失了自由表達的欲望和權利,因此他們的生存方式由此僅有一個——渾渾噩噩地看。
(二)余華所處時代的“狂語”
余華的小說營造了一個迷狂的、瘋魔的、邪惡的世界,有死亡、鮮血、斗爭、傷殘、欺騙、背叛、暴力、欲望、金錢等,似“鮮血如陽光般四射”[11]。余華極盡筆墨揮灑出特殊年代下的死亡和苦難,竭力全面揭示現實中人性的丑惡。可以說,在余華的小說中,看客文化發展到了極致。人民群眾每時每刻每處每地都處于完全裸露的看與被看之中,所有人都患上了一種癔病。
四、結語
結合跨時代的兩個作家的作品中的看客形象,從行為表征到心理狀態進行了細致的分析,追溯到看客精神壓抑思想“異化”的深層原因——時代環境的造就。無論是余華小說中黑白顛倒的沒有情感、沒有人性的革命時期,還是魯迅筆下的家國危在旦夕新舊斷裂的混亂年代,都揭示了巨變時代之下的人民群眾精神壓抑與道德失常的“異化”之態。看客的“異化”是自我人格的缺失,是社會使命的失責。勒維納斯說過,“從我到我自己終極的內在,在于時時刻刻都為所有的他人負責,我是所有他人的人”[12]。所以對自我與他人負責,是完成人格健全的兩個主要因素,看客的人格缺失直接反映出時代信仰與時代精神的批判和理性的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