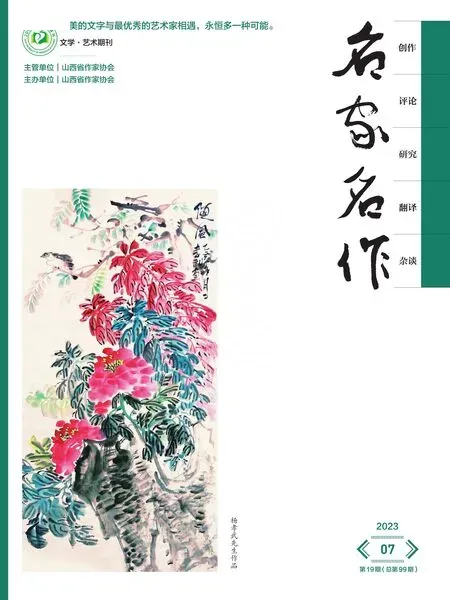淺析特殊即普遍的哲學思想
——圍繞西晉一郎道德哲學的基本原理
李立業
西晉一郎的哲學思想在1931 年的著作《忠孝論》中達到了學術的頂點,形成了一種獨具特色的哲學體系。隈元認為自西晉一郎就任廣島高等師范學校教授以來的30 年是其哲學體系的形成期,此后的十數年則是其道德哲學的實踐期①隈元忠敬:《西晉一郎哲學》,溪水社,1995,第67 頁。。本文聚焦其最早發表的《倫理哲學講話》,通過考察西晉一郎思想形成初期確立的學術方法和基本原理,試圖揭示西晉一郎道德哲學的構造及其思想本質的一個側面。
一、哲學乃修身之道
西晉一郎在《倫理哲學講話》開篇便將哲學視作修身之道,他認為:學問是促進人自我改進、提高修養最有力的因素,而在各種學問中,專注于探究真理的哲學最符合這一目的。真正的哲學不應僅探索普遍性真理,更應借助普遍性真理去發現個體的獨特天性。②西晉一郎:《倫理哲學講話》,育英書院,1915,第2-8 頁。(以下注解中都省略為《講話》)其認為普遍性真理不能脫離個體特殊性存在,只有充分認識并發揮自身的獨特性,普遍性真理才能真正實現。
西晉一郎指出雖然事物在根源上是獨立自全的,但事物獨立存在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產生相互關系,從而“自然地、必然地”產生為某一目的而存在的屬性,學問亦是如此,所以應該以關聯的視角看待學問。基于上述理解,西晉一郎將事物獨立自足的一面稱為“仁”,將為某一目的存在的一面稱為“義”。仁是事物內在具備的特質,義則需要進行相對性的考察。相對性考察的方式即做學問的目的、動機,將極大地影響做學問的結果。目的和動機是左右整個修學過程的根本動力,為了獲得正向的原動力,西晉一郎主張應該尊重賢哲的教誨③《講話》,第9-12 頁。。
以上是西晉一郎對于哲學或學問的基本觀點,從中可以明晰其學術立場和哲學思想的根本出發點。此外,西晉一郎基于事物皆獨立自足又相互依存的觀點,主張“在探究實在時,應該從絕對與相對、仁與義的辯證關系出發,不能簡單地將二者看作是各自獨立的二元對立關系”④《講話》,第13 頁。。他的實體論正是基于此展開的,對立統一的思維方式貫穿其哲學思想的始終,是其哲學體系的根本出發點。
二、實在的真相
西晉一郎認為在探討實在時應從普遍與特殊、不變與變化的相對性出發。雖然實在本身沒有這些相對性,但由于我們以有限的意識無法客觀全面地認識實在的真相,常常會偏執于某一方面。這也是西方哲學史上各種實體論相互對立、爭論不休的原因⑤《講話》,第15-16 頁。。西晉一郎以伯格森的流動哲學為例,指出其過于偏重變化。因為在邏輯上,變化是與不變對立的,如果沒有不變,變化也就無法成立。在實際經驗中,我們體驗到變化時必然已經承認其背后的不變,否則就無法區分出變化⑥《講話》,第17 頁。。
西晉一郎認為相即不離的理念同樣適用于普遍和特殊的關系。普遍離不開特殊,同樣特殊背后也必然蘊藏著普遍。西晉一郎通過“普遍中有特殊、特殊中有普遍”“因為普遍所以特殊,因為特殊所以普遍”等觀點描述特殊與普遍相即不離的關系①《講話》,第24 頁。。
實際上這一理念適用于一切具體事物。比如以菊花為例,西晉一郎指出眾多菊花中的每一朵都有自己的獨特性,而每朵菊花背后又蘊含著菊花之所以為菊花的普遍性。在主觀層面,這種普遍性讓我們具備了直接感受每朵菊花獨特性的審美基礎;在客觀層面,它意味著一株菊花擁有繁衍出千萬朵菊花的普遍力量②《講話》,第26-28 頁。。我們的精神世界亦是如此,在千變萬化的精神世界中我們能夠體會到其背后存在著始終不變的某種普遍性,得益于此我們作為獨立個體的人格才能成立。當特殊的精神世界生活越是發自內心深處的普遍性,我們的人格就具有獨立特質。西晉一郎認為普遍與特殊密切關聯所形成的具體且唯一的境界即為實在,在其看來普遍和特殊是實在的兩個方面,二者相即不離、對立統一,實在的真相即是“特殊即普遍”。
三、實在與道德
西晉一郎的哲學立場是基于歷史現實的道德實踐,其理論探索始終與個人、社會、國家等具體現實的道德實踐密切相關。
西晉一郎將實在視為純動至變,“純動”指流動而無間隙;“至變”指變化而無斷續③《講話》,第42 頁。,這種無間斷的變動意味著不斷更新創造的過程。西晉一郎認為更新不止、流動不停則為純,此等純粹的狀態也是至靜的境界,純粹是實在的存在方式。西晉一郎描述“實在的真面目在于純粹無雜之處,在于其呈現出的無間無隙、充實徹底、無法拆分、渾然天成之處”④《講話》,第42 頁。。如果基于現實道德生活描述實在的這種純粹境地的話,即是“一心一意、心無雜念”⑤《講話》,第42 頁。的心境。道德生活中的這種心境即為“誠”,在西晉一郎看來道德“誠”即是實在。隈元指出西晉一郎的道德哲學將實在與道德視作同一物,其一直通過道德來揭示實在純動至變的本質⑥隈元忠敬:《西晉一郎哲學》,溪水社,1995,第15 頁。,可以說其道德哲學的重點在于闡明實在只有在具體現實的道德生活中才能充分展現其真實面貌。
在個人、國家和社會的不同層面,道德會展現出各種特殊形式,但在特殊形式的背后,存在著人類共通的普遍性。因此不能將道德中的人類共通性與國民個人的特殊性割裂開來。《論語》中有言,“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忠信篤敬是適行于所有國家的普遍性道德,西晉一郎指出普遍性道德是深藏在每個人內心的理,而此理運行能夠衍生出各種道德形態⑦《講話》,第66 頁。。其以日本的楠木正成和中國的岳飛為例詳細闡述了這一理念。他們作為個人只是歷史洪流里一個特殊的小我,然而至今仍被視為道德典范就是因為隱藏在他們特殊生涯背后的普遍性道德 “忠誠”一直在無形中發揮著作用。“忠誠即實在,普遍存在于萬物之中、不受時空限制,其能夠引導農夫成為良善之人,亦能鞭策教育者成為有良心之人。”⑧《講話》,第66 頁。忠誠即是具體的普遍性實在,其遍布在萬物之中并推動事物朝著正善的方向發展,其在楠木正成和岳飛的人生經歷中雖然表現形式各具特殊性,但內在的忠誠卻完全一致。西晉一郎將此稱為道德的同化原理并解釋道:“因為具體普遍性是無法離開個體特殊性而獨立存在的,所以它的現實顯現始終采取特殊與特殊交相感化的形式。”⑨《講話》,第67 頁。普遍與特殊是對立統一的,二者相即不離,因此在提倡社會普遍性道德的同時應充分尊重個體的特殊性,而在彰顯個體特殊性的同時也應注重實現社會的普遍性道德。
四、實現道德生活
實在的本質是普遍一致的,但其作用必然通過特殊的形式顯現,即實在只有在現實的特殊形式中才能顯現出其普遍性。那么我們究竟應該以何種特殊相立身于世、又該如何在保有個體特殊性的同時實現道德生活呢?對此,西晉一郎也基于實在的“仁”和“義”兩方面進行了論述。
西晉一郎認為實在包含純動、至靜兩方面,動靜交替則意味著生長,因此實在即是生命。生命包含了動與靜,離不開新生與完結。實在的本質即為動而萬物生起與靜而完結自足⑩《講話》,第78 頁。實在的本質是純動即純靜的觀點,可以追溯至周敦頤(1017—1073)的動靜學說。其在《太極圖說》中表示:“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并且在《通書》的第十六章“動靜”中寫道:“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可以看出西晉一郎在以動和靜論述實在的本質時明顯吸收了周敦頤的動靜學說。。因此,其將實在動與新生的一面稱為“仁”;將靜與完結的一面稱為“義”。西晉一郎在探討實在的“仁”時又引入了“愛”的概念,主張實在即是生命,而生命便是“仁”或“愛”。其借用了程顥的名句“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來說明實在的“仁”即愛,是延續不斷的生命流通,愛體現了實在的生生不息①《講話》,第82-83 頁。。
基于實在即生命、愛的論述,西晉一郎以施恩和報恩的關系來闡述道德生活的本質。“恩”即恩惠和滋養,代表草木萬物萌生②《講話》,第84 頁。,意味著生生不息的真理。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只將他人為我著想、為我付出的行為視為恩惠,而沒有意識到即使對方并非有意為我,但我也得益于此立足社會,這一切皆是對我有恩。例如,“父母盡責撫養子女,子女盡心敬愛父母”③《講話》,第88 頁。,親子關系中的施恩和報恩是生生不息的實在之理的具體表現。如果從更廣泛的社會生活來看,人們似乎都是為了自己工作,但事實上所有人的工作最終都成了互相成就。畢竟人類彼此依賴才能共存,“每個人努力工作既是依靠他人之助,同時也在回報他人”④《講話》,第94 頁。,對我們而言是他人的施恩之舉,但對其本人而言卻又是直接的報恩行為,因而施恩與報恩發生在每個人各自的人生道路中。我們只有深刻理解并實踐施恩和報恩的意義,才能認識到我們生命本源中存在著的普遍性實在,實現道德生活⑤《講話》,第97 頁。。
隨后,西晉一郎又從實在的“義”的一面探討了如何實現道徳生活。實在的特殊相種類繁多,而基于人們特殊關系形成的特殊性更是廣泛普遍。例如,“在家庭中,男子作為丈夫、父親、子女、兄弟,每個身份都有著不能混淆的特殊性。因此我們常常聽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類的描述,皆是為了明確各自身份的特殊性”⑥《講話》,第125 頁。。生活在集體中的人們應切實踐行自身的責任,維護好自身的形象。如此一來,人們各自角色的特征才會日益明確,進而形成鮮明的人格魅力,與此同時人生的普遍性意義也能得到充分展現。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社會和國家層面,職責是個人立足于世的關鍵,因此更應該盡力保持其特殊性⑦《講話》,第126 頁。。在社會和國家中,人都是彼此依賴、共生共存的,而這種相互依賴關系的存續需要每個人履行好自己的職責才能實現。因此“一方面應該像德國哲學家費希特所說一般,將自己的職責視作公共工具并發揮其相應的功能,回報自己賴以生存的社會;另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特殊性,展示出與普羅大眾絕對不同的獨立面貌”⑧繩田二郎:《西晉一郎的一生與哲學》,理想社,1953,第60 頁。。職責是實實在在的社會和國家層面顯現出來的特殊形式,同時也是我們參與到實在普遍性的途徑。通過履行職責,我們可以更好地對公共的社會生活做出自己的特殊貢獻,職責意識越強烈,生活的內在本質將越顯現,我們也將進一步認識到自我存在的意義。
為了論述方便,西晉一郎從實在的“仁”和“義”兩個方面探討了實現道德生活的途徑。但需要注意的是,實在本身是一貫統一的,實在概念下的“仁”和“義”本質上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仁”蘊藏著“義”,而“義”是實現“仁”的基準,因此在道德生活中并不能將“仁”和“義”二者割裂開來。在社會和國家賦予我們的特殊職責中毫無保留地自我奉獻,那么最終每個個體行為的實現同時也是普遍性道德生活的實現。
特殊與普遍的關系是哲學實體論的重要議題之一,區別于對立看待特殊與普遍關系的傳統哲學觀點,西晉一郎在《倫理哲學講話》中提出“特殊即普遍”的觀點。這一“即”的觀點并不是將特殊與普遍看作是對立的抽象概念然后尋求二者的相即性,而是將二者作為實在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普遍離不開特殊,實在的普遍性只有借助個體的特殊性發展才能顯現;同時特殊中蘊藏著普遍,個體只有通過實現實在的普遍性才能更好地彰顯出自己的特殊性。正如繩田評價的一樣,在該書中西晉一郎首次形成并確立了自己獨特的學術體系,“特殊即普遍”是貫穿全書的基本概念,也成為后來西晉一郎道德哲學的根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