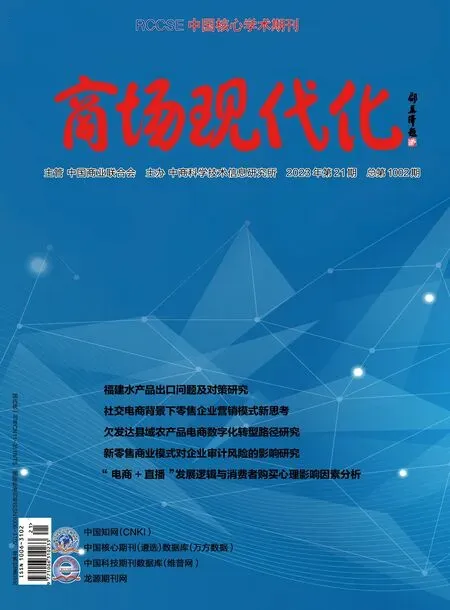區塊鏈技術對企業信用風險承擔能力影響的研究
■白咸芳
沈陽化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一、引言
“十四五”規劃綱要指出,我國正處于大力發展數字經濟時期,區塊鏈技術作為新一代確權工具,能夠有效解決信任問題,實現價值的自由傳遞,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企業作為推動經濟運轉的主體,是我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企業發展面臨的高度不確定性對其風險承擔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依托區塊鏈技術提升企業信用風險承擔能力,對企業順利實現數字化轉型以及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信用風險也稱為違約風險,目前對信用風險的研究主要以構建信用風險預警模型為主。隨著區塊鏈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應用,學者們愈發關注區塊鏈技術與風險管理之間的問題。陳志斌等(2022)、王智博等(2022)、俆晨陽等(2022)立足我國實際情況,對區塊鏈技術與企業風險管理之間的問題展開研究。綜上所述,區塊鏈技術通過介入企業的風險管理對其產生影響。與此同時,零壹智庫聯合數字資產研究院發布的《中國A 股區塊鏈上市公司全景報告(2022)》中指出,目前上市區塊鏈企業開展業務的方式主要包括自主研發、合作研發和投資持股等。因此,本文從是否布局區塊鏈以及具體的業務類型入手,研究其對信用風險承擔能力的影響。首先構建微觀層面的企業信用風險承擔能力評價指標體系;其次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對區塊鏈與非區塊鏈兩類企業開展實證研究,旨在揭示其中的作用機制,期望能為有效提升企業風險承擔能力提供可行建議。
二、區塊鏈技術與企業信用風險承擔能力
1.區塊鏈技術特性
區塊鏈技術以其去中心化、信息公開透明、信息可溯源等技術優勢廣泛應用于各個場景,目前區塊鏈主要有公有鏈、聯盟鏈和私有鏈三大類,其中聯盟鏈與私有鏈在企業管理領域中成為主流趨勢。
去中心化是區塊鏈技術最核心的特點之一,使數據能夠脫離第三方中介在各區塊間實現安全交換。區塊鏈系統的安全性由密碼技術與數據公開透明同時保障,系統中的每個參與方都可通過全賬本數據的獲取實現對數據的全方位監管,使參與方在獲取信息的同時起到相應的監管作用。在信息可溯源方面,產品制造、生產以及流通等環節的信息能夠全部存儲在鏈上,且由于信息不可篡改的特性,任何產品信息都能通過掃碼溯源的方式得到。目前,區塊鏈技術在企業內部可賦能于銷售、物流、財務以及企業管理等各個方面,使得企業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創造出更大的價值。包含區塊鏈在內的數字化技術從各個方面對企業的運營與發展產生影響,如區塊鏈技術的應用使得企業內部各部門之間、合作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得以解決,大大消除風險的不確定性,企業借此可通過內部可控性的提高與外部合作方的篩選,提升信用風險承擔能力。因此,探究區塊鏈技術的引入對企業信用風險承擔能力的影響,必然會為數字經濟發展時期積極參與數字化轉型的企業提供風險治理新思路。
2.區塊鏈技術與企業信用風險承擔能力
本文研究的企業信用風險承擔能力是在風險承擔能力的基礎上定義的,風險承擔能力主要是指抵抗風險的能力。本文將企業的信用風險承擔能力理解為企業能夠抵抗信用風險的能力,信用風險承擔能力與企業特征、公司治理、財務狀況等多個方面有關。
就企業特征與公司治理而言,本文將兩者歸納為非財務影響,在此影響因素下,區塊鏈技術的引入對企業的管理框架、人力資源管理、創新發展等產生多維度的影響。例如,企業可利用區塊鏈技術進行部門重構,以此更新企業的管理框架,就產品生產而言,將企業的生產、銷售、倉儲物流等部門的多環節信息上鏈存儲,形成基于區塊鏈技術的產品生產—銷售—倉儲物流信息網,將生產信息上鏈存儲并向所有參與產品銷售環節的部門公布。區塊鏈技術可用于企業人力資源的管理與組織架構的調整,通過區塊鏈人才信息存儲和智能合約設置,可實現招聘流程的簡化與人才晉升機制的科學性,同時,區塊鏈技術可通過改善企業內外部的信息不對稱,助力企業實現扁平化轉型與合作企業的篩選,在企業內外部建立有利于企業健康發展的互信平臺。在財務影響的因素下,企業將區塊鏈技術應用于財務管理,實現賬目信息透明、審計監管簡便等目標。
三、研究設計
1.企業信用風險承擔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已有文獻對企業風險承擔能力的衡量方法各有不同,如觀測期內股票價格波動、盈利波動、企業的財務狀況等,參考相關文獻,結合本文對企業信用風險承擔能力的定義,從非財務指標與財務指標兩個方面共選取16 個指標構建評價指標體系,采用主成分分析后的綜合指標對信用風險承擔能力進行衡量,具體指標如表1 所示。
2.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由于開展區塊鏈業務對企業信用風險承擔能力產生的影響存在一定的延遲效應,因此本文參考零壹智庫聯合數字資產研究院發布的《中國A 股區塊鏈上市公司全景報告(2021)》,將其公布的區塊鏈企業名單作為選擇基礎,根據新浪財經官網公布的企業相關數據,剔除ST股票、*ST 股票以及信息嚴重缺失的企業,最終選取56家上市區塊鏈企業與14 家非區塊鏈企業作為本文的分析對象。
3.主成分分析
為降低指標之間的冗余性,本文選擇主成分分析方法對數據進行降維分析,運用分析后的綜合指標衡量企業信用風險承擔能力。本文選擇SPSS 25 軟件對數據進行標準化及主成分分析,其中提取方法選擇主成分分析法,旋轉方法選擇凱撒正態化最大方差法,分析結果通過KMO 和巴特利特檢驗,表明對本文選擇的數據進行主成分分析是合理的。如表2 所示,根據總方差解釋表中的累積方差貢獻率,前7 個公因子對總體的代表性達到總方差的83.21%,因此本文確定7 個主成分以衡量企業風險承擔能力。

表2 總方差解釋
依據旋轉后成分矩陣中各因子的載荷系數確定原始指標歸類,得到降維后的7 個綜合指標,公因子F1包含三個指標,由于本文以企業的營業收入反映企業規模,因此主成分1 中的X1、X10以及X11共同反映了企業資產的周轉效率,將F1記為周轉效率。公因子F2包含X5、X9、X15以及X16,綜合反映了企業的報酬率、變現能力以及現金流量狀況,記為營運能力。公因子F3包含X12、X13和X14,綜合反映了企業的負債與償還能力,記為償債能力。公因子F4包含X6、X7和X8,記為發展能力。公因子F5包含X2,反映了企業決策權的集中度,記為股權集中度。公因子F6包含X4,表明企業主營業務的獲利能力,記為盈利能力以及公因子F7包含X3,反映了企業獲取各方面關鍵資源的能力以及對公司治理產生的相應影響,記為治理結構。
4.DEA 模型分析
本文將企業信用風險承擔能力作為產出指標,根據企業開展區塊鏈業務的實際情況對區塊鏈服務生產力的效率進行研究,以此探究區塊鏈技術與企業信用風險承擔能力之間的關系。數據包絡分析(DEA)是用來測量決策部門生產效率的有效方法,其基本原理是保持決策單元的輸入、輸出不變,借助線性規劃和統計數據確定相對有效的生產前沿面。
(1) 投入產出指標的確立
本文選擇企業的營業成本和區塊鏈業務類型作為DEA分析的投入指標,并將企業風險承擔能力作為產出指標。
(2) DEA 模型分析
本文選擇SPSSAU 在線數據分析軟件以及BCC 模型對樣本企業進行DEA 模型分析,樣本數據共計70條,分析結果中重點展示了綜合技術效益(TE)、規模效益(SE)和純技術效益(PTE)。在區塊鏈企業中,有9 家屬于自主研發,18 家屬于合作研發,29 家屬于投資持股或者全資控股子公司,因此本文對所有樣本分類后的均值進行綜合比較,如表3 所示。

表3 綜合比較結果
以企業開展區塊鏈實際狀況對數據分析結果進行分析,9 家自主研發區塊鏈企業在綜合技術效益、規模效益和純技術效益三個維度的均值均為1,達到了DEA 強有效。合作研發、投資持股或全資控股子公司以及非區塊鏈企業在三個維度的效率值均達到了DEA 近似有效,但非區塊鏈企業的效率值要略低于區塊鏈企業。
區塊鏈企業在三個維度的總均值均優于非區塊鏈企業,這表明布局區塊鏈業務對企業風險承擔能力存在一定影響,區塊鏈企業規模效益總均值為0.961,表明布局區塊鏈業務的企業存在較為顯著的規模效益;純技術效益總均值達到0.949,表明布局區塊鏈業務能夠以較高的技術水平轉化為企業的風險承擔能力。
開展自主研發的區塊鏈企業在三個維度上的效率值表現最優,其次是合作研發,最后是投資持股或全資控股子公司,這可能是因為企業本身綜合實力較強且自主研發區塊鏈對企業原有業務的開展存在較大的促進作用,綜合來看提升了企業的風險承擔能力;而以合作的形式開展業務研發,能夠在較大程度上利用合作方的各種資源優勢,對企業的風險承擔能力有較大的促進作用。
綜上所述,企業開展區塊鏈業務確實能以較高的技術水平和規模效益對企業風險承擔能力產生影響,但相關企業也需要注意到布局區塊鏈的類型與本公司原有業務的整合程度,以此確定具體的區塊鏈業務類型,從而在較大程度上提升企業的風險承擔能力。
四、結論與不足
1.結論
復雜且不確定的發展環境使企業信用風險承擔能力的提升成為被重點關注的問題。本文研究了企業開展區塊鏈業務的實際情況與信用風險承擔能力之間的關系,運營主成分分析與DEA 模型分析法,對70 家樣本企業信用風險承擔能力的綜合技術效益、規模效益和純技術效益進行統計分析,結論如下。
① 企業開展區塊鏈業務的實際情況對風險承擔能力存在一定的影響。從區塊鏈企業與非區塊鏈企業綜合對比來看,前者在企業信用風險承擔能力方面的表現更為優越。從區塊鏈企業三個維度的總均值來看,區塊鏈企業信用風險承擔能力效率均值為DEA 近似有效,表明企業開展的區塊鏈業務能夠以較高的技術水平和規模效益轉化為企業的風險承擔能力。
② 從自主研發、合作研發、投資持股或全資控股子公司三種類型來看,自主研發和合作研發類區塊鏈企業風險承擔能力的提升要明顯優于投資持股或全資控股子公司,這提示企業開展區塊鏈相關業務時要根據企業自身實力或原有業務進行決策。
③ 企業應同時關注純技術效益和規模效益兩個方面,在技術和規模兩個方面進行合理的資源配置。投資持股或全資控股類區塊鏈企業在開展相關業務時,要重點關注純技術效益產生的影響,以解決因純技術效益較小而引起的綜合技術非DEA 有效的問題。
2.不足
本文的不足之處主要有以下兩點:首先是采用了傳統的DEA 模型分析,并未考慮環境變量的影響;其次是數據的選取方面,本文只對不同類型的決策單元進行了橫向維度的比較,并未對同一決策單元不同時間的企業信用風險承擔能力效率值進行比較,且數據量相對較少。因此在未來研究中,環境變量對企業信用風險承擔能力是否存在影響以及如何產生影響是值得關注的重點,同時在數據選取方面,可從時間維度擴大樣本量,實現更多維度的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