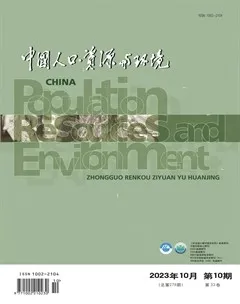碳減排政策、銀行系統性金融風險與“雙支柱”調控
胡小文,項后軍
(1.安徽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2; 2.廣東金融學院金融與投資學院,廣東 廣州 510521)
低碳轉型是實現中國“雙碳”目標、建設“美麗中國”的必由之路。然而,低碳轉型必將影響經濟發展路徑,還可能對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產生負面影響。前英國央行行長Carney認為,低碳轉型風險會通過經濟主體和金融機構傳播,影響資產價格與金融穩定[1]。2021年,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明確提出央行要及時評估低碳轉型對金融穩定的影響,并將其納入央行的風險管理體系。那么,商業銀行作為低碳轉型風險的重要傳播載體,會受到怎樣的負面影響?不同類型減排政策對商業銀行金融穩定的影響存在怎樣的差異?中央銀行如何制定政策以防控可能引發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這些問題非常前沿而又緊迫,對于減排時間緊、任務重的中國,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1 文獻綜述
環境政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可追溯到Grossman等[2]提出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此后環境政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受到了學者廣泛關注,主要形成了雙重紅利假說[3]、成本假說[4]和波特假說[5]。考慮到經濟的動態性、隨機性和政策制定的前瞻性,近年來學者多構建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研究碳減排政策的經濟效應。Fischer等[6]將污染中間品直接納入生產函數構建價格彈性的DSGE模型,分析碳稅、總量控制、強度標準政策的長期增長和短期波動效應。Annicchiarico等[7]構建價格粘性的DSGE模型,分析三種碳減排政策的經濟效應。國內學者也構建了環境DSGE 模型,分析不同類型碳減排政策的經濟效應[8-10]。
相對而言,環境政策對金融系統的影響研究卻明顯滯后。Batten等[11]對一些氣候事件造成的經濟后果進行分析,發現氣候變化及其政策會降低棕色資產的價值,導致其產生信貸約束,進而影響金融穩定。Dunz等[12]對綠色支持因子和碳稅的不同政策組合下的金融穩定狀況進行了情景分析,發現碳稅在培育銀行綠色貸款和企業投資方面比綠色支持因子更有效。王博等[13]探討了綠色支持因子和碳稅兩大政策對金融穩定的影響,發現綠色支持因子政策會增加企業部門不良貸款,而碳稅對金融體系的影響經傳導后的作用效果有限。潘冬陽等[14]討論了綠色金融政策與金融穩定的關系,發現綠色金融政策能夠緩解綠色部門的融資約束,降低其融資成本與杠桿率。
2008年金融危機后,眾多研究開始關注“雙支柱”政策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政策效果。在利率沖擊[15]、信貸沖擊[16]、住房偏好沖擊[17]和金融沖擊[18]下,實施“雙支柱”政策既能穩定金融風險,又能緩解經濟波動。然而,針對減排政策沖擊引發的金融風險防控,還少有學者關注。Carattini等[19]明確表示,氣候政策可能引發金融風險上升,事前的審慎監管能抑制風險產生。王博等[20]模擬發現碳稅和碳交易對金融系統穩定產生了負面影響,“雙支柱”調控能降低該風險。
上述研究為該研究提供了極有價值的線索,但是,有關減排政策影響金融穩定的研究主要從信貸需求角度分析,未考慮到減排政策還會從銀行信貸供給角度影響金融穩定。而且,現有研究主要討論碳稅和綠色支持因子對金融穩定的短期影響,缺少總量控制、強度標準和碳稅的比較研究。無論是從學術還是現實角度,三大政策對金融穩定的影響比較研究,都值得探討。
鑒于此,文中構建一個包含碳減排政策-宏觀經濟-金融穩定的DSGE框架,將總量控制、碳稅、強度標準政策納入該框架,從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兩端分析碳減排政策對銀行系統性風險的影響,并模擬包含審慎特征的貨幣政策和“雙支柱”政策在應對轉型風險上的效果差異。該研究的邊際貢獻在于:首先,在環境政策-宏觀經濟的DSGE模型基礎上,考慮商業銀行資產和負債兩方面,較為系統地關注減排政策對銀行系統性風險的影響;其次,在一個框架下分析總量控制、碳稅和強度標準政策對金融穩定的長期和短期影響,并進行比較研究;最后,分析“雙支柱”政策應對低碳轉型風險的效果。
2 模型構建
在Annicchiarico等[7]基礎上,構建包含碳減排政策通過資產和負債渠道影響銀行系統性風險的DSGE分析框架。模型框架包含五大經濟主體:家庭部門、生產部門、商業銀行、中央銀行和政府部門。家庭部門選擇合適的消費、勞動力供給、國內存款與商業銀行股權投資來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生產部門包含中間品企業、最終品企業和資本品企業。中間品企業利用勞動、資本和能源三種生產要素進行生產,且生產過程中需要向商業銀行融資購買資本;最終品企業利用中間品加工成最終產品,提供給國內居民消費和資本品企業生產投資品;資本品企業生產資本品,出售給中間品企業作為生產要素。商業銀行吸收家庭存款和股權融資,為企業提供貸款,其資本充足率會受到逆周期監管的約束。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政府部門實施財政政策和環保政策。
2.1 家庭部門
假設代表性家庭能夠無限期生存,其效用取決于家庭的消費ct、勞動ht和活期存款dt:
其中:β為貼現因子,?和θ為勞動、存款對效用的相對貢獻度,σ、γ、ω反映消費跨期替代彈性、勞動供給彈性和存款跨期替代彈性。家庭除了消費和儲蓄外,還投資銀行股權資本獲得回報。家庭跨期的預算約束:
其中:dt、st分別為家庭存款規模和家庭投資的銀行資本規模,分別為存款利率與銀行股權資本回報率,?t和Tt分別為銀行破產概率和一次性稅收。在式(2)約束下,居民為實現預期效用貼現和最大,選擇最優的消費、勞動供給和存款規模。
2.2 生產部門
2.2.1 中間品企業
中間品企業i在相同技術水平at下,利用勞動hi,t、資本ki,t和能源ei,t進行生產:
參考Annicchiarico等[7]思路,設定碳排放與碳減排成本方程分別為:
其中:ui,t為碳排放努力程度,φ為單位能源的碳排放量,γ1、γ2為減排成本技術參數。
其中:ut為碳排放努力程度(減排激勵程度),φ為單位能源的碳排放量,γ1、γ2為減排成本技術參數。
參考Calvo[21]的交錯定價形式,設定企業最優定價后的通脹方程:
其中:λf=βρψ-1,λb=ζψ-1,λmc=(1-ζ)(1-ρ)(1-分別表示通貨膨脹、預期通脹、通脹慣性的波動,表示實際邊際成本波動,ζ,ρ,β分別代表企業遵循后向預期定價比例,保持價格不變比例和貼現因子。
2.2.2 企業家
參考Bernanke等[22]的研究,企業家需要向銀行融資,用于購買資本品進行生產。融資的預期收益為Etft+1=,其中qt為資產價格;融資的預期成本為Etft+1=,Ω(?)為風險溢價函數,設置為Ω(?)=(qtkt+1/nt+1)?,Ω"(?)>0,nt+1和分別為t期末的企業凈值和銀行融資的機會成本。
現實中企業會破產,設定每期企業的破產概率為ζ。企業凈值為nt+1=ζVt,Vt為企業的資本價值ftqt-1kt減去借款成本Et-1ft(qt-1kt-nt)。
2.2.3 資本品生產企業
參照Kiyotaki 等[23]的研究,設定資本品生產過程中存在二次可調成本0.5χ(it/kt-δ)2。其利潤最大化方程為,優化得最優資本品價格滿足qt-1-χ(it/kt-δ)=0,其中qt為資本品價格。另外,資本轉移方程kt+1=it+(1-δ)kt。
2.2.4 最終品企業生產
最終品企業部門生產函數為yt=,θ為中間品的替代彈性,yt(i)為第i個中間品企業的產出。最終品企業在利潤最大化下,得到最終品價格滿足Pt=。
2.3 商業銀行部門
商業銀行吸收家庭存款dt和持有股權成本st,為企業提供貸款lt。假設銀行貸款過程中存在二次可調成本0.5κ(st/lt-η)2st,其中κ、η表示調整系數和最低資本充足率。在χdt+st=lt約束下,銀行利潤最大化得到最優狀態下銀行可貸資金成本為:
其中:χ為存款準備金率,λt=st/lt為資本充足率,η為最低資本充足率。參考Suh[24]的研究,設定銀行破產概率?t與資本充足率負相關,即?t=F(λt-1)=,F"(λ)<0,νa,νb為參數。
2.4 貨幣政策
設定我國的貨幣政策服從泰勒規則:
2.5 財政政策
政府部門執行財政政策,面臨預算約束Tt+pz,tzt=gt。
2.6 環保政策
參考Annicchiarico等[7]設置碳減排政策如下:
(1)無環境政策。此時pz,t=0,ut=0。即企業排污成本為0,減排努力程度也為0。
(2) 碳稅。政府對單位二氧化碳征收固定稅率的環境稅τz,此時碳稅等于碳價pz,t=τz。
(3)總量控制。政府規定企業總排放不超過-z,即zt≤-z,同時以市場價格pz,t向生產者出售排放許可證,只有取得許可證的企業才可以進行碳排放。此時,許可證的價格為pz,t。
(4)強度標準。政府規定企業碳排放強度標準不超過ν,即zt≤νyt。此時,zt/yt=(1-ut)φ≤ν,同時以價格pz,t向生產者出售排放許可證。
2.7 市場均衡
當各經濟主體最優決策時,產品市場均衡時有yt=ct+it+gt+cat;所有中間品企業消耗的勞動、資本和能源之和等于總勞動供給、資本量和能源量。
2.8 模型沖擊
模型中包含技術沖擊、能源價格沖擊、政府支出沖擊和貨幣政策沖擊,設定各沖擊均服從一階自回歸過程。
3 參數估計
3.1 參數校準
參考劉斌[25]的做法,貼現率β設定為0.99,消費跨期替代彈性參數σ設置為2,勞動對效用的相對貢獻度?為1,資本份額α為0.5,能源份額ν為0.1,不能調整價格的廠商比重ρ為0.75,稅收占比穩態值T/y設置為0.18,銀行存款準備金率χ為0.2。參考李天宇等[26],設置存款跨期替代彈性參數ω為2,存款對效用的相對貢獻度θ為0.035。參考袁申國等[27]設置中間品企業生存概率ζ為0.97,折舊率為0.03,風險溢價系數τ為0.01,邊際成本穩態值為0.91,可調成本系數為χ為0.7,風險溢價穩態值為1.0056,穩態的資本與資產凈值比率k/n為2.38。參考Heutel等[28]的研究,選擇減排技術系數γ1和γ2分別為4.625和2.800。按照外生設定的原則,技術水平穩態值a、資產價格穩態值q、碳價格穩態值pem和能源價格穩態值Q均為1。參考李健等[29]的研究,設定無碳減排政策下的碳排放強度穩態值φ為0.45。按照近5年我國不良貸款率均值,設定銀行的破產概率?為1.5%,校準得到參數νa和νb分別為10和175。按照巴塞爾協議要求,設定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穩態值η為8%。
3.2 參數估計
需要說明的是,下面的參數估計是在無碳減排政策模型框架下進行,主要原因是目前中國還未實施碳稅、碳總量控制等政策,缺少相關數據。但在后面的分析過程中,將在無碳減排政策框架基礎上納入碳總量控制、碳稅和強度標準政策,進行反事實模擬。
選擇產出、通脹率、政府支出、利率對文中動態參數進行貝葉斯估計,樣本范圍為1996年第1季度至2022年第4季度。采用國內生產總值、國內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一年期存款利率、政府實際最終消費分別表示產出、通脹、利率和政府支出,數據來自于國家統計局和中國人民銀行網站,估計結果見表1。

表1 無環境政策模型的參數貝葉斯估計
4 碳減排政策影響商業銀行金融風險的機制分析
通過穩態求解,分析減排政策對經濟和金融變量的影響,目的是梳理減排政策影響商業銀行金融風險的機制。需要說明的是,變量不加下標t表示其穩態值。對企業行為優化求解可得實際邊際成本為:
其中:H=Q+pz(1-u)φ+γ1uγ2=Q+(1-u)γ1γ2uγ2-1+γ1uγ2,H可理解為減排成本。H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能源價格,另外一部分為(1-u)γ1γ2uγ2-1+γ1uγ2。顯然,當不存在碳減排政策時,H=Q;而實施碳減排政策時,碳減排努力程度u>0,此時減排成本H會增大。由邊際成本得到:
式(14)表明,在其他條件下,碳減排政策引起減排成本H增大,導致居民實際工資下降。由企業生產函數與優化結果,可推導得到:
因此,碳減排努力程度u提升,會增大減排成本進而降低碳排放強度。碳強度下降引起企業生產收縮,資本回報率下降,投資占比上升。進一步,根據企業優化結果推導得出:
假設稅收占比不變,則能源消耗占產出比重隨著減排成本H上升而下降。顯然,若不實施碳減排政策,則碳減排成本占產出比重為0,碳價也為0;實施減排政策引起減排成本占產出比重上升。碳價格與碳減排努力程度u成正比,即碳價格越高,碳減排努力程度越高。結合政府約束條件和市場出清條件得到:
在假定稅收占比T/y不變下,政府支出占比會隨著減排政策的實施而上升,因為減排政策增加了政府的收入。隨著投資占比、政府支出占比和減排成本占比均增大,消費占比下降。由生產函數變形可得:
這說明,減排政策對產出的影響與多因素有關,1/w增大、c/y減小、h/y增大,綜合效應下產出降低。由式(15)、式(17)、式(18)、式(22)可知,碳排放量、投資、能源、消費都隨著總需求y的下降而減少。綜合居民的優化結果、商業銀行優化結果相結合可得下列等式:
因此,隨著居民收入和消費下降,居民存款降低;企業貸款也隨著企業投資減少而降低;貸款需求下降超過存款時,引起銀行資本和資本充足率下降。
總結以上機制,實施減排政策會提升企業減排努力程度,增加其生產成本;導致經濟活動收縮,產出、投資、消費等降低;銀行資本和資本充足率下降。
5 碳減排政策對銀行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影響
5.1 長期影響分析
長期影響分析主要通過穩態值求解來實現。要計算實施減排政策時各變量的穩態值,需要先設定減排目標。鑒于中國政府在哥本哈根會議上承諾的減排目標為強度目標,因此設定的減排目標是碳強度分別下降20%和40%。根據穩態方程,求出無政策和存在環境政策下的穩態值,見表2。

表2 實施環境政策下各變量的穩態值與相對下降比例
由表2可知,各種碳減排政策可以達到相同的減排目標。當碳強度下降20%時,三種碳減排政策具體如下:實施碳稅政策,則碳稅等于碳排放價格0.0286,此時不對企業進行其他碳限制;實施碳強度標準,則設置的碳強度上限為0.4909/1.3635=0.36,此時還以價格為0.0286出售排放許可證;實施碳總量配額政策,則配額量為0.4909,同時以市場價格0.0286出售排放許可證,只有取得許可證的企業才可以進行碳排放。同樣,當碳強度下降40%時,三種碳減排政策如下:實施碳稅政策,則碳稅等于碳排放價格0.0840;實施碳強度標準,則設置的碳強度上限為0.3409/1.2626=0.27;實施碳總量控制,則配額量為0.3409。
表2還顯示:當碳強度下降20%時,碳減排努力程度上升為0.0813;當碳強度下降40%時,碳減排努力程度上升至0.1479。碳減排努力程度上升,導致企業減排成本上升,企業總成本上升,生產規模收縮。正如預期,減排目標提升會增大經濟損失和金融風險。具體地,若碳強度下降20%,產出下降4.74%,碳排放量下降23.79%,居民存款下降4.94%,銀行貸款下降5.90%,銀行資本下降17%,資本充足率下降11.79%;若碳強度下降40%,產出水平下降11.79%,碳排放量下降47.08%,居民存款下降11.96%,銀行貸款下降14.48%,銀行資本下降43.45%,資本充足率下降33.88%。因此,我國目前難以承受短期高強度減排目標,當出現20%的碳強度下降,會導致產出下降4.7%,資本充足率下降了11.79%。
比較發現,實施減排政策導致產出、消費等變量的穩態值下降,下降幅度較大的是銀行資本和銀行資本充足率。當碳強度下降20% 與40%時,各經濟變量穩態值呈現非線性下降,且金融變量穩態值下降相對程度更大。這說明,碳減排政策對金融穩定的影響不容忽視。
5.2 短期影響分析
短期影響主要是分析外部沖擊下,實施減排政策的效果。現實經濟環境中,存在各種不確定性沖擊。當這些沖擊發生時,各種碳減排政策的效果存在差異。下面選擇技術沖擊和能源價格沖擊,從脈沖響應和社會福利損失兩個方面比較各減排政策下的短期影響。模擬過程中假設各碳減排政策目標是碳排放強度下降20%,這能保證三大碳減排政策效果的可比性。
5.2.1 脈沖響應分析
(1)技術進步沖擊。圖1顯示,技術進步引起產出、企業信貸、碳排放量、銀行資本充足率上升,通脹與銀行破產概率下降。經濟機制為:技術進步,引起企業邊際成本下降,投資需求增加,產出和通脹上升;這也擴大了企業對能源的需求,導致碳排放量增加;經濟擴張下,銀行股權資本上升幅度超過信貸上升幅度,資本充足率上升,系統性風險下降。

圖1 技術進步的影響
比較發現,相對無碳減排政策情形,實施三種碳減排政策都有利于緩解產出、信貸、碳排放變量波動,但是會增大通脹波動。主要原因是:實施碳減排政策,實質上是對企業的生產擴張過程起到抑制作用。碳減排政策會抑制企業生產,后果是企業對勞動和資本的需求減少,工資和租金下降較無減排政策下幅度大。因此,碳減排政策下,邊際成本的下降幅度較無減排政策下大,即通脹的下降幅度較無減排政策下大。還發現,碳總量控制抑制產出和金融波動的能力最強,其次是碳強度政策,最后是碳稅政策。這是因為碳總量和強度控制均是對碳排放數量約束,而碳稅是對碳排放量的價格約束,并且碳稅成本占企業總成本比重低。
(2)能源價格下降沖擊。由圖2可以看出,當能源價格下降時,企業會增加能源使用量,碳排放量上升、產出增長,通脹因企業的邊際成本下降而下降;銀行資本也在企業擴張下增長,資本充足率上升,銀行系統性風險下降。總體上,實施碳減排政策會降低各個經濟和金融變量的波動。因為,碳減排政策會制約企業碳排放,這等價于約束企業的生產活動,抑制了因能源價格下降而產生的順周期性。需要說明的是,圖中碳強度政策下的碳總量波動非常小但并不為0,而與產出波動一致;但是,總量政策下的碳排放波動為0。

圖2 能源價格下降的影響
比較看出,三種碳政策中,無論是緩解經濟變量和金融變量波動,還是控制碳排放方面,總量控制和強度標準政策效果基本相同,都是不錯的選擇;而碳稅政策的力度較弱。主要原因是:碳總量和強度標準是數量型政策,作用直接且力度較大,企業因此會較大幅度縮減生產規模;而碳稅政策作為價格型政策其作用時期長且柔和,對企業生產的影響較小。
5.2.2 社會福利損失分析
將居民的效用函數在穩態處二階泰勒展開,可得社會福利損失函數:
其中:符號Var(ct)為消費的方差,Uc為居民效用函數關于消費的一階偏導,c為消費的穩態值,其他變量的含義類似。下面給出技術沖擊和能源價格沖擊的福利損失值,見表3。

表3 不同沖擊下的社會福利損失值
比較看出,面對兩大沖擊,相對于無環境政策,各碳減排政策下的社會福利損失都有下降。這說明,碳減排政策能夠起到減少社會福利損失的效果。不同沖擊下,各減排政策的效果也不相同。當遭遇能源價格沖擊時,碳減排政策的調控效果較為明顯,尤其是總量和強度控制政策的效果較好;而遭遇技術沖擊時,碳減排政策的調控效果不明顯。該結果與前面的脈沖模擬分析結果一致。
以上結論恰好證實了總量和強度政策的優越性,不僅能夠有效降低碳排放,還能緩解減排過程中的經濟和金融波動,這為我國的減排政策實踐提供了理論支持。
6 “雙支柱”政策應對減排政策轉型風險的效果
“雙支柱”政策包含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貨幣政策設置如式(12),宏觀審慎政策設置如式(29)。之所以如此設置,是因為巴塞爾協議III要求對銀行的資本進行逆周期管理。當經濟過熱時提升資本緩沖,抑制信貸的過度增長;反之,則降低資本緩沖。因此,式(11)中最低資本充足率η動態變化且滿足:
參數φy、φl均大于0,分別表示商業銀行的最低資本充足率對產出和信貸波動的響應系數。
同時,文中還設置包含低碳轉型風險的貨幣政策規則如式(30),目的是比較其與“雙支柱”政策效果的差異。鑒于碳減排政策可能引發信貸風險,因此,在式(12)基礎上設定擴展型貨幣政策,即利率不僅關注產出和通脹波動,還盯住信貸波動:
考慮到包含低碳轉型風險的貨幣政策重心仍是調控經濟波動,將ρl設置的數值為0.1;宏觀審慎政策側重于實現信貸穩定,參數φl設置為1.5。以碳總量控制政策沖擊為例,各種情形下的脈沖圖如圖3所示。此時,不設置總量控制為zt≤,而是設定。為避免重復,不給出碳強度和碳稅政策沖擊的結果,結論與碳總量政策的結果一致。

圖3 不同情形碳總量控制的影響
圖3顯示,碳總量控制政策短期內降低了碳排放數量,但是卻引起產出下降、通脹上升,銀行股權資產、銀行貸款和銀行資本充足率下滑。比較發現,無論是擴展型貨幣政策還是“雙支柱”政策,都能夠降低碳總量政策引起的產出和金融變量的波動,而且還不會影響總量政策的碳減排數量;雖然“雙支柱”政策與擴展型貨幣政策在穩定經濟波動方面的效果差異不大,但是“雙支柱”政策在穩定金融風險方面的效果最優。
產生上述結果的原因是:面對碳總量政策引起的經濟下行、信貸下降,此時若實施擴展型貨幣政策會引起利率較大幅度的下降,從而刺激需求上升,部分抵消了減排政策對經濟和金融的負面效應;此時若實施“雙支柱”政策,逆周期資本監管會降低銀行的計提資本,增加銀行的可貸資金規模,促進經濟發展,也會部分抵消了減排政策的不利影響。由于逆周期資本監管政策主要是調控金融穩定,對金融變量的關注程度高于經濟變量;而擴展型貨幣政策的重心是調控經濟波動,對金融變量的波動程度較低。因此,逆周期資本監管政策對金融變量的穩定效應要強于擴展型貨幣政策。
7 結論與建議
文中構建了包含環境政策—宏觀經濟—金融風險的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碳減排政策對銀行系統性風險的影響,以及“雙支柱”政策調控該風險的效果。研究發現:第一,碳減排政策會減少碳排放,但也會提升企業的減排成本;還會減少銀行利潤,引起銀行資本充足率下降,系統性風險上升。第二,長期影響方面,若碳強度下降20%,會引起產出下降4.7%,銀行資本充足率下降11.79%;而碳強度下降40%,產出下降將達到11.79%,銀行資本充足率下降33.88%。這說明,碳強度下降對經濟增長和金融風險的影響呈現非線性遞增變化,而且對金融穩定的影響程度更大。第三,短期影響方面,碳減排政策具有穩定產出和金融變量波動的效果;且總量控制的效果最優,強度標準次之,碳稅政策效果最弱。第四,風險防控方面,逆周期資本監管“雙支柱”政策效果優于包含宏觀審慎的貨幣政策。
基于以上結論,給出如下建議:首先,要從實際出發、積極穩妥推進雙碳工作。①考慮到中國存在區域能源結構和經濟結構差異性,對于能源結構優、產業結構輕的地區要堅持低碳發展,率先完成碳達峰;而對于煤炭能源比重大、產業結構重的地區要優先節能減排,大力發展清潔能源,逐步實現產業轉型,力爭保持與全國碳達峰節奏一致。②考慮到中國區域要素稟賦和能源消耗差異,東中部地區可在承接西部能源基礎上,逐漸有序轉移高耗能產業至西部,擴大西部地區能源消納能力,實現經濟和低碳區域協調發展。其次,構建以控制碳排放總量和強度為主導的“雙控”低碳政策體系。①要從空間和時間上綜合考慮,科學合理統籌分配各地區的碳排放量。空間上,要綜合考慮地方經濟發展狀況、能源分布和高耗能產業發展等;時間上,要充分考慮能源消耗季節性、產業布局周期性和能源設施建設的長周期性等。②借鑒能源雙控發展狀況,按照先強度、后總量順序,約束指標和預期指標結合,形成碳排放“雙控”約束機制。最后,“雙碳”工作必須堅持防范風險,樹立底線思維,預防轉型風險。①商業銀行要構建地區、行業和企業層面的資產碳密度的宏微觀數據,掌握高碳資產和高碳投資數據,從微觀角度預防轉型風險。②中國人民銀行可根據中國宏觀審慎政策現實,合理使用防范低碳轉型風險的審慎政策工具。如在碳周期上行階段,可增加計提的逆周期資本緩沖,抑制碳排放;對于高碳資產業務占比高的商業銀行,央行可提升其資本充足率要求;對于低碳資產業務占比高的商業銀行,調低其最低資本要求,鼓勵其進行綠色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