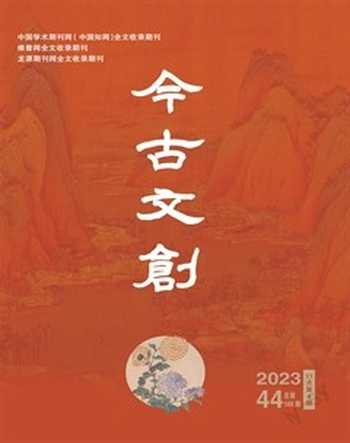王晉康科幻小說中的身體景觀研究
【摘要】王晉康有“中國科幻的奠基人和思想者”之稱,他的作品被稱為哲理科幻,其中“新人類系列”科幻小說以人類被更高級生命形式取代為主題,描寫了多種形態的身體景觀,傳達出他對技術化身體的多種想象與理性思考。本文聚焦王晉康“新人類系列”小說中的身體書寫,分析作品中豐富的身體景觀,以及技術化身體帶來的人類身份認同問題,從而揭示作者積極構建人類未來身體景觀的創作意圖。
【關鍵詞】王晉康;后人類;技術化身體;異化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44-004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4.015
1997年,第一只克隆哺乳動物多莉羊出生,人類象棋棋王敗于智能電腦深藍之手。王晉康根據兩大事件在《克隆技術與人類未來》中對克隆技術的發展和人類未來的身體做出預言:人類“革命性”的異化已經不再是海市蜃樓,不再是科幻作家的異想天開,相信在一個世紀內就會出現。試管嬰兒和即將出現的克隆人既是自然人類衰老的第一塊老人斑,又是新人類誕生的第一聲宮啼。[9]362006年,他再一次發表《超人類時代宣言》,指出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科學技術對人類在物理層面進行的異化已經遠遠超過自然的作用。[8]24
鑒于此,王晉康以生物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為整體創作背景,在“新人類系列”科幻小說中繪寫了體細胞克隆、基因嵌接等技術干預下的多種人類身體景觀,傳達出他對克隆和基因技術打破人類演化規律的思考和對人類未來身體的想象,為人們窺探技術化身體的形態、困境和未來走向提供了一面具有啟發意義的棱鏡。
一、技術化身體:后人類身體形態
現代技術時期,技術直指人本身,二者的關系比任何時候都更緊密,人類對技術的依賴程度也越來越高。喬瑞金教授指出:“技術作為人的生存環境,如同人的自然環境一樣,在本質上已經成為人自身。”[2]2技術重要性的凸顯及其對身體的干預使得“技術化身體”成為現代技術與身體關系的顯像,王晉康看到技術的強勢力量,認為人類向后人類的躍遷不可逆轉,并且歷史將證明這是一種進步。他將技術化身體分為“補足式異化”“改進式異化”[8]24和“革命性異化”[9]36三種類型,在“新人類系列”科幻小說,即《癌人》《豹人》《海人》《類人》中塑造了多樣的技術化身體景觀。
所謂的“技術化身體”概念,最早由英國社會學家克里斯·希林(Chris Shilling)提出,可以理解為以身體本身為中心,將技術以外置于身體或內嵌于身體的方式來肯定、解放、改變、重塑身體,由此產生技術與身體互相建構的新的主體形式。此時,技術與身體的關系是技術圍繞身體需求而被建構。而后,美國技術哲學家唐·伊德(Don Ihde)從三個維度將身體分為體驗的身體、文化建構的身體和技術化的身體,表明技術可以是作用于身體的主體,二者是彼此尊重、互為中心的關系。也就是說,技術化身體可以被定位為處于一定社會和歷史條件下,由處于主導地位的文化和價值觀念所塑造、根據技術的發展由人的需要而確立的、將技術與身體融為一體的新型身體。[11]230王晉康將新型身體區分為補足式異化的身體、改進式異化的身體以及未來的革命式異化的身體三種類型,前兩種身體形態在“新人類系列”科幻小說中得到展示。
第一,補足式異化的身體。不論是先天缺陷或是后天意外致殘的病人都渴望享有正常的身體,用于滿足這一愿望的技術為人類認可,補足式異化的身體應運而生。如《癌人》中肝器官衰竭的海拉外婆,憑借移植人造肝臟來延續生命,這是對生理層面的身體進行補足;《類人》中為滿足人類對仆人擁有感情但人格又低于人類的要求而生產出的類人仆人,則是文化意義上的另一種補足。前者對修復身體缺陷具有積極的正面作用,后者因以服務人類為目的也沒有引起激烈爭議。
第二,改進式異化的身體。補足式異化的身體以將病人恢復為正常人為目的,改進式異化的身體則源于人類對更持久、更強大、更優秀的超人類的追求,這種異化“將首先在基因技術、人腦的電腦化兩大領域里實現”[8]24。人類身體擁有完美的外形和精巧的功能組合,但部分功能與技術物或動物相比處于弱勢地位,具有修改、編輯功能的基因技術實現了對身體的主動書寫而非被迫修改,如《豹人》中的謝豹飛憑借在體內嵌入獵豹基因而獲得獵豹般的奔跑能力;《癌人》中的海拉借助癌細胞無限繁殖的特性而獲得器官再生和永生的能力;《海人》中的海豚人結合海豚與人類的基因而適應海洋生活等,證明基因編輯技術改進后的身體具有超人性質。此外,對身體的改進還有另一種形式,即拋棄身體的物質存在,如《類人》中類人工廠的另一管理者是一位無身體或者說是虛擬身體的人腦的電腦化存在,其擁有智慧、理性、情感,擺脫身體局限的同時獲得了無限的生命,某種意義上實現了人類魂牽夢縈的永生夢想。
第三,革命式異化的身體。相較于拓展、加強身體功能的改進式異化身體而言,符合治療范圍的補足式異化身體事實上已經成為生活中隨處可見的景觀,二者都是已然的存在。而革命式異化的身體更多是一種未來指向,它指涉全人類,是人類整體在身體上的徹底異化,目前還處于未完待續狀態。
二、身體焦慮:后人類的身份認同危機
身份建基于自我與他者的對立,我群與他群的區分,是一個古已有之的問題。以技術化身體形式呈現的后人類在身體層面與自然人類存在根本差異,身體焦慮的存在迫使人類與后人類共同面臨身份危機:人類憂懼自身的主體和主導地位被后人類取代,后人類渴望得到人類的認可和尊重。
學者王飛指出:“當個人與他人/社會能夠取得認同時,則可以建構身份,獲得身份認同;個人與他人/社會不能認同,則相應產生焦慮。與身份問題正面表征的認同相對,焦慮是身份問題的負面表征,也是身份問題的最初體認,更是建構和重構身份認同的基礎和開端。”[4]39
作為少數群體、后來者和他者的后人類,建構主體身份的前提是獲得人類的認同,身體充當身份認同的建構者角色,非自然的技術化身體是人類拒絕后人類的最直接原因。對于后人類來說,技術化身體既是其賴以產生的前提,又成為妨礙其融入人類社會的最大困難。自古以來,不論中外,人們對異族普遍秉持不信任態度,甚至是敵意。并且,強勢群體往往恃強凌弱,排擠或企圖消除弱者,“非我族類,雖遠必誅”的事例比比皆是。這種心態和立場在人類與后人類的身份認同危機中得到延續:《癌人》中,面對由癌細胞克隆而成的癌人,即使癌人并無侵犯人類的行為和傾向,做出多種努力如將售賣自身器官的資金用于建造收留人類棄兒的孤兒院、接濟窮苦之人等以試圖得到人類社會的許可,但大部分人因忌憚具有無限繁殖能力的癌細胞會使得癌人侵占人類社會而對癌人持憤恨、排斥的敵對態度。克隆人盡管具有友善的態度和強烈奉獻精神,“有母無父”的尷尬出生和永生特質使其得不到人類的身份認可。體內嵌有異種基因的人,如《豹人》中由自然人基因與獵豹基因結合而成的謝豹飛,即使為奪取世界冠軍付出了不遜于自然人的艱辛努力,即便贏獲了世界冠軍,依然不能得到認同。《類人》中以服務人類為宗旨、在工廠流水線上造就的類人,沒有指紋是他們與人類的唯一區別,也是產生身體焦慮的直接原因。類人中不乏為得到人類的尊重、獲得與人類平等地位而努力的個體,如偷偷嵌入人類指紋信息的雅君、努力工作且無私奉獻的基恩、能力出眾的宇和劍明等,但無一獲得真正的成功。不論是何種形態的技術化身體主體都沒能通過自身的爭取克服身體焦慮,他們無法說服人類越過身體問題去接受他們。
與排斥后人類的自私、冷血、狹隘的人類不同,王晉康筆下具有多種身體形態的后人類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可貴的品質和精神,他們的善良、包容、真誠、慷慨等品德甚至超過部分人類,但身體問題始終是橫亙在兩個群體之間的鴻溝,后人類始終既不能逾越又無法填平這一溝壑。然而,當人類與后人類的處境對調,在人類失去絕對話語權之時,占據主導地位的后人類是那樣優雅、高貴和寬容,如《海人》中的所有海豚人,他們給予人類的唯一幸存者以尊重、照顧、認可和青睞,沒有一星半點的傲慢和偏見。在他們的世界里,技術的魅力蕩然無存,僅僅是封存于箱底的棄物;世界是一個共同體,沒有我群與他群的區分;個體、群體的生老病死讓位于自然的生態規律。人類與后人類的種種問題在這樣的氛圍中倏忽而逝。海人的生存哲學是道家式的“自然無為”,沒有過多的欲望,沒有爭強好勝的脾性,取而代之的是恢宏的整體觀念和足以容納百川的寬闊心胸。遺憾的是,在源遠流長又根深蒂固的人類中心主義籠罩之下,后人類身份認同困境始終以后人類的消亡告終,二者的身份認同問題始終處于懸而未決的狀態。
三、革命式異化:人類未來的身體
科學技術尚未發展之前,人類多以鍛煉、節食或宗教式禁欲等自律方式來塑造身體,科技的觸角伸向人類身體以后,身體成為可以被創造的事物,自然進化與人工進化共同形塑人的身體。王晉康指出,人與其他哺乳動物在解剖學意義上并沒有明顯的界線,依循克隆技術的發展,在龐大潛在利益的誘惑下,克隆出人類是注定會發生的事。只是盤旋在克隆技術利益之上的是人類的革命性異化,“這種異化同猿人向人類的進化具有同等的分量,不同的是,猿人到人類的進化是由于上帝(大自然)的選擇,花費了幾百萬年;而人類向超人類的進化,則是依賴科學技術的力量,是人類用自身之力異化了自身。”[8]25從補足式異化到改進式異化,技術與身體的關系從拼接走向嵌入,革命式異化之中,身體面臨被技術部分或完全取代的風險。
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在《人類簡史》中歸納總結了導致智人(人類)走向末日的三種技術:生物工程、仿生工程與無機生命工程,認為自然選擇在這三種技術的干預下讓位于智慧設計,人類的演化規律將被人為打破。[10]128福山在《我們的后人類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后果》中表明對生物技術革命的態度:“展望現代科技的發展前景時,必須要擺脫人類中心主義的思路,唯其如此才能遇見危機。與此同時,反思現代科技所帶來的倫理問題和政治問題時,人類中心主義卻是必須堅持的原則和底線,唯其如此才能解除危機。”[1]10
王晉康認識到技術打破自然演化規律的必然性和人類中心主義的危險處境,認為“雖然革命式異化必然與人類信仰大轉變攜手并進,但是人類幾十萬年來建立的信仰不會突然斷裂,它會延續滲入到新人類的信仰中去。但不要指望自然人所有的觀念,甚至是某些我們十分珍視的觀念,都一定能延續到將來。人們如今視之為邪惡的某些觀念如人獸雜交、人機雜交也將有新的解釋”[9]36。
回顧人類的進化史,人類從四肢著地到慢慢挺直胸膛,從猿人變為人類是一個巨大進步。但是當時的智者在審視猿人的蛻變時,恐怕并不認為這是一種進步,而是將之視為一種異化,正如人們今天看待新的生命形式一樣。王晉康認為科技發展最前沿的領域如基因嵌接、克隆技術、人工智能給人們帶來了恐懼,科學家們常常處于進退兩難的境地,科學技術正在一點點割去人類對自身生命的敬畏,而這個“敬畏”正是人類所有道德、倫理、宗教賴以存在的基礎。[9]35面對科學技術打破諸多桎梏又劃出新的禁行線這一困境,王晉康認為人類劇變無可逃避,“無論對于儒家人本主義的中國人來說,還是對于宗教人本主義的西方人來說,這種前景都令人不寒而栗”[9]36。作為自然人末代的我們應該跳出“舊人類”(即用自然方式繁殖的,使用自然智力的,原則上不依靠更換器官來延長壽命的人類)的圈子,承認這個變革不可避免,承認我們珍視的許多觀念不得不被淘汰——如此一來,許多道德的怪圈將自動化解。[8]25
換句話說,王晉康認為人類未來的身體必定會發生革命式的異化,堅守飽含偏見、有失公允的人類中心主義只會讓人類在諸多自我設置的障礙里困頓不堪,雖然科學技術具有無限的、巨大的力量,但是“科學并不能幫助人類進入絕對的自由王國,歸根結底,人類的發展之路要由外在的客觀規律所決定,而不是取決于人的自由意志”[8]25。保持敞開的心態和立場,用“站在過去看未來”的歷史眼光面對技術化身體的變革式異化才是正確的選擇。
四、結語
科幻小說兼具想象與科學的雙重特征,往往能夠較為準確地預見技術發展之下人類未來的諸多可能。對生物科學技術發展具有敏銳捕捉力、對科學持有真誠而熱烈之愛的王晉康,在其科幻作品中多次涉及克隆人、基因編輯等后人類題材,他以一種宏大、先進、包容的眼光看待技術對身體的改變,坦然接受身體經歷補足式異化、改進式異化到變革式異化的過程,并將之視為一種無法逆轉的進步趨勢。面對后人類在人類中心主義把握話語權的情況下身份尚未得到認同的困境,王晉康認為人類不應該擔心、恐懼人類身體的異化,如同猿猴變成人類是一種進化,人類邁向后人類是技術時代的進化,是歷史的必經歷程,應當給予后人類以平等的地位。
不可否認,技術在修復殘缺身體方面的重要價值和意義,人類希望倚靠技術獲取更健康、長久的身體也無可厚非,我們需要注意和警惕的是技術本身的不可控性和技術加劇階層分化的弊端。技術本身并無善惡好壞之分,但作為人類工具之一的技術具有價值烙印,它在高度發達之下會成為捆綁人類的無形力量。身體作為人之為人的特征之一,人們設想在極端情況下可以將之舍棄,以數字化的虛擬形態繼續存在,但是針對身體的改進面臨諸多導致不公平、不道德的問題,在此類問題尚未得到妥善解決之前,技術不應該用于改進身體。人們應該認真反思人與技術的關系,審視技術背后的巨大潛力和危害,更應該重視身體的重要性,保護原初的、純粹的、獨立的身體,回到身體的在場。
參考文獻:
[1]弗朗西斯·福山.我們的后人類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后果[M].黃立志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2]喬瑞金.技術哲學教程[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3]王晉康.癌人[M].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
[4]王飛.焦慮與認同:石黑一雄小說中的身份問題研究[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20.
[5]王晉康.豹人[M].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
[6]王晉康.海人[M].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21.
[7]王晉康.類人[M].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
[8]王晉康.超人類時代宣言[J].科技與文化,2006,(11): 24-25.
[9]王晉康.克隆技術與人類未來[J].金秋科苑,1997, (05):34-36.
[10]尤瓦爾·赫拉利.人類簡史[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20.
[11]廉佳,文成偉.技術化身體及其審美旨趣困境分析[J].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21(03):228-234.
[12]Shilling C.The Body in Culture,Technology and Society[M].London:Safe Publications,2005.
[13]Ihde D.Bodies in Technology[M].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1.
作者簡介:
葉德潤,女,貴州興義人,浙江財經大學,文藝學專業,研究方向:文藝基礎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