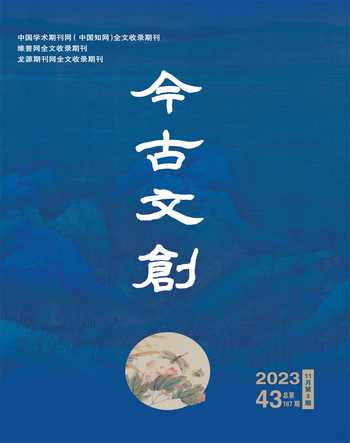淺談列夫派的 “ 紀實文學 ” 理論及其影響
【摘要】左翼藝術陣線,也稱列夫派,于1923年成立,1928年正式解散。在其存在的六年時間里,該團體的理論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從最開始的“生產藝術”理論到后來的“紀實文學”理論,尤其是“紀實文學”理論對后來西方各藝術領域產生了良好的影響。本文旨在分析列夫派的“紀實文學”理論及其影響。
【關鍵詞】列夫派;紀實文學;未來主義;特列季亞科夫;羅琴科
【中圖分類號】I512?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43-006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3.021
左翼藝術陣線是一個文學團體,它的建立是未來主義發(fā)展的一個新階段。在其存在的段時間里,列夫派的理論觀點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我們可以將列夫派的發(fā)展時期一分為二,20世紀20年代初期,列夫派致力于在藝術文本的形式和內容上進行各種各樣的先鋒實驗,擴大文學的可能性和與生命的融合(這些觀點反映在“藝術生產”理論中)。而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當時詩歌不再處于文學的中心問題,列夫派在雜志《新列夫》提出了一種新的理論——紀實文學。該理論否定藝術的虛構,要求藝術家不加美化地描寫生活中的真實,“紀實文學”理論在電影領域影響廣泛。
一、左翼藝術陣線的成立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俄國革命的結束,未來主義者們宣稱共產主義和未來主義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當共產主義消滅了過時的、壓迫性的沙皇制度時,未來主義正在消滅資產階級的思想和舊體制的傳統(tǒng)藝術。他們堅稱,共產主義提供了一個新的政治和經濟框架,而未來主義將塑造新的文化形式。
革命后,未來主義者們出版了唯一一期的《未來主義者公報》,發(fā)表了他們的第一個革命宣言。而單靠宣言無法保證未來主義者的生存,他們需要制度的支持,當時新成立的蘇聯(lián)文化行政當局在文藝界遭到了敵意,因此愿意做出讓步來獲取未來主義者的支持。盧那察爾斯基也認為在當前階段與未來主義者合作有利于俄羅斯文化生活的復興,他認為未來派是唯一一個表達親革命情緒的成熟團體,因此有助于使蘇聯(lián)文化管理合法化。
在盧那察爾斯基的幫助下,未來主義者作品的發(fā)表變得非常容易,他們在雜志《公社的藝術》中倡導把未來主義作為新興文化的基礎。不過盧那察爾斯基很快便發(fā)現(xiàn)自己資助了一個激進的左派組織,這跟他最初想要安撫所有文化團體的想法不符。第二期《公社的藝術》刊登了馬雅可夫斯基的詩歌《高興得太早》,這首詩是未來主義者對新舊藝術分離的必要性的聲明,馬雅可夫斯基呼吁要鏟除過去封建藝術的殘余,這得到了列寧和盧那察爾斯基的警告。
盧那察爾斯基的警告并沒有阻止未來派加緊控制蘇聯(lián)藝術的活動。1919年1月,在庫什納的領導下,一個名為“共產主義—未來主義者(簡稱‘康夫’)”的組織在彼得格勒成立。康夫社是第一個無條件歡迎新政權并立即響應其號召的團體,在康夫的宣言里寫道:“所有形式的生活、道德、哲學和藝術都必須在共產主義的基礎上重新創(chuàng)造。沒有它,就不可能進一步發(fā)展共產主義革命。” ①“必須立即開始建立自己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tài)。必須無情地打擊資產階級過去所有虛假的意識形態(tài)。必須將蘇聯(lián)文化教育機構置于新成立的共產主義文化意識形態(tài)的領導之下。” ②康夫聲稱未來主義是官方文化政策的新權力,而他們則是革命前立體未來主義的直接延續(xù)者。因此,康夫(和立體未來主義者一樣)呼吁“無情地打擊資產階級過去所有虛假的意識形態(tài)”。在面對“康夫”要求在黨內獨立地位的要求時,地方黨委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這一建議。1919年5月,列寧公開批評未來主義藝術,他說:“……很多時候,最荒謬的鬼臉都被當作新的東西來呈現(xiàn),而任何不自然和愚蠢的東西都被當作純粹的無產階級藝術和無產階級的文化。” ③1921年康夫社解散,未來主義走向衰落。
然而很快未來主義者們的轉機就來了,列寧在1921第十次黨代會的演講中提出了新經濟政策,出版業(yè)的形勢就此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1921年11月,蘇聯(lián)人民委員會允許在沒有政府補貼的情況下成立私營和合資出版企業(yè),導致文學市場上出現(xiàn)了大量低俗和反蘇作品。為此蘇共于1922年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協(xié)調文化活動與政府保持一致,最初的干預措施就是給予各文學團體作家在國家出版社上發(fā)表文章的機會。政府愿意對各個作家團體做出讓步,資助他們出版作品,以便為成立一個親蘇作家團體做好準備。1922年3月5日,馬雅可夫斯基的詩《開會迷》得以在《消息報》上發(fā)表,這也是未來主義者第一次能夠在《消息報》上發(fā)表文章。列寧對馬雅可夫斯基這首詩的主題表示贊揚:
“昨天我偶然在《消息報》上讀了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政治題材的詩。我不是他的詩才的崇拜者,雖然我完全承認自己在這方面外行。但從政治和行政的觀點來看,我很久沒有感到這樣愉快了。他在這首詩里尖刻地嘲笑了會議,諷刺了老是開會和不斷開會的共產黨員。詩寫得怎么樣,我不知道,然而在政治方面,我敢擔保這是完全正確的。” ④
黨的決定以及列寧對馬雅可夫斯基認可的公開聲明,使得未來主義者們重新以一個有組織的團體的形式出現(xiàn),但他們有了一個新的名字——“左翼藝術陣線”(列夫)。
二、列夫派的“紀實文學”理論
《列夫》雜志只發(fā)表了七期就停刊了,列夫派也解散了。不過很快列夫派就重整旗鼓,創(chuàng)辦了《新列夫》雜志,馬雅可夫斯基被任命為責任編輯,編委會的成員得到了擴充,新加入的有拉維尼斯基、帕斯捷爾納克、羅琴科、斯特潘諾夫、什克洛夫斯基和艾森斯坦等。《新列夫》開始推行新的理論,也就是“紀實文學”理論。在1928 年《新列夫》的元旦賀詞中,特列季亞科夫進一步闡明自己的文學觀念:
“列夫明確地、不妥協(xié)地在事實的文學和照像式地反映生活中得到鞏固,我們把這一點列為自己的成績……我們說,思想意識不存在于藝術所采用的材料之中。它存在于這種材料的加工方法之中,存在于形式之中……列夫對一切具有美學麻醉功能的藝術都表示懷疑。列夫主張采用準確記錄事實的方法。列夫認為非臆造的事實文學高于臆造的美文學,并注意到回憶錄及札記的需求量在活躍的讀者層中正在增加。” ⑤
同年,列夫派頒布了自己的文學綱領,完善了特列季亞科夫的觀點:“列夫的文學工作重心正轉向日記、報道、采訪、小品文之類報紙工作中使用的‘低級的’文學形式;列夫把報紙工作視為文學工作中最現(xiàn)代化的形式……因此列夫反對藝術的文學,贊成事實的材料……因為要能有條理地描述某一事件……恰恰需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學素養(yǎng),這自然就是通向文學技巧的途徑。” ⑥
列夫派一再強調,“紀實文學”根本不是理論,而是他們所支持的文學現(xiàn)象。布里克于1927年寫道:“你必須熱愛事實,你必須精確而尖銳地區(qū)分事實和虛構,你不能把這些事情搞混。”作為列夫派的主要理論家之一,他認為“編輯事實”比虛構的文學情節(jié)要長得多。另一位藝術家特列季亞科夫認為,藝術總是扭曲真實的“材料”,而“現(xiàn)在主要對最原始形式的材料——回憶錄、編年史、簡介、文章、報紙”。因此,“紀實文學”基本上延續(xù)了“藝術生產”理論的概念,否認對現(xiàn)實的任何扭曲。
根據(jù)列夫的觀點,小說中的人物應該是真實的人,而不是虛構的人物。列夫派認為小說的體裁已經過時了,因為它們未能滿足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的要求。他們將被“人類文獻”(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документ)所取代。特列季亞科夫寫道:“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由時代的經濟性質所決定的寫作方式。綺麗的形式對于封建主義是典型的,而在我們這個時代,它不過是一種風格上的摹擬之作,是不善于用今天的語言表現(xiàn)的一種征候。我們不必等待托爾斯泰們,因為我們有我們的史詩。我們的史詩就是報紙。” ⑦事實上,列夫派理論家們呼吁用新聞代替文學,最好是用紀錄片。
在戲劇《防毒面具》中特列季亞科夫進一步發(fā)展了“紀實文學”理論,在這部作品中,他并沒有以現(xiàn)有的方式呈現(xiàn)虛構的情節(jié),而是選了一個真實的故事來說明社會現(xiàn)狀的變化。特列季亞科夫認為,在戲劇中使用真實的事實不僅可以喚起人們的情感,還可以為理性的社會批判提供機會。該作品將事實和情節(jié)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是“紀實文學”理論在戲劇上的成功。除此之外,特列季亞科夫的長詩《怒吼吧,中國!》后來被改編成戲劇并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怒吼吧,中國!》是特列季亞科夫以發(fā)生在中國的真實故事為題材寫的。這首長詩的音節(jié)是以北京街頭的吶喊和音響聲為基礎。此外,特列季亞科夫詳細描述了他在城市街道上看到的細節(jié),大部分詩歌都是由細節(jié)構成的,這首詩是特列季亞科夫將詩歌技巧與“事實文學”結合起來的典型例子,這也使得《怒吼吧,中國!》成為“紀實文學”理論的一個實例。
作家瓦爾拉姆·沙拉莫夫對列夫派的理論非常感興趣,并在其回憶錄中記錄了他是如何看待“紀實文學”的。《新列夫》的編輯特列季亞科夫在一次與沙拉莫夫的會面中談到了關于對公寓的描述:
“我們將描述這所房子,我們拍攝了兩百三十五套公寓的照片。我檢查過了,我需要強調的是……當你走進一個房間的時候,你首先看到的是什么?”
“鏡子。”我回答。
“鏡子?”特列季亞科夫問道,思考片刻后,“不是鏡子,是容積。” ⑧
因此,完成某一項任務的方法完全取決于執(zhí)行者的觀點——一個人首先看到物體本身及其反射,另一個人看到空間的體積和組織,這就增加了“紀實文學”的主觀性。
列夫派對電影和攝影的關注也不是偶然的,還有什么能比攝像機更能捕捉到事實呢?“攝像機鏡頭——社會主義社會中文化人的瞳孔”這是羅琴科說的,他是創(chuàng)新攝影師、畫家、裝飾家和設計師。1924年,羅琴科開始進入攝影行業(yè),他的第一批有名的作品是肖像照(馬雅可夫斯基、阿謝耶夫、母親的肖像等)。作為一名攝影師,他在形式上追求創(chuàng)新,經常嘗試令人想不到的角度進行拍攝,通常是俯視或者仰望,其構圖手法讓他名聲大噪。在20世紀30年代,羅琴科開始進行公共宣傳,特別是為《蘇聯(lián)建筑》雜志拍了很多照片,后來又開始畫畫。在列夫時,羅琴科仍然是該先鋒運動的主要攝影師,他在《新列夫》倒數(shù)第二期發(fā)表了一篇文章《警告》,敦促不要“戀物癖”。在他看來,這不僅是不必要的,而且對攝影有害。就像馬雅可夫斯基在詩歌中說的那樣,羅琴科鼓勵只做高質量的工作,避免出版廢片:“拍攝事實就像描述事件一樣簡單,但問題是,簡單的拍攝事實就能掩蓋繪畫,簡單的描述事實就能掩蓋小說。你們這些事實迷卻很難寫出來。同志們,你們很快就會分不清,哪邊是左,哪邊是右。” ⑨對羅琴科來說,簡單的拍攝事實不僅不利于攝影中的文化和文化價值,并且這種抽象的理論對實踐者構成了巨大的危險。
三、“紀實文學”理論的影響
列夫派的文學主張無疑是一種先鋒理論,持續(xù)時間短暫。不過特列季亞科夫在《新列夫》主張的紀實文學(當然包括紀實戲劇)對西方藝術的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國學者陳世雄在其文章《從特列季亞科夫看“列夫”的悲劇》中詳細梳理了20世紀西方劇作家的紀實性戲劇,并指出:“特列季亞科夫和‘列夫派’其他人所主張的‘紀實文學’是有其合理因素的”,該理論“對蘇聯(lián)戲劇,乃至對整個現(xiàn)代歐洲戲劇的貢獻都是不可否認的”。我國學者劉天藝也指出,列夫派強調“真實”的觀念對后來的藝術創(chuàng)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電影領域,與‘列夫派’關系密切的蘇聯(lián)電影家維爾托夫在同一時期提出了‘電影眼’理論,其1929年的紀錄片《持攝影機的人》中出現(xiàn)了展示攝影者拍攝過程的畫面。這種手法深遠地影響了以后的電影敘事理論……在文學領域,敘事者介入敘事、有意強調文本虛構性等手法的例子更是不勝枚舉。”此外,亞歷山大·羅琴科經常在雜志上發(fā)表他對攝影的見解,這也是當今世界攝影領域正在研究的材料。
四、結語
盡管列夫派在當時逐漸衰落并走向毀滅,它的藝術遺產卻沒有失去其重要性。它的思想主張對20世紀20年代的藝術創(chuàng)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列夫派的雜志為才華橫溢的詩人、作家和視覺藝術實踐者提供了發(fā)展空間,影響了世界攝影、電影、繪畫、裝飾藝術和廣告設計的形成與發(fā)展。
注釋:
①②③Людвигович А.,Советс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 за 15 лет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ация,Огиз-изогиз Москва Лениград,1933,p.159.
④中共中央編譯局:《列寧全集(第三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頁。
⑤⑥⑦翟厚隆:《十月革命前后蘇聯(lián)文學流派(上編)》,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196頁,第257-262頁,第259-260頁。
⑧Шаламов В.,Новая книга: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Записные книжки.Переписка.Следственные дела, Издво Эксмо,2004,p.21.
⑨Родченко А.“Предостережение”,Новый Леф, 1928,No11,p.37.
參考文獻:
[1]陳世雄.從特列季亞科夫看“列夫”的悲劇[J].戲劇(中央戲劇學院學報),2015,(05):5-17.
[2]翟厚隆.十月革命前后蘇聯(lián)文學流派 上編[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
[3]岳鳳麟.淺談列寧對未來主義的論述[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04):35-41.
[4]劉天藝.“列夫派”作家筆下的中國革命文學——特列季亞科夫與他的《鄧世華》[J].文學評論,2022,(05):94-102.
[5]張捷.十月革命前后蘇聯(lián)文學流派 下編[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
[6]Воинова Ю.Г.ЛЕФ и конструктивизм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культуры 1920-х гг[J].Молодежный вестник СПБГИК,2019,(12):145-147.
[7]Житенев А.А. Дискурс ошибки и репрезентация революции в материалах журнала"Новый Леф"[J].Ивестия смоле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18,(03):60-71.
[8]Кириллов Н.М.Журналы"Леф"и "Новый Леф":становление языка ранней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и кино-критики[D].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2006.
[9]Сватухина Е.Н.Журнал"Новый ЛЕФ"как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источник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Левый фронт искусств"[J].Культура.духовность.общество,2021,(01):62-70.
[10]Сватухина Е.Н.К вопросу о причинах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выпуска журнала левого фронта искусств ЛЕФ[J].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2014,(04): 39-41.
[11]Ярослав З.Д.Периодические издания ЛЕФ:история,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D].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м.А.С.Пушкина,2012.
作者簡介:
武淑暉,女,漢族,山東濰坊人,哈爾濱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羅斯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