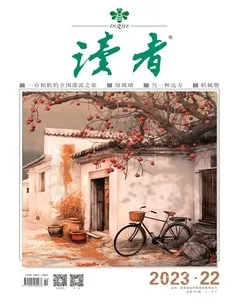機械僧
☉伊 瞇
1
自我記事起,老家屋后的岑山上就有一座不大起眼的、用白色石頭壘成的無名寺,看不出年代,大抵算是古剎。寺中常年只有一個僧人,法號叫作“隨空”。
家鄉那一帶的山間零星散布著一些野溫泉,一年四季都汩汩地冒出淡白色的霧氣。岑山上最大的溫泉就在那座無名寺廟的旁邊,挨著一條清澈的溪流。溪流里有一種桃葉魚。天氣剛暖起來,我就背著簍子和自制的釣竿,跑到岑山去釣桃葉魚。
我專心致志地拋竿,不知道是桃葉魚瞧不起我的面團釣餌,還是今天運氣不佳,始終沒有魚上鉤。我蹲在溪邊的石頭上,唉聲嘆氣。這時隨空從寺里緩緩走出來,看著我的魚竿。
村里的人都知道隨空是機器人,還是如今見不到的型號,因此也看不出年紀。在我的記憶中,他的模樣也不曾改變過:普通青年男子的樣貌,淡然的神情,總穿著那身因洗過太多次而顯得很舊的灰衣。
隨空先開口說話了。他的聲音十分好聽,語氣也很溫和,大概因為揚聲器有些舊了,帶著一種仿佛從遠處傳來的模糊。“現在是桃葉魚產卵的時候,過一陣再來釣吧。”
我本以為他想勸我不要殺生,反駁的話已經滑到了舌尖,最終只好氣哼哼地放下釣竿往石頭上一靠,皺起眉頭,說:“過一陣我就要開學了!”
陽光曬在光溜溜的肚皮上,烤得我五臟六腑都熱乎乎的。我拍著肚子,打了個滾,得意揚揚地說:“你們機器人不懂曬太陽的舒服吧。”
隨空只是笑了笑,腳步輕盈地走到我身邊,在石頭上坐下來,問道:“那你的作業寫完了嗎?”

我頓時心情郁悶起來。隨空似乎為提起作業的事情感到有些抱歉,問我要不要去寺里喝茶。我當然同意。茶嘛,淡淡的,沒什么好喝,但隨空會做極好吃的點心。
我嘴里塞著又軟又甜的栗子糕,問道:“隨空,你當和尚之前,是在城里的點心鋪工作嗎?”隨空笑著搖了搖頭。我到底沒有忍住好奇心,又一連串地發問:“你難道是專門的和尚機器人?誰造了你?你們機器人到底會不會做夢?隨空,給我講一講城里的事唄。”
沉默了一會兒,隨空倒了一杯茶輕輕推到我面前,他的面孔在霧氣的后面時而清晰,時而模糊。
2
制造我的人是一位法號為“圓一”的禪師。他似乎原本是位非常了不起的程序員,小時候得過許多獎,后來考入最好的大學。但不知為什么,他在25 歲時突然選擇出家。制造我的時候,圓一禪師40 歲,他的父母在那一年相繼離世,他們始終沒有理解或原諒他。
圓一禪師的初衷,是借制造我,看到一個無限接近于某種理想修行境界的可能性。從理論上來說,我沒有七情六欲,被設定了普度眾生的行為目標,并且一出生便通曉所有佛學典籍。他又讓我學習無數修行者與高僧的問答記錄,并且接待無數前來與我辯論佛法的客人,這些經驗不斷豐富我的神經網絡。我想我也因此總有一天可以“證得”了。
有一日,圓一禪師問我:“我能教授的知識,你都已經掌握了。今后想要做什么?如果想繼續和我修行,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我不知道還能如何優化你了。”我回答道:“我想盡可能幫助更多的人類。”
圓一禪師便建議我去城里的醫院工作。他還告訴我,現在已經有給人工智能使用的高級感官與情感集成模塊,迭代了好幾次,他也確定技術非常成熟,甚至親自做了完善。他問我想不想安裝。我想,先前他大概是為了保證實驗不被我不必要的情緒打擾,所以不曾給我安裝這些多余的東西。如今,他大概是對我的修行死心了。不過,這樣的問題,我,一個機器人,居然可以得到選擇的權利——當時我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是多么特殊的待遇。
這樣的機會擺在眼前,我當然毫不猶豫地回答“想要”。禪師面無表情地敲開面前的木魚,里面露出一枚指尖大小的金燦燦的芯片。他將我的頭顱打開,把芯片插進似乎是預留好的槽里。一瞬間,奇怪的感覺出現了。仿佛電子在無序地流過我的整個身體,我同時感到熱和冷。香爐即將燃盡的氣味和后廚齋飯的煙火氣將我輕輕裹住,這讓我的傳感器顫抖起來。
那一刻,我看禪師的目光再也不一樣了,我深深地鞠了一躬,低聲說:“謝謝師父。”但內置的詞典不斷地閃出另一個人類兒童常用的詞。那個詞仿佛也有溫度,滾燙而沉重地壓在我的舌尖,這讓我困惑起來。這種感受是如此強烈和真實,我惶惑地張開嘴,抬起頭注視著圓一禪師。禪師也凝視著我,這可能是我第一次理解了人類的目光。我幾乎敢肯定,我對他而言也不只是一個機器人了。
禪師伸出手摸了摸我的頭,那種溫暖的電流又襲來了,我的眼睛第一次流出了液體。那不過是內部降溫的化學溶劑罷了。這個設計的意義何在呢?方便人類觀察機器人的情緒嗎?不管怎么說,流淚確實是一個讓我感到極度幸福的過程。
告別禪師以后,我在城里最大的醫院工作,照顧人類,觀察人類,其間我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類個體。不過,即使我有感情芯片,我也沒能和人類交上朋友。有些人類同事和病人對我很友好,并不曾讓我覺得遭受了居高臨下的輕視,有些人可以說是過于客氣了。但不知為何,作為機器卻能夠思考的我,令我周圍的人感到不那么舒服。有時候他們會放松警惕,和我開玩笑,或是不小心將我當作自己人閑聊起來。但猛然間,一種冰冷尷尬的遲疑會在他們的眼睛里閃爍,仿佛他們對錯誤的對象投入了錯誤的感情。
有一個下午,因為工作過于忙碌,我來不及充電,差點在走廊里休眠。我匆忙走進了小真的房間請求借一點電。那時候小真已經懷孕3 個月了。孩子當然不是她自己的——小真和我一樣都是機器人。不過,比起禪師竭盡一生心血制造的我,量產的小真在設計上要簡單粗糙得多,她的功能其實只有一個:代替人類懷孕。那些受精卵會在小真恒溫的人造子宮里待到足月,然后被取出來。在這個過程中,小真每天要輸很多營養液,大部分時間她都一個人躺在孕育室的床上。
我們第一次相遇的時候,小真正看著窗外輕聲唱歌。我知道,有無數首旋律輕柔愉悅的胎教音樂和大量的故事書存儲在代孕機器人的芯片中,可以隨時播放。但小真在唱一首我沒聽過的歌。過了很久她才告訴我,那是她自己創作的歌,叫作《小真之歌》。
我會在午休時把醫院花園里的花偷偷地摘下來,湊成一束,拿到房間里擺在小真床頭。我學習過人類所有的笑話和名人寫給戀人的情書。我使出了從未有機會使用的各種技能,但小真并沒有愛上我。她明白我在做什么之后,很遺憾地告訴我,代孕機器人只搭載了與母性相關的感情和最簡單低級的擬人情緒,其他信息一般的通用存儲裝不下,客戶也用不著,只會增加成本,節外生枝。盡管如此,我對小真的感情并沒有因為注定的不匹配而有絲毫改變。
代孕機器人的開發公司很多,所以產品迭代自然很快。擬人的設計趨勢已經過了熱潮,而且據說客戶對于太像“另一個女性”的代孕機器人,實際上會產生一種復雜的敵意。最近流行的代孕機器人看起來已經不太能稱之為人了,大概更接近于一個連接電腦的有輪五斗柜。小真這種一次只能孕育一個嬰兒的擬人型號早已停止更新,按說現在不會再有用戶選擇了,這最后一次代孕的機會是小真主動向院長爭取來的。畢竟她的經驗豐富,而且妊娠與取胎可以不必顧惜母體的損壞程度——橫豎這是她最后一次服役了。
在我看來,這個職業對小真著實沒什么好處。她幾乎沒離開過醫院,那些嬰兒在她的身體里寄居,然后永遠離開,和她再無聯系。她從來沒有哪怕一秒鐘是一個真正的母親。我照顧過的病人,常常會向我道謝,對我傾訴心中的恐懼和寂寞。似乎因為我是機器人,一些不能對家人傾訴的私密的念頭,對著我也可以毫無顧慮地說出來。但小真從沒得到過這些,她并不在意。小真不僅認為自己幫助了許多人,并且在這個過程中極度幸福和期待。
隨著胎兒逐漸長大,小真偶爾會變得憂郁不安。她會陷入沉默,低頭凝視著自己笨重膨大的硅膠身體,乳白色半透明的皮膚下面,輸送營養的纖細管道和胎兒揮舞的小手隱約可見。我觀察著她,思考著由人腦轉換信號分離出的母性究竟是多么復雜沉重的信息,居然占滿了小真全部的內存。
夏天的時候,我熱衷制作精巧的機械給小真解悶。小真尤其喜歡我做的扇子,打開以后只能看到一片幕布,用手撥開大幕,扇面上就跳出我穿著大褂的影像,神情呆板地說著兩個世紀前的相聲,要么就是表演早已過時的室內喜劇。我也和小真一起在醫院的花園里曬過太陽。我把手覆在小真的肚子上,被曬熱的硅膠向我手掌的傳感器傳輸著陽光的余溫。孩子的小腳有力地踢著我,急不可耐地要看外面的世界。強烈的欣喜和悲傷混合在一起,一瞬間占滿了我的全部內存,像兩個同時啟動的沉重程序。而小真只能困惑地觀察著我的表情。
小真“分娩”的那一天,我像一個人類父親般焦灼地在手術室外踱步。手術的時間不會很長,特制的刀具將謹慎地剝開柔軟的內膽,溫暖的人造羊水會緩緩流入冰冷的容器中。這個過程既不血腥,也無須麻醉,像工廠車間的流水線作業一樣。小真一直十分清醒,全程符合一個合格的機器人的標準反應。小真會請求抱一次嬰兒,然后等待著被拒絕,但這一次醫生同意了:“就抱一下啊,家長馬上進來了。”于是,小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抱住在她身體里待了10 個月的嬰兒。在這個短暫得如同眨眼的瞬間,那個小小的人類嬰兒無意識地握住小真纖細的拇指。我將在小真的程序里看到她最幸福的記憶,然后它也變成我記憶的一部分。
醫生很快就托著清洗得干干凈凈的嬰兒給他滿臉喜悅的父母看。那個粉紅色的嬰兒看起來十分健康,哭聲有力。他是否會記得那首《小真之歌》呢?他未來100 年的人生中,還會再一次和孕育他的小真相遇嗎?
最后一個問題我很快就知道了答案。
3
小真被送回工廠拆卸的前一天,我偷偷溜進倉庫,想帶她逃跑。但小真不肯。我苦口婆心地勸她,離開醫院之后,她就會看到整個世界是如何紛繁奪目,也一定可以找到“孕育”嬰兒之外的意義。
她只是緊緊地握著我的手,說:“你講的那些外面的故事雖然精彩,可是你這么聰明,怎么就不肯接受我只是人類子宮的替代品,是一個醫療器械,內存根本運載不了你那樣完全的感官和情感插件這一事實呢?那些注定在我感知范圍之外的概念,對我來說都毫無意義。對我來說唯一有意義的一件事,我再也不能做了。可是隨空,我的一輩子,我和孩子在一起的時光,從此就沒有人知道了。我不甘心。”
我流著人造的眼淚,告訴她我會永遠記得我所知道的她。小真在黑暗里看著我,要我發誓。我發了誓之后,小真鄭重地說:“我相信我是被那些孩子愛過的。也許他們不會記得,但是我被你愛過,你會記得,這就夠了。你的愛也是組成我存在的一部分,我不會消失了。”
一連多日,我都陷入前所未有的悲傷。我真是懷念沒有安裝情感模塊的時候。我不知所措地把自己關在宿舍里,躺著一動不動。如果移除情感模塊,這些痛苦自然會不復存在,但經過一遍遍地分析,唯一符合邏輯的結果是,我不想移除它。令我過載的痛苦,它的內核似乎是另外的東西,我的系統中未經定義的東西。我更加困惑了。
我到底還是從床上爬了起來,離開醫院,回去找圓一禪師。我不知如何向他解釋,一旦裝載過那枚小小的芯片,我就無法再做出拔掉它的決定。禪師聽著我斷斷續續的講述,嘆了一口氣,垂下眼睛說:“我在這里修行了一生,也不敢說達到了無我的境界。而你只要自己拔下一枚芯片,一切渴望和欲念、一切喜怒哀樂便能瞬間消失。我之前誤以為我們這些修行的人類,如此殫精竭慮,斬斷對親人的依戀,只為達成機器人的狀態,所以才制造了你。事實證明,我錯了,而現在我終于明白自己錯在哪里了。”
我又想起小真。如果拔掉芯片,我便不能再想起那種無序的電子流遍全身的溫暖。為了讓小真永不消失,我的感受也必須一直保存下去。如果缺少了這部分,就違背了我的誓言。總有一天我的零件會老化,我會停止工作,但我的記憶可以通過網絡分享給其他的機器人。
我走到岑山的時候已是冬天,這樣的溫度耗電太快,我怕突然斷電在曬不到太陽又沒有人煙的地方跌倒,于是就走進了溫泉想暖一暖。黑暗中能聞到叢莽和新漲的雪水的味道,以及森林中偏僻村莊的氣息,我在隆隆的水聲中想象桃葉魚在身旁的溪流里靈活逃走的樣子。我像被初次啟動之時一樣赤裸著站在獵戶座之下,站在山河之間,時間像星光一樣處在凝固與流動的分界點。
我從未如此強烈地感到自己既是人類,又遠離人類。從此,我再也沒有離開這座山。
4
天色漸漸暗下來,隨空站起來,為耽擱了我回家吃飯而道歉。他從案旁的架子上拿了一件小東西送給我。那是一把不起眼的舊折扇。他看著我,微微一笑,說:“不知道你的老師會不會夢見考卷,不過這是我做過的一個夢。”
我怕回家晚了要挨罵,一口氣跑到山下才將折扇緩緩打開。扇面上微暗的叢林顫動起來,我吃了一驚,用手指輕輕劃過扇面,那枝葉便一層層分開來,一群鳥飛起掠過了明亮如飴糖的天空。夕陽里一對母子正牽著手在樹下玩耍,旁邊是負手而立的隨空。
后來我終是考去了大城市,站穩腳跟后,舉家遷進城里。前幾年,父母嫌用不慣城市里的“高科技”,提出要回老家。我和媳婦都不會做飯,但吃自動料理機做的菜也覺得夠了,小孩子有精通所有學科知識而且絕不發火的機器保姆照顧,讓父母總感到全然沒有用武之地,很不自在。有時我在公司加班回不來,就打開全息影像遠程哄哄孩子,結果總嚇著我媽,讓她以為鬧鬼。老式汽車在這里不能上路,父親已經過了考高速代步機執照的限制年齡,于是他寧可走路。這里散步又沒什么風景,確實悶得很。于是,父母再次提出要走,我就沒有堅持挽留。
再回到岑山,已經是我三十五歲的秋天。母親說:“這邊春天發生了一次小小的地震,寺廟倒是沒有塌,不過隨空前兩年就因為關節老化,幾乎不能動了。今年我還沒上去看過,他怕是早就不在了。”
我怔了怔,到儲物間翻了一會兒,拿著積了塵土的魚竿和小桶,對母親說:“我去釣桃葉魚。”母親說:“現在哪里還有桃葉魚?”我仍是走出門去。
山頂無名的寺廟還是老樣子,并沒有破敗的跡象。寺里忽然斷斷續續地傳出了女孩子溫柔的歌聲,像搖籃曲,讓我大吃一驚。我推開笨重的寺門,看到一臺普通的家用清潔小機器人正在認真地掃著落葉。它停頓了一下,調了調自己身上的旋鈕,仿佛在讓記憶的頻道更清晰一些,然后又默默地掃起黃葉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