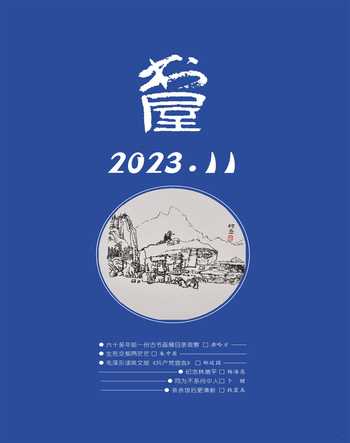中西醫學交流的使者愛德華·胡美
魯建文
愛德華·胡美,不僅是一位較早將西方醫學帶到中國來并開辦醫院的美國醫生,還是對中國醫學進行過潛心研究并將中醫之道帶回美國進行交流傳播的先驅。前者,由于他所始創的湘雅醫院和湘雅醫學院至今依然屹立于湖湘大地而為人們所熟知,而后者知道的人卻很少。
胡美1876年出生于印度。由于父母長期在印度傳教,1901年,他從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獲得博士學位之后,便回到印度,創立了當時孟買唯一一家由美國人開辦的醫院,決心在這里發展自己心愛的醫學事業。但正當他的事業打開局面之際,他收到了正在中國調查的美國雅禮協會畢海瀾博士的來信,邀他到中國湖南去發展,這原本是胡美畢業時雅禮協會的一個安排,只是當時他以父母均在印度為由拒絕了。這次,畢海瀾來信說中國比印度更需要他,并告訴他:“湖南人很聰明,有教養,富有創造性。他們一定會歡迎一位熟練的西方醫生來創辦一所現代醫院,而且不要多久你就能夠開辦一所大學醫學院。”這一點正契合胡美的人生追求,他毅然決定改變自己的人生規劃。1905年,他懷著忐忑的心情來到了中國。在當時封閉保守的環境下,他通過學習中文,“入鄉隨俗”,很快在當地站住了腳跟。次年,他就在長沙西牌樓街辦起了雅禮醫院,后來又創辦了雅禮醫學專科學校,更讓他未能預料的是他后來與中醫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成為最早踐行中西醫學結合治療疾病的“洋醫生”。
胡美與中醫學結緣,緣于一張簡單的中醫病理解剖圖。醫院開辦不久,他收治了一位中年女性患者,患者出身于大戶人家,讀過不少中醫學著作。來到醫院后,她向胡美醫生介紹說自己腹部爛有一個口子,已有數月之久,看遍了長沙城所有知名的醫生,都不見好轉。接著,她便交給了胡美醫生一張自己根據中醫理論繪制的簡單的病理解剖圖。她在上面附言說:“吾病有因四:其一在于腎,其一在于腹股溝,其一在于脊椎,其一在于腸,請君診斷四者之中孰為真正的病因。”經過檢查診斷后,胡美決定一方面給她進行分階段的手術治療,另一方面接受了她自己提出的中醫食療方案。這樣雙管齊下,她的病情日見好轉。可惜的是,已經看到希望的她,卻在第四次手術后,由于沒有嚴格遵守醫囑,急于起身接待前來探望的親友,最終死于胃腸意外出血。她去世后,胡美倍感遺憾,望著那張留下來的解剖圖,他開始認真思考:中國的傳統醫學不學解剖,不做實驗,憑什么探尋病因,作出診斷?一個未經專門訓練的女性,僅憑閱讀醫學著作,也能繪出這樣一張病理解剖圖,且對自己的病因能說出一個大概,奧妙究竟在哪里呢?
正當胡美對中國醫學產生興趣的時候,醫院里又送來了一位患傷寒的女孩。她的母親陶太太看上去知書達禮,頗有涵養,聽了胡美醫生的治療意見后,感到與東漢名醫張仲景著作中的方案有許多相似,心里很是信服。為了能給胡美醫生的治療提供一些幫助,她急忙回到家中找來了張仲景的專著《傷寒論》,送給胡美醫生參考。《傷寒論》是中國古代最有名的醫學著作之一,書中關于傷寒致使患者出現食欲不振、畏寒頭痛、鼻孔流血、發熱等癥狀的記述,以及不能猛藥泄瀉,應以豬膽汁摻醋灌腸和冷水浴降溫治療的記載,讓胡美醫生感到非常佩服。他以為,就是一千多年后的西方醫學家奧斯勒對傷寒的描述也不過如此,可見這位長沙太守的偉大。他發現,東西方兩位醫學大師都曾在著述中提示,要特別注意兩周后患者癥狀的變化情況,這是患者能否被治愈的關鍵期。結果不利癥狀還是接踵而至,胡美醫生最終沒能挽留住這位女孩的生命,但在這位女孩的救治過程中,他得到了一個意料之外的收獲,就是陶太太送來的張仲景的《傷寒論》。從此以后,他便開始了對這部中國醫學經典的研究。
不久,一位姓陳的先生來醫院請胡美醫生出診。這次出診,對正在探究中國醫學的胡美觸動不小。陳先生是到日本留過學的,比較信任西醫,他太太已懷孕四個月,突然腹痛嘔吐,粒米難進。做過檢查后,胡美醫生認為要治好陳太太的病,唯一的辦法是進行手術取出腹中的胎兒。否則,患者只會中毒越來越嚴重,不僅嘔吐難止,還會危及生命。對胡美醫生的治療方案,陳先生表示贊同,但其父母卻堅決反對。無奈,陳先生只好再去找城里最有名的張醫生。據說,張醫生是張仲景的后裔,醫術高明,治好了不少疑難雜癥。張醫生來后,經過仔細把脈,開了三劑中藥,并叮囑了一些飲食調理的要求。然后,他對陳先生說:“請放心,會好起來的。”果然,剛服一劑藥,陳太太的嘔吐便基本打住。三劑藥服完之后,病情便徹底好轉。六個月后,陳太太生下一個白白胖胖的男孩,一家人高興得無法形容,逢人便夸張醫生藥到病除。胡美醫生得知這一消息后,一個又一個的問題在他的腦海中浮現:張醫生到底開了什么特效藥給陳太太服了?中醫藥材中,那些烘干的根莖花果、蟲殼獸皮,哪來這么大功效?
面對一連串的疑問,胡美醫生決定對中醫藥材進行一番考察。一天,他在中國醫生侯先生的陪同下,來到了城中心的一家藥店。藥店的墻上供奉著一尊藥王孫思邈的像;柜臺后面的屜柜內分別裝著樹皮草根、干花枯葉、蟲末獸粉之類的東西,氣味濃郁;旁邊的貨架上擺滿了大小不一的壇壇罐罐,里面裝的全是一些他叫不出名字、據說能滋補身體的名貴藥材。他一邊看,一邊聽侯醫生的介紹:有用來治療眼痛的熊膽,有能止嘔吐的虎胃,有用來醫治肺癆的水獺肝,還有“能治百病”的犀牛角和治療風濕的蛇肉。侯醫生一一道來,無不讓他感到新奇。他發現這些藥材,有些與西方醫學在原理上還頗有相通之處,如用含碘豐富的海藻治甲狀腺腫大,用脂肪豐富的魚肝治肺結核,他仔細琢磨著這些中藥所含的成分,深深地感受到中國醫學的魅力。打這以后,他不僅耐心地研究張仲景的《傷寒論》、王叔和的《脈經》,還開始翻閱中國的藥典,一有時間便到城里的藥店去轉,了解中醫藥材的藥理藥性,在給患者看病時,除用西醫設備進行檢查外,也學著把起脈來。
在探究中國醫學的過程中,胡美醫生除研究傳統經典著作外,還常與中國醫生進行交流。城里一位姓梁的布政使病了,下肢浮腫,十分痛苦,家里人急得團團轉,請去了一位姓王的老中醫,又來請胡美醫生。胡美醫生以為,這是自己與中醫進行交流的極好機會,于是立馬趕去。看到童顏鶴發的王老先生后,他便讓其先為病人把脈問診。王醫生經過一番細心的望聞問切,便作出了診斷,說梁先生患有嚴重的腎臟疾病。這時,胡美醫生才上前為梁先生量體溫、聽心肺、測血壓,并吩咐助手趕緊取樣回醫院化驗尿液。做完這些檢查,他對王老先生說:“我傾向于認可您的結論,不過最終診斷還得等化驗數據出來。”不等多久,化驗結果送來了,他對王老先生不用任何設備設施便能作出與自己同樣的診斷感到由衷佩服。他隨即誠摯地邀請王老先生去醫院實驗室參觀,感受現代西醫的不同。王醫生沒有應邀,只是說他希望一定不要讓我們的學生忘記了自己祖先的脈理與醫道。在胡美醫生的再三邀請下,王老先生后來每個學期來校為學生講授一次中國醫學理論,這不僅讓學生受益匪淺,也給胡美醫生了解中國醫學之道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隨著研究的深入,胡美對中國醫學有了較深的理解。他不僅在治療疾病的過程中不時會用上中醫的診療方法,而且在國際刊物上發表了大量有關中國醫學的文章,還撰寫了《中醫之道》一書。他曾在文章中說:“受過實驗科學培養的西方醫生,起初對中國醫生抱懷疑態度。沒有解剖,沒有可供鑒定的實驗,幾千年以來有什么科學研究的依據呢?科學家們很詫異:藥店出售的藥品除了‘自古沿用這幾個字以資吹噓,是否還有可貴之處?那些龍牙、虎骨和鹿茸究竟有什么醫療價值呢?可是,自從西方的醫生以諒解和同情的態度生活在中國,他們就逐漸改變了這種看法。某些古代醫藥知識顯示出不容置疑的價值。古老的診斷和治療方法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良好的療效讓西方醫生也難以做出解釋。”他以為,中醫與西方醫學相比,雖然路徑不同,但目的與效果卻是一樣,“道一風同”,且“中國醫學和西方醫學的相遇是不可避免的”。晚年回到美國后,他便在母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專門開課講授中國醫學,幫助美國人民了解認識古老的中國醫學之道。
像胡美這樣認識了解中國傳統醫學的“洋醫生”,我想,無論在過去還是在今天,恐怕都屬鳳毛麟角。可見,他不僅擁有一種與眾不同的寬闊胸襟,更是一位懂得如何獲取比較優勢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