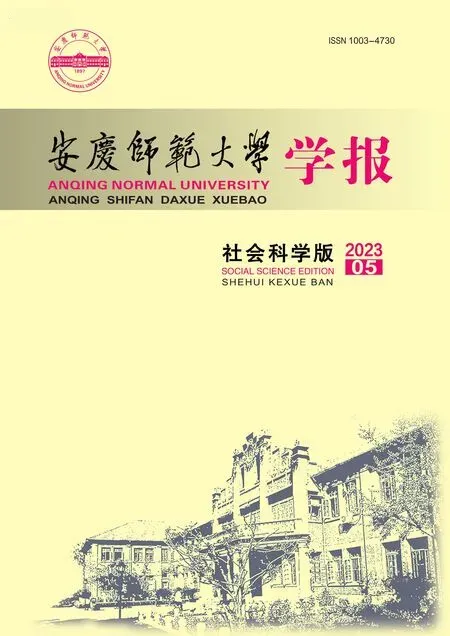“清初三大詞人”芻議:兼談顧貞觀與納蘭性德的易位
何 揚
(安慶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安徽 安慶 246011)
“清初三大詞人”的概念每見于詞評,也有研究者曾撰文探討其生成①參見孫欣婷《從清詞總集看“清詞三大家”的經典化生成》,《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事實上,“三大詞人”并非約定俗成,大略有兩種說法,一為陳維崧、朱彝尊、顧貞觀,如姜宸英《題蔣君長短句》云:
梁溪圓美清淡,以北宋為宗,陳則頹唐于稼軒,朱則湔洗于白石。譬之韶夏異奏,同歸悅耳[1]177。
杜詔《彈指詞序》也云:
夫彈指與竹垞、迦陵埒名[2]545。
一為陳維崧、朱彝尊、納蘭性德,如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云:
長短調并工者,難矣哉。國朝其唯竹垞、迦陵、容若乎[3]3472。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云:
納蘭相國(明珠)子容若侍衛,所著《飲水詞》,于迦陵、小長蘆二家外,別立一幟[4]2793。
那么,為何會出現兩種并稱現象?顧貞觀與納蘭性德的易位揭示出詞壇發展的何種規律?并稱之形成與演進又受到哪些因素影響?下文試作探析。
一、顧貞觀與陳維崧、朱彝尊并稱的原因
陳維崧、朱彝尊分別為陽羨與浙西詞派宗主,二人領袖一時,對清代詞壇產生了深遠影響,當時及后世對二者地位都有確認,曹溶云:
其年與錫鬯并負軼世才,同舉博學鴻詞,交又最深,其為詞亦工力悉敵,《烏絲》《載酒》,一時未易軒輊也[5]。
陳廷焯《詞壇叢話》則云:
詞至國朝,直追兩宋,而等而上之。作者如林,要以竹垞、其年為冠[6]。
兩家之外,也有論者將顧貞觀與陳維崧、朱彝尊相提并論,如前文所引姜宸英,杜詔之言。姜宸英的《題蔣君長短句》作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其時他與眾人飲于納蘭性德的“花間草堂”,席間諸人各賦《臨江仙》以詠紗燈圖繪古跡。姜宸英以當事人身份對與會者作出品評,明確了顧、陳、朱的三大家地位,這也是三人最早并稱。后來,杜詔于《彈指詞序》中對這一觀點有所發展,云:
迦陵之詞,橫放杰出,大都出自蘇、辛,卒非詞家本色。竹垞神明乎姜、史,刻削雋永,本朝作者雖多,莫有過焉者。……若彈指則極情之至,出入南北兩宋,而奄有眾長,詞之集大成者也[2]545。
此序作于雍正二年(1724),杜詔對顧貞觀頗多溢美,或與其“生平瓣香,實在彈指”[2]545的取徑有關。不過,聯系杜詔曾一度師事朱彝尊,“詞體為之稍變”[2]545的經歷,以及當時詞壇為浙西詞派所籠罩的背景,他認為“彈指與竹垞、迦陵埒名”,應當是在對整個詞史有著一定把握基礎上所發表的意見,非僅出于私阿。后來,《清史稿》《清史列傳》皆將顧貞觀與陳維崧、朱彝尊目為“詞家三絕”,也是沿襲姜宸英、杜詔的說法。顧貞觀能夠與陳維崧、朱彝尊并稱,原因大略有三:
其一,顧貞觀與陳維崧、朱彝尊年歲相近,為同輩人,三人創作時間主要在康熙前期。
顧貞觀從何時開始填詞,因文獻闕如難以斷定,《彈指詞》中標明時間最早的一首詞為《驀山溪》,詞題為“庚子秋題長干水榭”[2]116。“庚子”為順治十七年(1660),詞人二十四歲。顧貞觀棄詞不作是在好友納蘭性德去世后,自陳“伯牙之琴,蓋自是終身不復鼓矣”[7]385,其《大江東去》(倚樓清嘯)附記也云:“容若已矣,余何忍復拈長短句乎。”[2]445時間為康熙二十四年(1685),詞人四十九歲。顧貞觀作詞時間愈二十五載。陳維崧(1626—1682)涉足填詞時間亦難以考訂。不過,據朱彝尊《陳緯云〈紅鹽詞〉序》所云:
方予與其年定交日,予未解作詞,其年亦未以詞鳴[8]233。
序中所言訂交在順治十年(1653),當時陳維崧雖未以詞鳴世,但已開始作詞。陳維岳為陳維崧詞集作跋時云:
先伯兄中年始學為詩余,晚歲尤好之不厭[8]90。
可見,陳維崧填詞是一直持續到晚年的。朱彝尊(1629—1709)作詞初始年代在順治十三年(1656),客于曹溶幕府中,棄詞不作則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歸田后,其《水村琴趣序》云:
予既歸田,考經義存亡著為一書,不復倚聲按譜[8]339。
又據《書〈東田詞〉卷后》之“其年歿后,予詞亦不復多作”[9],可知在陳維崧去世后,即康熙二十一年(1682),朱彝尊填詞興趣大為減淡。根據上文,可以繪制出顧貞觀與陳維崧、朱彝尊的創作簡表(見表1)。

表1 顧貞觀、陳維崧、朱彝尊創作時間簡表
由表1 清楚可見,顧貞觀與陳維崧、朱彝尊創作時間主要在康熙前期,且時間跨度都比較長,這也是清代詞學云蒸霞蔚,最為絢爛的時間段之一。
其二,顧貞觀與陳維崧、朱彝尊均以杰出的成就蜚聲詞壇,三人在當時有著重要影響力。
陳維崧與朱彝尊,一開陽羨詞派,一開浙西詞派,二人地位不待多言。顧貞觀在清初也煊赫一時,其“才名驚爆海內,所傳長短句,詞壇奉為赤幟”[2]552。龍榆生《論常州詞派》云:
顧梁汾(貞觀)之《彈指詞》,陳其年(維崧)之《湖海樓詞》,皆能干之以風力,無纖淫枯槁之病。……宜、錫詞風已骎骎與浙西旗鼓相當[10]。
對顧貞觀與陳維崧,以及浙西詞派領袖朱彝尊之才力相埒作出說明。再舉一例。陽羨詞派后勁史承謙被公認為是陳維崧的繼承者,但史承豫為其《小眠齋詞》作序卻云:
(史承謙)尤精于倚聲之學,自南唐兩宋以迄昭代諸名家,靡不搜采研誦,吸其精英,而淘洗出之。高者直軋白石、梅溪,次亦不失竹垞、華峰諸前輩[11]。
序中提到的宋詞典范為姜夔、史達祖,清初詞典范則為朱彝尊與顧貞觀。
顧貞觀不僅創作成就突出,也有建派樹幟的雄心,他與納蘭性德合作編纂具有“鏟削浮艷,舒寫性靈”[12]497目的的《今詞初集》即為明證。《今詞初集》初刻于康熙十六年(1677),考慮到顧貞觀與納蘭性德在康熙十五年(1676)才訂交,又由顧貞觀《與栩園論詞書》所云:
容若嘗從容問余兩先生意指云何,余為述倦圃之言曰:“詞境易窮。學步古人,以數見不鮮為恨;變而謀新,又慮有傷大雅。子能免此二者,歐秦辛陸何多讓焉?”容若蓋自是益進[12]502。
可知此時納蘭性德仍處于習詞初始期,詞學觀尚未成熟,故《今詞初集》應當是在顧貞觀主導下完成。《今詞初集》選顧詞(二十四首)多于納蘭詞(十七首),一方面與顧貞觀之于納蘭性德亦師亦友的身份有關,另一方面,也表明顧詞相較于納蘭詞更適合作為性靈典范。
朱彝尊與顧貞觀宗尚異趣,曾直接指言二人存有歧見,如其《水村琴趣序》云:
予嘗持論,謂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錫山顧典籍不以為然也[8]339。
評王錫《嘯竹堂詞》又云:
曩與梁汾典籍論詞,典籍以拙詞近南宋人,意欲盡排姜、史諸君。余無以難。使見《嘯竹》一集,定當把臂入林,恨晚也[13]。
朱彝尊之所以如此看重他與顧貞觀的詞學分歧,并努力尋找機會來闡釋自己的觀點,某種程度上,是因為二人取徑實際上反映了清初詞壇南北宋之爭。康熙二十八年(1689),顧貞觀為侯文燦《十名家詞集》作序,云:
今人之論詞,大概如昔人之論詩。主格者其歷下之摹古乎?主趣者其公安之寫意乎?邇者競起而宗晚宋四家,何異牧齋之主香山、眉山、渭南、遺山?要其得失,久而自定[14]4543。
文中“主格者”指以朱彝尊為代表崇尚醇雅的浙西詞派,顧貞觀不滿浙派詞人效法南宋,溺于有格無情;“主趣者”指以陳維崧為代表注重性情的陽羨詞派,顧貞觀僅是拈出,并未置辭,或與該派重視主體情性,與其詞學相近有關。顧貞觀與朱彝尊皆將彼此視為對立話語者,二人觀點的交鋒博弈,是清初詞學復興進程中的重要話題之一。
顧貞觀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棄詞不作,歸隱鄉里后,仍在詞壇留下了他的身影。康熙三十五年(1696)沈時棟編成《古今詞選》,曾邀請顧貞觀、朱彝尊等人審定選本,顧貞觀后又為選本作序。可見,不論顧貞觀與朱彝尊的詞學存在何種分歧,二人在清初都是被目為宗主大家的。
其三,顧貞觀與陳維崧、朱彝尊有著相似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經歷,他們是納蘭性德府邸最為杰出的詞人。
顧貞觀、陳維崧、朱彝尊三人家族與明末政壇聯系緊密,他們都歷經社會動亂,對明清之際動蕩的歷史有著深刻記憶。顧貞觀曾祖父顧憲成是晚明東林黨領袖,陳維崧祖父陳于廷亦為東林黨人,其父陳貞慧為“復社四公子”之一。明末,幾社與復社同時并起,順治二年(1645)幾社在蘇州演變為滄浪會;六年(1649),滄浪會分為慎交社和同聲社,顧貞觀與陳維崧皆為慎交社成員,二人身上染有較為濃厚的政治色彩。朱彝尊曾祖則為明大學士朱國祚。顧貞觀與陳維崧、朱彝尊又都經歷家道中落,迫于生計曾奔走四方。康熙元年(1662)至十年(1671)顧貞觀一直在京師游宦,僅做過一些小官;陳維崧“中更顛沛,饑驅四方”[8]90;朱彝尊則“依人遠游,南逾五嶺,北出云朔,東泛滄海”[9]12。應當說,正是在納蘭性德府邸,三人酬唱交流,切磋砥礪①參見黃天驥《納蘭性德和他的詞》,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1-247頁。,助推了“一時詞學之盛,度越前古”[1]177的中興熱潮。
顧貞觀嘗云:
吾友容若,其門地才華,直越晏小山而上之。欲盡招海內詞人,畢出其奇,遠方骎骎漸有應者。而天奪之年,未幾輒風流云散[12]502。”
納蘭性德卒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去世時年僅三十一歲,填詞不過十載左右,應當說,在詞壇聲望上尚難以號召群雄。而納蘭詞“哀感頑艷”的基調既不合于承平盛世,也不適宜浙西詞派主導下崇尚醇雅的詞壇環境,所謂“骎骎漸有應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納蘭性德的家族權勢使然。康熙年間“家家爭唱飲水詞”[15]現象的形成,以及納蘭詞在選本中地位的不斷攀升,也當有這方面因素。顧貞觀與陳維崧、朱彝尊雖都富有詞才,但與納蘭性德地位懸殊,三人以其門客身份獲得并稱似更為合理,而縱觀整個康熙詞壇,似也沒有論者將納蘭性德與陳維崧、朱彝尊并稱。
二、納蘭詞的再發現以及與陳維崧、朱彝尊并稱的確立
納蘭詞在康熙年間選本中地位頗高,到了有“清初清詞選本中的殿軍”[16]之稱的《草堂嗣響》,入選數更是躍居首位(編者自選詞除外),這或與顧彩“主情”的詞學理念有關②參見拙文《論清代〈彈指詞〉與〈飲水詞〉的接受及其原因》,《民族文學研究》2021年第4期。。《草堂嗣響》選陳維崧、朱彝尊詞分別居于第二、第三位(編者自選詞除外),此為“清初三大詞人”另一說法發軔。不過,自納蘭性德的父親納蘭明珠被罷相以及病逝后,《飲水詞》的傳播也受到影響,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中的一段話透露個中消息,如云:
(納蘭容若)登康熙十二年進士,時相國方貴盛,顧以侍衛用,趨走螭頭豹尾間,年未四十,遽亡。后相國被彈罷黜,侍衛之墓木拱矣[4]2793。
納蘭詞還遭到謗傷,“或者謂‘高門貴胄,未必真嗜風雅;或當時貢諛者代為操觚耳’”[17]432。雍乾年間,納蘭詞的接受跌至谷底,這一時期,甚至沒有出現過一個刊本。
嘉慶二年(1797)梁溪詞人楊芳燦率先手抄《納蘭詞》,并為之作序,云:
倚聲之學,唯國朝為盛。文人才子,磊落間起,詞壇月旦,咸推朱、陳二家為最。同時能與之角立者,其唯成容若先生乎[17]432?
楊芳燦為袁枚門生,他視納蘭為“隔世之知己”[17]432,是由于納蘭詞“主情”特質契合了其主張。楊芳燦的觀點遙接顧彩,表明納蘭詞再一次進入接受者視野。袁枚之子袁通在秉持家學時也援引“性靈”入詞,其《捧月樓綺語》“情之一往而深”[8]646,是“標舉性靈”的最佳佐證。袁通刊刻納蘭詞也是試圖通過文獻整理的方式為詞壇提供典范。道光詞人汪元治“精于倚聲,落筆輒似納蘭氏,不獨肖其口吻,抑且得其性情”[17]433,他曾在袁通刻本基礎上搜羅增補,得詞323闋,并付諸剞劂,進一步擴大了納蘭詞影響。趙函《納蘭詞序》云:
國朝詩人而兼擅倚聲者,首推竹垞、迦陵,后此則樊榭而已。……納蘭容若以承平貴胄,與國初諸老角逐詞場。……詞則卓然冠乎諸公之上[17]433。
已然是將納蘭性德標舉為清詞中最為杰出者。趙函的小序還記載了這樣一樁趣事:
聞吳門彭桐橋家藏有《通志堂集》,亟往借觀。桐橋告余曰:唏!是書藏余家數十載,無有顧而問者。昨婁東友人寓書來索是集,今吾子又借觀,豈此書將復顯于是耶[17]433。
文中“婁東友人”即指汪元治,彭桐橋“復顯于是”的預判也得到驗證。
郭麐為浙西詞派后期詞人,曾拜入袁枚門下,又與袁通為莫逆之交,他在論詞時不可避免地受到“性靈說”影響,如其《桃花潭水詞序》云:
是在學之者之心思、才力足以與古相深,而能自抒襟靈,乃為作者[18]。
《梅邊笛譜序》則云:
后之學者徒仿佛其音節,刻劃其規模,浮游惝恍,貌若玄遠。試為切而按之,性靈不存,寄托無有[19]。
郭麐在創作中也能自抒胸臆,不作涂飾,如《蘅夢詞浮眉樓詞序》云:
中年以往,憂患鮮歡,則益討沿詞家之源流,借以陶寫阨塞[20]。
由是觀之,郭麐標舉納蘭詞也是題中應有之意了。再來看看《靈芬館詞話》中的一段話:
竹垞才既絕人,又能搜剔唐、宋人詩中之字冷雋艷異者,取以入詞。……同時諸公,皆非其偶。梁汾時有俗筆。……唯《飲水》一篇,專學南唐五代,減字偷聲,骎骎乎入《花間》之室[21]1504。
郭麐為浙西詞派殿軍,他推崇朱彝尊自是無需多言,不過,這段論述也反映出他對《飲水詞》的傾心,而指出“梁汾時有俗筆”,則可見其軒輊顧詞與納蘭詞的態度。
一定意義上來說,正是經過清中葉這一批性靈詞人的集體推介,納蘭詞才能夠再次回歸人們的視野,并基本確立與陳維崧、朱彝尊的并稱地位。
晚清是納蘭詞接受的重要時期,這一階段又表現出兩點較為明顯的特征,一是以譚獻、況周頤為代表的派內之人,他們出于立論之需,將納蘭詞標舉到清人第一的位置;二是以丁紹儀、謝章鋌為代表的派外之人,他們不沾門戶之見,以流變發展眼光來看待清代詞壇,進一步明確納蘭性德與陳維崧、朱彝尊的鼎足地位。先說前者。譚獻《篋中詞》標舉“詞人之詞”[22]4013,選了二十五首納蘭詞,冠絕選本。又云:
有明以來,詞家斷推湘真第一,飲水次之。其年、竹垞、樊謝、頻伽,尚非上乘[22]3996。
在譚獻看來,明清兩代以晚明陳子龍為第一,納蘭性德則為清人第一。譚獻還以納蘭詞為典范來衡量當世詞家,如云:
(馮煦夢華《蒙香室詞》)單調小令,上不侵詩,下不墮曲,高情遠韻,少許勝多,殘唐北宋后成罕格。夢華有意于此,深入容若、竹垞之室,此不易到[22]4000。
值得注意的是,王鵬運也曾談到:
嘉道以來詞人,周稚圭似竹垞,蔣鹿潭似迦陵,而蓮生則近容若①王鵬運《〈憶云詞〉識語》,項鴻祚《憶云詞》,王鵬運四印齋鈔本。轉引曹明升《納蘭詞在清代的接受及其經典化要素》,《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
可見納蘭詞在晚清已獲得公認,成為了詞壇標桿。不過,真正意義上將納蘭性德標舉為“國初第一詞手”[14]4520的還屬況周頤,《蕙風詞話》云:
容若承平少年,烏衣公子,天分絕高。適承元明詞敝,甚欲推尊斯道,一洗雕蟲篆刻之譏……其所為詞,純任性靈,纖塵不染[14]4520。
對其在清代詞史上的意義以及詞之特質的揭示可謂知言。后來,王國維接續譚獻觀點又有所發展,云:
譚復堂《篋中詞選》謂‘蔣鹿潭《水云樓詞》與成容若、項蓮生,二百年間,分鼎三足’。然《水云樓詞》小令頗有境界,長調唯存氣格;《憶云詞》精實有余,超逸不足,皆不足與容若比[23]4259。
又云:
納蘭侍衛以天賦之才,崛起于方興之族。其所為詞,悲涼頑艷……同時朱、陳,既非勁敵。后世項、蔣,尤難鼎足[23]4276。
況周頤與王國維對納蘭性德的標舉,將其與陳維崧、朱彝尊拉開了距離。后來,錢基博于《現代中國文學史》中云:
論清初詞家,當推成德為一把手,朱、陳猶不得為上[24]。
便是這種觀點的嗣響。
與譚獻、況周頤等具有較為強烈的個人化審美偏嗜相比,丁紹儀、謝章鋌對納蘭詞的定位則基于詞史立場,顯得更為客觀公允。丁紹儀云:
自來詩家,或主性靈,或矜才學,或講格調,往往是丹非素,詞則三者缺一不可[4]2575。
在頗為通達的詞學觀照下,他認為納蘭詞“于迦陵、小長蘆二家外,別立一幟”。謝章鋌則從“長短調并工者”的角度,認為清代詞壇只有納蘭性德與陳維崧、朱彝尊能夠兼善其美。與丁、謝二人持相近觀點的詞家還有不少,沈世良云:
老輩朱陳樹鼓旗,家家傳寫遍烏絲。誰知天授非人力,別有聰明飲水詞[25]。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也云:
國朝譚詞推朱陳兩家。迦陵病在熟,竹垞病在陳,顧迦陵勝于竹垞者,筆意靈也。余子不足數。求于迦陵鼎峙者,其容若及金風亭長乎[26]!
由上可以看出,經過各派以及不同觀念的詞人推舉,納蘭性德不僅牢固樹立與陳維崧、朱彝尊的鼎足地位,還時常凌駕于陳、朱之上,被目為清詞第一人。“清初三大詞人”的內涵在晚清得到確立毋庸置疑。
三、顧貞觀與納蘭性德易位反思
康熙年間,顧詞與納蘭詞在選本中都經歷由平至顯的接受過程①參見拙文《論清代〈彈指詞〉與〈飲水詞〉的接受及其原因》,《民族文學研究》2021年第4期。,不過,這一階段顧貞觀與陳維崧、朱彝尊并舉似更為詞壇所接受。納蘭和陳、朱的鼎足地位肇始于顧彩的《草堂嗣響》,經清中葉楊芳燦、郭麐等性靈詞人集體推介,至晚清成為定論。顧貞觀與納蘭性德的易位帶給我們如下反思:
其一,易位的基本著眼點很大程度上在于二者間具有共同性,而顧貞觀與納蘭性德無論其人還是其詞都具有相似之處。
顧貞觀與納蘭性德相識于康熙十五年(1676),在二人訂交過程中有一個繞不開的人物——吳兆騫。順治十四年(1657)“科場案”發,吳兆騫受到牽累被流放寧古塔。顧貞觀為營救吳兆騫,曾連同納蘭性德向納蘭明珠求救,據記載顧貞觀不僅屈膝下跪,在面對巨觥時素不善飲的他甚至一吸而盡②參見袁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頁。。此后,顧貞觀又以詞代簡填寫了兩首《金縷曲》(季子平安否)(我亦飄零久)。最終,在納蘭性德的幫助下,吳兆騫于康熙二十年(1681)返回帝京。納蘭性德與吳兆騫此前并不相識,而其以一諾之重使吳氏生入榆關,可見篤于友誼。納蘭性德《祭吳漢槎文》也云:
自我昔年,邂逅梁溪,子有死友,非此而誰。金縷一章,聲與泣隨,我誓返子,實由此詞[7]286。納蘭性德相交之輩多為江南寒士,徐乾學云:
君所交游,皆一時俊異,于世所稱落落難合者[17]417。
這些人中,顧貞觀堪稱他交誼最深的朋友。而據筆者統計,納蘭詞中涉及顧貞觀的作品也最多,達十余首。納蘭性德與顧貞觀交往乃是基于心靈相通,納蘭詞中之“后身緣、恐結他生里”(《金縷曲·贈梁汾》);“相思何益,待把來生祝取,慧業相同一處”(《大酺·寄梁汾》),都是表達與顧貞觀世世結交的愿望。
顧貞觀與納蘭性德皆重情重義,二人不僅心性相近還“持論極合”[12]496,共操選政編纂的《今詞初集》“主于鏟削浮艷,舒寫性靈”。《彈指詞》與《飲水詞》以情韻取勝的總體風貌也頗為相近,正如謝章鋌所云:
納蘭容若(成德)深于情者也。固不必刻畫花間,俎豆蘭碗,而一聲河滿,輒令人悵惘欲涕。情致與彈指最近[3]3415。
梁啟超于《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的情感》一文中將古典詩歌表情方式歸納為六種,“迸進的”“回蕩的”“蘊藉的”“象征的”“浪漫派的”“寫實派的”,他認為“回蕩的表情法”用來填詞最為適宜,列舉的清詞典范即為顧貞觀與納蘭性德①參見梁啟超《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的情感》,梁啟超《梁啟超古典文學論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214頁。。清初,二人以相近的心性,相同的理論,相似的詞風馳騁一時,無疑為后世批評中的易位提供可能。
其二,納蘭性德在嘉道以后的詞壇地位不斷攀升,其本質是由于清人對納蘭詞“主情”特質的認識進一步深化,為了自身理論建構而將其推出,顧貞觀詞則因不具有典范性被罷黜,至晚清近乎湮沒。清人退顧而進納蘭的行為體現出對本朝經典序列的調整。
杜詔于《彈指詞序》中針砭“學姜、史者輒屏棄秦、柳諸家,一掃綺靡之習,品則超矣,或者不足于情”[2]545的浙西詞派,標舉“極情之至”的顧貞觀,大有藥救浙西詞派末流弊病的意圖。在杜詔看來,“彈指與竹垞、迦陵埒名”。不過,到了楊芳燦的《納蘭詞序》,與陳維崧、朱彝尊角立者卻變成納蘭性德。楊芳燦為乾嘉時期著名詞人,他生長于梁溪,不可能不了解顧貞觀這位在詞壇上標舉“性靈”的鄉賢,他推出納蘭性德而回避顧貞觀,選擇與杜詔不同的取法對象,表明在其看來納蘭詞更適合作為言情典范。楊芳燦的行為說明詞壇接受范型出現了分歧,顧詞與納蘭詞在張力運動中呈現出分庭之勢。
值得注意的是,清中葉性靈詞人并非完全漠視顧貞觀,只不過在顧貞觀與納蘭性德之爭中選擇了后者。郭麐認為“本朝詞人,以竹垞為至”[21]1503,與之相較者又舉出顧貞觀、李符以及納蘭性德。不過,郭麐對顧、李頗有微詞,認為“梁汾時有俗筆。耒邊錦瑟,苦無動人”,唯有對“專學南唐五代,減字偷聲,骎骎乎入《花間》之室”[21]1504的《飲水詞》持肯定態度。郭麐曾給予顧貞觀的三首《金縷曲》(季子平安否)(我亦飄零久)(馬齒加長矣)以高度評價,但“時有俗筆”的論斷,相較對于納蘭詞的全面肯定,可見其褒貶態度。郭麐因受到袁枚影響,將性靈理論援引入詞學領域,納蘭性德作為其標舉典范再一次被關注。嘉慶年間常州詞派并未在真正意義上登壇樹幟②不少人將嘉慶二年(1797)張惠言、張琦編纂的《詞選》視為常州詞派建派標志,事實上,《詞選》最初只是張惠言為歙縣金榜子第授課所用,其流傳也只是在弟子與同里小范圍內,《詞選》的開宗意義主要來自常州詞派后人追認。,此時除浙西詞派后期詞家,影響最大的就是楊芳燦、郭麐這些深受詩壇性靈之風浸染的詞人。應當說,納蘭詞在浙西、常州詞派交替之際回歸了詞壇,并開啟晚清的接受高潮。郭麐抑揚顧詞與納蘭詞的思路在后世也得到接續,況周頤《蕙風詞話》云:
容若與顧梁汾交誼甚深,詞亦齊名。而梁汾稍不逮容若,論者曰:失之脆[14]4521。
一方面肯定二人詞成就相近,另一方面又指出顧詞不足,認為尚不能真正與納蘭詞相提并論。
應當說,顧詞與納蘭詞的特點在不同歷史階段得到不同程度的挖掘,納蘭詞相較顧詞言情更為真切自然,具有更強的感發力量,納蘭詞為“詞人之詞”,顧詞為“才人之詞”,③參見拙文《論清代〈彈指詞〉與〈飲水詞〉的接受及其原因》,《民族文學研究》2021年第4期。二者由于易感性差異,在晚清詞壇“主情”思潮下形成不同的接受命運。顧貞觀與納蘭性德的易位揭示出清詞演進中的一個重要現象,即清人為了自身理論建構自覺對本朝經典序列作出調整,而在這一過程中,清人對顧詞與納蘭詞特質的認識不斷深化。晚清時期納蘭性德取代顧貞觀登上經典壇坫,與陳維崧、朱彝尊鼎峙基本成為共識。
其三,清人通過分析師法取徑、藝術風貌等差異指出納蘭性德與陳維崧、朱彝尊并稱的理由,這一策略是借助三者所具有的不同典范特征來實現的,從而確立清人心目中的本朝經典。
楊芳燦于《納蘭詞序》中最早指出納蘭詞與陳、朱二人詞的差異,云:
陳詞天才艷發,辭鋒橫溢,蓋出入北宋歐蘇諸大家;朱詞高秀超詣,綺密精嚴,則又與南宋白石諸家為近;而先生(納蘭性德)之詞,則真《花間》也[17]432。
在此之前姜宸英、杜詔也是從這一思路指出顧貞觀與陳維崧、朱彝尊的分歧。可見,顧貞觀與納蘭性德易位之轉捩就發生在楊芳燦這里。如果說《草堂嗣響》只是從選詞上隱約昭示納蘭與陳、朱的鼎足地位,那么,楊芳燦則“從詞史上花間、北宋、南宋這三種風格的并傳來為納蘭定位的,并且首次明確提出納蘭的詞史地位應同儕于朱、陳”④參見曹明升《納蘭詞在清代的接受及其經典化要素》,《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我們知道,在詞學主張上,顧貞觀以北宋為宗,兼取南宋,具有兼容并包的特色,納蘭性德則獨尊晚唐北宋,一定意義上來說,稍顯狹隘的取徑因特點鮮明,往往更適宜作為范式。楊芳燦以典范風格標舉納蘭詞的思路也得到晚清詞家熱烈響應,汪元浩云:
國初才人輩出,秀水以高逸勝,陽羨以豪宕勝,均出入南北兩宋間。同時納蘭容若先生則獨為南唐主、玉田生嗣響[17]435。
謝章鋌云:
竹垞以學勝,迦陵以才勝,容若以情勝[3]3472。
胡薇元也云:
陳天才艷發,辭鋒橫溢;朱嚴密精審,超詣高秀;容若《飲水》一卷,側帽效顰,為詞家正聲,散璧零璣,字字可寶[27]。
納蘭性德與陳維崧、朱彝尊被不斷標舉,無疑是清人以本朝詞家為典范建構詞史的重要實踐,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清人于詞之創作一道的高度自信。
四、小 結
并稱是一種頗有意味的批評方法,從并稱者的更替中不僅能夠看出清人詞學觀念的變化,而且能夠加深對批評對象的認識以及了解其接受命運。顧貞觀與陳維崧、朱彝尊在清初并稱更為符合詞壇實際。顧貞觀與納蘭性德的易位則反映出清人對本朝經典序列的自覺調整,與之同時,顧詞與納蘭詞的特質經過清人細致辨析與多維評價也愈加明確。納蘭性德逐步取代顧貞觀成為“性靈”典范,雍乾詞人特別是楊芳燦、郭麐發揮了很大作用,這是詩壇因素介入詞壇的一次重要反饋,也是詞壇對情感呼喚的結果。隨著時間距離的拉開,經過晚清詞人進一步地推尊與鞏固,納蘭性德與陳維崧、朱彝尊之并稱得到公認,最終共同樹立起清初詞壇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