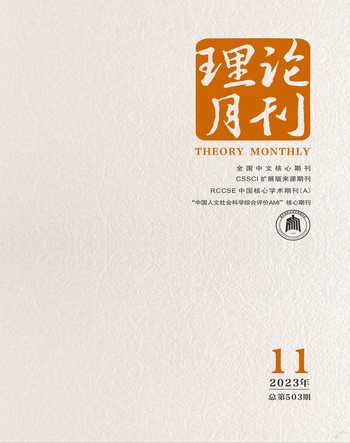論《莊子》內篇心靈轉化的三種模式
李宇 李巍
[摘 要] 《莊子》內篇在描述心靈轉化時,有三種主要模式——由心到神、由心到氣、由心到德,它們皆指向認知方式的調整。這種調整旨在破除在個人有限的、固化的、偏好明顯的認知方式控制下的感官活動,而非否認感官本身,并且期待在面對物、事、人時,以流動的、變化的環境作為認知與行動導向。相關的文本主要存在于《養生主》篇“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人間世》篇“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德充符》篇“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中。其中,“不以目視”“無聽之以耳”“不知耳目之所宜”在以往的解釋中常被認為是對感官及其活動的消解,進而弱化了心靈轉化過程中涉及的認知轉變。然而,這樣的解釋在回歸文本語義系統時,難以實現邏輯上的融貫,從而使得與此關聯的心靈轉化的詮釋也出現了偏差。因此,遵循文本語脈,明晰這些否定詞的指向,進而發掘心靈轉化的不同側面,是合理且需要開拓的研究路徑。
[關鍵詞] 《莊子》;心靈轉化;感官;認知
[DOI編號] 10.14180/j.cnki.1004-0544.2023.11.016
[中圖分類號] B223.5? ? ? ? ? ?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1004-0544(2023)11-0148-08
作者簡介:李宇(1994—),女,中山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李巍(1982—),男,武漢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在《莊子》內篇中,心的問題關涉著認知的調整,心的轉化實際上指向認知方式的改變。而這種改變在與感官密切關聯時,尤其是以耳目為代表的感官與心的轉化同時出現時,需要研究者謹慎面對。原因在于:一方面,相關文本在提及心的轉化時,出現了多次以耳目為代表的感官參與。在《養生主》篇中,庖丁解牛的故事提到“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1](p111)等主張;在《人間世》篇中,孔子與顏回的對話提到“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1](p137),“夫循耳目內通而外于心知”[1](p139)等主張;在《德充符》篇中,對于王駘的描述提到“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1](p176),“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1](p179)等主張。因此,從文本出發,如果要談論心靈的轉化,那么以耳目為切入點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在探究《莊子》文本中心的轉化與耳目感官的關系時,歷代解釋紛爭較多,主要呈現以下幾種特征:第一,在心的轉化過程中,以耳目為代表的感官及其作用被弱化或消解。例如畢來德認為,“官知止而神欲行”代表感官不再介入,精神按照意愿行動①。第二,對心的轉化與耳目之間關系的解釋存在語義重復的問題,諸如林希逸的解讀皆有待推進①。第三,用神秘的體驗方式來說明心的轉化及其與耳目等感官之間的關系,或認為在耳目等感官作用下的心靈轉化難以用語言表達。正如劉笑敢所言,“官知止而神欲行”意味著真人神秘的精神直覺,而非凡人之知。又如劉暢所言,“心齋”是一種無須依賴感官、難以用語言表達的體悟真理的途徑②。除此之外,在講述神與耳目之間的關系時,楊儒賓的關注點主要在于“身體的意識化”。在他看來,“神”是對耳目作用以及全身動作的統攝,身體經由“神”的作用成為行動的主體,感官不再居于主宰意識的地位③。本文遵循楊儒賓的說法,但試圖提升對下列問題的關注度:在身體意識化之前,認知層面究竟發生了何種轉變,以及這種轉變是如何進行的。本文期待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能夠對以下問題作出些許推進:《莊子》內篇在以否定的形式談論耳目時,是否意味著否定以耳目為代表的感官及其作用;到底是“感官懸置不用”[2],還是“莊子并不排斥感官知覺和知識”[3],抑或是“莊子拒絕了眼睛和耳朵,從而拒絕了它們所代表的知識”[4](p59);身心二分的探究方式是否適用這些文本,語義重復的解釋如何被推進,語言能對文本義理做出何種程度的解析。這些都是現階段的研究需要關注和回答的問題。
一、由心到神
在內篇中,《養生主》篇首次出現了“目”與“心的轉化”之間的互動,文惠君問其技為何能合桑林之舞之妙,庖丁答:“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1](p111)在這段話中,出現了“目”與“神”,“官”與“神”的更迭。歷代學者對此句的解釋各有側重。縱觀這些解讀,“官”與“目”的釋義基本一致,并無太大異議,一般都指向感官④。而對于“神”的解釋以及“神”與感官之間關系的處理則爭議較大,主要呈現為以下三種觀點:第一,以心釋神,認為“神”“心”“精神”等可以通約⑤。第二,以神釋神,用“神氣”之類的詞語來表述“神”或將“神”字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⑥。第三,對“神”進行解讀,且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將“神”視作“心”的收縮義,如郭象、成玄英就將“神”解釋為“順理”狀態下的“心”,并且認為這種心靈狀態伴隨著感官作用的廢止。“順理”在郭象與成玄英的注疏中是指,在解牛的過程中“不橫截”“不橫截以傷牛”[1](p113)。第二類將“神”看作感官經驗的統合或超越狀態,將“神”的作用與感官經驗聯系起來,認為前者是后者的一種整合狀,如楊儒賓、畢來德皆持此觀點①。第三類從“神”帶來的狀態對其進行刻畫,將“神”看作是超越感知、超越技術層面的精神狀態,如徐復觀、陳少明、陳赟②。基于上述研究現狀,此處對“神”的爭議現仍然存在著有待推進或明晰的地方:第一,“神”與“心”的關系,二者是否能被等同;第二,“神”完全否定感官,還是基于感官;第三,“神”是否不可言說。回答這些問題需要重回庖丁解牛的語義系統。
首先,庖丁將自己解牛描述為“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1](p111),并且這個過程也被描述為“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1](p110)。由此能夠確定的是:庖丁解牛不只停留在日常經驗的技術層面,這一點在故事結尾也能夠得到驗證,即“為之躊躇滿志”[1](p112),這說明“庖丁能從解牛的過程中獲得滿足感,至少有些內在獎勵”[5](p209)。因此,將“神”解釋為感官統合的說法有待推進:一方面,在用“感官的統合”之類的說法來解釋“神”時,還應進一步明晰由“感官”主導形成的認知與在“感官的統合”作用下形成的認知的差異。無論是楊儒賓所持的“神”能統合耳目、身體的觀點,還是畢來德將“神”看作整合的動能狀態的說法,“神”的解釋仍然有值得推進的地方,讀者對文本的疑問似乎從“神是什么”轉向了“整合、統合到底是何意義”。另一方面,這種解釋忽略了庖丁解牛帶來的審美感受以及庖丁獲得的自足的積極感受。例如,畢來德雖然試圖探明解牛的過程,但他將庖丁解牛的過程與切面包、學外語等活動進行類比,這顯然違背了“技進乎道”的旨意。其次,“神”也并非脫離感官,因為即使實現了“以神遇”的狀態,但庖丁遇到骨節交錯之處,仍然需要眼神專注,動作謹慎,即“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1](p112)。因此,“神”并未完全否定或者拋棄目所代表的感官及其作用。根據上述兩點分析,此處的“神”既沒有完全止步于感官作用,又未脫離感官作用。由此可以肯定的是:“官知止而神欲行”中的“止”并非指完全停止、廢棄感官及其作用。但要獲得“止”和“神”的確切意義,則要在解牛的三個層次的小語義系統中來探究。
在第一個階段中,庖丁“所見無非(全)牛者”[1](p111),無論是“全牛”還是“牛”,相較于第二個階段,都意味著人對物的認識在起始階段的粗略特征,指人開始接觸物時形成的認知;在第二個階段中,庖丁“未嘗見全牛也”[1](p111)則表達了人對物的認識由粗略到精細的轉變,相較于第一個階段,這是人對物的認識不斷深化時獲得的認知;在第三個階段中,庖丁則能“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1](p111)。如上所述,“不”和“止”在此處并不表示對感官及其作用的廢棄,但又確實表達了一種否定的意義。因此,對于否定的對象就需要進一步探究。在第三個階段中,庖丁在解牛時的表現被描述為:“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1](p111-112),這是指庖丁能夠依照牛的天然構造來進行解牛。這不僅需要人掌握牛的構造特征,還需要人在面對牛的不同部位特征時,心靈能夠依據位置的改變作出相適宜的認知與行動。這種反應不再是人規定物的結果,而是人遵循物的表現。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對感官的否定,而在于對由感官而獲得的固化認知的反對。莊子就是要不斷地打破這種認知方式,他看到了人在認識事物時由感官主導的固化自我認知對“天理”的破壞。前者代表了個人形成的慣用認知模式,后者則代表事物的天然結構。人在與物互動時,往往“以我為法”而非“以物為法”,對物的效用、特征等進行人為限制。并且,個人認知往往趨向固化,如莊子在《齊物論》中提及的“成心”;物的效用、特征等可能被個人認知縮小或扭曲,如莊子在《逍遙游》中提出的“大而無用”。
莊子并不否認人的認知需要經由感官形成,但這種“以我為法”的認知一旦固定之后,個人就幾乎只根據這種已有認知來判斷感官接收的信息。然而,在莊子看來,這種認知方式違背了物的天理。因此,莊子才要提出“官知止而神欲行”“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1](p111)。庖丁否定的不是“目”所代表的感官,而是由感官主導而形成的“成見”,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層次的意義:第一,“神”代表著一種認知,但不等同于“心”,是“心”的收縮義;第二,“神”是對心中固化的個人認知的破除,即對“成心”的拋棄,“官知止而神欲行”意味著“放棄那些阻礙身體和心靈反應能力的習慣”[3](p8);第三,“神”仍然需要感官的參與,感官活動是實現“神”的狀態無法避免的過程,但此時的心靈不再以經由感官形成的已有知識體系來對事物進行人為的限制,而能夠以開放的姿態面對感官接收到的信息。這種開放的心靈狀態能夠尊重事物天然的特征,并且在不斷變化的場景中,作出與物最適宜的互動,而這種互動則代表著心靈由固定走向了開放。由此,人與物的關系不再是一種規定與被規定的關系,而是人的感官、認知、行動隨著物的天然構造以及情境的變化而不斷流轉。這種遵循物的天然構造的做法,是莊子理想的人與物的互動模式,是與天理相契合的心靈轉化模式。只有在這種人與物的互動中,人才能游刃有余,獲得自足感。
由此可知,在庖丁解牛中,目所代表的感官與由心到神的轉化緊密相關:感官是無法跳過或拋棄的存在,但由于個人經由感官形成的認知以自我偏好為中心,呈現出單一性、狹隘性、固定性。因此,必須借助心的轉化來突破這一困境。心代表著認知,心的轉化意味著對以往認知方式的糾正。由心到神意味著心的收縮,這種收縮是對與“道”相合的認知方式的接受與趨近,這也就意味著:心靈放棄固有判斷,在與物接觸時能夠跟隨事物的天然特征,在流動的環境下作出適時的反應。庖丁解牛顯然“包含了深度的專注,自我意識的喪失,以及行動者的行動和環境的融合”[5](p209)。
二、由心到氣
在《人間世》開篇中,莊子借助顏回與孔子勸諫衛國國君之事的對話,展示了政治生活中的艱難與危險,并由此提出“心齋”,以期走出上述困難與險境。“心齋”涉及心的轉化,且在這種轉化中出現了對耳的否定,即“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1](p137)。然而,要明確這一主張的旨意,就須從故事整體語境來分析。
首先,顏回試圖勸諫衛國國君是因為其異常暴虐,從而導致“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1](p124)。在顏回看來,他勸諫衛國國君愛惜人民就如同醫生給病人看病一樣正當。然而,孔子卻認為這是“好名顯智”的表現,會招致禍患。不過,他仍然和顏回討論了如何勸諫暴君的問題,這實際上展示的是莊子對現實政治環境的認識與應對,正如王夫之所說:“此篇為涉亂世以自全而全人之妙術。”[6](p108)
其次,顏回將自己試圖勸諫國君的方式講給孔子聽,但皆被孔子駁回。他認為,顏回的方式非但不能實現勸諫目的,反而有可能使其自身難保,原因在于“猶師心者也”[1](p135)。在這種情況下,孔子提出了“心齋”的主張:“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1](p137)由此可見,“心齋”的提出旨在破除“師心”,而“師心”就是指個人以自己的偏好來判斷是非的固化立場。關于這一點,莊子在《齊物論》中已經有所說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1](p56)具體而言,“心齋”呈現出三個階段:耳—心—氣。第一個階段以否定的形式出現,第二個階段以肯定又再次否定的形式出現,第三個階段則以肯定的形式出現。因此,要解讀三者的含義,必須聚焦于心齋的落腳處——“氣”。莊子認為“氣”的特征在于能夠“虛而待物”,并指出“心齋”的關鍵就在于“虛”,“聽之以氣”要破除的是以“己”為中心的認知。以此反觀“耳”與“心”的階段,則能得出以下結論:二者所形成的認知并不具備“虛”的特征,且與個人固化認知的形成密不可分。在這一基調下,“聽之以耳”的原因逐漸清晰:以耳為代表的感官是認知形成的基礎,人的認知的形成需要感官的參與,但以耳為代表的感官只是形成人的認知首先要經歷的階段,認知的形成并不止步于此,即“聽止于耳”。因此,莊子才進一步提出了“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具有思慮判斷功能的“心”標志著認知的形成,人依靠“心”處理由感官接收的信息。
至此能夠明晰的是:“無聽之以耳”并不否認感官及其作用,“無”旨在說明感官只是形成認知的一個階段,不能止步于此;“無聽之以心”也并不否定心靈,而是不主張用“以我為法”而形成的認知來對感官接收的信息進行人為的限定;“聽之以氣”則是克服在前兩者作用下形成的認知。“虛而待物”的“氣”代表流動、開放、虛己,由此可以克服固化的、單一的、以己為中心的認知缺點。故而,以成玄英為代表的學者將“心齋”的關注點聚焦于“虛”的解釋是合理的①。由此,若要探討“氣”屬生理還是精神性質②,還應明晰在開辟精神境界前涉及的認知轉變。在這里,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氣”應該被劃分在身心二元的哪一方,而在于“氣”具有“虛”的特征,“虛”則能夠適時而變。“聽之以氣”意味著心靈不再以固有的、“以我為法”的知識體系來劃分感官所接收的信息,感官也不再在接收外界信息時因心靈的已有判斷而呈現出有限且單一的特征,而是能夠在開放的心靈狀態下對不斷變化的情況作出適宜反應。這種反應不再以人形成的知識體系為標準,而要關注不斷變化的環境,以流動的場景為依據,適時地選擇、調整自身關于事物的認知與行動。在這里,就是指顏回能夠不斷地調整勸諫的方式,甚至放棄勸諫這一目標以求自保。這也就是說,“聽之以耳相當于簡單地接收感官輸入。聽之以心意味著根據先入為主的意義框架分析經驗。然而,聽之以氣則需要積極地觀察(或接受)正在經歷變化的情況”[7](p564)。“心齋”仍然需要心靈判斷能力的參與,但判斷的標準是不斷變化的情景,正如孔子下文對顏回所說:“入則鳴,不入則止。”[1](p138)顏回“應該利用一種未形成的、開放的接受能力對新的情況產生自發的反應,而不是依賴于先前的知識來識別和回應”[5](p203)。
因此,“心齋”就是指“感官及其作用(耳)—以我為法的個人認知(心)—虛己的認知方式(氣)”這樣一個層層遞進的轉化過程。感官與心的轉化之間的關系再次在“心齋”的修煉方式中得到明確:一方面,對于“心齋”來說,感官是認知形成及認知方式轉變的基礎,無法被拋棄;另一方面,心的轉化意味著認知方式的轉變,這種轉變需要克服借助感官形成的、具有明顯偏好色彩的認知,而不是要消除感官本身。這從“夫循耳目內通而外于心知”[1](p139)等表述中也能看出來:“循耳目內通”說明莊子并未放棄感官及作用,“而外于心知”則說明感官接收的信息不被心靈以往慣有的知識所劃分。“心齋”是借助感官作用實現的心靈轉化過程。
在“心齋”涉及的感官與心靈轉化的關系中,心靈的轉化仍然意味著認知方式的變化。對于個人而言,要獲得關于事物的認知,就必須首先運用聽覺之類的感官能力。然而,個人在接觸外界事物時,時常以已經形成的自我偏好為標準,事物會因這種偏好而被規定。只有認識到這種自我認知的單一與狹隘,以及事物與環境的多樣和復雜,才能進行認知方式的轉化。對于莊子來說,轉化的方式就在于:要意識到事物會在不同的環境中呈現出不同的作用,如“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1](p88);要意識到事物也會因不同的場景設置而呈現出不同的效用,如“朝三而暮四”[1](p68),“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1](p69)。并且在此基礎上,要專注于環境的變化,從而及時調整自身的認知與行動,以實現人、事、物的最佳搭配。這種適時而變并“不是‘不經意(heedless)意義上的‘無思無慮(thoughtless),相反,它要求全神貫注于所處的境遇”[8](p221-222)。
三、由心到德
在《德充符》篇中,出現了以耳目為代表的感官和心的轉化之間的互動,其發生在兀者王駘的故事中。王駘是魯國一個身體有殘缺的人,但愿意跟隨他學習的人卻很多,并且王駘并不會教授那些跟隨者豐富的知識,這在常季看來難以理解。因此,他向孔子發問:“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1](p173)這句話傳達了三層意思:第一,常季對王駘的認識是從他的外在形體出發的,即王駘足有殘缺;第二,在上述認識基礎上,常季對王駘的認識是根據他的跟隨者眾多得出的,即王駘雖身體殘缺但其跟隨者的數量卻能與孔子相媲美;第三,常季對王駘的認識還源于王駘獨特的教學方式,即王駘并不發長篇大論來教化跟隨者,而是不教不議,但他的跟隨者卻能在回去的時候有所收獲。由此,常季指出:有不用言語的教導,并且形體殘缺,“而玄道至德,內心成滿”[1](p174)的人嗎?這樣的人又是怎樣的人?對此,孔子只是表達了自己對王駘的贊賞。因此常季接著發問:“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1](p175)由這段話能夠看出,常季對王駘的疑問主要源于兩點:一方面,在常季的認知里,身體殘缺的人不符合常人對形體的正向判斷;另一方面,對于形體本來就不符合常人認同的人,內心要實現怎樣的狀態才能吸引如此眾多的跟隨者。這兩個疑問的提出是由于常季對王駘的認知與現實情況發生了背離。
面對這種疑問,孔子開始進行正面回答:“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1](p175)這句話從死生、天地覆墜兩種非常大的變化狀況來舉例,旨在說明王駘并不會因為任何變遷而擾亂自身的心靈狀態。對于這個解釋,常季仍然心存疑惑,于是孔子開始了第二次的說明,在這次的說明中出現了“耳目”與“心的轉化”的互動:“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1](p176)這段話要分為兩個層次來理解。首先,從異來看,肝膽雖在一身卻仍被認為相距甚遠,如同楚越之距;從同來看,萬物雖有不同但卻被看作是同一的。這里的“視”實際上是指心靈的認知方式,旨在說明人在與物相處時,認知上的差異會導致對事物的判斷不同。并且,莊子借孔子的回答要對比的是“異”與“同”兩種方式。其次,如果能夠用“同”的認知方式來與物相處,那么帶來的結果就有以下兩個方面:第一,“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1](p176);第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1](p176)。第二句話是說王駘既將萬物看作“一”,則不覺得有所喪失,身體上的殘缺對他而言就像是身體上掉了一塊泥土一樣。前者很難直接從字面意思來理解,容易產生未突破表面文字的、忽略文本語義關聯的解釋①,因此需要層層解析。
對于“且不知耳目之所宜”來說,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耳目之所宜”在王駘這個故事的語義系統中所指的對象是什么。回答這一問題需要反觀前文常季對王駘的質疑。上文已經指出,常季質疑王駘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身體上的殘缺不符合常季對形體的正面認知,“兀者”在這種認知下會被判斷為目所不宜的形象。這也就是說,認知才是引起目之所宜或不宜的原因,這種認知由耳目喜好為主導而形成,反過來又對耳目喜好進行了肯定和加固。與此認知判斷中的“宜”相匹配的事物則是“耳目之所宜”,反之亦然。這就是“自其異者視之”的體現。
由此,在這段話的語義系統中,“自其異者視之”“自其同者視之”是兩種認識事物的不同方式:前者根據由感官喜好主導而形成的知識來對事物進行判斷,后者是對前者的反對。“且不知耳目之所宜”不是對耳目感官及其作用的否定,而是對已有的、具有偏好性的認知影響下的耳目感官及其作用的反駁②。然而,“自其同者視之”到底是指怎樣的認知方式,還需要進一步確定。在下文中,常季與孔子的問答仍在繼續,常季對于孔子第二次的回答仍然有所疑惑,不知王駘為何能有如此多的跟隨者。孔子在第三次的回答中,提到了一組意象,即“流水”與“止水”:“人莫鑒于流水而鑒于止水,唯止能止眾止。”[1](p178)這句話是說,人無法從流動的水中來照自己,但卻能從靜止的水中來照自己,只有像止水一樣,才能“留停鑒人”“物來臨照”[1](p179)。根據常季的第三次提問可知,這里實際是將王駘比作止水,將王駘看待萬物的認知方式比作止水對來照之物的映射。而這種認知方式在《莊子》文本中與“心”相關聯,因此,“流水、止水,皆以喻心”[9](p85),止水本身澄澈靜止,外物來此皆能被映照。因此,王駘在面對自身形體的改變時,并不以由個人感官偏好形成的固化認知來看待這種變化,而是在已經發生改變的環境下作出相適宜的認知與行動,這顯示的是一種流動的、變化的而非固定的、單一的認知方式。因此,下文孔子對王駘的描述便也明晰了起來:“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1](p179)“一知之所知”并不是要把所有知識窮盡,而是能夠用靈活的認知方式來面對外界的事物,人、事、物組成的環境變化不斷,那么心靈若能跟隨這種變化,則“心未嘗死者乎”。由此,在這種認知方式下,萬物能夠在開放的心態下被納入不同的情景之中。物的效用不再被扭曲,耳目所代表的感官也不再因固有認知來作用,“心靈會積極地進入那些缺乏明確定義的地方,并容納情景創造的可能性”[7](p570)。王駘能夠將形體殘缺看作變化的情景中的新狀況,從而作出與新狀況相適應的反應,即“視喪其足猶遺土也”,這就是“自其同者視之”的認知方式。
從上述層層推進的語義邏輯來看,“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旨在說明感官以變化的環境為導向,對包括自身身體在內的物不斷地作出適應時機的判斷與反應,“故放心于道德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曠然無不適也”[1](p177)。
四、結語
在庖丁解牛的故事中,“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表明人在面對物的時候,不再以已有的、固化的、具有個人偏好的認知方式來認識物、改變物,以求實現自身的需求;而是伴隨著環境的改變,在尊重物天然特性的前提下來調整自己的認知與行動,以此實現自身對物的需求。在顏回與孔子的對話中,“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表明人在面對事情時,不以個人已形成的價值判斷為立場,而根據環境的改變來適時調整自身的認知與行為。在常季與孔子的討論中,“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表明人在面對自身形體時,要破除以耳目等感官為主導而形成的認知。在莊子看來,形體的優劣、美丑、完備與殘缺等價值判斷意味著以人的感官喜好為標準的認知,人需要消解這種己知。在這些過程中,莊子要破除的不是耳目等感官及其作用,而是僅基于個人耳目等感官喜好形成的認知,以及這種認知對耳目等感官之欲的肯認與固化。在上述心靈的轉化即認知方式的轉化中,感官仍要發揮接收信息的作用,但感官之欲、感官偏好不再是認知形成的標準,這種己知不再成為人判斷物、事、人的準則,人的認知與行動需要跟隨環境的改變進行適時調整。這種動態的方式并非隨意扭轉認知,而是以契合“道”“氣”“德”為原則①。“道”“氣”“德”在上述心靈轉化的過程中都旨在以物為法,以虛為主,以變為要。即尊重物的天然狀態,用虛無之心來應物處世,面對形體變化能夠不被常人的成心所束縛。由此能夠看出,在《莊子》內篇中,心靈的三種轉化實際上意味著認知方式的調整,雖然文本中時常出現與耳目相關的否定詞,但這些否定詞真正指向的并不是感官,而是在經由感官形成的認知方式與感官欲望及偏好的互動中被固化的己知。
參考文獻:
[1]郭慶藩.莊子集釋[M].王孝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3.
[2]陳赟.論“庖丁解牛”[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52(4).
[3]Massimiliano Lacertosa.Sense Perception in the Zhuangzi[J].Philosophy Compass, 2022,17(1).
[4]Jane Geaney. On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Senses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M].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2.
[5]Chris Fraser. Heart-Fasting, Forgetting, and Using the Heart Like a Mirror: Applied Emptiness in the Zhuangzi, in Nothingness in Asian Philosophy[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 2014.
[6]王夫之.老子衍 莊子通 莊子解[M].王孝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9.
[7]Carl Joseph Helsing. The Wandering Heart-Mind: Zhuangzi and Moral Psychology in the Inner Chapters[J]. Dao, 2019(18).
[8][英]葛瑞漢.論道者:中國古代哲學論辯[M].張海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9]林希逸.莊子鬳齋口義校注[M].周啟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責任編輯? ?羅雨澤
1參見[瑞士]畢來德:《莊子四講》,宋剛譯,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9頁。
①“官,耳目鼻口也。官知止者,言凝然而立之時,耳目皆無所見聞也。耳目之所知者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謂自然而然也。”參見林希逸:《莊子鬳齋口義校注》,周啟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50頁。
②參見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修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68頁;劉暢:《寓言隱喻:作為一種“思想修辭”范疇——以〈莊子〉為分析文本》,載《浙江社會科學》2020年第3期。
③參見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321、322 頁。
④例如,“官者,主司之謂也。謂目主于色、耳司于聲之類是也”。參見《莊子注疏》,郭象注,成玄英疏,曹礎基、黃蘭發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65頁。“官,耳目鼻口也。”參見《莊子鬳齋口義校注》,第50頁。“官謂手足耳目之官。”參見陸西星:《南華真經副墨》,蔣門馬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49頁。“官,謂耳目等五官也。”參見釋德清:《莊子內篇注》,黃曙輝點校,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64頁。劉笑敢、王博、畢來德都持此種觀點。參見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修訂版),第168頁;王博:《莊子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51頁;[瑞士]畢來德:《莊子四講》,第9頁。
⑤ 劉笑敢、方勇等學者都持此觀點。參見劉笑敢:《莊子哲學及其演變》(修訂版),第168頁;方勇:《莊子學史》(第一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頁。
⑥例如,釋德清只說“而神即隨其所行”,未對其進行解釋。參見《莊子內篇注》,第64頁。林希逸則是將其表述為“不言之神”,也未具體闡釋。參見《莊子鬳齋口義校注》,第50頁。
1 “‘神超越了耳聰目明,但又統合了耳聰目明。神不只統合了耳聰目明,它還統合了全身的動作。”參見《儒門內的莊子》,第322頁。“這個‘神只能是行動者本身那種完全整合的動能狀態。”參見《莊子四講》,第9頁。
②參見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石濤之一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63頁;陳少明:《“庖丁解牛”申論》,載《哲學研究》2016年第11期;陳赟:《論“庖丁解牛”》,載《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2卷第4期。
1“氣無情慮,虛柔任物。故去彼知覺,取此虛柔,遣之又遣,漸階玄妙也(乎)。”“如氣柔弱,虛空其心,寂泊忘懷,方能應物。”參見《莊子注疏》,第80、81頁。
②“他所追求的精神生活,不能在人的氣上落腳,而依然要落在人的心上。因為氣即是生理作用;在氣上開辟不出精神的境界;只有在人的心上才有此可能。”參見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348頁。
1如郝大維、安樂哲從一與多、同與異的角度來分析此處。參見[美]郝大維、安樂哲:《孔子哲學思微》,蔣弋為、李志林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0頁。
②正如福永光司所說:“‘耳目之所宜指的是聽到便覺得悅耳、看到便覺得悅目,泛指所有以感官為媒介的價值判斷。‘不知則說的是不被這種感覺判斷所束縛。” 參見[日]福永光司:《莊子內篇讀本》,王夢蕾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9年,第 172 頁。
1心靈轉化需要契合道、氣、德,這一點可參考以下文本:“臣之所好者道也。”“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游心乎德之和。”參見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11、137、1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