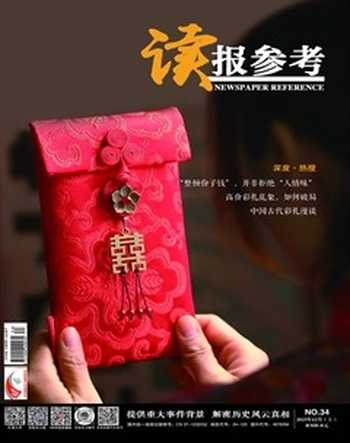連麗如:說書也新潮
連麗如,1942年生于北京,著名評書表演藝術家、評書大家連闊如之女;創辦宣南書館,錄制《東漢演義》《三國演義》《康熙私訪》等長篇評書;曾到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等地演出,是把評書帶到國外的第一人。近日,她參與編著的《江湖續談》一書出版,再次引來各方關注。
“父親是評書藝人,也是媒體人”
連闊如是京派評書的代表人物、連派評書的創始人。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名滿京華,曾有“千家萬戶聽評書,凈街凈巷連闊如”一說。“每天中午12點,北京大街小巷,綢緞莊、理發館,門口擱著大喇叭(不是家家都有收音機),蹬三輪的不蹬了:‘拉您上珠市口,不成。我得把連闊如這段《東漢》聽完了才走呢。我放學路上回家,廣播里都是‘姚期馬武岑彭杜茂,至今記憶猶新。”連麗如說。那時候,連闊如還以“云游客”為筆名,在北平《時言報》上發表長篇連載“江湖叢談”,種種曲藝沿革、行業規矩、騙術內幕信手拈來。1936年,文章被結集成書《江湖叢談》出版,暢銷京城。后人稱它“奇人奇書”。
編著《江湖續談》,也是連麗如重新認識父親的過程。“說起來,父親不僅是評書藝人,也是媒體人,算是你們的同行。他不僅做過報館的編輯,也親自作過很多采訪調查。”連麗如對記者說。《江湖續談》里有一篇文章《社會調查之一老豆腐鍋伙》,講的就是老豆腐買賣人的生活。所謂鍋伙,在當時指單身工人、小販等組成的臨時性的、設備簡單的集體食宿處。通過調查,連闊如發現當年的北京,做老豆腐買賣的涿州人居多,花幾元錢置份挑兒,往老豆腐鍋伙一住,熬一鍋豆腐,“平均起來,每人能賣六七斤豆子,維持生活綽綽有余”。
連闊如好奇心極盛,每逢聽見哪兒有奇事,總得要去瞧瞧。有一日,他聽聞來了位沒有雙臂的怪人“萬能腳”,便前去拜訪,并作了一問一答的采訪,寫成文章,將那人的來龍去脈一一道來。此外,他還到天橋探訪女演員唱大鼓說書的茶館,揭秘江湖藝人賣大力丸、萬應膏的內幕……
連麗如記得第一次說書時,父親叮囑了一件事——貼身靠兒。“這是行話,就是每天開書前半小時,要坐在書臺上,和聽眾聊天兒。聽眾往往比你知道得多,聽的書也多。”連麗如說。直到現在,她始終不忘父親的這個理兒。下午兩點開書,她總會提前到,坐在門口賣票的方桌后,和相熟的聽眾寒暄閑聊。
懂多大人情說多大書
從18歲登臺說書到現在,除去在工廠的12年,連麗如說了半個世紀的書。但最初,父親并不愿意讓她走這條路。轉變發生于1958年,連闊如被下放到書館說書。不久,連麗如從師大附中退學,看到父親身邊沒有徒弟,她決定學評書。早先,連闊如認為女孩子不能說書,但在上海看到了評話名家王少堂的孫女王麗堂,16歲就上臺說“武松打虎”,很受啟發,最終同意了。
1960年,連麗如進入宣武說唱團當學員。她學評書,從聽書開始,“不聽書,不接觸社會,就學不出來”。這年冬天,她第一次去茶館聽父親說《三國》,從劉、關、張,說到伯樂、姜子牙、酈食其。后來,在東安市場鳳凰廳,她又聽父親說《列國》,“記得最清楚的是他說‘竊符救趙,講虎符,講那上面的花紋是怎么回事,整整講了一場”。散場后,父親還帶她逛東安市場,一邊逛一邊講東安市場的形成、鳳凰廳的由來,講風俗人情、衣食住行。
在連麗如看來,連派評書重在一個“評”字,評人、評事,也評情、評理。父親說書,不只是說事件,而且對當時的歷史背景、官制禮節、民間風俗、地理山川以及武術拳腳、戰爭場面,都講得頭頭是道。他向生活中各個階層的人求教,也請教學有所成、術有專攻的文人學者,還查閱古代典籍,手不釋卷。
一年后,連麗如就登臺說書了。評書演員要學張飛、說李逵,過去沒有女演員,她是中國第一個評書女演員。頭一次說長篇大書是在天橋劉記茶館,“爸爸花50塊錢,給我做了一件和王麗堂一樣的青緞子夾襖,綢子里兒,琵琶盤扣兒”。1961年9月1日到30日,她從“三讓徐州”開書,一直說到劉備進西川,每天倆鐘頭,天天滿座兒。當時,她沒在臺下看到父親,后來聽眾告訴她:“連老先生來了,在窗戶外面,看你說書。老爺子流了眼淚,走了……”
連麗如在說書界算是有了一席之地。剛說書時,因為拔尖,脾氣又執拗,她總受排擠,經常鬧得不愉快。父親就勸她收起學生作派,多學些江湖規矩和人情世故。后來,說的書多了,吃透的人物多了,她漸漸懂了其中的道理。
有一天,她問父親:“怎樣才能成為一個評書藝術家?”父親說:“要想成為一個藝術家,你再聰明、再能干、再能說,可是有一樣要記住——說透人情方是書,懂多大人情說多大書。心眼兒窄的人絕說不了肚量寬的書,你將來懂得人情世態了,必能成家。”這句話,令連麗如豁然開朗,她也銘記至今。
1964年,曲藝界開始“說新唱新”,禁止說傳統書目,連麗如《東漢》剛說了7天,停演了。3年后,宣武說唱團解散,她被分配到人民食品廠,每天收汽水瓶子,此后12年再沒上臺說書,直到1979年。
把真正的藝術遺產接收過來
評書最講傳承。“傳的是什么?是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1979年重新登臺后,連麗如便恢復了長篇大書的演出。她“闖關東”,為電臺、電視臺錄制《東漢演義》《康熙私訪》等多部評書;她“下南洋”,從1993年起多次到新加坡、馬來西亞演出、講學,后來還把評書帶到了美國。2007年,她創辦宣南書館,同年收王玥波、李菁、賈林、梁彥為徒。
“我辦書館的目的不是懷舊,而是讓評書藝術更有活力,讓更多年輕人來聽來學,把這門藝術傳承下去。”連麗如說,評書的魅力都在書館里,在現場親眼看、親耳聽。而作為臺上的說書人,“書在腦子里隨編隨說,不容你考慮,一人一臺戲,服裝、布景、導演、演員、群眾、角色都是我。動手交鋒,還得十八般兵刃件件精通,一部書說下來幾十天,說完回家,累得邁不開步,卻有種說不出的愉快”。
宣南書館如今常常是座無虛席。“許多人認為聽評書的大都是老年人,其實不然,聽書的主流是中青年,小學生也越來越多。要說這年輕人為啥喜歡?評書表面上是講故事,實際講的是社會道理、人生哲理,能夠豐富人生閱歷,懂得許多社會知識,對當下的工作、生活都有很大幫助。”對她來說,長篇大書早已說得滾瓜爛熟,現在難在“攏神”,“我得與時俱進,知道現在的聽眾想聽什么,有的聽眾一走神,得馬上換內容,必須把觀眾攏住”。
為了攏住觀眾,連麗如時刻關注當下社會的流行,關注不同觀眾的喜好。有一次,她說《列國》,講息媯的故事。息媯被楚王納入后宮,封為夫人。楚王死后,其弟弟子元愛慕息媯,在她的宮室旁邊造一座房舍。得知息媯晚上賞月,子元出來唱歌表白。說到這里,連麗如開了嗓,唱:“你問我愛你有多深,我愛你有幾分,我的情也真,我的愛也深,月亮代表我的心……”“就點綴這一分鐘,與臺下觀眾就通了,給你反應了,這段就成了。”
“你必須得跟聽眾相通。我的聽眾都說我很新潮,一點兒不像80多歲。”連麗如自豪地說。她有兩個手機、一臺iPad,每天看新聞,偶爾刷刷抖音。她也關注到現在網上不少人在“說書”,“拿起一本書,稍加改動就錄下來,放網上播,可播完了以后,你就會說書了嗎?”
“其實,我已經這個年紀了,所有的精氣神,都凝聚在了那每周1小時的舞臺上面。”連麗如說,她舍不得舞臺,離不開聽眾,依然在等待著下一次開場。
(摘自《環球人物》陳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