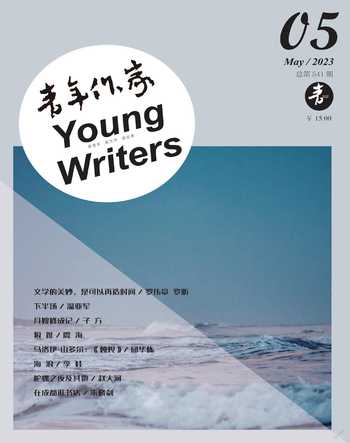斑馬線
一
天還沒有亮,張小魯就起床了。迷迷糊糊之間,若蘭覺得自己剛挨著他躺下不久。耳邊盛開的窸窣聲,淹沒了她一肚子繁茂的私心雜念。她伸出光溜溜的手臂去摸,那個壯實的男人已跨過自己下床了。客廳里的燈亮了一下又滅了,像眨了眨蒙眬的睡眼。很快,樓下就響起了大貨車的響聲。
空氣流淌著火,身體也流淌著火,整個世界就像一個被藍焰包裹著的煤球,即使夜里也沒有一點涼意。張小魯剛坐進駕駛室里,就出了一身大汗。黑暗中的公路像一個幽深的煤窯,燈光打在上面閃著鐵青色的光芒。他要把車開到百公里外的煤廠,那是方圓百公里唯一允許開采的煤礦。頁巖磚廠需煤量大,拉煤的大車也多,只能按先來后到的順序排隊。去晚了,車子就會排到后面,等裝好煤天就黑了,再拉到磚廠后回家就是半夜了,兩頭都不見天亮。多年黑白顛倒的生活讓張小魯覺得自己活得像個鬼一樣。
今年夏天的氣溫高得離譜,很多司機就歇人歇車了。張小魯還在堅持拉煤,運費是家里唯一的收入來源。
車窗外的樹木、房屋還是一串黑影,遠山是一張折痕不齊的黑紙,一齊向他涌來。張小魯在這條路跑了十多年,他知道每一處的情況。他根本不在乎車窗外鬼魅般的黑暗,他心里想的是若蘭。昨晚,她是幾點回來的?有好長一段時間了,若蘭都回得晚,有時候到了凌晨才回家。張小魯辛苦了一天,回家倒頭便睡,她回來的時候,他睡得正香。他們只能在黑夜里見面,在黑夜里相愛,他努力在腦海中翻找若蘭的模樣,可是只有一團模糊不清的樣子。
張小魯把車開到煤廠的時候,天空中才透出一層迷蒙的灰白色來。河谷仍然一片灰暗,只有橘黃的車燈錯亂地在黑色的山谷里晃動著。貨車沉重的喘息聲此起彼伏,湍急的河水發出巨大的轟鳴,把原本寧靜的大山吵成了一個熱鬧的早市。煤廠在河谷東邊的大斜坡上,煤窯在陡峭的坡腰上,除了兩根粗壯的滑索和黑洞洞的窯口外,就只能看見一面凹凸不平的黑乎乎的山坡。
從出煤口下來,橫倒的M型黑泥路上已經排了十五六輛大貨車,河對岸的公路上還有車燈在晃動,正朝山谷里開過來。他把車開上坡,趕緊排在那條粗壯的長龍后面。
“哧——”張小魯拉起手剎,車子發出了刺耳的放氣聲,他打開車門跳了下來。淡藍色的彩鋼棚里早已坐了人,有的趴在黃色大圓桌上睡覺,有的坐在鋼條椅子上抽煙,還有人精神頭十足地相互開著玩笑。棚子靠著山體的一側是三間簡陋的廠房,住著掏煤工人和工頭,當中隔著一間水泥空心磚砌起來的食堂。食堂里冒著騰騰的熱氣,胖大姐正在給大家煮面條,十塊錢一碗。靠墻角的一個簡易木架上有香煙、方便面、袋裝鹵味小吃等小商品,工人們早已吃完飯進窯出煤去了,她是在給司機們準備早飯。司機們起得早,幾乎都沒有吃早飯就開車上來排隊了。等著裝煤的時候,司機們就堵在那間彩鋼棚里抽煙、打牌、擺龍門陣。
張小魯用微信掃了十塊錢,要了一大碗面條,又自己動手調了油辣椒、面條鮮、陳醋,還特意加了兩個鹵雞蛋,才端到外面桌子上來坐下吃。往天,他通常只吃面條,有時也只買一袋方便面吃。今天算是奢侈了。但他胃口不好,覺得胸口有一股子濁氣堵著,心情不舒暢。
他吃完面條才開始吃那兩個茶色的雞蛋,但手有些笨拙,挑了幾筷子都沒有撈起來,還差點掉到了地上。他把肥厚的嘴唇放到碗邊,才把雞蛋趕進嘴里。
“張胖子,你好久沒有吃雞蛋了吧?”
張小魯白了麻桿一眼。麻桿身材瘦弱,叼著一支細桿煙,細直的煙霧從鼻尖升上去,把一臉嬉笑劈成了兩半。
“不吃能長這么胖?”
“胖也是虛胖。干正事不行。”
“都像你?”
“看你鬼迷日眼的樣子,昨夜肯定沒有干成好事嘛。”
張小魯心里陡然有些生氣了,但他還是涎著臉笑了。
“都像你。”
二
“不打了。”
張小魯斗了幾把地主,輸掉三十多塊錢,賭氣將紙牌扔在桌上。
“你咋是這個樣子喲?平時贏我們那么多錢。”
“他不來,我來。”旁邊早有人按捺不住,很快填補了空缺。賭場從來不缺人。
張小魯沒有回答,點了一支煙,徑直向棚外出煤口走去。今天出煤慢,天氣太熱,工人少。麻桿和老工人正在裝車,他在上面又蹦又跳,像籠子里一只找不到出口的長臂猩猩。隨后又從老工人手里奪過鐵锨在車頂使勁兒拍打。
“你看你喲,多裝得了幾斤?”張小魯覺得麻桿整得太夸張。
“你沒整過?”
張小魯從地上撿起一個空煙盒,裝了兩支煙,又裝了一塊亮晶晶的煤在里面,向車頂拋了上去。麻桿伸手接住,遞給老工人一支,吹了一口,也給自己點上了。
“這就走?”張小魯問。
“不走,你管午飯啊?”
麻桿抓住車幫一躍而下,拍了拍手上的灰,又在屁股上搓了兩把,便鉆進了駕駛室。見張小魯沒有上車的意思,他又使勁按了一下喇叭,把張小魯嚇了一大跳。“上車啊。”
張小魯一邊掏車鑰匙一邊往棚子里跑去。轉眼之間,他又跑回來上了車。
回程的公路順河而下,陽光燎烤著大地,對岸山坡上的玉米地一片枯黃,公路兩邊的稻田里,谷子黃了,田埂都裂開了。灼熱的風撲進駕駛室里,像是給人淋了一身開水。張小魯戳了一下按鍵,打開空調,駕駛室里隨即風聲喧鬧。麻桿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沒有說,要是他一個人的話,是舍不得開空調的。常年風里雨里,他們都習慣了。
煤、運輸、頁巖磚,形成了縣內一條重要的產業鏈。這條公路去年剛剛整修過,水泥路面上標線清晰醒目,公路穿過小鎮的時候,改成了漆黑的瀝青路面。張小魯跳下車,鞋子像是墊著海綿,太陽將瀝青曬軟了,黃色的中心線粘上了瀝青黑斑和輪胎灰印,已經不太清晰。麻桿的車高高在上地碾過瀝青路面,不時搖晃幾下,又喘著粗氣。他開得緩慢而小心,似乎比通過一段坑洼不平的泥濘路還要艱難。
小鎮沿河而建,像一只龐大的腔腸動物,那條公路直通首尾,只在橋頭有一條分岔公路向右延伸出去。路口設置著小鎮唯一的斑馬線,連紅綠燈都沒有安。那組白線油污不堪,“禮XX人”中間兩個字看不太清了。斑馬線右面,掛著清閑居茶樓淡綠色的大招牌,小鎮上很多人在那里面閑度四季時光。今年天熱,茶樓的生意特別火爆,空調從早開到晚,老板還管飯,如果晚上不想回家,還可以在房間的沙發上將就一晚。
若蘭不在家。肯定又到茶樓去了。一開始,張小魯并不想讓若蘭到茶樓去。
“我一個人在家,就是浪費。”
若蘭抱怨她成天無事可做,要開空調,要買菜做飯。到茶樓里去,不僅能混時光,而且不做飯不費電,劃算得多。張小魯覺得若蘭說得有道理,自然也不勉強,他也不敢勉強。
當初,若蘭是看不上他的。若蘭長得漂亮,苗條,是當地為數不多的美女之一。張小魯胖,一動全身的肉都在抖動,但他實誠、顧家,跑了幾年大貨車,不僅還清了買車的貸款,而且還改造了臨街的瓦房,建起一幢三層樓的新磚房。若蘭的父母看中的正是這一點,如果女兒嫁過去,日子會過得衣食無憂。“帥氣能當飯吃?還是找個老實人安穩些。”
若蘭覺得自己嫁得勉強,心里總有一種失落感。要是繼續外出務工,憑她的模樣找個好工作不是多大的問題。但到了父母催婚逼嫁的年紀,她也只好將就了。
三
淘了一小碗米放到電飯鍋里后,張小魯拿出兩個土豆削皮切片,又切了三個泡椒兩根泡豇豆。一個人吃飯,他只需要做一個酸辣土豆片就夠了。躺在沙發上看了一會兒手機,電飯鍋就跳閘了。他把鍋里的飯和菜全部盛在一個不銹鋼大碗里,端到客廳沙發上吃起來,若蘭是不會回來吃飯的。家里無所事事的日子,讓她閑得無聊,她學會了打牌,而且一玩就上了癮,沒有時間給他做飯。最近,經常到了凌晨才回家。
張小魯吃得滿身大汗,肚子更加圓了。他沒有開空調,一個人在家沒有必要浪費電。再說,屋里比太陽下好多了。洗好鍋碗,他就站在陽臺上抽煙,目光慵懶地掃描著街面。對面人家的空調都在忙碌著,風機上積了一層黃土。一個月沒有下雨,一個月持續高溫,人行道上的小葉榕樹精神不振,葉子軟塌塌的。那條灰黑的柏油馬路上面散落著白的紅的黃的紙巾、雪糕袋、零食袋,在正午陽光的照射下,像是一片正在燒烤的海帶,冒著滋滋的油光。路口那組白色的斑馬線僵直地橫躺著,腳印、輪胎印為它薄薄地蓋了一層陰涼。張小魯想把煙蒂扔到馬路上,他又擔心會把那條油滋滋的馬路點著了,在陽臺瓷磚上使勁地揉了一圈,才扔下了樓。他準備回到客廳,在沙發上睡個午覺。
這時候,他看見住在斑馬線左面的楊三娃子從樓梯間下來了,那樣子是要到對面的清閑居茶樓去。他穿了一件寫滿五顏六色字母的T恤衫,黑色西褲筆直堅挺,腳上是一雙锃亮的高幫皮鞋。他洗了頭,梳著整齊的分頭,面容白凈。他走路一陣風,衣袂飄飛,風流灑脫。
“手機里一千塊錢都沒有,瀟灑個球。”
張小魯歷來看不起他。那是一個好吃懶做的二流子,除了像女人一樣打扮自己,啥也不會干。看人嘛,體體面面的,但口袋比臉還干凈,家里亂得像雞窩。他那個苗條瘦小的老婆經常被他打得鼻青臉腫,很少有人看見她抬起頭在大街上走過。
張小魯見過一次她的臉。那是去年夏天一個下午,他從河邊洗澡回來,那個女人端了一盆鹽菜到河邊去淘洗。他往上走,她往下走,錯身而過的時候,女人看了他一眼。一縷頭發從她窄瘦的臉上垂下來,半掩了女人的小嘴直鼻,那雙眼睛透著半是春水半是桃花一樣的憂傷,眼角似乎有一滴清淚隨時會掉下來。張小魯覺得那滴眼淚隨時會砸在自己的心上。他故意向她那邊撞了一下,女人有些驚慌,向旁邊一閃,隨即又抬起頭來,眼睛里閃現出一絲被擠壓的張皇。
楊三娃子并不喜歡那個女人,幾乎天天都在清閑居茶樓里混,一日三餐也在茶樓里解決,他和一群年齡大小不一的女人們熟得很,大家都愛拿他開玩笑。再出格的玩笑,他都不生氣不發火。他偶爾回家,不是洗頭洗澡,就是換一身衣服,再回到茶樓來。張小魯覺得他唯一的優點就是不抽煙。
小時候,街坊四鄰常拿兩人說事打趣,說到老實顧家的時候,就拿張小魯做榜樣。說長得俊秀,穿得干凈,就拿楊三娃子做榜樣。兩人從小心里就較著勁,努力把自己的優點發揮得最好最明顯。若蘭最早是被媒人說給楊三娃子的,若蘭倒也沒有什么意見,但她父母不同意,認為長得再好看也不能當飯吃,過日子還是要實誠些好。媒人靈機一動,轉頭又把她說給了張小魯。若蘭有些不情愿,但父母喜歡。從此,兩個男人心里又多了一層尷尬和戒備。
路口的斑馬線,像一座懸在深淵上的吊橋,橋面高低不平,被慘白的光照得時隱時現,橋下地獄一般幽暗,閃爍著點點磷光。楊三娃子左右看了兩眼,才將皮鞋輕輕放到那串白色的木板上,他怕瀝青粘到了鞋底上。有一輛小車從他前面閃過,風卷起了衣衫,那橋似乎隨著他的步子一左一右搖擺起來。張小魯心里一陣發緊,生怕他掉進了無底的深淵。可轉瞬之后,他又高興起來。掉下去才好呢,免得看著心煩。
楊三娃子周周正正地走過斑馬線,站在人行道上跺了跺腳上的瀝青,又向左右看了兩眼。看見張小魯站在陽臺上,他把頭一揚,就踏進了茶樓升起的卷簾門里。
“神氣個啥?馬屎外面光,里面一包糠。”張小魯也把頭一揚,向路口吐了一口唾沫。
躺在沙發上,他熱得睡不著,若蘭吃飯了嗎?若蘭和楊三娃子說話了嗎?他們開的什么玩笑?他一腦子疑惑。
四
火紅的太陽落山的時候,張小魯才把煤拉到磚廠,煤坑前堵著一面厚實的紅磚墻,剛出窯的磚還沒有來得及轉運。張小魯嘆了一口氣,只好把大貨車停靠在一邊,接著跳下了駕駛室。
“好久能搬完?”他生氣地嚷了一句。
“估計要到晚上九點多。”
“咋把煤坑堵上了嘛?”
“天熱,人手少,搞不過來。”
“搞快點哈。”說完,他給叉車師傅遞了一支煙。
磚廠老板不在,他打開車門坐在駕駛室里給他打電話。“今天的煤34噸。”
“多4噸?”
“你要不來看一下。”
“不來了,我曉得了。”
掛掉電話,張小魯就坐在駕駛室里刷視頻。他只好等著,他要把煤卸完,把車開回去,明天早上才好早起去排隊。
回到小鎮停好車,已經是晚上十點了。張小魯在樓下看到,客廳里亮著燈,掛在墻上的空調風機嗚嗚地轉個不停。今晚回來得這么早?打開房門,一陣涼意,若蘭果然在家。她穿著睡衣,蓋著涼被,躺在沙發上看手機。聽到門響,她眼睛向上翻了一下,目光從額頭上滑過,又穿過蓬松的頭發看過來,隨即又收回去盯著手機。張小魯看見她拉著臉不高興的樣子,心里倒是一喜。輸了吧?這下可能要歇幾天了。
“咋這么晚才回來?”若蘭心里似乎有氣。
“在磚廠等他們卸煤。”
“往天不是早就回來了嗎?”
“煤坑騰不出來。對了,你今晚咋不打牌了?”
“打個鏟鏟。”
“哪個惹你了?”
“莫哪個。”
張小魯不再過問。他起身到廚房里轉了一圈準備做飯。
“你還沒有吃飯?”若蘭的話冷冷的,在張小魯的心里驚起了一陣風。
“你吃了?”
“沒有。”
“咋不做飯吃呢?”
“不想做。”
“你想吃啥?”張小魯轉身又向廚房里走去。
“別做了,我們出去吃吧。”
“好吧。”張小魯猶豫了一下,心里有些涼意。
晚上睡下后,若蘭說,今天在茶樓里,那一群娘兒們開玩笑,說他長得黑,像個掏煤的,她簡直就是一朵鮮花插在了煤堆上。而且經常不在家,兩人的夫妻生活肯定不好。不然,結婚都快三年了,她那肚子咋還不見一點動靜呢。她們說話露骨,羞得她頭都抬不起來,恨不得推倒了牌就走。但賭博場上,她不能這樣做,否則以后就沒有人跟她同場了。見她不說話,她們就更加放肆了。楊三娃子在另一個房間打牌,若蘭有意不跟他同場。他和了牌,上完廁所手都沒有洗就跑到她這邊來看牌。若蘭把牌全部扣了,不讓他看。他又指揮她打牌,她偏不聽他的,結果讓對門糊了自己一個大番。若蘭有些生氣,說他給別人遞眼色,聯合起來欺負她。哪知那群娘兒們又拿她取笑,說她和楊三娃子才般配,是天生的一對好夫妻,哪有夫妻胳臂外拐的呢?楊三娃子肯定是真心幫她的。還說,當初她要是同意了楊三娃子,現在就名正言順了。楊三娃子也嬉皮笑臉地跟她們一起說,如果跟他成了夫妻,他們就是一對革命同志了。說完,他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拍拍,又把手伸過來,想跟她來個革命同志式的握手。若蘭生氣,一巴掌打開了他的手,推了牌就走了。
若蘭受了欺負,張小魯覺得自己吃了啞巴虧。但這種事兒,找誰去算賬呢?
“輸了好多錢?”
“三百多。”
“輸了就算了。以后少打吧。”見若蘭埋著頭不吭氣,張小魯又說:“我多跑一趟車就賺回來了。”
第二天,張小魯照舊早早醒來了。若蘭伸出光溜溜的手臂摸了摸男人壯實的脊背和寬闊的肚腹,偏頭又睡了。客廳里的燈亮了一下又滅了,很快,樓下就響起了大貨車的響聲。
五
天氣還是熱得像火烤,張小魯覺得昨晚開空調,一冷一熱,中暑加重了一些,渾身燒得發燙,頭腦暈乎。車窗外,玉米秸響起一陣焦黃的碎裂聲,楊樹葉在黑暗中低垂著,張小魯來得早,搶到了一個好位置,比以前的排位前進了五輛車。他跳下車,來到食堂里,買了一袋方便面,又自己燒了一壺開水泡上。河谷里仍舊沒有涼意,他撩起煤跡斑斑的襯衣,抹了一把臉上的汗水,敞露出鼓圓的肚子。
“狗日的張老板,掙了我們這么多錢,連電風扇都舍不得給我們整一個。”
沒人理他,來得早的司機們有的在駕駛室里睡覺,也有的來到彩鋼棚里把兩張椅子連起來躺在上面補瞌睡,還有的在山南海北地擺龍門陣。
張小魯把方便面吃得山響,香氣四散。躺在椅子上睡覺的人皺了一下鼻子,喉頭一聲輕響,痰水濃重地咳嗽了一聲。
“我看你那個樣子,昨晚肯定吃了一頓飽飯嘛。”
“飯都不吃夠,哪有勁來掙錢嘛。”張小魯說完,又要了一包方便面泡上。
湛藍的天空里鋪排著瓦塊一樣的白云,清澈地籠罩在河谷上。張小魯望著天空,坐在棚子里悠閑地抽煙。煤廠這面坡還籠罩著一片藍色陰影的時候,就該他裝車了。
“師傅,你負責放煤,我來幫你裝車。”
老工人把鐵鍬交給張小魯,就爬到索道旁邊的小煤車旁坐下了。張小魯賣力地把他放下來的煤平鋪到車廂里,又用鐵鍬拍打一遍,接著又撒上一層,再拍一遍。
“差不多就行了,別人看見不好。”老工人在小煤車旁邊抽煙。張小魯似乎沒有聽見他說話。
車廂裝滿后,張小魯抬頭對老工人說:“再放一車。”
他把那一小車煤均勻地灑開,再把四邊的煤往當中趕了趕,又掄起鐵鍬把三面拍結實,才把鐵鍬遞給老工人。
張小魯開車到達小鎮的時候,太陽還沒有把瀝青路面照全,靠河邊的半邊路面黑得似乎要把路面壓翻。他抹了一把臉上的汗水,遠遠地看見了若蘭,正向清閑居茶樓的方向走去。她穿了一件淡綠色的連衣裙,腳上的高跟鞋敲打著人行道上的青灰色地磚,苗條的身姿如風一樣擺蕩著。張小魯加了一腳油,想上前跟她打個招呼。若蘭沒有發現張小魯的車在身后,每天經過小鎮的拉煤車多得讓人熟視無睹。她看了一眼手機,又向公路對面看了看,繼續往前走。來到斑馬線的時候,她站在那里盯著手機,手指飛快地打著字。楊三娃子從樓梯上走下來,妖嬈地向路口走來。若蘭向對面看了一眼,臉上蕩漾著一圈笑意,隨即頭一揚,快步向茶樓走了上去。楊三娃子也快步走過斑馬線,把一座吊橋踩得左搖右晃。張小魯加了一腳油,貨車轟隆隆地叫了起來,向前竄了一下,輪胎在軟軟的路面滑了一步,車身晃動了兩下,把散碎的煤灑到了路面上。張小魯本能地踩了一下剎車,向右打了一下方向,又趕緊向左邊打了一點方向。楊三娃子飛身向人行道上跳去的時候,龐大的車身就從斑馬線上碾了過去。
張小魯覺得自己燒得越來越迷糊了。
六
小鎮來了一車警察。烈日下,全鎮男女老少都出動了,把橋頭路口擁得密不透光。漆黑的瀝青路面更黑更重了,各式各樣的鞋子掩蓋了斑馬線,掩蓋了那座懸掛在深淵上的白板吊橋。
“讓開,讓開……”
警察一邊轟趕著人群,一邊拉起了警戒線,把一張薄薄的灰色床單覆蓋的楊三娃子和一大攤烏紅的血跡圈了起來。
“誰是車主?”
張小魯趕緊跑上前去,“我是。”
“把證件拿出來。”
“在車上。我去拿。”張小魯趴在車上,高高地撅著肥碩的屁股。
“說一下情況。”警察大檐帽下有一張鮮紅的嘴,一口細密的白牙,上唇一抹淡青色。但字語清晰威嚴。
張小魯簡單陳述了事情的經過。這段時間,天氣太熱,把瀝青路面曬軟了,輪胎有點打滑。曉得這個情況,自己開車很小心,尤其是過場鎮街道的時候,是小心了又小心,生怕出了事。事情怪就怪在,越小心越出事。這幾天拉煤的人少,裝好煤他還在河邊休息了半個小時,洗了一個澡,抽了兩支煙,整個人就感覺到很涼快。
“說重點。”
“我把車開到小鎮的時候,就快要吃午飯了。我開得很慢,很小心。路面打滑,我不敢開快了。快要到這個路口的時候,我看見楊三娃子穿著一件五顏六色字母的T恤衫正在過斑馬線,他想到對面的茶樓去打牌。我又不敢踩剎車,就使勁按了一下喇叭,我想提醒他有車。他轉頭看見我的車來了,還向我笑了一下,像是在給我打招呼。我們是街坊鄰居,從小就認識。我又按了一下喇叭,示意讓他快點走過去。哪個曉得,他又轉身往回走,我又不敢剎車,就把方向盤往右打了半圈。可能他覺得跑回對面要遠些,又折身往右邊跑過來。我看見他跳起來想跳到人行道上去,可是來不及了。他被撞出三米多遠,輕飄飄地落到了地上。眼看就要碾上他了,我又趕緊往左打方向,車子就沖進了那間商店里,右后輪胎就把楊三娃子掃上了。你看,車上的煤灑得到處都是,楊三娃子都埋進了煤堆里,證明我是采取了緊急避險措施的。但是,我們把他掏出來的時候,他就斷了氣。我嚇慌了,還是他們提醒我,我才趕緊報了警也報了保險。”
“還有其他事情沒有?”
“沒有。”
事故發生后,那個懦弱的小女人把街面上的門面騰空,搭起了靈棚,又請人買了一副棺材裝殮了殘缺不全的尸首。張小魯從派出所回來后,先和女人談妥了賠償事宜,又幫助女人把楊三娃子送上了山。小鎮很快又恢復往日的寧靜,只是若蘭這段時間一直沒有出去打牌,天天躲在空調屋里發怔,依然不買菜不做飯。張小魯偶爾回來做好了飯叫她,她總說不餓,像丟了魂一樣,人也瘦得肩胛窩能養金魚。喊她睡覺,她也不睡,張小魯就把她抱到床上躺下,但她整夜都睡不踏實,嘴里含混地嘀咕著什么。
警察出具了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張小魯承擔百分之六十的責任,楊三娃子承擔百分之四十的責任,死亡賠償可以參照這個比例。但是,張小魯已經和那個女人談妥了,他幾乎承擔了全部責任的賠償。保險公司賠付了大部分,剩下20萬元還需要張小魯自己承擔。張小魯從銀行里取出了10萬元現金,又找人借了10萬元送到對面女人的家里。
若蘭仍是一副精神不振的樣子,張小魯照常出車,回家后還是小心照顧著她。晚上,張小魯關切地問:“嚇著你了?”若蘭搖了搖頭,張小魯一聲嘆息。
“若蘭,我們結婚已經兩年多了,你跟著我受苦了。我沒有別的本事,只會開車。我給不了你想要的生活。這次出事后,家里還要掙錢還賬,往后的日子可能更加艱難。要不,我們離婚吧。我不能拖累了你……”
若蘭怔怔地聽著。
“以后你就可以去追求你想要的生活了。”
若蘭哭出了聲。
“好在我們還沒有孩子。只要你同意,我們可以協議離婚。”
若蘭倒伏在沙發上,裸露的肩背不停地抽動著。
“我們不爭不吵,自愿離婚,辦理起來快。”
若蘭眼中淚水無聲地滑落下來。
第二天早上,若蘭收拾了一個行李箱,坐上了一輛長途車走了。小鎮上的人都說,張小魯扛得起事情,對若蘭也好,是一條漢子。
晚上,張小魯回家,站在陽臺上抽著煙。暗藍色的天空中云影飛動,月光下的瀝青路面一片漆黑,路口的斑馬線時隱時現,仍像是掛在深淵之上的一座吊橋。公路對面,楊三娃子的家里燈光昏暗,粉色的窗簾拉上了,上面固定著一個女人的身影。張小魯看見,那身影低著頭,臉龐窄瘦,小嘴直鼻,神態憂傷,像春天里粉色的桃花雨砸在自己的心上。
【作者簡介】馬希榮,生于1973年,四川通江人;作品發表于《青年作家》《草原》等刊;著有報告文學集《村上一棵樹》;現居四川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