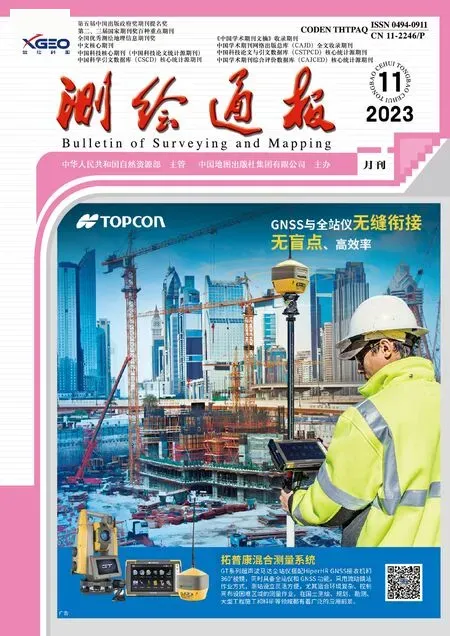平原農區全域土地綜合整治“三生”空間格局優化效果評價
江 嶺, 張大鵬, 黃丹妮, 黃驍力, 陳 西, 李 鵬, 陳萬里, 汪永豐, 王 崠
(1. 滁州學院實景地理環境安徽省重點實驗室,安徽 滁州 239000; 2. 安徽省國土空間規劃研究院,安徽 合肥 230601; 3. 肥東縣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安徽 合肥 230601; 4. 安徽建筑大學環境與能源工程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平原農區是指地形以平原為主且經濟活動中農業占主要地位的地區,已成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核心區[1]。作為平原農區人類、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載體,“三生”空間(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和生態空間)格局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國土空間開發保護的質量與效率[2-4]。然而,隨著快速的城鎮化進程,“三生”空間布局不協調的問題日漸突出,造成了生產空間低值低效、生活空間無序空廢、生態空間無序污損等問題[5-6]。“三生”空間既相互獨立又相互關聯,是一個共生共融、緊密聯系的有機整體,合理優化“三生”空間格局可以實現整體效益大于部分效益之和[7-9]。因此,加快“三生”空間格局優化是平原農區構建高質量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新格局的迫切需求,對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實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10-12]。
在國土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在“三生”空間內,從全區域視角統籌安排農用地整治、建設用地整治和生態保護修復等內容,是一項綜合性系統工程[13-15]。相較于傳統的土地整治,全域土地綜合整治更加強調整治范圍的整體性、整治對象的綜合性,并以優化“三生”空間格局為基本內容,已成為當下國家正在推進的重大工程[16-17]。相關實踐表明,全域土地綜合整治所產生“三生”空間格局優化效果的優劣直接影響到“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目標能否全面達成[18-20]。針對全域土地綜合整治,開展“三生”空間格局優化效果評價不僅必要,更為亟須[21]。
當前,有關“三生”空間格局的研究集中在“三生”空間優化理論[2, 22-23]、時空演變[24]、綜合評價[25]等方面,上述研究雖未基于全域土地綜合整治背景,但為該背景下“三生”空間格局優化效果評價提供了有益借鑒。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已逐步成為研究熱點,在土地綜合整治基本原理[26]、潛力測算[27]和戰略價值[28]等方面取得豐富成果。然而,整治后“三生”空間格局優化效果評價研究尚為新課題,現研究對象多為單一空間的農用地或建設用地[29-30],評價區域也多為縣鎮以上的較大尺度范圍[21],鮮見對平原農區鄉村小尺度范圍的“三生”空間格局優化效果系統性評價。圍繞評價方法,層次分析、模糊評價模型[31]、熵權法[32]等得到廣泛應用并取得良好效果,特別是投影尋蹤模型具有通過空間降維探測高維空間數據結構特征的優勢[33],為全域土地綜合整治“三生”空間格局優化效果評價提供了良好支撐。因此,本文以肥東縣古城鎮范店社區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省級試點為研究區域,從空間數量、質量和結構3個維度,構建全域土地綜合整治“三生”空間格局優化效果評價方法,系統分析平原農區“三生”空間格局優化效果。
1 數據源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肥東縣古城鎮范店社區(如圖1所示)為安徽省首批全域土地綜合整治試點區。該區域位于肥東縣東北部,地處江淮平原,是典型的以傳統耕作方式為主的平原農區。范店社區境內最高海拔64 m,最低海拔29 m,地勢較為平坦;總面積為1.05萬畝(1畝≈666.667 m2),其中耕地約0.69萬畝;擁有8個自然村莊,共864戶3459人。社區因人居條件較差、經濟發展落后、生態環境質量不佳,外出人口打工比例約為50%,存在嚴重的耕地撂荒和空心村等問題,迫切需要調整優化區域“三生”空間格局。

圖1 研究區位置及國土空間現狀
1.2 數據源
采用的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前土地利用數據來源于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成果,整治后土地利用規劃數據(含道路、溝渠等)來源于肥東縣自然資源和規劃局。范店社區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省級試點項目通過安徽省自然資源廳2022年6月組織的專家會審。
1.3 研究方法
“三生”空間格局是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的結果表現,是“三生”空間數量關系、空間質量關系和空間結構關系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集中體現。因此,本文從“三生”空間數量、質量和結構變化3個方面,對全域土地綜合整治“三生”空間格局優化效果進行系統性評價(如圖2所示)。
1.3.1 “三生”空間數量
“三生”空間面積是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的重要指標。本文采用土地利用轉移矩陣定量表示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前后“三生”空間之間的轉化情況,并顯式揭示區域“三生”空間轉化的規模與方向。土地利用轉移矩陣的數學模型為
(1)
式中,Ai表示轉移前i類土地面積;Aj表示轉移后j類土地面積;n表示土地利用類型數。
1.3.2 “三生”空間質量
“三生”空間質量反映了單一空間自身的生產能力或服務水平。生產空間的耕作分布和耕地條件能夠反映農業現代化和規模化程度;生活空間的居住集約和宜居品質情況展示宅基地建設有序程度和基礎設施共享程度;生態空間的調控能力和景觀價值則強調了生態環境的自然能力和生態功能的綜合提升。因此,為深入分析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前后“三生”空間質量變化,本文構建了空間質量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表1 空間質量評價指標
1.3.3 “三生”空間結構
“三生”空間結構是“三生”空間內各要素通過其內在相互作用而綜合表現出的組織狀態,其優劣評價應立足于“三生”空間數量關系和質量關系,即由多元空間數量和質量指標匯聚形成定量表征“三生”空間的高維特征空間,并利用該高維特征空間綜合評價“三生”空間結構的優劣。本文采用投影尋蹤模型,通過空間降維把這一高維特征空間投影至低維子空間,并探測出能綜合反映“三生”空間結構優化成效的投影值。值得注意的是,“三生”空間要素存在明顯的異質性[34]。為更好探測全域“三生”空間結構優化效果,本文采用分區形式開展評價。
對于投影尋蹤模型,降維過程中尋找最優解是綜合評價的關鍵問題。粒子群優化算法可以通過個體之間的協作和信息交互獲得最優解。為此,綜合粒子群優化算法優勢,本文所采用的粒子群優化投影尋蹤模型主要求解過程如下。
(1)樣本數據歸一化,公式為
(2)
式中,xij為第i個樣本第j個空間質量評價指標的原始值(i=1,2, …,n,j=1,2, …,m,n為樣本個數,m為指標個數)。
(2)樣本線性投影即從不同角度觀察數據,尋找能挖掘數據的最優投影方向,公式為
(3)
式中,zi為樣本i在一維空間的投影方向為一維投影(a1,a2,…,am)上的投影特征。
(3)構造投影值目標函數,公式為
Q(a)=s(a)d(a)
(4)
(5)

(6)
式中,Q(a)為目標函數;s(a)為類間距離;d(a)為類內密度;f(t)為階躍信號;R為局部散點密度的窗口寬度;rik為樣本間的距離。
(4)粒子群求解投影值:當前粒子位置為式(3)中的投影方向a,將其代入式(3),計算投影特征;據式(5)和式(6)計算類間距離s(a)和類內密度d(a);依式(4)計算投影指標函數Q(a),為該粒子的最優位置。當t+1與t時刻的粒子最優位置不再發生變化或達到最大迭代次數時,Q(a)即為最優投影值。
2 “三生”空間格局變化分析
2.1 “三生”空間數量變化分析
整體上范店社區“三生”空間的分布差異較大,見表2。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前生產空間面積最大,面積占比為66.79%;其次為生態空間,面積占比為26.42%;生活空間面積占比最小,為6.78%。整治后,生產空間面積占比仍最大,且增加了10.61%,升至77.40%;生活空間面積占比減少了0.87%,降至5.92%;生態空間面積占比減少了9.73%,變為16.68%。

表2 “三生”空間轉移矩陣 hm2
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前后“三生”空間之間的轉化關系主要表現在:生態空間和生活空間轉化為生產空間(見表2)。生產空間中約77.10 hm2來自于生態空間,約32.41 hm2來自于生活空間。生態空間和生活空間轉化為生產空間的部分主要分布在研究區的中部和東部(如圖3所示)。導致這一轉化的主要原因是范店社區中部和東部是原生產空間主要分布區域,零散的生態空間和生活空間影響了生產空間的連片規模效益,制約了生產空間的高效高值產出。全域土地綜合整治通過這一空間轉化,提高了生產空間的規整度、生活空間的聚集度、生態空間的連通度,促進了生產空間增量提效、生活空間穩量提質、生態空間保量提能,使得重組后的“三生”空間規模與范店社區經濟社會發展所需相適應。

圖3 “三生”空間規模分布
2.2 “三生”空間質量變化分析
2.2.1 生產空間質量
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前,由于范店社區居民點、林地和水域空間分布零散,導致耕地地塊形狀不規則、空間破碎度較高,嚴重制約了生產空間的高值高效產出。通過整治,將凌亂分散且分布在耕地中間的居民地、林地和水域轉化為耕地,并以修建的田間道路網為骨架,使破碎且分布不規則的耕地地塊變得更加聚集和規整,呈現出集中連片的耕地格局(如圖4所示)。這主要體現在:①整治后耕地面積由458.24 hm2增長至517.46 hm2,地塊個數由193個降至170個,平均地塊面積也由2.37 hm2提升至3.04 hm2;②對比整治前后耕地地塊破碎化程度,整治后地塊形狀指數由1.90降少至1.43,地塊形狀趨于規則。

圖4 整治前后耕地和基礎設施變化
由圖4(b)可知,整治后的田間道路規整地貫穿于耕地區域。整治前后,田間道路長度分別為26.33、58.61 km,增長了近 122%,其中38.15%所增加的田間道路來源于原有非耕地;田間道路密度由3.76 km/km2增長至8.37 km/km2,且田間道路平均寬度也由原來的3.59 m提高至4.18 m。整治后的田間道路不僅補充了農用設施覆蓋度,還將耕地分割為規整地塊,凸顯了耕地集中保護的理念。
全域土地綜合整治還規劃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包括溝渠、涵管、節制閘和提灌站等,這些水利工程密布于耕地地塊之間,形成了耕地的灌溉排水系統。據統計,土地綜合整治前溝渠的長度為38.53 km,整治后增長至70.81 km,提升近180%。全域土地綜合整治還設計了約128個涵管,使得溝渠連通度指數由2.71增長至6.30,大大提升了溝渠的連通度,凸顯了耕地灌溉排水系統網狀分布的優勢。
全域土地綜合整治針對平原農區生產空間的低值低效問題,解決了耕地集中連片程度不高和基礎設施覆蓋度低等問題,優化提升了以高標準農田為核心生產空間的質量。生產空間質量的優化為機械化、規模化、專業化的現代農業種植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2.2.2 生活空間質量
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前,范店社區生活空間分布較為零散,8個自然村莊自身和整體的聚合度均相對較低,并且村莊整體人口空心化嚴重,外出務工人口約占總人口的50%,如圖5(a)所示。高破碎度和低聚集度的生活空間分布導致社區公共基礎設施共享率較低、設施服務質量較差,迫使生活空間走向無序空廢的窘境。
面對生活空間的無序空虛問題,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將多個自然村莊聚合為3個規整的居民區,并布設豐富的公共設施用地(如圖5(b)所示)。據統計,整治前分布于多個自然村的建設用地地塊平均面積為4.38 hm2,分離度指數達0.21;整治后的居民區平均地塊面積為9.15 hm2,分離指數僅為0.04。這兩項指標充分說明,整治后的居民居住地集約程度得到了較大優化提升,為居民區沿省道布設和村道交通網布局提供了基礎。在由省道和村道構成的交通網絡下,居民由住地步行到達公路的平均時間由8 min縮短至3 min,較大提升了居民區宜居品質。同時,居民區高聚集度也可以減少電網、自來水、污水排泄系統等基礎設施的建設成本,避免因居民點分散造成的鋪張浪費。
2.2.3 生態空間質量
范店社區生產空間和生態空間約占總面積的90%,耕地、林地和水域自然資源較為豐富,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潛力較大,如圖6(a)所示。然而,社區缺乏有序的生態廊道體系,生態空間連通性較差,林地稀疏和水域淤積等生態環境衰退現象凸顯,生態空間無序污損問題較為突出。針對此,全域土地綜合整治通過開展“旱改水”、修建生態塘和生態濾溝等措施,結合生產空間的溝渠網絡等生態要素,構建高連通性的生態斑塊-廊道-基質模式,優化提升生態空間的調控能力和景觀價值(如圖6(b)所示)。

圖6 整治前后生態空間變化
圍繞優化提升生態調控能力,整治后社區布局12個生態塘、1條生態濾溝和128條生態溝渠,形成生態凈化系統。特別是以生態塘為載體,結合人工手段,能夠對生活污水中的污染物進行高效降解和吸附,大幅改善鄉村水體環境;以生態濾溝和生態溝渠為綠色海綿體,能夠實現雨水自然化管理。在生態景觀價值方面,范店社區的生物豐度指數由62.55增長至65.35,生境質量指數由34.22增長至37.16,整治后生態資源和景觀生境狀況得到明顯優化提升。值得說明的是,在社區整治后林地和水域面積有所降低的情況下,生態景觀價值得到優化提升的主要原因在于,社區布局13 hm2“旱改水”地塊,增強了斑塊-廊道-基質模式賦能的生態綜合效應。
2.3 “三生”空間結構變化分析
以范店社區功能區規劃為依據,將社區分為6個單元探測“三生”空間結構特征(如圖7所示)。整治后,除單元2外,各子單元生產空間面積均得到提升,有3個子單元的生產空間面積占比超過80%;單元5的生產空間面積增長量最大,生態空間面積減少量也最高。為更好地探測“三生”空間結構特征,參與各子單元投影尋蹤模型計算的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指標數量相等。計算指標共計21個,包括“三生”空間的面積和質量指標及其變化量。粒子群優化投影尋蹤模型的各項參數設定為:種群規模(粒子群個數)300,慣性因子0.9,加速常數2,最大迭代次數200。探測結果見表3。

表3 空間結構優化成效

圖7 范店社區分區評價單元
生產空間結構優化效果最優的是單元5,最差的是單元3。主要原因是整治后單元5的生產空間面積占比由51.31%增長至86.78%,且耕地也呈現集中分布;而單元3的耕地分布相對較為分散。生活空間結構優化效果第一的是單元3和單元4,效果較差的是單元5和單元6。主要原因在于單元3和單元4的居民區沿省道建設,居民出行的便捷度提升,且單元3和單元4的居民分離指數分別由0.42、0.35下降至0.05、0.04;而單元5和單元6的生活空間面積下降較大。生態空間結構優化效果第一的是單元6,效果最差的是單元5。主要原因在于單元6內存在大面積“旱改水”項目,生境質量和生物豐度指數均大幅提高;而單元5的廢棄坑塘和稀疏林地轉化為生產空間,生態空間規模下降較大。綜上可知,空間結構優化成效既受到空間規模變化的影響,也受到空間質量變化的影響。
整體而言,“三生”空間結構優化效果排序和生產空間優化效果排序幾乎保持一致,這揭示出“三生”空間結構優化效果受生產空間結構變化影響較大。因此,在土地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當通過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優化“三生”空間結構時,不僅需要優化單一空間的規模和質量,還需要協調3個空間之間的結構關系,即某一空間結構變化會對其余空間結構產生影響,需要充分結合實際,合理統籌布局“三生”空間。
3 結論與討論
本文從空間數量、質量和結構3個方面系統開展了平原農區全域土地綜合整治“三生”空間格局優化效果評價,主要結論有:①平原農區“三生”空間既相互獨立又相互關聯。在有限的國土空間上,全域土地綜合整治通過空間組織重構、要素重組和結構重塑,在空間數量關系、空間質量關系和空間結構關系上實現了“三生”空間格局優化。②平原農區中生產空間占比最大,其空間格局優化效果相比生活空間和生態空間格局優化效果更為突出,且“三生”空間格局優化效果受生產空間格局優化效果影響較大,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可以考慮優化生產空間為重點。③范店社區通過全域土地綜合整治優化了“三生”空間格局,較好地處理了社區現存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的土地利用沖突,基本解決了生產空間低值低效、生活空間無序空廢、生態空間無序污損等問題。
值得說明的是,本文是從空間格局視角開展評價,后續可通過融入糧食單產、村民收入等全域土地綜合整治效益信息,進一步健全“三生”空間格局優化效果評價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