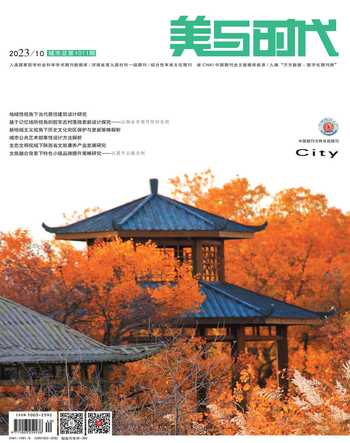“敘事轉向”下博物館展廳的跨媒介敘事研究
摘 要:博物館作為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播的重要陣地,在社會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博物館展廳是承載其社會功能的關鍵場所,觀者的一系列體驗都發生在這一被構建的場域之內。近十幾年來,隨著人們眼界的拓展和審美水平的提升,各種展廳同之前相比,無論是空間布局還是展示形式都有較大變化,與傳統審美型器物陳列、藝術品展示不同的敘事型展廳成為主流。討論博物館展廳的跨媒介敘事,以“敘事轉向”視角分析國內博物館展廳的發展現狀,著重探討博物館展廳面對同質化危機,如何利用互聯網結合增強現實(AR)、虛擬現實(VR)等技術手段實現破局,進而為博物館的發展提供新思路,讓其內部紛雜的碎片信息得到有效呈現,以降低觀者的理解成本,從而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果。
關鍵詞:博物館展廳;“敘事轉向”;跨媒介敘事;數字技術
早在1990年前后,“敘事”的概念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進了大眾視野,在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等諸多領域中,通過敘事的方式進行研究、分析成為一種普遍現象。20世紀末,國內博物館面臨著同質化困境,然而在“敘事轉向”風潮的影響下,大部分的策展人、設計師開始在之后的策劃設計中引入敘事學視角,通過敘事來厘清博物館展示空間中的信息脈絡。自此,把“故事”講好成為每個策展人和設計師的基本素質。以實物為文化媒介、以空間為傳播場域的博物館展廳不同于書籍、屏幕這樣的單一載體,想要在博物館展廳中“講好故事”,就不得不考量空間、時間之間的關系。跨媒介敘事能夠通過聲音、影像、裝置等媒介有效打破靜態陳列的時空限制,以彌補展廳在時間上的表征不足,幫助展示空間走出單純做“信息定位”的同質化困境,讓被展示對象更加生動、飽滿,內容更加有血有肉。借由觀者的“出位之思”,脫離被動的信息灌輸,使得觀眾成為故事的參與者,能積極參與互動,融入展示空間中,進而產生共鳴。同時,博物館空間也在跨媒介敘事的語境中完成了構建文化認同的使命。
一、當代博物館展示空間的“敘事轉向”
“敘事轉向”早已在文學藝術、傳媒傳播、社會科學等領域嶄露頭角,不同于傳統的線性敘事結構。受到“敘事轉向”啟發的研究者更傾向于探索多元的敘事形式,如非線性敘事、交叉敘事、多重敘事等。20世紀90年代之后,博物館展覽也開始融入敘事理念,并在展覽形式和語言上不再局限于傳統模式[1]。如今,國內大部分博物館、紀念館已經摒棄了單純展示物件和制作文字簡介的傳統器物定位型展覽方式,尤其是內部展示空間,已經從存“物”轉向了存“事”,展示空間成了“立體化”的場所,展品也不再局限于某個物件,可以是某場戰役、某個事件甚至是某種觀念、行為,能由物件、文字、圖像、音響等勾勒出一些抽象展品的輪廓。
如果把展廳理解為敘事發生的空間,那毫無疑問,策展人或策展團隊就是講故事的人,觀眾就是聽故事的人。策展人在設計展廳空間的時候需要著重考慮兩個關鍵要素:主題、情節。如坐落于江蘇省的南京博物院,其官網標語“中華文脈,蘇韻流芳”足以彰顯其敘事主題。一方面,南京博物院的藏品來自全國各地,是數千年中華文明的見證;另一方面,南京博物院中更多的是江蘇地區出土的文物,極具江蘇地域特色。在主題確定后,南京博物院根據主題進行了敘事情節的設計與編排,并以此串聯事件。其中的六個展館(歷史館、特展館、藝術館、非遺館、數字館、民國館)各自擁有獨立的故事線,有著序言、章節和結語這一完整框架。在南京博物院數字館中,開端為“萌動與發軔”,講述了中華民族先民將原始圖騰凝練成象形文字的過程;“進取與成長”部分承上啟下,引出高潮;而后的“擴張與融合”部分是展覽的核心所在,“南都繁會”“都市繁華”包攬其中,講述了歷史中江蘇的繁華與興盛;結尾的“中華文脈”和“生命樂園”是整個展館的總結和升華,使觀眾在沉浸式的體驗中把諸多分散的情節整合為一個整體。對觀眾來說,在數字館的體驗更像是觀看一部電影,而非去圖書館按照指示牌信息查閱資料。
在這類敘事性展廳中,展覽內容即文本,敘事學理論將文本所處的環境稱為文本空間,即文本所處環境的結構性框架,結構性的框架又處于文本空間之內。正如在淮海戰役紀念館中,一位觀者將注意力集中于展廳中一份戰略地圖的同時,必然會不由自主地關注到旁邊的說明性文字、周圍的燈光或者展品所處展臺的材料,也可能被旁邊相關聯的其他展品或是屏幕上介紹性的影像、文獻資料吸引。文本空間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有組織結構且固定的文本空間;第二種是開放性的文本空間,其中允許出現不同的組織方式;第三種是不具備任何組織結構的文本空間。根據上述博物館展覽的特征可知,博物館展廳屬于第二種文本空間,所謂的博物館展覽均可被視作廣義上的文本空間。然而在實際研究中,對文本的分析往往局限在狹義的內容文案層面,而非用于指涉展覽的整體機制[2]。因此,在博物館展廳中判斷一個敘事的發生,除了內容外,還要考慮其中的形式因素。
在形式層面,主要包含形式的實質對象和形式的表達方式。形式的實質對象即展覽所包含的多元媒介,包括但不限于聲音、文字、影像、光效、裝置等,設計者會搭配這些媒介來傳達展覽信息,即處理信息與媒介之間的關系。形式的表達方式即展覽中各媒介不同的組合方式,主要處理媒介和媒介之間的關系。如果策展人在展覽設計時利用跨媒介手段來豐富敘事層次,那么必定會考慮到形式的實質對象和形式的表達方式,結合影像、聲音、燈光、裝置等多種媒介渲染展廳氛圍,利用數字技術處理展覽信息,綜合視覺、聽覺、觸覺等多種感官,使觀眾以更直觀的方式在其中沉浸、體驗并探索。
二、數字時代博物館展廳的跨媒介敘事
第三次科技革命打破了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之間的隔閡,計算機與信息技術在科技領域實現了重大飛躍,帶領全人類邁向信息化的數字時代。博物館展覽也前所未有地同可視化交互、全息成像、動作捕捉、透明OLED顯示屏、可穿戴設備等新興數字技術與設備相結合,使觀眾的參觀體驗感得到了質的提升。在數字時代背景下,傳統導覽的敘事方式面臨著審美疲勞的同質化危機,博物館不能僅局限于傳統的圖文展示,展廳的跨媒介敘事形式應更加多元化。國內博物館展廳對于以新興數字技術為載體進行跨媒介敘事的策略并不陌生,早在2003年就已成立中國博物館學會數字化專業委員會,以探索博物館的數字化建設路徑。國內一些博物館展廳也早已引進虛擬現實、增強現實、全息投影等先進數字技術,使得重在提升體驗感的交互式敘事方式喚醒了觀眾主動參與的意愿。
以2018年國家圖書館舉辦的“曠世宏編 文獻大成——國家圖書館藏《永樂大典》文獻展”為例,該展覽通過全方位、立體化的互動設計來展示《永樂大典》這部中國古代編纂規模最大的類書,將這件不朽的文化瑰寶以嶄新的面貌呈現給大眾。展覽由大典猶看永樂傳、合古今而集大成、久閱滄桑惜弗全、搜羅頗見費心堅、遂使已湮得再顯五個單元組成。展覽序廳采用一塊長達14米的弧幕,并利用投影技術播放《永樂大典》纂修、流傳的動態影像,讓觀眾獲得身臨其境的沉浸式體驗。展廳開端選用明代畫家謝環的《杏園雅集圖》搭建立體場景,給展廳營造文化氛圍的同時,生動形象地將編著《永樂大典》的歷史背景傳達給觀眾,通過敘事性的演繹讓靜態的文物“活”了起來。展覽空間以回字形布局為基礎,構建了引人入勝的展覽流線,引導觀眾穿梭其中。在其他五十余件古籍展品的陪襯下,展廳正中央十二冊《永樂大典》原件散發著璀璨的光輝。該展陳設計以突出“皇家巨著”為出發點,圖文信息的版式模仿古代行文方式,從右到左,豎排布局,在設置的電子畫屏、紀錄片播放區等進行展示,并通過書法臨摹、多媒體互動游戲等實現寓教于樂。在此設計下,觀眾可以在展覽中以交互方式實現和珍貴資料的“零距離”接觸,踏上有深度、多維度的文化體驗之旅。
通過結合新興數字技術,《永樂大典》文獻展以新媒介融合多元化互動的模式構建了新語境,使得展覽空間中的文本變得更有張力,讓展覽在新的能指鏈中傳遞出更深層次的意義和價值。在新技術跨媒介敘事互動體驗中,來訪人員的觀眾身份逐漸被瓦解,由接收信息的旁觀者變成接力文化傳承的踐行者。雖然新興數字技術對如今的博物館展陳方式產生了巨大影響,展覽的面貌也不同以往,但是其核心價值依然在于遵循“以人為本”的理念,場景和敘事才是賦予展覽文化內涵、賦予受眾價值判斷的“內核”[3]。另外,在數字時代,還要警惕數字技術手段成為噱頭而迷失敘事本源,避免泛數字化敘事形式消解敘事內核深度,要以積極正面的態度面對博物館跨媒介敘事形式轉型帶來的新挑戰。
三、互聯網技術對博物館展廳跨媒介敘事的啟發
互聯網自誕生以來,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滲透社會各個角落,影響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博物館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也不例外。互聯網對博物館展廳跨媒介敘事方式產生的影響是變革性的。一方面,互聯網打破了傳統展廳的時空限制,使得觀眾不再受限于地理位置,而是可以通過在線參觀、虛擬導覽等方式步入跨媒介敘事的場域之中,并且可以在終端設備上同展覽內容進行互動,通過社交媒體平臺分享參與體驗,在線上以留言、投票等方式表達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另一方面,互聯網技術推動了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技術的發展,為博物館展廳營造了更加深入的沉浸式敘事環境,在博物館展廳可以利用增強現實技術將數字媒介、虛擬講解同實際的展覽場景相結合,借助互聯網技術,使觀眾在現實空間中可以與虛擬空間內容進行實時互動,沉浸于敘事場域,仿佛穿越了時空。另外,觀眾在實時互動的過程中,可以及時向館方提供反饋,以便其根據反饋內容對展廳進行調整改進,在節省成本的同時,優化觀眾體驗。
上海天文館就開發過一款基于增強現實技術的微信小程序,能協助觀眾深入學習天文知識。觀眾可以在移動設備打開小程序,之后將攝像頭對準周圍環境,其屏幕中就會出現不同種類的天體的3D形象,使用者通過手勢操作就能夠獲得360度全方位的觀察視角體驗。此外,使用者可在交互界面提示的協助下了解到“范德格拉夫環形山”“云海”等專業概念。在使用者體驗小程序的過程中,增強現實技術能成功吸引使用者的注意力。當使用者將移動設備中的現實和虛擬建模形象混合并將其當作真實世界的內容后,會逐步“懸置懷疑”,然后會忽略混合影像中虛擬部分帶來的不適感,進而去了解館方提供的天文知識。相比于館內普通展品帶來的距離感,這種基于AR技術的參展體驗則更加直觀。
除此之外,廣東省博物館、武漢自然博物館、成都博物館等也都陸續推出了接入互聯網的AR導覽服務。例如,觀眾戴上AR眼鏡之后,就可以在展廳中近距離和展品進行“跨時空對話”。觀眾只要對準文物,就可以實現智能識別,結合立體視聽體驗對展品歷史進行了解,并在人工智能技術的輔助下查看復原的破損文物的遠古時期樣貌,甚至能近距離接觸還未實地展示的珍貴文物,這讓文物重新“活”了起來。武漢自然博物館也已經正式上線了結合互聯網技術、AR技術的導覽服務,使得游客們可以在AR眼鏡里看到“活”的古生物——侏羅紀馬門溪龍的骨架化石開始動了,不一會兒就長出了肉身,隨后沉睡的馬門溪龍被喚醒,伸出長長的脖子,開始走出展示區,伸著懶腰向游客打招呼。無獨有偶,湖北省博物館也選擇借助新興數字技術講述文物背后的歷史,讓游客們佩戴AR眼鏡參觀春秋時期的越王勾踐劍,殘損的文物也通過AR眼鏡實現了動態修復,文物由此獲得了新生。互聯網+AR技術的加持以全新形式實現了博物館展廳的跨媒介敘事,輔助觀眾從多個維度了解展覽全貌。
四、結語
受“敘事轉向”趨勢的影響,似乎每個博物館都在爭先恐后地強調自身的敘事性,急于組合各種媒介輔助敘事,博物館展覽的總體水平也在跨媒介敘事的呼聲中結合各種新興數字技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數字技術使參觀者變成了參與者,博物館的敘事由自上而下“以物為主”的教育宣傳型向平等擴散“以人為本”的服務型過渡。無論利用怎樣的技術手段來輔助敘事,使呈現的形式千變萬化,觀眾的體驗感才是衡量一個博物館展覽成功與否的標準。通過跨媒介敘事喚醒觀眾的文化認同感才是博物館的價值所在,本著“以人為本”的理念才能避免博物館展廳再度陷入同質化困境。每個展廳都有各自的受眾群體,博物館空間作為敘事的載體,通過跨媒介方式展開敘事時,需結合歷史的實際情況,考慮文化語境下的現實因素,在此基礎上“講好故事”,激活傳統文化的生命力,激發社會群眾的創造力,增強多元群體的凝聚力,從而完整履行其社會職能,讓博物館的力量充分釋放出來。
參考文獻:
[1]周曉曉,王松寒.展覽敘事中的歷史還原與當代更新:以金陵圖數字藝術展為例[J].新美域,2022(9):106-108.
[2]吳寧.淮海戰役紀念館改陳提升項目設計探析[J].徐州工程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23(2):44-48.
[3]趙祎君.博物館展覽的敘事性判定[J].東南文化,2021(4):151-157.
作者簡介:
王國丞,蘇州科技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博物館跨媒介敘事和信息可視化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