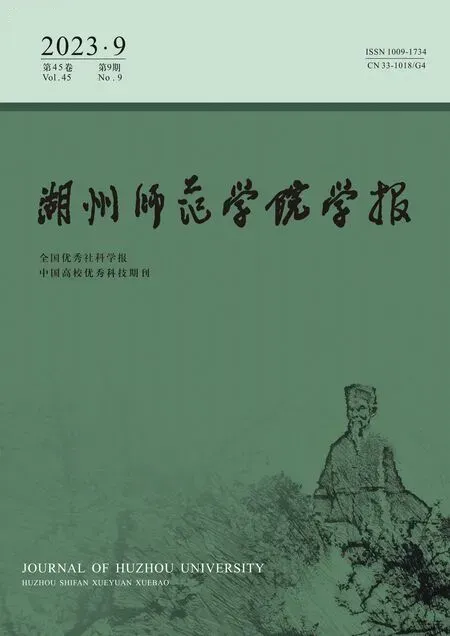文學創作的變奏與啟蒙觀念的博弈*
——以淪陷時期北平文壇的“色情文學”論爭為中心
高姝妮
(沈陽師范大學 文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4)
1940—1942年間,公孫嬿在《中國文藝》發表的愛情小說因其對肉欲的大膽描寫而被冠以“色情文學”之名,傳統的道德倫理觀與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啟蒙需要決定了“色情文學”飽受爭議的“文學身份”,于是1942年圍繞“色情文學”的價值與意義,北平文壇展開了關于“色情文學”的論爭。以《藝術與生活》為代表的批評者從道德倫理的角度批判“色情文學”對讀眾精神的腐化,而以《國民雜志》《中國文藝》為代表的支持者則以西方現代主義的文學觀認可“色情文學”的文學價值,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然而,北平特殊的政治語境與“建設新文藝”的倡導使得浪漫主義的“色情文學”確乎成為一股文學啟蒙的逆流,但這股逆流并不是公孫嬿的隨性而為,“色情文學”描寫人病態的情欲與異化的肉欲,呈現出畸形社會對人性的扭曲,作者以欲望的書寫深切地表現了北平文人在道德自遣與靈肉分離交合下的苦悶、彷徨、無力、憤懣、自責的復雜心態。
一、公孫嬿與“色情文學”的創作
公孫嬿(原名查顯琳)畢業于輔仁大學西語系,是北平文壇頗有影響的詩人,外文專業的教育背景使他深得西方文學思想的真諦,其中西方浪漫主義文學流派對公孫嬿的文學創作有著深遠的影響,以濟慈、拜倫、雪萊為代表的浪漫主義詩人強調個人情感對現實的觀照,倡導個體精神的解放以及自然的審美理想,因此公孫嬿的詩歌對自然意趣、生命靈性和個人欲望的表達則顯現出西方浪漫主義的精神烙印。如果說追逐欲望、追求自然之美的浪漫主義詩歌構筑著公孫嬿的詩學觀,那么“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創作理想,以及主張客觀真實的自然主義文學思想則構成了他創作“色情小說”的理論基礎,于是王爾德、莫泊桑、勞倫斯的小說為公孫嬿的創作提供了一定的文學借鑒,繼而大膽描寫肉欲、表現個人情欲、追求詩美理想的“色情小說”便悄然登場于北平文壇。
1940年11月,《中國文藝》發表了公孫嬿的處女作《海和口哨》,然而他并沒有想到這部在“暑假百無聊賴中”[1]42創作的“狹窄與粗淺”[1]42的小說,卻使他“背負色情文藝作家罪名”[1]42,隨即公孫嬿在《中國文藝》又相繼發表了《鏡里的曇花——韶華不為少年留》《北海渲染的夢》《流線型的嘴》《解語花》《卸妝后的生命》五部中短篇小說,此外公孫嬿還分別在《新民報半月刊》《國民雜志》發表了《紅櫻桃》《珍珠鳥》,它們與《中國文藝》刊載的六部小說一起被一些批評者被劃歸為公孫嬿的“色情小說”之列。對于“色情”的評價,公孫嬿一方面汗顏于一些讀者將“色情”與“淫穢”概念的混淆,他認為“色情”表現的是男女正常的生理與情感的欲求,而“淫穢”則“以描寫性交的動作聲音”[1]42毒害青年的思想。相比之下,“淫穢”對性活動本身的關注卻暴露了它齷齪不堪的低俗與卑鄙。一些批評者認為公孫嬿的“色情”描寫是在散播淫穢思想,污穢文學的啟蒙價值。面對眾人的指責,公孫嬿并沒有為自己辯解開脫,也無意接受“色情文藝作家”的稱謂,他將“色情”視為對文學的褻瀆,因而“色情文藝作家”亦隨之變成他精神的罪責。以“淫穢”褻瀆文學的藝術追求與審美理想,這是公孫嬿最為痛心的,為此他重新詮釋“色情”的含義,確立“色情文藝”正當的文學身份,故而另一方面公孫嬿又表現出對“淫穢”臆斷者的否定與反擊,他認為:
我們不要只記憶住“色情”二字而忽略了原作的本意和內容,與他好含蓄,一個表現時代,或對某一方面自己主觀見解的怨尤地方。……“色情”二字的成立當非絕對性的捕逮,有時候是技巧增加以后文章的力量,有時候是渲染增加文章的美妙。[1]42
公孫嬿將色情描寫作為表現美、渲染美的創作方式,從其作品便可見其并不著意于“色情”的描寫,而情感的困頓、欲望的釋放、時代的憂郁、青春的易逝、個人的迷惘才是色情小說表達的真意,因此以“色情”定義公孫嬿的小說是不妥的,甚至還造成了對小說主題的誤讀和曲解,“色情”只是其小說內容的點綴,其承載的復雜情感和創作心緒更值得關注與思考。
盡管北平文壇倡導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認為創作要表現民眾生活、反映時代,但公孫嬿卻以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探索人復雜的心靈世界,欲望的放大指涉著異化的非理性世界,因而公孫嬿的小說展現了異變時空下人們掙扎、疏離、隱忍、盲從的心態。“淪陷”使日本的殖民意識形態抽離了民眾的個體意識,精神的解放與人性的復歸,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族意識的自覺,因此由生命本能的肉欲激發了人對自我的認知。無論是《海和口哨》《流線型的嘴》,還是《解語花》《卸妝后的生命》,摩登女郎對男性欲望的魅惑構成了公孫嬿既定的敘述模式,于是男性消泯了自我而變為對女性的仰視者,刻意強化了女性的主體地位,這一敘述視角的改變突破了傳統愛情小說的創作理路,小說中傳統的兩性關系表現出一反常態的畸形與裂變,而兩性關系的異化則成了欲望異化的動因。公孫嬿的欲望書寫,意在表現人在非理性意識下的異化狀態,欲望對人的奴役導致了人格的異化與分裂,由此深刻地反映出社會制度的病態與畸形,以及淪陷區民眾復雜的情感結構。
在公孫嬿的“色情小說”中,青春與欲望有著莫名的關聯,青春代表著情竇之初的韶華記憶,它懵懂、純粹、青澀、短暫又美艷,不僅牽動著人對青春最真切的向往,還引發了愛之初欲的迷思。“我”(《鏡里的曇花》)愛上了“淳樸”“自然”“純凈”的“小原”,然而作為有婦之夫,“我”斷然拒絕了這樣的感情,與其說“我”貪戀青春,不如說是青春復蘇了“我”的愛欲,讓“我”的生命重新得到洗禮。《海和口哨》中摩登女郎的青春時代被一個欺騙她的男人消磨殆盡,痛苦的青春記憶使她產生了報復心理,她戲弄男人的感情,通過男人的愛欲確證自己的青春,最終她選擇以死來祭奠青春、救贖自我。易逝的青春帶走了青澀的年華,情欲最初的萌動迸發出生命的激情與活力,公孫嬿的小說往往帶著青春的感傷,無論是男性對青春少女的迷戀,還是女性對青春的悵惘。然而青春的意義不止于此,它還關聯著作者的民族之志。轉瞬的青春年華不應在碌碌無為中消磨,人的青春應貢獻于民族與國家,在民族危機的緊要關頭,淪陷區需要青年力量的支持以重振民族精神,因而公孫嬿對于青春易逝的感傷充滿了焦慮,甚至將這種心態以極端的方式呈現,諸如中年男人對青春少女的迷戀,以及女人以死保留青春的決絕,可見時不我待的緊迫感使公孫嬿的內心變得焦灼與急迫。
國破家亡的淪落、日本統攝之辱、亡國奴的無奈、尋求自救的掙扎、生存危機的窘迫,致使淪陷區民眾呈現出復雜的精神圖景,進步文人思忖民族精神的崛起,沉默的知識分子無聲地堅守士人的道統,浸在苦難中的百姓在麻木與盲從中求取自保,曲意逢迎的投機者趁機鉆營謀權。日本的“脅迫”更替了“北平”時代的氣象,“北京”使無所適從的“北平人”變成了屈從的“北京人”,于是同一“屈從”的狀態下便顯現出不同價值立場的選擇,他們潛隱地掙扎抵抗或是沉默地堅守自我,他們被迫行事或是投機謀權,他們軟弱無力或是盲目自保,總之“屈從”使每個人在壓抑的精神空間里凝神屏息,他們的表里不一最終導致了異化的生存狀態。在這一意義上,公孫嬿的“色情小說”即是將人們異化的生存狀態凝縮至欲望的書寫中,他的目的并不是找出病因而是列出癥狀,在日人的統攝下病因無以解除,但癥狀卻直接表現了病因之惡,間接表明了作者的寫作立場和反日態度。
欲望的異化呈現出社會體制的異化,可見公孫嬿的色情小說不只是坦露欲望的抒情小說,還是暴露社會暗角、揭示畸形社會對人格的異化的現實批判小說。公孫嬿的色情小說內容反映“異化”的社會形態,它貫通著人性的欲望從而表現出欲望的美感,加之公孫嬿詩化的語言將小說的藝術表現力提升至美丑共融的境界,在此公孫嬿的色情小說突破了以往抒情小說構寫兩性關系的創作理路,展現出獨特的創作風格。然而公孫嬿的色情小說一經發表便引起了一些反對者的不滿,他們攻擊“色情小說”,否定了它的文學價值;贊同者則肯定了“色情小說”的文學價值,認為它融合了西方浪漫主義與自然主義的創作思想,具有一定的開拓意義,于是1942年關于“色情文學”的論爭便由此展開。
二、關于“墮落文學”的聲討
公孫嬿色情小說中的身體描寫引起了若干文學評論者的不滿,他們以傳統的道德觀批判色情小說,否定它的文學價值,于是1942年圍繞“色情文學”的意義與價值問題,北平文壇展開了深入的討論,其發端要追溯至1941年公孫嬿發表的《關于“新詩”中的“長詩”》[2]9與《一年來華北創作界》[3]14。公孫嬿的這兩篇文章分別從詩歌創作和文學技巧兩方面來反思北平文學的困境,指出要提高文人的文學素養,重新規范文學創作的導向,然而公孫嬿的觀點卻遭到了反對者的質疑,于是《藝術與生活》同時發表了穆穆的《答公孫嬿君》與謝薄謙的《謾罵批評家》,針對公孫嬿兩篇文章的內容予以堅決地批判,由此激化了公孫嬿與反對者的矛盾。1942年5月,《藝術與生活》又刊載了“色情文學爭論戰特輯”,否定了公孫嬿色情小說的文學價值。然而《藝術與生活》對“色情文學”的攻擊不僅針對公孫嬿本人,還將矛頭指向了刊載公孫嬿色情小說的《國民雜志》和《中國文藝》,于是《國民雜志》刊載了“關于色情的文學”的筆談會,表明了對“色情文學”的支持態度,間接回擊了《藝術與生活》的質疑,北平文壇的“色情文學”論爭便由此展開。
《藝術與生活》主編袁笑星對公孫嬿的色情小說似乎并不認同,無論是刊載穆穆、謝薄謙對公孫嬿的批判文章,還是“色情文學爭論戰特輯”的發表,都是在袁笑星的授意下(1)袁笑星:《我的表白》,《藝術與生活》1942年第5期。袁笑星在該文中說道:“那兩篇是由我授意而寫的。”。 完成的,盡管他幾番強調“文學要有公理”,但仍然無法掩蓋《藝術與生活》執意批判“色情文學”的立場。從《藝術與生活》刊載的“色情文學爭論戰特輯”可知,參與討論者嚴厲批判公孫嬿及其“色情文學”,呈現“一邊倒”的批評傾向,所謂的“爭論戰”全然變成了對“色情文學的討伐”。參與“色情文學爭論戰特輯”的討論者共六人,分別是陸白人、劉溫和、孩子、黑羽毛、不丁和某某,他們從小說主題、思想淵源、受眾群體以及創作態度等方面指責色情小說對文學建設及社會風氣的不良影響。陸白人通過分析外國浪漫主義的文學作品,以西方文學思想反觀淪陷區特殊的社會形態下色情文學。他認為,色情文學的墮落和淫穢暴露了社會的黑暗和丑惡,體現出文學對現實的觀照,具有現實主義的創作傾向,而這樣的色情文學“我們當然不反對”[4]26,但若是歌頌性欲則散播了不良思想,有礙于社會風氣的建設,“應當予以極端的反對”[4]26。在此,陸白人并沒有界定“色情”的含義,只是從文學的主題區分了色情文學的不同思想價值取向,可見他對色情文學的態度是相對客觀的,但卻不失保守的中立態度。
相比之下,參與“色情文學爭論戰特輯”的其他討論者則持有鮮明的反對態度,他們以傳統的道德立場全盤否定色情文學的文學價值。劉溫和認為公孫嬿的色情文學是“耽于聲色肉欲”[5]25的頹廢主義的文學,它“以激發別人的行動為能事”[5]25,表現出卑下、低級的趣味。黑羽毛指出公孫嬿的小說有些“鴛鴦蝴蝶派”的遺風,人物扁平化,“主人公永遠是一個詩人、畫家、公子哥等多情的人物”[6]28。一些批評者則從接受群體的角度批判色情文學的社會影響,不丁認為色情文學誤導年輕人,他們會模仿、效法小說的情節追求異性,這對他們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傷害;署名為“孩子”的作者坦言,“公孫嬿的色情文學作品是可怕的”[7]27,“看公孫嬿作品后,我知道女人是美的夜里也做著女人的夢”,從此他的精神被小說的污穢“蹂躪得頹廢不振”。這些批評者認為,色情文學傳播低級卑下的思想,誘導青年走上道德的“歧途”,渙散了青年人的青春激情與思想斗志,為此他們堅決抵制色情文學,而作者公孫嬿無疑成為眾矢之的。
不丁對公孫嬿的《有感于:〈文藝家與毒品販賣者〉》(2)余皖人:《有感于:文藝家與毒品販賣者》,《藝術與生活》1942年第1期。這篇文章是公孫嬿對《吾友》雜志刊載的《文藝家與毒品販賣者》的回應,《文藝家與毒品販賣者》批判了公孫嬿的色情小說,認為公孫嬿如同販毒者散播不良思想,麻痹民眾,對此公孫嬿甚為氣憤,因而文章的語言犀利,甚至有點失了分寸。余皖人是公孫嬿的又一筆名。給予嚴厲的批判,他指責公孫嬿態度傲慢,毫無羞恥之心,“在說別人之先也不妨勞駕照一下自己的‘尊顏’,這樣的罵,不比‘鄉里野兒’的罵來得更高明”[8]29,隨即他談道,公孫嬿“謾罵式的批評”不僅暴露了自己傲慢的個性,還“為文壇撒下不良的種子”[8]29。同時,對于公孫嬿在《有感》中“謾罵式的批評”,某某表示反對,他認為這表現了公孫嬿“說風涼話似的可憐”,而公孫嬿的“嗜毒的販毒論”(3)公孫嬿在《有感于:文藝家與毒品販賣者》中回擊反對者時談道:“‘販賣毒品’的人能販賣毒品,一定是有人嗜毒,兒子養的不孝順不能罵他的祖宗三代。”是對文學不負責任的表現,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放棄了自己的底線與原則,正如色情文學對讀者思想的危害。關于文學的社會影響,某某論及了新文學的啟蒙價值導向,他談道:
一想起每天里因戰爭不知要死掉多少年輕小伙子,死身填滿了溝壑,填滿了河流,和戰場上的血肉橫飛。我們全身感到一陣痛苦的痙攣,立刻就覺得“美麗的小姑娘呀”這樣的文字描寫的不必需。[9]30
時代需要的是“大眾的呼聲”[8]29和“有意義的生活”[8]29,因為“生活早就壓得我們喘不出一口氣來了,你們這些寫作家應拿出點天良來”[8]29,對此某某提出了新文學的創作要求以及嚴肅作家的創作態度,倡導文學作品須激勵與振奮苦難的同胞。這一觀點深化了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民族啟蒙價值,弱化了浪漫主義文學創作的情感訴求。某某以民族啟蒙的歷史要求作為新文學建設的重要導向,故而強調個體意識的色情文學成了不合時宜的存在,它與主流啟蒙話語的不同路向決定了它難以為繼的歷史命運。
從“色情文學爭論戰特輯”的討論內容來看,雖然批判的是公孫嬿及其色情小說,但《藝術與生活》卻不經意地把斗爭的矛頭指向了刊載色情小說的《國民雜志》與《中國文藝》。《國民雜志》與《中國文藝》這兩大官辦期刊對公孫嬿的色情小說持支持態度,這其中有官方的授意,而公孫嬿的色情小說無疑成為日本文化陰謀的一顆棋子。一方面,日本的新感覺派小說與公孫嬿的色情小說都強調人的主觀意識,在創作理路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日本借此擴大日本文學在中國本土的影響力,積極促進中日文學的合作與交流;另一方面,公孫嬿的色情小說以主觀抒情為主,與北平文壇倡導的暴露社會、表現時代的現實主義文學是完全不同的創作理路。由此推知,日本對色情小說的支持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北平文壇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甚至間接影響了文學啟蒙話語的建構。《藝術與生活》的文人對公孫嬿及其色情文學的批判不僅就其文學的道德立場,在文學啟蒙話語重構的意義上,他們的態度還暗示出對日本殖民文化政策的抵抗,由此民辦期刊《藝術與生活》與官辦期刊《國民雜志》《中國文藝》構成了色情文學論爭的兩大陣地。
三、“色情文學”的價值認同
《藝術與生活》批判公孫嬿及其色情文學創作,而《國民雜志》則從色情小說的文學資源探討其文學價值和創作困境。1942年2月,《國民雜志》發表了《論色情文學描寫》(夏蟲之流),為“色情文學”的筆談會做了鋪墊,該文以《北海渲染的夢》(公孫嬿)為例,結合勞倫斯、莫泊桑、薩克萊和《金瓶梅》的創作理路,探討色情文學的道德觀和價值立場。夏蟲之流指出,色情文學的身體描寫并無“蠱惑讀者”或是“博取利益”之意,而是對畸形道德觀的批判與卑劣人性的暴露,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夏蟲之流認為公孫嬿創作的意圖有二:其一“為強調道德責任的力量”[10]68,其二是“暴露封建遺留之禮教勢力的專橫”[10]68,然而公孫嬿并沒有將他的創作意圖深入小說創作的肌理中,因此他的作品對現實的批判有一定的局限性,這是夏蟲之流擔憂的。夏蟲之流希望華北文學在追求美的同時還須深化它的社會意義,這就要求作家“推挽社會的進化”[10]68,在此夏蟲之流關注到色情文學的啟蒙價值,以期通過抒懷主觀情感的色情文學表現淪陷區復雜的社會形態。
1942年5-6月,《國民雜志》連載“關于色情的文學”筆談會,共有11人(4)他們分別是:楚天闊、而已、王朱、公孫嬿、謝人堡、耿小的、阿翦、陳逸飛、楊亞風、劉針、李麥靜。參與此次討論,筆談的議題即圍繞中外作家、作品及人物形象(5)“色情的文學”筆談會圍繞10個問題討論,這10個問題分別對谷崎潤一郎的小說、《當代英雄》《維里尼亞》和《大學生私生活》三部作品、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沙陀布里昂筆下的亞達娜形象、《金瓶梅》與《野叟曝言》、薩克萊的小說、王爾德的作品、《蕩婦自傳》的女主角。闡釋色情文學的創作困境、思想意蘊以及文學價值等,從而使讀眾擺脫色情文學的認識誤區,重新明確色情文學的啟蒙價值。劉針從“色情文學”的產生根源分析讀眾的閱讀心理,他認為,“色情文學”的產生是人們欲從單調、疲勞的生活中尋求刺激,于是讀者通過肉欲的官能得到了滿足,然而現代的社會生活卻改變了“色情文學”的價值導向,使“色情文學”表現出更為理性的社會思考,由此拓展了“色情文學”的闡釋空間。即便如此,仍有相當一部分人對“色情文學”的認識停留在“淫穢”的偏見中,造成了對“色情文學”的誤讀。對此楚天闊指出,人們因對色情文學的錯誤認識,故而貶抑甚至抹殺了色情文學的文學價值,他結合王爾德的《道林格雷的畫像》探討色情文學對“藝術美”的審美追求。同時,他還認為,莫泊桑的小說則利用自然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通過色情描寫暴露“人類的獸性”[11]24,與之相應的還有沙陀布里昂、萊芒托夫和薩克萊的作品,這些作品的色情描寫非但沒有誤導文學的價值導向,還通過人的精神困境揭示畸形社會對人格的異化與人性的壓抑,具有一定的道德批判立場,于是色情文學的文學價值得到了討論者的認同。一些反對者從道德立場否定色情文學的價值,認為色情文學散播社會不良風氣,悖逆于社會倫理道德,對此麥靜反駁道,利用道德觀批評文藝,終究無法真正理解文藝,所以不能用道德觀作為文學評價的標準,若用道德觀解讀《金瓶梅》,它無疑是一本荒誕的“淫書”,但《金瓶梅》的思想價值恰恰在于它對人性私欲的暴露。對于“衛道者”來說,“色情文學”與“淫穢”是相通的,在這一意義上“色情文學”步入了“淫穢小說”的后塵。陳逸飛對“淫穢小說”與“色情小說”做了簡要的區分,他認為,“文學是表現人生的,‘色情’也是人生的一種,所以我們毋庸反對”[12]32,但“專門述說性交”的便“不是描寫色情”,而是“淫穢小說”。
《國民雜志》“關于色情的文學”筆談會的10個議題以中外作家及其作品為中心,一方面基于文本內容,認可色情文學的文學價值和美學意義,另一方面從色情文學的思想資源與創作理路,肯定其精神內涵的現實效用。無論是西方文學的浪漫主義與唯美主義對色情文學審美理想的建構,還是自然主義與現實主義對色情文學啟蒙意蘊的拓展,不同的創作理路打通了色情文學中個體意識與社會現實的分界,主觀抒情的色情文學在社會現實的觀照下呈現出作家的現世焦慮。公孫嬿的色情小說即是在多元文學思潮的融合中形成的,他不僅得益于勞倫斯、王爾德等西方作家的創作理路,還借鑒了中國作家的創作技巧,正如公孫嬿所言,“我私下喜歡讀沈從文與老舍二人的小說,對于穆時英的新感覺派,有了更深的偏愛。……我受到另一本勞倫斯的《查特萊的夫人》影響不少”[1]42。這些作家的作品深刻影響著公孫嬿小說的敘事模式和價值傾向。《國民雜志》的筆談會既沒有褒貶色情作家的功過,也不妄加批駁反對者的觀點,討論者明確了色情文學的文學身份和啟蒙價值立場,一定程度上對《藝術與生活》的反對之音予以了回應。
然而《國民雜志》的討論者并沒有對公孫嬿及其色情小說作出具體評價,甚至規避了與《藝術與生活》的正面沖突,而公孫嬿在《國民雜志》的獨立發聲,似乎更為直接地回應了《藝術與生活》的質疑。針對《藝術與生活》中孩子、劉溫和等人指責色情小說對青年思想的毒害,公孫嬿反駁道:
創作小說偶有一些關于“色情”的描寫并不為過。一切性行為是人人皆知的,是與生俱來的動物本能;請問貓狗豬牛之類動物是誰教會他們性交,難道他們也受色情文藝的引誘嗎?……非某作品之有貽害,而是“色情人”自尋貽害。[1]42
繼而公孫嬿又談到了創作小說的初衷,他說道,“寫小說前,我沒有想到為誰去寫,我很愿意緘默寫些文章來娛樂自己”[1]42,“我還不清楚什么叫色情,只知道我要這里寫便這么寫”[1]42,從那時起“我的篇篇文章被稱為色情文字”[1]42。無論是談“色情”的“貽害”,還是論及創作小說的初衷,公孫嬿并不認同批評者對色情文學的道德綁架與惡意攻擊,他不斷地申明道德立場,明確色情文學的價值導向。公孫嬿本意是要創作脫離低級趣味、體現文學審美理想和人的精神困境的“主觀抒情小說”,卻被反對者冠之“色情”的名號,于是“淫穢”“低級”“齷齪”概括了“色情小說”,造成了對“色情小說”的誤讀。就色情文學道德立場而言,公孫嬿與反對者矛盾不斷激化,此時《國民雜志》有意將色情文學討論焦點轉移至文學創作的理路分析與現實價值的考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論爭的矛盾。
作為北平文壇最大的文學期刊,《中國文藝》是刊載公孫嬿的色情小說數量最多的“文學陣地”。在“色情文學”論爭之前,《中國文藝》就明確表達了對“色情文學”的認可。1942年3月,林慧文在《中國文藝》發表了《關于色情文藝》[13]14,該文從“色情文學”的概念、理論淵源、道德立場與讀者接受態度等方面肯定了色情文學的意義和價值。林慧文認為,色情文學的產生深受浪漫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影響,它不僅是“人生”的反映,還體現了“人的意識”的解放,由此他認可色情文學的進步意義。就其道德立場而言,色情文學并非不道德,“真正的不道德的文學是猥褻的文藝,非人道名分的文藝”[13]14,而色情文藝是表現“人間苦悶”的文學,因此“站在社會的或道德的觀點,都沒有反對的必要”[13]14。對于讀者的接受態度,林慧文表示了擔憂,并提出讀者需要端正態度,“不以企求滿足肉欲或娛樂的心理去讀”[13]14,同時還應領會“作品的深刻含義”。上官箏認為,“今日‘色情文學’發生的社會原因是生活苦悶造成的頹廢傾向”[14]7,而單純地把“色情文學理解為現實生活的逃避”[14]7是膚淺的,并沒有深入其精髓,讀眾需要深入色情文學的肌理窺探“今日社會的畸形”[14]7。無論是“人間苦悶的表現”還是“今日社會的畸形”,對于《中國文藝》的文人來說,色情小說不僅是中國文學對西方浪漫主義創作理路的借鑒,同時也是對文學啟蒙話語的艱難探索。《中國文藝》是色情文學的積極推行者卻無意于參與色情文學的論爭,而林慧文的《關于色情文藝》無疑代表了《中國文藝》對色情文學的態度與立場,這是一種不言自明的宣告,為《國民雜志》的筆談會提供了理論基礎與思想借鑒。
在1942年的“色情文學”論爭中,《藝術與生活》顯示出重要的推動作用,它刊載的“色情文學爭論戰特輯”開啟了色情文學的論爭,于是以《藝術與生活》為核心的色情文學的反對者,與以《國民雜志》與《中國文藝》為代表的色情小說的幕后支持者,形成了文學論爭的兩大對立陣營。《國民雜志》與《中國文藝》極力避免與反對者的正面沖突,他們既不為公孫嬿及其色情小說作辯護,也不著意回擊《藝術與生活》的反對者,他們從色情文學的思想資源和創作導向出發評判色情文學的內在價值。相比于《藝術與生活》的反對者對色情文學的道德攻擊,《國民雜志》與《中國文藝》顯示出更為冷靜的學理思考,因而色情文學論爭的最后結論也在其影響下得到了認可。可以說,這場文學論爭絕不止于文學道德觀的論爭,它還關聯著新文學的創作理路與建設導向的商榷,對于北平文壇來說,“色情文學”的論爭既是一次文學的自省,同時也越加明晰了文學啟蒙的任務和標準,最終促使北平新文學的理論建設日臻完善。
特殊的政治語境壓抑著人的主體性,個體意識被邊緣化,而公孫嬿的色情小說則以欲望化的書寫極力表現個體意識。公孫嬿借鑒了西方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這不僅是一次文學創作的實驗,也是一次創作理路的探索。然而公孫嬿的創作理路遭到了反對者的質疑,于是1942年北平文壇展開了關于“色情文學”的論爭。盡管在這場論爭中,對“色情文學”的肯定之音占據了上風,然而“色情文學”并沒有因此得到充分的發展,浪漫主義的創作理路無法滿足重振民族精神啟蒙需求,這就意味著表現個人欲望的色情文學受到了民族主流話語的沖擊,從而成為邊緣化的存在,最終“色情文學”還是悄然地退離了北平文壇,而它的回音還縈繞在歷史的上空,留存著淪陷區文人的精神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