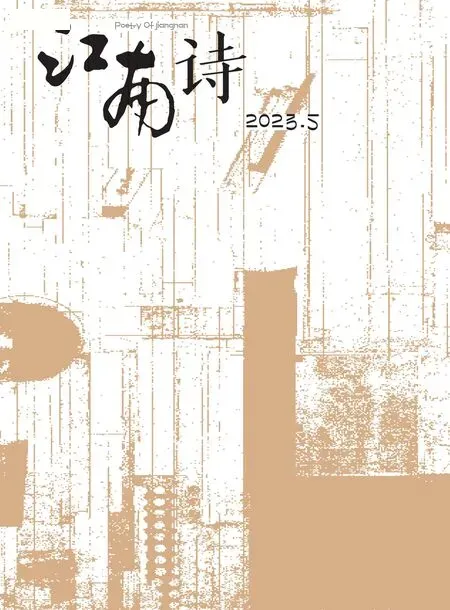詩與遺忘的途中
◎張雪萌
一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將下筆的詩歌視為一首首的“道中作”。
“道中”,占據著某種物理層面的意味。去年來到英國,地理意義上的遠游,更是加重了這一層確信。
我們基于不同的衡量尺度來談論旅行的有效。一座城市,在朋友圈的鏡頭中留下吉光片羽式的映像,似乎是最便攜的紀念品,也作為“是的,我曾經到往過那里”的證明。桑塔格談到,照片實際上是被捕捉到的經驗。可那些逃逸于捕捉之外的,又為人所切身經歷的事物,這些沉寂的、未被析出的經驗,又被打掃進了哪些角落?
我時常感到與外地之間相互凝視的關系——我觀測經驗之外的異域情調,而異域也在打量我,一個外來者的隱微的不安。這種齟齬不斷催促著行人駛向別處,而高度差異化的經驗,往往在來不及被記憶存留前,便延伸向新的遺忘的途中。
幾乎像一種庇佑,作為寫作者,尚有詩歌,可以滿足旅客收集癖的私心。
回顧并點數歷往的寫作,每一首詩歌像一處錨點,標定著瞬時的驚異。途中的見聞,早已下潛到記憶的深水區,然而對文本的重新進入,都引領你再一次返回,并觸摸、聞嗅到世界曾經表露出的知覺。我仍然記得2021年初,在深夜時分的廣州南站,候車大廳天花板的吊燈,在人潮褪去后,開始重新奪回空氣中光亮的體積,那是屬于《車站》這首詩的場景;去年年底,在回劍橋路上的無數火車站臺,電子告示牌上金黃色的列車到站訊息,閃爍在冬日的寒霧里,那股鼻腔里的冷意,再一次襲來,每當我讀到《夜晚,謝菲爾德》的時候。
2023年,我的詩歌由大量的敘事與戲劇化寫作,轉向對生活經驗本身的測定,在《墓園》《克萊爾》中,這樣的嘗試多少帶著印象派的懷舊,即對于暫時性和轉瞬之感的刻意保留。盡管,十分清楚的,在這些努力背后,是行人身份下無法擺脫的焦慮。
二
今年4月,旅行途中和兩年未見的朋友在斯特拉斯堡小聚。再次開啟的談話,讓我越來越擔憂自己趨向模糊的記憶。說起的那些人、事、物,借由他的重提,我才意識到自己幾乎讓渡了對許多回憶的保管權(反而,我的朋友們大多成為了我們共享回憶的守門人)。如貝恩所寫那樣:
……但每天有很多經過你身邊,
推廣過,外向型的,
存在主義的擔心,夫妻的爭斗,稅務問題
所有這些你自己都不關注,
一大堆五花八門形式的人生
事實上,對于生活中大量細節的遺忘,我又樂于持有一種悠游無謂的態度,這似乎是對于連貫的寫作習慣幫助看守記憶的盲目樂觀。在經由語言再造的現實,和真正的現實之間的孰輕孰重,過分倚重前者,也多少夾帶著些狂妄的天真。在這一點上,我又與那些絕望的攝影師們沒什么不同。
三
詩的形式暗示我們,它曾誕生于對遺忘的恐懼之中。一個韻母首先是其自身,它被下一個偶然的發音所找到,如果不是“a”,那就繼續調整發音的位置,直到講述間隙的停頓,開始對上一處作出回應。韻由是誕生,并以規律的形式,在游吟者和說書人之間顯露,以抵抗口耳相傳帶來的記憶必要的磨損。
自此,詩與時間達成合作。自覺或不自覺地面向遺忘,詩歌是我們在海岸行走,沿途彎腰扎下的作為路標的石子。然而,像斯特蘭德所言,它只贊美或賞識處于消逝之中的語氣,思想和事件。即使當詩歌稱許歡樂,它也攜帶著那歡樂已經結束的消息。潮浪將那些石子卷入海底,持續的牽引作用對你做出來自未來的許諾:那些路標并未真正消失。但人并非海浪,在有死性的預言下,寫作是重復這樣彎腰、標記、起身的姿勢。
不僅是寫這一動作涵蓋了如此無盡的遺忘,關于遺忘的詩歌主題也何其之多。詩人擅長在遺忘的內部把握遺忘,一首歌在奏響第一個音符時便注定逸散在空氣中。詩人言說,仿佛是在回憶,但如果他在回憶,那也是用遺忘來回憶,布朗肖如是說。
四
詩寫的過程圍繞被篩選和析出的經驗展開,以一種主動遺忘的姿態面對被動遺忘的必然。
如此說來,遺忘是最精巧的剪輯師,勝過它任何的同行。甚至,像卡達萊在《H檔案》中所述那樣,它屬于創意的構成部分。沒人知道這樣的去蕪存菁按照何種機制,它的偶發不斷構成意外和意外之間的原創。
不應以悲觀作為遺忘的底色。有的詩歌追緬遺忘,為遺忘摘下帽子,許諾讀者靜默的一分鐘閱讀。在這屏息的寫與讀之中,我們無意來到內部時間的場所,并與外在流動的時間的重量相分離。詩歌以內聚性的凝記,為擺脫現世的遺忘賦予一種輕盈。閱讀一首關于遺忘的詩歌,使我們所經歷的遺忘變得美麗。
五
我不懂人們為什么還在譴責集體的遺忘,好像那并非流淌在我們體內的天性。
我并不需要為寫作,為當代處境下的詩歌,施以某種崇高的招魂術,言必提及“救贖”“見證”,或“再造現實”,好像詩歌以戰勝遺忘為傲,并對人類文明與歷史負過高的責任。我想,更準確來說,詩歌從不應以一己之任對抗業已彌散的生存危機,并且,任何言之鑿鑿宣稱詩歌對這一切應負最大責任的口號,仍是高蹈至可疑的。
文學史是進入詩歌的視角,但只是其一。著史者所處理的是人們面對遺忘時的某一特定情感,但并非全部。還打算伸出它的食指,為后來者說教些什么的詩歌是幼稚的:它既不對詩歌長期以來的存續與生機保有信心,又將那些非詩性的特質掩過自身。
六
哪怕是自己所寫下的同一首詩,每次的返回帶來不一樣的心境。我們從遺忘不同長度的坐標走向那首年輕時寫下的詩。
遺忘豐富人們玩味故我的審美。再次閱讀時,我被再次帶往詩誕生時的混沌,盡管這樣的情感已非為我所有許久。借助遺忘,一首詩的生成性也是可以被這樣詮釋的:多年前栽植的樹木,從未因我們的遠去暫停它的生長。我們無法從以秒分、時日計算的線性日常中感知到差異,但卻在幾年后,一次對詩稿的整理中,你抬起頭,發現不知何時被它如此繁茂的樹蔭所覆蓋。
七
遺忘的詩歌沒有表情,甚至沒有一張完整的臉。那是一張嘴唇,緊繃著,試圖抑制住即將泄露的嘆息。
八
“四月十二號,朋友們去紅海潛水,我留在住處,赫爾格達的臨海民宿里。
這個區域接近任何一個旅游城市中成片分布的度假莊園,白色墻壁、帶有泳池的獨棟小別墅,毗鄰又分散彼此。赫爾格達占有的紅海海岸線一帶,大多平整直暢,但在El Gouna附近,卻顯得破碎支離,不知道是否因為人工填出才呈現出這樣的景致。下午三點的陽光仍然毒辣,像冶金的巧匠,把金屬的顏色潑灑在碧色的海面。隔著一片小沙灘的圍擋,院子內的泳池則是天藍色的,從院子向不遠處望去,兩片水域,像是工匠在大地的面板上淬出的異色玻璃制品。強勁的熱風從西邊吹來,坐在遮陽傘下讀書,喝薄荷茶,不一會兒便被那種暖融的波動包裹得昏昏沉沉。
M回來了。她擦著被海水打濕的發綹,我們聊著近況。談到了什么,她突然停頓一陣,嚴肅對我說:‘你總是這樣忘性大,疏于細節。’
整理筆記時,我讀到年初寫下的不成段的散文。關于忘性這一點,我們沒有進一步探討。我還記得M擦拭身上水漬的樣子:那些在蒸發下,逐漸結晶的、小小的海水顆粒。我沒有提起,詩歌于我,作為另一種結晶的方式。真的,“它以結晶存在于我們手中難以理解”,麗澤·穆勒將愛比作鹽,而詩歌又未嘗不是以這樣的形式保存著。
諷刺的是,如果沒有這段筆記,我幾乎又要將我們的談話,還有那旅途中的住所遺忘。
九
多擅長教人記住的時代:記住生日,記住結婚紀念日,記住登錄密碼,記住企業秋招,記住單詞和高效學習法,記住這條幫你少走彎路的人生哲理。
我不需要在此之中多寫下一首教誨自己與他人記住的詩歌。如果只是將一首詩作為一件備忘簿,我想我的寫作還不足夠勇敢。我更應該擁有那樣的決心,從寫下第一行時,便將它從風中遞送出去,抱定它朝向遺忘的力和飛行。我欣喜它掙脫固定的任何可能。“用遺忘來回憶”,我想,如果那是寫作與詩歌“真正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