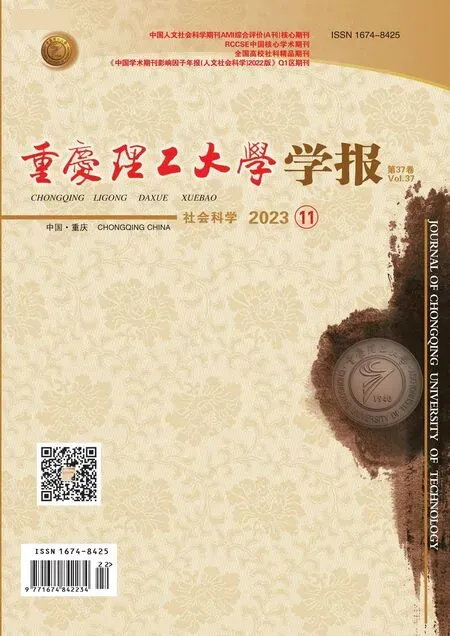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耦合對碳減排效率的影響研究
楊朝均,葉瑞娟
(昆明理工大學 管理與經濟學院, 云南 昆明 650093)
一、引言
我國經濟總量和綜合國力取得長足進步的同時,作為全球能源消耗與排放大國,我國也面臨著嚴重的環境污染與碳排放問題,為未來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帶來隱患。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要求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建設,健全現代環境治理體系并著力完善碳核算、碳交易制度。回顧已有研究,碳減排目標的實現存在多種渠道。王海星等[1]指出產業集聚能顯著促進區域碳減排效率的提高,范東壽[2]發現農業產業的結構優化能同時實現碳減排與技術創新效應,史明霞等[3]研究表明稅制綠化程度與碳排放顯著負相關。鄭媛媛等[4]發現制造業服務化轉型能顯著抑制本地與鄰近城市的碳排放量。無論是產業集聚、行業結構調整,還是稅制綠化,最終都可歸因于政府的環境規制力與市場的產業結構升級力。環境規制作為協調發展與保護之間的平衡關系而制定與執行的一系列政策,是對環境領域市場失靈的有效補充,與產業結構升級有著重要的邏輯關聯[5-6]。能否嚴格執行各項環境規制政策,并充分利用產業結構升級帶來的技術進步與內部優化效應,是關系我國碳減排目標能否順利實現的關鍵。為實現我國各項建設的可持續發展,有必要對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耦合對碳減排效率的影響進行研究。
二、文獻回顧
關于環境規制、產業結構升級與碳減排效率的文獻和研究成果頗為豐富,主要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已有文獻側重研究環境規制對碳減排效率的影響,主要有3類觀點:(1)“促進論”認為合理的環境規制政策能夠通過激勵企業開展技術革新來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從而實現減排效果[7]。代應等[8]基于制造企業面板數據分析,證明環境規制能顯著促進企業綠色設計行為的實施,進而提升環境效益。(2)“抑制論”指出當國家承諾削減對化石燃料的需求時,會使燃料供應商感受到環境政策的威脅,反而導致化石能源開采的提前加速,造成碳排放的急劇增長[9]。王東等[10]通過中介效應模型分析得到環境規制通過抑制技術進步與能源效率降低碳減排效率的結論。(3)“不確定性假說”認為環境規制與碳減排效率間存在非線性關系,鹿才保等[11]研究發現政府主導型規制政策與碳減排效率間存在“U型”曲線關系。
第二,已有文獻側重分析產業結構升級對碳減排效率的影響。王文舉等[12]基于投入產出模型測算了均衡產業結構下不同發展目標所產生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認為產業結構升級對中國“雙碳”目標實現的最高貢獻度為60%;孫麗文等[13]指出第三產業的發展能夠有效降低總體碳排放強度,技術創新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孫凌宇等[14]立足我國“雙碳”目標的現實背景,運用動態空間面板模型探究產業結構升級的減排效應,發現產業結構合理化能顯著抑制區域碳排放強度,且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該抑制作用逐年增強。
第三,綜合環境規制和產業結構升級對碳減排效率的共同作用。張楨鈺等[15]研究指出產業結構升級有利于長江經濟帶的生態文明建設,環境規制在其中表現出顯著負向影響,而兩者交互項與地區生態文明建設表現出微弱的正相關關系。龐慶華等[16]建立自回歸模型探究產業結構、環境規制與碳排放之間的關系,發現三者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同時,短期內區域碳排放量會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上升而增加,隨著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提升而下降。徐軍委等[17]以產業結構升級為門檻變量,發現正式與非正式環境規制都對地區綠色全要素生產效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并在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表現出一定異質性。
綜上,現有文獻更多是分別研究環境規制和產業結構升級對碳減排效率的影響。但是,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具有一定的協調互補關系,且學界對這種協調互補關系在碳減排效率中的作用尚未進行深入分析。因此,本文借助熵權法、耦合協調模型和非期望產出SBM模型,探究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耦合對碳減排效率的影響,期望對關聯領域研究進行一定的補充。
三、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一)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的互動機理
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作用路徑主要包括:(1)技術創新效應。“波特假說”認為環境規制可以鼓勵企業開展低碳技術革新和引進活動,當創新補償效應抵消并超過污染控制成本時,將帶來企業生產效率的改善與經濟產業的高質量發展[7]。(2)產業轉移。規制水平的提高使企業為污染型產品所支付的環保費用不斷上升,促使企業將污染程度較高的生產線遷移至管制松散的地區,使環境規制嚴格地區的產業結構走向更高級形態[5]。(3)產品結構。受環境法規約束,市場上安全性與環保程度較高的產品不斷增多,污染型產品減少,由此帶來產業結構的高級化。(4)外商直接投資。新研發的清潔型產品能夠幫助企業率先占據市場份額,所獲得的超額利潤吸引外資流入,并通過溢出效應與競爭效應等改善本土產業經營環境,從而有利于區域產業結構升級[18]。
產業結構布局與水平差異也會作用于環境規制。一方面,第二產業作為地區生產總值與稅收收入的重要來源,其表現直接影響該地區政府的政績考核結果;同時,第二產業也是主要的污染源頭,需要政府加以管制和引導,由此形成博弈關系。產業結構水平較低時,區域發展模式粗放,在政績激勵與職位晉升的誘使下,地方政府過度重視發展速度與規模,抱有機會主義心理,傾向于施行寬松的管制標準,以污染換取地區財政收入與生產總值的增長;而當第二產業占比達到一定閾值,區域生態退化嚴重時,為阻止環境污染的加速發展,政府會執行趨緊的管制標準以維持當地生態與經濟發展之間一定程度的平衡[19]。
(二)環境規制和產業結構升級耦合對碳減排效率的影響

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會引發能源消費結構與消耗效率的變動,抑制碳排放量的增長[21]。產業演變規律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指出,當產業結構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轉變時,特定的單位產出能夠凝聚更多的資本和技術,減少勞動力、能源消耗,進而強化現有產品的附加價值與環境友好程度,使經濟發展逐漸與環境退化脫鉤。同時,產業升級也是形成研發能力的重要因素,伴隨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和合理化,要素加快在產業內部與產業之間的流動,并最終選擇更優效率領域,進而減少資源錯配現象,給技術創新注入新動力。而通過產業結構升級,碳減排效率的提升也離不開環境規制政策的有效介入[22]。受經營者的有限理性與投機心理影響,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通常會經歷漫長的“陣痛期”,環境管控作為政府政策的信號燈,能夠彌補環境領域的市場失靈,憑借其權威優勢與強制執行力使各經濟主體意識到產業變革與環境保護的必然性,加快調整步伐,大大降低產業調整所造成的時間與經濟成本損失,使碳減排的效果達到最優。
綜上,環境規制和產業結構升級最終會導致碳減排效率的改善,無論是政府規制還是市場結構的升級,其帶來的碳減排效果是真實存在的,而環境規制和產業結構升級間存在的協同互補關系也意味著兩者的耦合協調效應能夠對碳減排效率帶來更為積極的影響。
因此,本文提出假設H1:
H1: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耦合對碳減排效率具有正向影響。

圖1 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耦合對碳減排效率的作用機理
四、研究設計
(一)變量選擇
1.自變量
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的耦合協調度是指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兩者間相互作用、產生協調互補效應,聯合促成某種正向關聯的過程。考慮到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是兩個結構復雜又彼此關聯的子系統,擬構建的指標體系應涵蓋兩者的各個維度,使其為后續耦合協調度的測算具備較全面、合理的評價能力。針對環境規制的指標體系,本文在已有文獻基礎上[23-24],從工業二氧化硫排放強度、工業廢水排放強度、工業固體廢物處置率、生活垃圾無害處理率和生活污水處理率5個方面展開測量。關于產業結構升級的指標體系,本文以三次產業增加值占比、產業結構合理化與產業結構高級化作為一級指標,并從中挑選出8個二級指標。具體指標體系見表1。

表1 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指標體系
本文采用熵權法計算2010—2020年我國30個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臺)的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相關指標權重與綜合得分,具體步驟如下:假設選取n個地區,設計m個指標,xij表示第i個地區的第j個指標評價(i=1,2,…,n;j=1,2,…,m),其中,Mj為xij中最大值,mj為xij中最小值。



步驟4:計算差異系數:gj=1-ej

基于Pile教授提出的物理耦合模型,本文拓展得到如下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的耦合協調度模型:
其中,C表示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的耦合度;T是綜合調和系數,即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的整體協同效應,取值介于0與1之間;?與β為待定系數,考慮到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對碳減排效率同等重要,本文取?=β=0.5;CCD為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的耦合協調度,CCD∈[0,1],參照已有標準和本文具體數值,分別以0、0.2、0.4、0.6、0.8和1為分界點劃分出瀕臨失調、輕度失調、中度協調、良好協調與優質協調5個階段。
今后幾年,河北省將全面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的意見》,在水利部的指導下,學習借鑒兄弟省(直轄市、自治區)的經驗,按照“打造亮點,突破難點,狠抓重點,大膽創新,全面提升”的工作思路和“可操作、可監控、可評價、可考核”的原則,積極穩妥地開展實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試點工作。
2.因變量
本文因變量為碳減排效率。已有研究多采用隨機前沿技術[25]、數據包絡分析(DEA)[26]以及基于兩者所改進的各類模型。其中,數據包絡分析技術因無需提前設定各投入變量與產出變量間的函數關系,能夠有效避免主觀性偏差而被廣泛采用。考慮到經濟生產過程中既存在期望產出,也伴隨著非期望產出,本文采用Tone所改進的非期望產出SBM模型測算碳減排效率,并假設規模報酬不變。以省份為決策單位,每個單元均存在投入向量、期望產出向量與非期望產出向量3類向量。其中,投入向量考慮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年末從業人口和能源消費總額,期望產出向量考慮地區生產總值和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非期望產出向量選擇二氧化碳排放量,具體指標體系見表2。

表2 碳減排效率指標體系
其中,地區生產總值以2010年為基期,通過平減處理得到;二氧化碳排放量(Carbonemisson)的計算借鑒王城等[27]的做法,具體公式見式(7), ?i為第i種能源消費總量,βi為各類能源折合標準煤系數,εi為二氧化碳排放系數,具體系數見表3。

表3 CO2排放系數與能源折合標準煤系數
3.控制變量
基礎設施水平(Infra):用地區公路里程數與地區總人數的比值表示。社會基礎設施的建設與運營過程中會消耗大量的資源與能源,導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
政府財政支持 (Gov):用地區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科學技術支出所占比重表示。財政支持是政府引導和幫助企業從事節能科技研發的重要渠道,對碳減排具有重要意義。
對外開放程度(Openness):用地區進出口總額與區域生產總值的比值表示。進出口貿易通常伴隨著先進技術與知識的擴散和轉移,有利于提升東道國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達到節約資源與減少排放的目的[28]。
能源消費結構(Energy):用煤炭消費總量與地區能源消費總額的比值表示。煤炭作為我國儲量最豐富的化石能源,每年燃燒所釋放的二氧化碳約占總能源消耗排放額的70%,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對我國生態環境已造成嚴重的負外部性影響[29]。
(二)模型構建
依據以上變量設置,本文構建如下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的耦合協調對碳減排效率影響的模型:
CERit=β0+β1CCDit+βilnxit+εit
其中,CERit表示第i個省份第t年的碳減排效率;CCDit表示第i個省份第t年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的耦合協調度;xit表示控制變量,為避免異方差問題,對控制變量皆進行對數化處理;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
(三)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0—2020年我國30個省份(不含西藏與港澳臺地區)為研究對象。研究所用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年度統計年鑒。研究所用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4。另外,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顯示 VIF指數都小于4,說明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變量間存在一定相關性,說明變量的選取具有合理性,具體可見表5。

表4 變量描述性統計

表5 相關性檢驗與多重共線性分析結果
五、結果分析
(一)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耦合協調度
本文使用Stata 15.0測算得到各省市2010—2020年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的耦合協調度,表6展示了各省市主要年份的耦合協調度計算結果。

表6 各省市主要年份耦合協調度結果
由表6可知:時間維度上,2010—2020年我國各省市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的耦合協調度整體呈現逐年增長趨勢,均值水平從0.419提高到0.590;空間維度上,總體呈現由東向西、從南至北逐漸降低的發展態勢。2010年絕大多數省市都處于輕度失調與中度協調階段,僅有天津與上海達到良好協調;2015年30個省市都已脫離失調階段,多數進入中度協調,處于良好協調階段的省市增加到5個,并新增2個優質協調單位,分別為北京與上海。2020年處于良好協調階段的省市增加到7個,處于優質協調階段的省市增加到3個,分別為北京、天津與上海。我國耦合協調度分布的地理差異較為顯著,東部沿海區域效率值領先,可能是由于區域地理位置與國家政策扶持的差異所致。
(二)碳減排效率
基于非期望產出SBM模型,本文利用Matlab軟件測算得到2010—2020年各省份碳減排效率,其時序發展趨勢如圖2所示。

圖2 地區碳減排效率時空演變特征
由圖2可知,整體層面上,中國碳減排效率始終呈現上升趨勢,均值由2010年的0.210增長到2020年的0.341,增幅約為62.4%;相較于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在效率水平與增長幅度上更為領先。為直觀展示我國區域間碳減排效率的分布差異,表7選取2010年、2015年和2020年3個年份,展示了各省市碳減排效率指標的計算結果。
由表7可知,地理區域間碳減排效率差異顯著,總體呈現從東南沿海向內陸地區逐漸降低的趨勢。省域層面上,除青海外,其余省份的碳減排效率在2010—2020年整體保持增長趨勢,幅度略有差異。其中,遼寧、北京與黑龍江的增長幅度最大,分別為407%、94.3%和91.1%,青海、貴州和云南的增幅最小,分別為-4.9%、2.2%和4.3%。這主要是由于地區間產業結構與經濟水平的差異,東部區域經濟發達,高新技術產業與服務行業規模較大,發展相對成熟,碳排放量較少;同時,污染集中治理與能源使用效率、碳減排效率較高。而內陸地區傳統行業和高污染、高排放工業占比較高,工業化與現代化水平低,產業發展模式相對粗放,地區碳減排效率低且增長速度較緩慢。
(三)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耦合協調對碳減排效率的影響
考慮到研究對象是30個省份2010—2020年的短面板數據,為防止回歸過程出現“偽回歸”問題,本文采用LLC與Fisher對數據平穩性進行檢驗,具體結果見表8。由表8可知,變量通過單位根檢驗,表現出平穩性,能夠進一步回歸分析。

表7 各省市主要年份碳減排效率結果

表8 LLC檢驗和Fisher檢驗結果
1.全樣本回歸
考慮到面板數據中個體效應與時間效應的存在,對研究數據進行豪斯曼檢驗,結果強烈拒絕原假設,因此宜選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后續回歸。表9列(1)~(2)是混合OLS回歸結果與隨機效應回歸結果,列(3)~(5)分別展示了時間固定效應、個體固定效應與雙固定效應的檢驗結果。
由表9可知,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的耦合協調度對我國碳減排效率表現出正向影響(β=0.623,?<0.01),說明隨著我國環境規制政策的完善與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兩者耦合協調度逐步上升,促進了我國碳減排效率的提高。在控制變量中,政府財政支持系數顯著為負(β=-0.103,?<0.01),可能是因為政府資金投入的效果具有滯后性,短期內難以表現出積極成效,需要較長時間積累才能看到質的效果。能源消費結構系數顯著為負(β=-0.095,?<0.01),說明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不僅造成大量碳排放,還嚴重阻礙了產業低碳轉型,形成的“資源詛咒”效應阻礙著我國碳減排效率的提高。金融發展規模系數顯著為正(β=0.035,?<0.05),說明金融事業的發展能夠有效緩解行業的融資困境,為低碳行業的發展和企業清潔技術研發提供資金支持,為區域碳減排事業做出貢獻。
2.異質性分析
考慮地理區域、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水平之間的異質性,本文劃分出東、中、西部三大區域: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等11省市; 中部地區包括黑龍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省; 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11省市。首先,分別測算區域間耦合協調度和碳減排效率的關系,回歸結果見表10;其次,以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的均值為標準,劃分出低環境規制與高環境規制地區、低產業結構升級與高產業結構升級地區進行回歸,以測算不同指標水平對耦合協調度和碳減排效率關系的影響,具體結果見表11。考慮到在固定效應模型中,個體固定效應模型相對擬合度更高,以下回歸皆為基于個體固定效應模型進行的回歸。

表10 按地理區域分組回歸結果

變量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1)(2)(3)Energy-0.126???0.097???0.007(0.00)(0.00)(0.58)Finance0.313???-0.0000.028(0.00)(0.94)(0.11)Constant0.068-0.792???-0.034(0.84)(0.00)(0.80)觀測值12188121R20.9000.6840.895
由表10可知,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耦合對碳減排效率的促進效應在中部地區的表現明顯高于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這是因為中部地區的工業占比較大,在提升碳減排效率上還有很大發展空間,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耦合對碳減排效率的正向影響較為明顯;東部地區低碳試點城市較多,環境規制的立法執法力度大,同時產業結構中科技產業與現代服務業比重較高,碳排放總額相對較低,碳減排效率的提升空間較小;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科技創新水平低,產業的低碳轉型與環保政策的落實難度更大,因此,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耦合對西部地區碳減排效率的促進作用最為微弱。

表11 按指標水平分組回歸結果
表11回歸結果表明,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耦合對碳減排效率的促進作用會隨著地區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不同而產生顯著差異:對低環境規制地區的影響大于高環境規制地區,這一結果證實了“綠色悖論”——環境規制強度的提高對碳減排效率表現出抑制作用。同時,對高端產業結構升級地區的促進作用要比低端產業結構升級地區更為明顯,這主要是因為當產業結構發展水平較低時,地區經濟發展模式粗放,政府進行環境保護、企業調整產值結構的機會成本較高,雙方更傾向于犧牲環境以換取經濟產值;而當產業結構發展水平較高時,區域發展更注重技術效率與要素質量的優化,將環境質量納入政府的考核體系與企業社會責任,雙方都愿意關注生態環境并追求可持續發展。
3.內生性分析
盡管本文已對能源消費結構、金融發展規模等變量進行控制,考慮到其他因素可能產生的影響,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的耦合協調度對碳減排效率的影響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為保證研究結論的準確性,本文選用工具變量法進行檢驗,將碳減排效率的一階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采用2SLS和差分GMM估計法進行檢驗,檢驗結果見表12。
模型(1)為2SLS法的檢驗結果:第一階段F值和第二階段Wald檢驗值皆大于臨界值,因此排除弱工具變量問題。同時,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耦合協調度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與上文研究結論基本保持一致。
模型(2)為差分GMM估計法的檢驗結果:AR(1)檢驗中P值小于0.1,AR(2) 檢驗中P值大于0.1,Sargan檢驗的P值大于0.1,表明差分GMM的模型選擇具有合理性,同時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和顯著性水平與上文回歸結果保持一致,說明在考慮內生性問題后上述研究結論仍然成立。
六、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本文基于中國2010—2020年30個省市的面板數據,運用熵權法、非期望產出SBM模型、耦合協調模型和固定效應模型,探究了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耦合對碳減排效率的影響。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全國各省市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的耦合協調程度不斷提高,多數地區進入中度協調與良好協調階段,總體呈現由東往西、從南至北逐漸降低的地理差異特征。
第二,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耦合協調度對碳減排效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即兩者耦合協調程度越高,地區碳減排效率也相應越高。
第三,不同地理區域間耦合協調度對碳減排效率的影響存在差異,中部地區影響最為明顯,其次是東部地區,西部地區影響最為微弱。
第四,耦合協調度對碳減排效率的影響會隨著地區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水平的不同而產生差異:對低環境規制地區的影響大于高環境規制地區,對高端產業結構升級地區的影響比對低端產業結構升級地區的影響更為顯著。
根據本文研究結果,基于國家對碳減排目標的要求,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加強政策的整體性與協同性。目前我國省市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明顯的耦合關系和區域差異,因此,地方政府應強化環保工作和產業發展之間的有效互動,以自身經濟基礎和功能規劃為落腳點,大力培育和發展科技研究、教育、旅游等高端服務業,推動地區產業結構向高級化、合理化方向發展,同時關注發展過程中的環境問題,建立各級政府生態保護議事機制,加快健全并落實不同產業準入門檻和規制標準,著重把握對重污染區域、行業和企業的監督治理工作,大力推動遙感、區塊鏈和大數據等技術應用,并通過財政補貼、稅制優惠等政策激勵企業開展低碳技術創新活動,自發進行生態無害化經營,加快促成地區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的和諧共進,進而提升碳減排效率。
第二,注重政策的地域性與靈活性。當前京津滬城市群環境規制與產業結構升級耦合已達到優質協調階段,可以將部分產業遷移至中西部地區,通過示范效應帶動這些地區加快產業轉型。同時加強與周邊省市的經驗交流與政策幫扶力度,為其他地區注入減排動力。中部地區產業結構偏重工業,要加快產業數字化轉型與落后產能淘汰,重點推進山西煤炭、安徽鋼鐵和江西有色金屬等傳統產業的改造工程,實施環境保護省際聯防聯控策略,共同形成對環境污染與違規排放等行為的震懾力。西部地區絕不走“先污染后保護”的老路,應根據自身資源稟賦與碳匯優勢,適當發展特色農業與新能源產業,選擇性承接東中部地區的優質產業轉移,重點把握核心技術,打造人才梯隊,持續擴大低碳產業規模,探索發揮區域優勢的可持續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