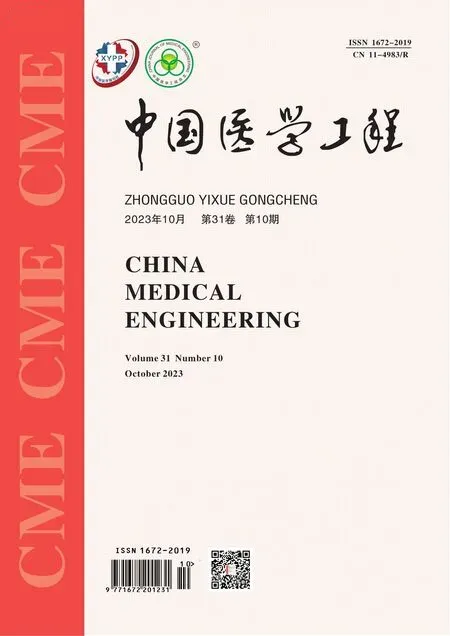3D打印技術在脊柱外科應用進展*
張繼偉,楊鎮源,韓李霞,將振興,鄧強
(甘肅省中醫院,甘肅 蘭州 730050)
3D 打印是一種起源于20 世紀80 年代的新興技術,已廣泛應用于醫療、工業生產等領域,其中在醫療領域主要應用于脊柱外科、復雜創傷、頜面外科、神經外科等專業,為臨床實踐及輔助教學提供了更加直觀的效果[1-2]。脊柱解剖復雜,周圍毗鄰脊髓、神經、大血管等重要結構,手術難度大,失敗率高,手術操作的精準化與個體化越來越多的被廣大脊柱外科醫師所重視[3];而3D打印技術的特點就是精準化與個體化,因而3D 打印技術在脊柱外科領域的應用發展迅速,在術前規劃、3D 打印導板輔助置釘、內植物的個體化制作、臨床教學等方面大大提高了脊柱外科手術效率[4]。現將3D 打印技術在脊柱外科的應用方面做一論述。
1 3D 打印概述
3D 打印技術又稱為“增材制造”或“快速成型”技術,其原理是通過采集CT 等影像學數據經轉換獲得3D 打印所需的數字模型文件,將數據傳送到3D 打印機,使用各種打印材料逐層附加制造出所需的打印對象[5]。目前3D 打印技術常用的材料加層方法主要有三種:①熔融沉積打印技術。該技術是將熱塑性材料通過噴嘴加熱至熔融態,在計算機控制下將材料經噴頭擠出并按設定的模型沉積出實物,這種技術簡單、經濟,材料利用率高。②立體光固化成型技術。該技術利用液態光敏樹脂為材料,通過控制激光照射液態樹脂表面逐層固化,并獲得完整的模型。這種技術具有成型快,精度高等特點,但打印設備造價高,材料昂貴,成型產品強度差,液態光敏樹脂有污染等缺點。③選擇性激光燒結技術。該技術以熱塑性聚合物粉末為材料,通過二氧化碳激光對規劃區域進行熔化和融合,不斷重復鋪粉燒結過程使粉末熔融堆積成三維模型,該技術打印材料廣泛,制作工藝簡單,材料可循環利用,缺點是打印產品表面粗糙,打印過程揮發異味等。
2 3D 打印在脊柱外科的應用類型
3D 打印作為一項新興技術在脊柱外科中有重要應用價值,該技術以其個體化、精準化及可視化的特點在脊柱外科的臨床治療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目前,3D 打印已廣泛應用于脊柱外科的臨床教學、術前規劃、手術模擬、個體化導航模板及個體化內植物等多個領域。
2.1 實物脊柱模型
2.1.1 3D 打印脊柱模型在臨床教學中的應用 脊柱外科是骨外科的重要分支,脊柱解剖輔助,周圍毗鄰血管、神經及重要組織結構,實物脊柱模型可以直觀的反應各相鄰結構之間的解剖關系,便于學生更好地掌握[6]。同時,3D 打印可以實現脊柱病變的實物模型,便于學生更好地理解病變脊柱的解剖,提高醫學生對病變脊柱的認知[7]。李曙明等[8]發現在復雜脊柱畸形教學中,通過3D打印實體模型與影像學資料對比與反思后,極大地提高了學生對疾病的閱片和診斷能力,而且在教學效率和效果上顯著優于傳統教學。
2.1.2 3D 打印脊柱模型在術前方案制定及模擬手術中的應用 脊柱解剖結構復雜,尤其當病變涉及上頸椎、頸胸段及脊柱腫瘤、嚴重脊柱側凸或后凸畸形等情況時,能夠了解患者病理情況下的解剖結構對疾病的診治至關重要[9]。以往只能通過傳統影像手段X 線、CT 或MRI 來了解脊柱的病理基礎,往往不能提供復雜脊柱疾病的全面解剖信息[10]。而依靠3D 打印技術所呈現的病理狀態下的脊柱實物模型可以為臨床提供更好的可視化信息及觸覺反饋,可以幫助制定精準、個體化的手術方案,在術前可以通過模擬手術增強術者的信心,術中通過對照脊柱實物模型可以更快、更精準地找到對應的解剖結構及病變部位,進而有效縮短手術時間,減少術中出血及透視次數[11]。PACIONE 等[12]通過應用3D 打印模型,對上頸椎畸形并顱底凹陷癥患者病變區域的骨性畸形、脊髓受壓情況及椎動脈走向進行了全面的評估,通過實物模擬操作,制定最佳的手術方案,術后患者恢復良好。
2.1.3 3D 打印脊柱模型在醫患溝通中的應用 在醫患矛盾日益加劇的今天,如何能讓沒有醫學知識的患者及家屬更加直觀的了解病情及手術方案成為擺在廣大醫務人員面前的一大難題。而3D 病理脊柱模型可以作為良好的講解工具,幫助醫生更好地闡明解剖異常,在醫患交流中發揮有效的溝通作用。對于患者來說,3D 模型可以幫助他們可視化“內部情況”。從圖像到手持模型的轉變,讓患者及家屬聽得懂、看得懂,提高醫患之間的術前談話效率,縮短術前準備時間,進而保證后續手術治療方案的順利實施。林鋼等[13]在術前使用3D 打印模型與患者及其家屬交流,提高了患者對手術的理解,提高了醫患溝通效率。
2.2 3D 打印個體化導板
脊柱外科術式多樣,其中椎弓根螺釘固定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所以如何有效準確地植入椎弓根螺釘又能避免傷及脊髓、神經根及周圍大血管是廣大脊柱外科醫生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14]。而目前徒手置釘仍然是最常見的置入方式,對于嚴重的脊柱側凸、脊柱骨折、脊柱腫瘤、上頸椎畸形等脊柱疾患,因椎體形態不規則,且多伴有椎體發育異常、椎體旋轉,椎弓根解剖標志不明確時,徒手置釘螺釘極易突破椎弓根,造成脊髓、血管損傷等嚴重并發癥,甚至危及生命。研究[15]表明,徒手置釘錯位發生率為20%~30%,神經、血管損傷等嚴重并發癥發生率占2%,因此如何提高置釘準確率,降低置釘風險越來越多地受到脊柱外科醫師重視。AZIMI 等[16]發現頸椎手術中3D打印導航模板可以提高椎弓根釘置釘的準確性,從而改善手術效果。近年來隨著3D 打印技術在脊柱外科應用普及,依據椎體表面形態數據結合工程設計制造出完美貼合骨性表面的3D 打印個體化導板,輔助椎弓根螺釘置入,可有效的避免對重要神經血管的損傷[17]。SUGAWARA 等[18]對12 例寰樞椎不穩定的手術患者應用3D 打印導板輔助置入寰椎側塊釘及樞椎椎弓根螺釘,左右螺釘均成功置入且未穿透骨皮質,術后復查影像學檢查發現與術前計劃的置釘路線偏差僅為(0.70±0.42)mm。盧炯炯等[19]通過手術對比,發現3D打印組螺釘置釘位置準確率高于CT 三維掃描組,且矯正率和并發癥發生率均明顯低于CT 三維掃描組。
2.3 3D 打印個體化內植入物
由于人體構造精密且復雜,在臨床應用中,廠家提供的內固定植入器械常常不能與患者的生理解剖相匹配,內植入物不能與人體骨骼良好貼合,造成患者功能恢復預后不良,影響植入物的生物安全性,給患者造成生理痛苦和心理創傷。3D 打印可根據人體的生理構造特點制作出具有特殊解剖結構的假體,使骨質與內植入物完全融合,比普通假體更加貼合,大大提高了內植入物的生物力學性能和安全性[20]。椎體旋轉、椎弓根缺失或畸形、節段異常這些復雜畸形都是脊柱側凸的表現,破壞了椎弓根插入的解剖標志。3D 打印模板以圖像為基礎,通過術前對葉片進行CT 掃描和計算機輔助設計,將設計好的文件以固定格式導出到3D 打印設備中,從而打印出個體化、精準的手術輔助置釘工具。該模板通過與脊柱表面形成特定的貼合,達到導向鉆孔和螺釘放置的目的[21]。WEI 等[22]在一例骶脊索瘤患者全骶骨整塊切除術后3D 打印骶骨假體進行重建中發現:3D 打印骶骨假體有兩個優點:①定制的植入物完成了腰骶骨盆環的最佳重建,提供了一個穩定、安全的力學支撐;②打印假體的多孔表面可誘導骨長入,促進假體與骨質的融合,增強功能結構的穩定性。徐會法等[23]在36 例3D 打印導板輔助置釘治療先天性脊柱畸形中,采用19 例導航下置釘作為對比,發現3D 打印組手術時間、置釘時間較導航組明顯縮短、且術中出血量顯著少于導航組,隨著術后時間推移,兩組患者視覺模擬評分法(VAS)、Oswestry 功能障礙指數(ODI)、日本骨科協會(JOA)評分均顯著改善。3D 打印組脊柱側凸研究學會22 項(SRS-22)量表評分術后及末次隨訪均優于導航組。相比之下,3D 打印導板技術治療先天性脊柱畸形在手術時間、置釘時間、術中出血量及患者滿意度方面更具優勢。
2.4 3D 生物打印
3D 生物打印是組織工程的重要技術之一,目前常用的3D 生物打印方法有噴墨打印、擠壓生物打印和激光生物打印[24]。傳統3D 打印中使用的生物材料被稱為分為天然生物材料和合成生物材料[25]。3D 生物打印在骨科是最有發展潛力的生物醫學領域之一,主要應用于骨與軟骨及皮膚與軟組織的修復,是連接生物材料和活細胞的一種新型技術,是組織工程中的一種重要方法[26]。骨缺損的修復一直是骨科醫生面臨的一個挑戰。3D 生物打印機制是將細胞、生物材料、生物活性物質結合,在損傷部位打印假體直接修復組織缺損。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和伴隨而來的慢性疾病,骨缺損的治療越來越困難,特別是由外傷、感染、腫瘤導致的大范圍的骨缺損,會發生骨不愈合,需要進行手術修復重建,常用的手術方式有骨移植、吻合血管移植等。3D 生物打印具有替換或修復受損組織和器官的優點,有望替代上述移植方式。3D 打印過程分為圖像采集、數據導入計算機制作軟件、打印機讀取及處理文件、打印移植體四個步驟。“生物墨水”是3D 打印的重要介質,具有黏度低、低毒、低抗原性和生物降解性,可以通過特定的表面受體與細胞相互作用,促進細胞遷移和細胞外分子的產生,從而促進細胞增殖[27]。常用的生物材料為藻酸鹽水凝膠、膠原蛋白和透明質酸等有機溶液。藻酸鹽水凝膠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能形成有利于細胞再生的多孔結構,膠原蛋白是人體細胞外基質的主要成分,透明質酸可刺激骨細胞代謝,促進骨組織修復,抑制炎癥反應[28]。要獲得最佳的模型效果,不僅要選擇合適的生物材料,而且印刷工藝的選擇也是至關重要的[29]。金屬基骨修復支架是骨科植入物的最佳選擇之一,事實證明,制造能夠復制組織和器官的結構和功能的金屬基骨修復支架具有挑戰性[30]。WU 等[31]通過模擬天然木材中的微/納米結構層次,將三維打印技術與水熱處理相結合,構建了多級多孔磷酸鈣生物陶瓷骨組織仿生支架,這種支架具有多孔天然木材分級孔及良好的骨誘導活性。這表明微/納米晶須涂層是調節細胞行為和骨誘導活性的關鍵因素。WILCOX 等[32]也證明了3D 目前用于脊柱外科定制假體以及“現成的”植入物,具有增強植入物性能、減少手術時間和改善患者預后的潛力。
3 總結與展望
3D 打印自問世以來,就已為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福音,其不僅應用于脊柱疾病的手術治療中,更涉及醫學教育、醫藥發展、生物醫學、外科整形等。3D 打印技術是一種創建計劃的新技術,它為提高藥品的功效、安全性和便利性創造了新的機會。在生物打印的廣泛使用方面,生物安全性、免疫原性和不斷上升的成本正日益受到關注。盡管如此,3D 打印模型無法同時滿足合適的生物材料、生物相容性及機械性能三者并駕齊驅,也就是說,目前的打印技術除了生物材料與細胞相融合的打印技術相對成熟之外,體外環境難以模擬細胞外基質,組織支架的打印模型還不能實現營養物質的良好交換,目前的3D 打印技術還達不到將人體精密又復雜的構造完全仿生的水平。除此之外,限制3D 打印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打印材料價格昂貴,這限制了3D 生物打印可開發生物材料的范圍。材料在組織支架生物打印中發揮著核心作用,大多數材料無法滿足植入生物材料的特性,從而導致打印材料成本高昂,給患者及醫療主體造成巨大的經濟負擔,打擊了研究者的積極性,影響其發展的前景。這也是3D 打印技術要應用于復雜脊柱畸形中才能最大價值地發揮其經濟效益,在普通病例中應用該技術難以做到資源最大化的利用,所以開發新型材料以克服現有材料所面臨的局限性是當務之急。如果這些局限性問題能得以解決,3D 打印技術的應用前景將會邁上更高的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