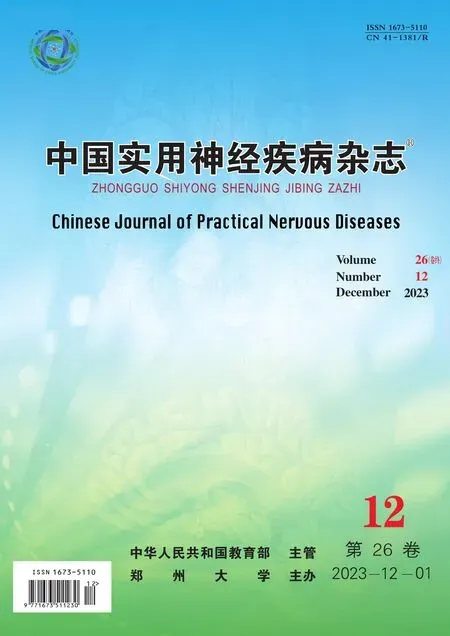中青年缺血性腦卒中后抑郁的影響因素及預測模型構建
韓 燕 奚廣軍 馬雪梅
南京醫科大學附屬無錫人民醫院,江蘇 無錫 214000
缺血性腦卒中的致殘率較高,易遺留軀體障礙等,造成患者生活方式和環境發生明顯改變,使生活質量下降。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PSD)是腦卒中患者常見的情感障礙,主要表現為消沉、煩躁、情緒極度低落,發生率可達10%~40%,以中青年患者的PSD發生率最高[1]。研究表明,PSD不僅可能加重患者軀體癥狀,使治療時間延長,同時增加患者精神壓力,不利于其回歸及融入社會,嚴重時還會增加患者自殺風險[2-4]。基于此,在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的臨床治療中還應明確PSD 的影響因素,進而識別PSD高危人群,積極預防PSD。本研究以102例中青年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為對象,分析PSD 發生情況及其影響因素。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納入2020-01—2021-03 于南京醫科大學附屬無錫人民醫院就診的缺血性腦卒中患者102 例進行PSD 模型構建,以2021-06—2022-10就診的82 例中青年缺血性腦卒中患者進行模型驗證。研究獲得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倫理號:KY21092)。
納入標準:(1)經顱腦CT診斷為缺血性腦卒中,且為首次確診;(2)年齡18~59歲;(3)入院時經評估無抑郁癥狀;(4)具備基本溝通與理解能力。
排除標準:(1)伴嚴重臟器疾病者;(2)伴惡性腫瘤、精神疾病、認知障礙者;(3)伴慢性消耗性疾病、感染性疾病者;(4)入院前半年內有嚴重創傷史者;(5)入院前服用過抗精神病藥或抗抑郁藥物者;(6)入院前有自殺傾向者;(7)有躁狂或輕躁狂發作史者;(8)有酒精和藥物依賴者;(9)短暫性腦缺血發作、腦出血、蛛網膜下腔出血者。
1.2 方法于缺血性腦卒中發病后2周左右采用抑郁自評量表(self-racting depression scale,SDS)進行PSD 篩查。SDS 包括軀體性障礙、精神性情感癥狀、精神運動性障礙、抑郁性心理障礙4個維度(共20個條目),每個條目0~3 分,20 個條目得分之和為總分,乘以1.25 倍后取整為最終得分。<53 分為無抑郁,≥53分為存在抑郁,其中53~62分為輕度抑郁,63~72分為中度抑郁,>72分為重度抑郁[5]。
根據PSD 篩查結果將患者分為PSD 組和非PSD組,比較2組患者的臨床資料,包括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家庭人均月收入、醫療保險、基礎疾病(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卒中發病部位、病灶數(單灶、多灶)、NIHSS 評分、病恥感應激量表(stigma stress scale,SSS)評分[6]、Herth 希望指數量表(Herth hope index,HHI)評分[7]。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確定中青年缺血性腦卒中后PSD的影響因素并構建預測模型。
1.3 統計學處理采用SPSS 25.0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符合正態分布,采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比較采取獨立t 檢驗;計數資料用例(%)表示,比較采取χ2檢驗;影響因素采用多因素Logistic 回歸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中青年缺血性腦卒中后PSD發生情況102例患者中30例出現PSD,發生率29.41%(30/102)。30例PSD患者SDS評分56~68(61.03±3.18)分,其中輕度抑郁26例,中度抑郁4例。
2.2 中青年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發生PSD 的單因素分析2 組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醫療保險、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卒中發病部位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PSD組患者家庭人均月收入≤5 000 元、病灶數為多灶的占比及NIHSS 評分、SSS 評分均高于非PSD 組,HHI 評分低于非PSD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單因素分析Table 1 Single factor analysis
2.3 中青年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發生PSD 的回歸分析將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學差異的變量作為自變量(賦值見表2),以PSD發生情況(PSD=1,非PSD=0)作為因變量進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家庭人均月收入、病灶數、NIHSS評分、SSS評分、HHI評分是中青年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發生PSD的影響因素(P<0.05)。見表3。

表2 自變量賦值Table 2 Assignment of argument variables

表3 PSD的多因素回歸分析Table 3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SD
2.4 PSD模型的構建與驗證根據回歸系數與常數項得出預測模型的表達方程:Logit(P)=0.395×家庭人均月收入+0.700×病變數+0.519×NIHSS 評分+0.641×SSS 評分-0.924×HHI 評分-27.984,根據患者評估結果帶入上述模型即可獲得患者發生PSD的概率,以最大約登指數計算出模型閾值為0.614。使用該模型預測82例患者發生PSD情況,以0.614為依據(>0.614 者預測會出現PSD,≤0.614 者預測不會出現PSD),以SDS量表測評結果為金標準。82例患者經SDS 測評診斷為PSD 患者21 例,非PSD 患者61例;模型預測PSD 患者26 例,非PSD 患者56 例。模型預測82例患者發生PSD的敏感度85.71%(18/21),特異度86.88%(53/61),準確度86.58%(71/82)。見表4。

表4 預測模型的驗證 [n(%)]Table 4 Validation of the prediction model [n(%)]
3 討論
研究認為中青年是社會及家庭的主要勞動力,承擔著較大的社會責任以及家庭負擔[8-9],因此該人群發病后的絕望情緒也更加嚴重,重度抑郁風險較高。本研究中102 例中青年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發病后早期(2周)PSD發生率29.41%(30/102),與以往研究[10-11]報道的卒中人群中33%的PSD 發生率較為接近。在抑郁嚴重程度方面,本組患者輕度抑郁26例,中度抑郁4 例,并未出現重度抑郁,提示中青年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的PSD仍以輕、中度為主,較少出現嚴重抑郁情況。分析原因,隨著醫學水平的進步,“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已成為主要的醫學模式,疾病對患者心理、情緒產生的影響也受到臨床更多的關注,使得針對心理方面的干預也越來越多,對疏導患者負性情緒、改善心理狀態發揮了重要作用,進而有效減少了重度抑郁的發生[12-15]。
本研究中單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 回歸分析顯示,家庭人均月收入、病灶數、NIHSS評分、SSS評分、HHI評分是PSD的影響因素。對于家庭人均月收入較低(≤5 000 元)的患者而言,發病不僅會失去收入,且醫療費用還會帶來一筆不小的支出,使得患者在面臨疾病對身體損害的同時,還要擔憂治療費用及家庭收入情況,容易產生較重的心理負擔而滋生焦慮等負性情緒,甚至誘發抑郁[16-17]。已有證據表明,腦卒中的病因與腦部血液循環障礙有關[18-20]。“血管性抑郁”假說也認為,血管性危險因素與抑郁癥的發病之間關系密切,抑郁癥發生率隨血管性危險因素的增加而升高[21-22]。本次研究也發現多病灶患者的PSD 發生風險更高,分析原因為多病灶患者更易損傷神經功能,尤其容易破壞情感調節環路,進而誘發PSD[23-24]。NIHSS 評分越高,患者神經細胞修復、再生能力越弱,神經損害越嚴重,預后也相對越差,患者易因神經功能缺損、生活不便、行為受限等導致發病后生理、心理平衡失調而誘發反應性抑郁癥狀[25-26]。卒中患者易因軀體障礙、自我懷疑等誘發刻板印象的病恥感[27-28]。中青年是家庭和社會的中堅力量,對后遺癥的擔憂往往使患者難以接受疾病和當前現實,甚至擔心難以回歸到工作崗位或回歸工作崗位后會因工作能力受到影響而被歧視,加深內心的病恥感,最終誘發抑郁[29-30]。研究發現,患者SSS 評分越高,病恥感越強烈,越容易出現回避社交行為、情緒極度低落等癥狀,大幅增加PSD發生風險[31-32],與本研究結論一致。希望水平影響患者的疾病感知,希望水平較高者往往能積極調整心態,同時增強其對未來的信心,進而積極應對疾病,PSD發生風險較低[33]。中青年缺血性腦卒中患者與其他年齡段相比更注重自身的家庭價值和社會價值,卒中發病對生活及工作的影響使患者產生自我懷疑,進而影響其希望水平,誘發PSD。
本研究基于多因素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構建了中青年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的PSD 預測模型,且經過驗證,該模型對PSD有較高的預測價值,預測PSD的準確度可達86.58%(71/82),說明臨床可使用該模型對中青年缺血性腦卒中患者PSD進行早期識別和預測,并針對高危人群開展針對性干預,最大限度降低PSD 發生率。本研究為單中心研究,進行模型建立和驗證的病例來源單一,加之樣本量偏小,使模型的代表性及科學性存在局限性,后續有待繼續擴大樣本量并建立更準確的預測模型,實現模型的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