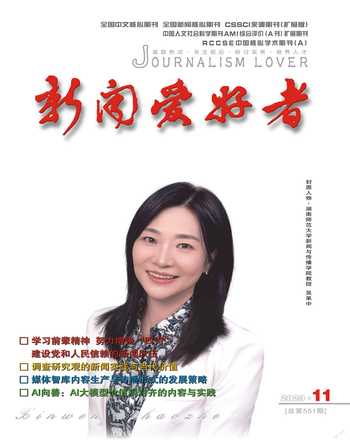逝者紀念賬號與數字哀悼的互構研究:平臺可供性的視角
【摘要】對于死亡、哀悼與社交媒體平臺之間關系的探討近年來逐漸增加。國內主要的社交媒體平臺陸續推出“紀念賬號”,將逝者社交賬號的可供性重新分配于數字哀悼實踐,以此回應已故用戶的不斷增長以及隨之而來的紀念和情感需要。以“實踐中的互構”為導向,探索數字平臺與哀悼用戶的動態協商過程,包括平臺設計“紀念賬號”的動機;不同平臺的技術支持和參與式文化催生出的可供性差異和平臺方言;用戶對消極可供性的反身性思考。紀念賬號的物質穩定性將逝者社交賬號從臨時檔案轉化為“永生不朽”,使其重新成為社交關系網絡中的活躍節點,由此激發了多元的記憶策展和情感分享體驗,推動哀悼活動融入數字日常生活。這雖然削弱了死亡和哀悼的禁忌哀傷色彩,但也帶來了必須應對的新問題。為了讓數字化生存(死亡)更有品質和尊嚴,平臺應不斷將用戶對新增功能及其局限性的回應納入技術架構中,充分尊重個人信息自決權和哀悼社區的多元需求。
【關鍵詞】社交媒體平臺;數字哀悼;紀念賬號;平臺可供性;個人信息自決權
一、數字時代的死亡與哀悼
無論在英語國家還是中國,死亡是被人們回避甚至憎惡的話題。[1]除非是名人或其他有新聞價值的人物逝世,否則在日常生活中直接討論死亡會被看成病態的表現。現代社會的死亡大多發生在醫院里,遺體被送到殯儀館和墓地,在城市的邊緣空間舉行哀悼儀式,生命的凋零過程被隱蔽起來。[2]不過,心理學已經從瀕死病人和喪親者的研究中發現,死亡有著物理和社會的不同維度,后者包括三個層次:“肉身消失、社會身份和社會連接的喪失。”[3]肉身死亡并不必然帶來社會互動的中止,與逝者保持“持續的聯系”(continuing bonds)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能夠幫助喪親者撫平悲痛。[4]
數字技術的發展進一步推動死亡和哀悼從思想觀念到行動實踐的改變。20世紀90年代已經出現了“網絡紀念館”(Cyber memorials)和“虛擬墓地”(Virtual cemeteries)。[5]死亡開始解除現代性的隔離,“被中介化而進入公共領域”。[6]與逝者之間的“持續聯系”獲得了新的可能,喪親者之間能跨越地理距離形成“哀悼社群”。[7]不過獨立網站上的“虛擬墓地”與實體墓地一樣,仍是將死者安置在與生者相區隔的空間。隨著社交網絡成為日常活動的中心,大部分個體進入“全面數字化的生存狀態”。[8]肉身死亡后,有大量“數字遺跡”(digital remains)留在各類社交媒體中。[9]技術不再只是一種和逝者取得聯系的媒介,逝者就存在于數字技術之中,甚至有望獲得“數字永生”(digital immortality)。[10]哀悼也不再遠離社交,越來越多的人轉向社交網絡紀念逝者,即“數字哀悼”(digital mourning)。[11]
過去十余年來,西方學術界對這一主題的研究興趣迅速增加。[12]根據牛津互聯網研究所的預測,到2100年,Facebook將有13億已故用戶,假如該網站保持現在的增速,那么到本世紀末,死亡人數將飆升到36.8億,Facebook有望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數字墓地”。[13]從2007年起,以Facebook為代表的平臺已經開始管理逝者社交賬戶、電子郵件。死亡、哀悼與Myspace、Facebook、Instagram等平臺的關系及差異之處成為研究者青睞的選題。[14]迄今為止,研究的地理范圍主要在北美和歐洲,集中在少數幾個大平臺上。然而,社交媒體作為哀悼實踐發生和協商的平臺,已經成為一種全球現象。[15]從2020年起,新浪微博、B站等國內社交媒體平臺陸續推出“紀念賬號”,開啟了逝者、生者和平臺之間“穿梭時空的對話”。[16]作為一種平臺數字交往,用戶如何與紀念賬號發生互動,對平臺的技術架構演變產生了何種影響,未來平臺和用戶如何在合作中規范數字哀悼活動,成為本文研究的核心問題。
二、實踐中的互構:理解平臺可供性
勞倫斯·萊西格(Lawrence Lessig)提出網絡空間是由其“架構設計”(Architecture)決定的,代碼作為架構的一種形式,成為實際的約束力量,控制著網上行為,比法律更有效。[17]時至今日,“代碼即法律”的觀點仍保有福柯式的穿透力。[18]但萊西格過于強調技術的支配力量,無法捕捉創新過程的復雜動態。
“技術可供性”(Technology Affordance)很好地調和了這種矛盾。“可供性”是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自創的概念,表達動物(人)與環境之間的“協調性”關系。在吉布森看來,可供性是環境固有的,動物(人)“看到事物就知道如何在它們之間行動,以及用它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19]唐納德·諾曼(Donald
Norman)批評吉布森未考慮到行動主體的心理和認知過程,他將技術人造物的“感知可供性”(perceived affordances)引入人機交互、界面設計等領域,[20]但也不免窄化了吉布森的思想。對此,威廉·蓋弗(William Gaver)提出可供性主要是“關于行動和互動的事實,而不僅僅是感知”,用“技術可供性”(technology affordance)來論證可供性是“以用戶為中心分析技術的有效工具”,潛在的可供性可以根據不同媒介揭示它們的能力來理解。[21]
在數字哀悼相關研究中,可供性的應用主要有兩大路徑:一種關注不同技術的特性在特定情境下如何創造或限制哀悼活動。例如,有研究發現,Facebook紀念頁面的復制、搜索和修改功能意味著逝者記憶向不同的網絡公眾開放,帶來合作和沖突。[22]另一種路徑則從用戶的能動性出發。例如關注Instagram用戶上傳的葬禮圖片,探討用戶如何在平臺的賦能和制約下創造性地形成“平臺方言”(platform vernacular)。[23]
與吉布森筆下穩定的自然環境不同,社交媒體平臺本身具有“動態”和“可塑”的特性。[24]目前的研究都是在技術和社會的兩端搖擺,[25]偏離了吉布森和蓋弗調和二者的初衷,無法揭示“人和技術互為主體”的復雜關系。[26]平臺和用戶之間存在著動態協商的復雜過程,研究平臺可供性不僅需要關注用戶對平臺的供給,還需要充分考慮到平臺也在不斷適應、學習和響應,隨著共享環境和用戶的變化而變化。[27]
數字時代的死亡與哀悼揭示了用戶和平臺共同進化的過程。社交網站最初是年輕人社交的空間,平臺的架構并未考慮到用戶死亡。社交媒體平臺不得不獨立面對法律的匱乏和實踐經驗的空白。在具有影響力的科技巨頭中,Facebook做出了最為持久的探索。刪除逝者賬戶遭到強烈抵制后,Facebook迅速調整,重新將自己定位為信息保護者。此后,個人和集體喪親之痛的現實復雜性不斷對平臺技術協議發起挑戰,Facebook也在不斷地與用戶協商并做出調整。
由此,在平臺架構與用戶哀悼行為之間,產生了一種不間斷的互構。社交賬號最初不是紀念物,通過架構調整,如紀念賬號、紀念頁面的設置,平臺將其物質性和功能性重新分配于紀念活動。在與新的平臺環境互動時,用戶在個體或集體的數字哀悼行動中產生對可供性的“積極解釋”,經由平臺機器學習系統的反饋回路,再次成為塑造平臺可供性的重要部分。從這個意義上,本文提出以“實踐中的互構”為導向,將平臺可供性視為平臺設計方的意圖和認知、技術的物質性和功能性、用戶的意愿和行動三者共同作用并不斷演化的產物。
具體而言,哀悼是“以記憶為基礎的情動體驗”[28],既是記憶描述,也是情感實踐,二者相互影響。因此,本文將從平臺的記憶可供性和情感可供性兩個維度來把握數字哀悼的關系性(relational)和過程性(processual)。采用的是本·萊特(Ben Light)等人提出的“漫游方法”(walkthrough method)。[29]研究問題包括平臺設計“紀念賬號”的動機、預設的使用環境和特定活動;技術的物質性和功能性如何驅動用戶行動,用戶又有哪些預設之外的哀悼實踐,對消極可供性的理解又將對界面設計產生何種影響。最后,本文還將從平臺技術架構的角度探索更好地支持數字哀悼的方式。
三、為了逝者的紀念:平臺架構與數字哀悼的互構過程
(一)從刪除到紀念:平臺變革之路
云端等備份機制讓數字信息看似不朽,但它遠比人們想象中更脆弱。誠然,硬件成本在下降,存儲介質的容量也在擴張,這些事實讓人誤以為存儲費用也在快速下降。但數字存儲涉及各方面的花費,文件格式需要調整,硬件需要更新,數據需要不斷管理和組織以保持其價值——“存儲的真正成本在于系統的硬件、軟件、維護、更新和人力管理”。[30]
既然每一個社交賬戶的保存都需要付出存儲成本,也無專門的法律規定各大服務商處理賬戶的權限,從商業運營的角度出發,不難理解一些平臺傾向于刪除久不活躍的賬號。相較于平臺的漠視,網友早已自發地將逝者的社交賬號轉化為追憶生命的網絡墓碑。罹患抑郁癥的網友“走飯”發出的最后一條告別微博,十年來幾乎每天都有網友去留言。類似的例子還有許多,快手“西藏冒險王”“開卡車的小輝輝吖”作者遇難身亡,B站博主“虎子的后半生”“卡夫卡松餅君”“墨茶”因癌癥去世,抖音博主梁晶在馬拉松越野賽中不幸去世,他們生前的視頻不僅吸引著熟悉他們的朋友,還聚集起了由陌生觀眾組成的數量可觀的哀悼社群。
在數字哀悼的背景下,用戶-逝者賬號互動引發的數據流引起平臺關注,用戶互動關系是平臺珍貴的資產,從逝者賬號的互動中挖掘價值,逐漸成為共識。2019年初,快手在卡車司機小輝輝夫婦逝世后發布的公告中就提到“小輝輝的351條視頻下面滿是回家的呼喚;數以萬計的老鐵打電話詢問捐助途徑”。①B站的產品運營也說,“當時我看到一些UP主去世后,評論區有許多用戶自發地留言、紀念,不停地回顧UP主以前發過的一些內容,當下就覺得,有必要把紀念賬號做起來”。②
在平臺積極介入之前,大部分已故用戶的賬號處于無人管理的狀態,一次軟件故障或平臺刪除不活躍賬號,都會導致逝者數據消失得無影無蹤。“黑客盜號”“用戶數據販賣”等灰色產業鏈的存在,更是讓賬號安全性雪上加霜。新浪微博是國內較早對逝者賬號進行調整的大型平臺。2020年9月17日,新浪微博發布公告稱“為了完善平臺服務,保障用戶權益,保護逝者隱私,防止逝者賬號被盜,站方將對逝者賬號設置保護狀態”,此后,B站、豆瓣、快手、抖音相繼發布了類似公告,主動調整平臺架構,加入數字哀悼的布局中。③B站稱此舉是為了“供大家緬懷逝者,追思其留下的點滴”。豆瓣產品團隊對豆友們“生命已逝,藝術不朽”的理念表示認同。
(二)紀念賬號驅動的數字哀悼
逝者賬號轉換為紀念賬號后,數字哀悼不只是個人自發的體驗,也是一種由平臺引導和限制的行動。平臺的“非正式環境”為新規則的探索提供了空間。圍繞紀念賬號進行的數字哀悼不完全由技術的物質結構所決定,也取決于用戶的想法和行動,由此產生了“可供性差異”和“平臺方言”。用戶的數字哀悼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預設的腳本,同時又在不同的參與式文化下,發展出新的記憶可供性和情感可供性。
1.記憶工作:從存檔到策展
社交媒體平臺已經激發了一種“存檔”文化,鼓勵用戶隨時隨地保存數字痕跡。不過這種存檔是臨時的,用戶隨時可以刪改。紀念賬號的創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質穩定性,使社交賬號從臨時檔案轉變為永生不朽,深化了檔案價值。因為逝者不可能再生成數據,平臺也不允許任何人編輯賬號內容,實際上提供了保存全部記憶痕跡的可能。作為個性化的微檔案庫,紀念賬號承載著逝者的自傳式記憶,諸如頭像、自拍、表情包等都能傳遞身份信息,將肉身轉變為“數字身體”而銘記。
不同平臺的數據結構也有所不同,“數字身體”在各大平臺上被改造為不同的存在形態。微博的文本信息、空間位置和時間標記數據可以識別出用戶鮮活生動的日常生活軌跡。同樣提供文本數據流的豆瓣,因其獨特的“書影音”功能保存了逝者讀過的書、觀過的影和聽過的歌。視頻分享網站允許用戶以流媒體數據的形式呈現和傳播自我,尤其是第一人稱視角的視頻博客承載的豐富的身體敘事和身體展演,具有鮮明的人格化特征。
存檔的技術結構不僅決定了可存檔的數據形式,也決定了其與未來的關系。[31]作為微檔案庫的逝者賬號具有時間上的復雜性。逝者的時間是“凍結”的,但由于賬號并未關閉社交圈,成為“被激活的節點”,進入到無止境的紀念過程。[32]用戶通過發表評論,添加關注,使用標簽符號、超鏈接、提及符號@等,使逝者賬號繼續活躍在好友圈和社交網絡中,同時也在向微檔案庫增添逝者的記憶碎片、自己生活的更新以及與逝者保持聯系的愿望。逝者的數字自我通過留下的數字痕跡顯現出來,也通過人與人、人與技術物、技術物與技術物的持續互動,進行記憶的增補、修改和維護,即“記憶策展”。
B站、豆瓣、抖音、快手等為用戶創作內容的UGC分享平臺在記憶策展方面創造了更多的可能性。這與平臺的技術支持有關,也與年輕“Z世代”(95后和10前)的活躍有關。以B站為例,UP主們利用截屏、錄屏的“可復制”“可存儲”“分享性”“瞬發性”等特征[33],將紀念賬號的原內容重新剪輯、拼貼和組合后進行視頻再創作,擴大數字哀悼的影響力。名為“豆瓣公墓”的豆瓣小組則展現出了集體策展的可能,該小組致力于紀念已經逝世的“豆友”。逝者賬號被遷入“公墓”中,一個個紀念貼以逝者用戶名和生卒年月為標題,在小組頁面上整齊地排列著,就像一塊塊矗立著的“墓碑”。發帖人發布網絡悼詞,附上豆瓣主頁鏈接,通過墓志銘和逝者賬號集體銘記逝者。無論是個人策展還是集體策展都是用戶結合平臺的技術特性創造出的超越預設的紀念形式。
2.情感實踐:從可見到共振
哀悼不僅是紀念活動,也是深刻的情感體驗。喪親是人生最艱難的經歷之一,即使在親密的家庭圈子里,公開談論一個家庭成員的逝去也是困難的。隨著社交媒體平臺使分享一切成為可能,曾經私密的情感變得公開可見,召喚了“情感公眾”(affective publics)的出現。[34]逝者紀念賬號的存在進一步起到了情感錨定的作用。
紀念賬號作為持久且具延展性的哀悼空間,不僅容納了悲傷情感的日常表達,也避免了直面死亡的可能。在傳統葬禮儀式上,哀悼者不僅能看到逝者遺容,還需要在身體距離上保持接近。社交媒體平臺為用戶提供了一種與逝者和他人交流的安全距離,減少了死亡和哀悼的禁忌恐懼色彩,為朋友和陌生人提供了積極溝通的渠道,在彼此可見中尋求安慰,因此圍繞紀念賬號的數字哀悼很少流露出極端的消極情緒。
B站、豆瓣和抖音在情感化設計上更細致。B站考慮到不同UP主在信仰和民族文化上的差異,選用了更普遍的蠟燭和簡潔的灰色文本框。豆瓣專門為逝者賬號定制了獻花功能,用戶只需點擊逝者頭像下方按鈕,屏幕上就會彈出粉紅花束和“你在他/她頭邊放了一束山茶”的文案。該創意出自戴望舒寫的悼亡詩中的一句“到你頭邊放一束紅山茶”。祭奠儀式上一般使用菊花和其他白色花朵,但在社交媒體平臺上,鮮艷的花朵也可以和哀悼的情感聯系起來。不管是灰色的克制,還是山茶花的明媚,都說明平臺試圖傳遞更加平和克制的情緒。
用戶可以遵循平臺設置的情感基調完成表演腳本,也可以探索新的情感實踐。各平臺都能觀察到的共同趨勢是悲傷的“數字化”。粉絲數、點贊數、評論數和轉發數等社交按鈕一般被視為賬號影響力的象征,而逝者賬號的這類指標被解讀為情感聯結的強度,計數器助長了這一趨勢。B站UP主“墨茶Official”在逝世前僅有200名粉絲,去世半年后,粉絲數已經飆升到近200萬,點贊數超過800萬。快手UP主小輝輝夫婦去世后,粉絲數也從21萬漲到180多萬。前來哀悼的用戶也注意到了數字變化,指出點贊和計數的情感價值:“還是投幣點贊了,只能用這種方式表達尊重和同情。”還有人認為不斷增加的關注數有更積極的意義,可以“幫助其他的墨茶”“提高對卡車司機群體的認識”。
哀悼者還利用互動中的符號載體尋求情感共振,表現為模因的復制與擴散。模因具有極強的情緒傳染性,不過也限制了多樣化的情感表達。平臺彈幕池和評論區一般都有字數限制,信息容量較小,彈幕更是轉瞬即逝,常表現為簡單的情感抒發,“一路走好”“逝者安息”“愿天堂里沒有病痛”是最常見的語言模因,哭泣、蠟燭、祈禱等表情包是頻率最高的視覺模因。這類符號表征未必構成信息增量,但所承載的情感才是其真正的價值。[35]哀悼者通過同質、同步的刷屏營造情感氛圍,使更多個體被感染并加入情感展演中,在分享悲傷的同時也獲得了共同在場的聯結感。
(三)用戶對平臺可供性的反身性思考
可供性有正負兩個維度,隨著實踐的深入,用戶在與平臺的持續互動中,反思自身的行動能力,由此產生了對平臺可供性的反身性思考。平臺剛推出紀念賬號時,用戶多做出積極回應。網友們贊嘆“溫暖小破站”“B站真是像家一樣的社區”“只要不被遺忘,就不會真正死亡”。然而,不少用戶很快對平臺單邊的技術協議感到不滿。
首先,紀念賬號的設置可能違背逝者意愿。平臺往往將決策權交由逝者的直系親屬,看似公開透明,實則矛盾重重。社交網站并不完全由親密關系組成,弱關系和陌生人占比很大,但后者沒有資格代表逝者申請紀念賬號。按照B站“紀念賬號收錄君”、微博“逝者如斯夫dead”等網友自發整理的逝者名單,仍有大量賬號處于未被紀念的狀態。一個重要原因是直系親屬并不知曉逝者在各個平臺上的社交賬號,紀念賬號的設置門檻成為限制行動的“消極可供性”。[36]
其次,平臺承諾完整保留逝者的數字痕跡,但由于逝者的社交圈并未關閉,新的“歸檔”實際上遮蔽了逝者生前留下的部分記憶。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評論區置頂的熱評會被后來者占據,視頻彈幕池達到上限后,新的彈幕也會替代最早發布的彈幕。另一個問題是負面信息的不可控,平臺雖有舉報機制,但需要其他用戶介入并等待平臺審核,有一定的滯后性。
最后,社交媒體平臺上的悲傷表達以數字化和模因化為主要特征。對于這種“啦啦隊”式的情感實踐,一些用戶也表達了失望情緒。當情感實踐被簡化成點擊社交按鈕和復制粘貼,那些到此一游的“悲傷游客”(grief tourist)顯得尤為可疑:到底是為了紀念還是自我呈現和表演。[37]相比之下,與逝者關系密切的人在如何表達悲傷、如何記住逝者的方式有著更深入和細致的要求。這些矛盾和沖突也暗示了數字哀悼的復雜性。
四、結論與討論
在大平臺時代,平臺巨頭擁有相當大的權力來影響數字哀悼如何展開,既能決定數字遺跡的處置方式,也能引導人們如何哀悼逝者。通過將逝者社交賬號的可供性重新分配于哀悼活動,紀念賬號逐漸成為充滿回憶與情感的空間,延續了對逝者的追憶,提供了療愈傷痛和情感支持的可能,使哀悼活動更能融入公眾的數字生活,削弱了死亡和哀悼的禁忌傷感色彩。不過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逝者人格利益是否得到尊重?逝者是否有選擇的權利?紀念賬號的保存、管理和繼承如何展開,是否應該保存所有未經過濾的數據?如何應對潮水般的哀悼評論和彈幕?如何滿足不同身份哀悼者的需求?這些問題讓我們意識到在面對數字哀悼這樣復雜的議題上,平臺需不斷地將用戶對新增功能及其局限性的回應納入技術架構中。
如何讓數字化死亡更有品質和尊嚴,首先需要充分尊重用戶的個人信息自決權,將決策權前置,交還到用戶手中。在尊重用戶“被遺忘”的意愿上,B站率先做出調整,用戶在生前就可以決定刪除還是保留賬戶,較過去“一刀切”的做法更能滿足用戶的不同需求。
如果用戶選擇保留賬號,平臺還可以設計更靈活、更包容的技術方案。在當前的技術支持下,不同社會背景的個人都被歸入“朋友”的扁平化類別,哀悼者之間的巨大差異被忽視。用戶的紀念和情感需求因人而異,“點贊”等社交組件與悲傷情感格格不入,讓沉浸在喪親之痛中的人們難以接受。平臺應從人性關懷的角度為渴望與逝者保持聯系的哀悼者提供更好的技術支持,增設新的標簽、頁面和社交按鈕,或根據用戶偏好提供定制服務,調整界面、集成或篩選內容等。
此外,平臺往往向近親屬開放管理逝者賬戶的權限,但出于隱私管理的考量,用戶未必愿意讓近親屬了解自己在社交賬號上的活動。相比之下,Facebook通過設置委托聯系人,賦予用戶更大的自由度來決定由誰來處理個人信息。④但尋找合適的委托聯系人并非易事。平臺也可以讓用戶決定逝世后賬號自動執行的具體任務,例如B站已經同意用戶刪除所有彈幕和評論,未來還可以考慮是否開放社交圈、是否可以被公開檢索,甚至開啟賬戶或數據有選擇性的繼承模式。
值得指出的是,作為一種新興的數字交往現象,“數字哀悼”還未被廣泛接受,它要想成為傳統哀悼習俗、空間和物質技術之外的另一種選擇,仍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由于法律對社交賬號這類數字資產未有明確規定,由商業機構全權負責處理用戶的數字遺跡將會帶來巨大的風險。一些激進的初創公司已經在發展“數字來世產業”(Digital afterlife industry),研發新的人工智能系統收集數字遺跡,模擬逝者社交行為,制造出類似聊天機器人的應用程序。[38]盡管主流平臺對此并未采納,但需持續關注這類技術實踐的過程,警惕對數字遺跡過度商業化的操縱,關注新的人工智能技術會以何種方式調節和塑造數字哀悼,以及隨之而來的法律、倫理和監管挑戰。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二戰期間來華猶太難民集體記憶的建構與傳播研究”(20YJC860004)階段性成果]
注 釋:
①老鐵是網絡用語,即鐵哥們。河北一對貨車司機夫婦在青藏線送貨時不幸身故,生前曾在快手開設賬號“開卡車的小輝輝”分享日常生活。快手在其官方號“快手日報”上發布了公告“司機夫婦的最后時光:陪你是無法完成的承諾,晚安成了永久的告別”,承諾將保存該賬號所有視頻。
②“UP”主是Upload的簡稱,指在視頻網站上發布內容的人。B站于2021年7月26日在其官方賬號上發布公告“一個人去世后,他的B站賬號會怎樣”?解釋了創設紀念賬號的動機。
③新浪微博:關于保護“逝者賬號”的公告,https://share.api.weibo.cn/share/227162453.html?weibo_id=4550080792898990;嗶哩嗶哩社區小管家:公告,https://t.bilibili.com/471903763512561872?tab=2;抖音:抖音上線逝者紀念功能 為賬戶設置保護狀態,https://wap.xinmin.cn/content/32000242.html;快手大事件:最后一條視頻,https://v.kuaishou.com/9GYQYA。
④Facebook頁面的幫助中心下設“選擇委托聯系人”和“管理已故人士的賬戶”等選項,網址為https://www.facebook.com/help/275013292838654/?helpref=uf_share。
參考文獻:
[1]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論死亡和瀕臨死亡[M].邱謹,譯.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05:2;胡宜安.現代生死學導論[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2.
[2]Sherwin Nuland. How we die:reflections on life's final chapter[M].New York: Alfred A.Knopf,1995:xv.
[3]Jana Kralova. What is social death? [J].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2015,10(3):235-248.
[4]Dennis Klass. Phyllis Silverman,Steven Nickman. Continuing bonds:New understandings of grief[M].London:Taylor & Francis,1996:xix.
[5]Pamela Roberts,Vidal Lourdes.Perpetual care in cyberspace:A portrait of memorials on the Web[J].Omega: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2000,40(4):521–545.
[6]Amanda Lagerkvist. New memory cultures and death: Existential security in the digital memory ecology[J].Thanatos,2013, 2(2): 1-17.
[7]Pamela Roberts. The living and the dead:Community in the virtual cemetery[J]. Omega: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2004,49(5):7–76.
[8]胡泳.數字化過后,又怎么樣?[DB/OL][2021-04-21].澎湃新聞.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317278.
[9]Jessa Lingel. The Digital Remains:Social Media andPractices of Online Grief[J].The Information Society,2013,29(3):190-195.
[10]伊萊恩·卡斯凱特.網上遺產[M],張淼,譯.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20:46.
[11]Deby Babis. Digital mourning on Facebook:the case of Filipino migrant worker live-in caregivers in Israel[J].Media,Culture & Society,2021,43(3):397-410.
[12]Dorthe Christensen,Stine Gotved. Online memorial culture:an introduction[J].New Review of Hypermedia & Multimedia,2014,21(1-2):1-9.
[13]伊萊恩·卡斯凱特.網上遺產[M].張淼,譯.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20:84.
[14]章戈浩.傳播與媒介研究的死亡盲點:一個生存媒介研究的視角[J].全球傳媒學刊,2020(2):21-34.
[15]Anna Wagner.Do not Click “Like”When Somebody has Died:The Role of Norms for Mourning Practices in Social Media[J].Social Media + Society,2018,4(1):1-11.
[16]陳剛,李沁柯.穿梭時空的對話:作為媒介“安魂曲”的數字遺產[J].新聞記者,2022(11):31-42.
[17]勞倫斯·萊西格.代碼2.0:網絡空間中的法律[M].李旭,沈偉偉,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89-101.
[18]戴昕.犀利還是無力?——重讀《代碼》2.0及其法律理論[J].師大法學,2018(1):252-268.
[19]James Gibson.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M].London:Psychology Press.2014:129,139,213.
[20]Donald Norman.Affordance,conventions,and design[J].Interactions,1999,6(3):38-43.
[21]William Gaver.Situating action II:Affordances for interaction:The social is material for design[J].Ecological Psychology,1996,8(2):111-129.
[22]Alice Marwick,Nicole Ellison.“There isn't wifi in heaven!”Negotiating visibility on Facebook memorial pages[J].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2012,56(3):378-400.
[23]Martin Gibbs,James Meese, Michael Arnold,Bjorn Nansen,Marcus Carter.#Funeral and Instagram:Death,social media,and platform vernacular[J].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015,18(3):255–268.
[24]Taina Bucher,Anne Helmond. The Affordances of Social Media Platforms[G]// Jean Burgess,Thomas Poell,Alice Marwick.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al Media,London and New York:SAGE Publications Ltd,2017:233-253.
[25]張杰,馬一琨.語境崩潰:平臺可供性還是新社會情境?——概念溯源與理論激發[J].新聞記者,2021(2):27-38.
[26]胡翼青,馬新瑤.作為媒介性的可供性:基于媒介本體論的考察[J].新聞記者,2022(1):66-76.
[27]張志安,黃桔琳.傳播學視角下互聯網平臺可供性研究及啟示[J].新聞與寫作,2020(10):87-95.
[28]周裕瓊,張夢園.數字公墓作為一種情動媒介[J].新聞與傳播研究,2022,29(12):32-52+127.
[29]Ben Light,Jean Burgess,Stephanie Duguay.The walkthrough method: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pps[J].Newmedia & society,2018,20(3):881-900.
[30]Jonas Palm. The Digital Black Hole[DB/OL].2006-04-28].https://cdn-kb.avanet.nl/wp-content/uploads/2019/05/31173546/Palm-Black-Hole.pdf.
[31]Jacques Derrida. Archive Fever: A Freudian Impression[J].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17.
[32]Tero Karppi.Death proof:on the biopolitics and no politics of memorializing dead Facebook users[J].Culture Machine,2013(14):1-20.
[33]宋美杰,陳元朔.為何截屏:從屏幕攝影到媒介化生活[J].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1):123-132+171.
[34]Zizi Papacharissi.Affective publics and structures of storytelling:Sentiment,events and mediality[J].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016,19(3):307-324.
[35]楊穎兮,喻國明.傳播中的非理性要素:一項理解未來傳播的重要命題[J].探索與爭鳴,2021(5):131-138+179.
[36]Tetsuya Kono. Social affordance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ecological linguistics[J].Integrativ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2009,43(4):356-373.
[37]許瑩琪,董晨宇.社交媒體中的哀悼行為與社會規范[J].新聞與寫作,2019(11):49-54.
[38]Carl hman,Luciano Floridi. An ethical framework for the digital afterlife industry,Nature Human Behaviour[J].2018,2(5):318-320.
作者簡介:單凌,新聞學博士,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上海 200444)。
編校:鄭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