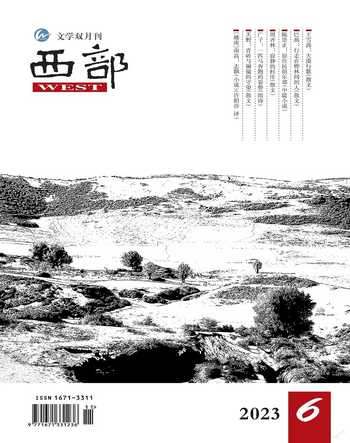行走在樺林間的人
割禮
克蘭河——我的母親河。很久以來,河中的石頭、岸邊的樺樹、我和我的族人,都是同根;我們生于這條河,然后順著不同的支流各自散去。就像那河面開出的幾朵形態各異的水花,一朵倒下去,下一朵立馬盛開,如此循環。
2001年的秋天,我與爺爺奶奶一起生活在中國版圖的最西北角,一個名為諾改特的小村莊里。那時我還屬于這片土地。爺爺家坐落在克蘭河上游的一片白樺林里,沿著河邊,他們是村里最偏的一戶,距離最近的城市有二十里路。家對面的草場像是世界的中心,無論是春夏還是秋冬,都是先降臨在這片草場上,再往外伸延。
這年的立秋,空氣中彌漫著墻漆清新的味道,院子里搭起了氈房。奶奶為我穿上了她親手縫制的帶有花紋的小馬甲,在她們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傳統縫紉這種老手藝是婦女們必須掌握的生活技能之一。父親和母親站在爺爺身旁,一起迎接著前來祝賀的客人。我頭頂著氈帽站在院子里,帽頂的幾根羽毛一會兒往東,一會兒往西搖擺。來往的客人們在喻義祝福的糖果雨(恰秀:一種祝福形式,由年長的婦人撒出糖果,撿到的人意味著撿到了福氣)中俯身親吻我的臉頰,小孩子們一窩蜂地爭搶著撿地上的糖果,我只顧著嫌棄地用袖子擦拭著大人們親吻我臉頰時留下的口水。爺爺說,阿帕(奶奶)們灑出的這些糖果都將變成美好的祝福降臨在我身上。如果真是這樣,我希望這些祝福也能降臨在夏卡爾身上,這年我五歲。
“夏卡爾,夏卡爾!”
夏卡爾是我最小的姑姑,她被年長的大人們使喚著,在土房子和氈房之間進進出出,幾滴汗珠順著她額頭的發絲滑落。那些年,我更多的時候是從她那里得到母愛,她的汗珠經常落在許多不同的地方,屋里、院子里、路上……時常也落在我的心底。
突然穿上了傳統的民族服裝讓我很不習慣。如果有人路過,一眼就能知道這戶人家在設宴,并且不用問就可以看出我就是今天的主角。畢竟誰也不會閑得在一個普通的日子里穿上這身傳統服裝。一群小孩子騎著從柴火堆里翻出來的樺樹枝,屋前屋后地追趕彼此。我也正忙著翻找一根合適的坐騎時,后面傳來了爺爺的聲音。
“哎,巴燕。過來孩子,該給你換衣服了。”
院子里是客人們慶祝的喧囂聲,爺爺哄騙著我往屋里走去。
“走吧孩子,只是給你涂個顏色而已……”
我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只聽所有人都在說我馬上就是一個男子漢了,那今天肯定是個好日子。畢竟被人稱之為男子漢,是每一個男孩子都不會拒絕的榮譽。剛一進屋,就看到一群男人坐在大板床邊。看到我進來后,一個頭頂白帽留著黑色大胡子的老人,扶了扶老花鏡先開口。
他說:“小英雄巴燕來了。”
“真是個懂事的孩子。”其他人也都跟著夸贊我,但我從他們的夸贊中聽出些許的不懷好意。
先開口的就是穆薩,他是我們村里一位德高望重的村醫,也是村里為數不多的回族人家。這天正是我的成人禮,是每個哈薩克族男孩都會在五六歲這個年齡段經歷的“割禮”。爺爺請穆薩來為我做包皮手術,這是成人禮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也是“割禮”一詞的由來。
爺爺將我抱上大板床,掙脫了被我死死攥住衣角的小手,幾個快步就出門而去了。沒等我反應過來,床邊坐著的大人們已經有說有笑地圍了上來,分別抓住了我的手腳,輕輕地按在床上。我躺著不知所措,但也沒有太過于掙扎。直到看到穆薩拿著銀色夾子和一把小刀走向我時,這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操著一口流利的哈薩克語,邊安慰著邊向我走來。
他說:“巴燕要成男子漢了,男子漢是不能流眼淚的,醫生爺爺只是給巴燕涂個顏色而已。”
突然,有人脫下了我的褲子,我的手腳也被摁得更緊。
“放開!放開!”我帶著哭腔開始掙扎。
隨著村醫的手起刀落,我的哭喊聲在院子里回蕩,在爺爺正在喝奶茶的碗里回蕩,在父親和母親躲著的牛圈里回蕩,在夏卡爾濕了的眼眶里回蕩。
“結束了,結束了。明天巴燕就可以騎爺爺送的禮馬了。”屋里的大人們安慰著。
穆薩處理好傷口后,為了防止我碰到傷口便扣了個瓷碗在上面。很久以后,那個瓷碗仍在被使用,每當奶奶從碗柜里將它取出來時,都要驚喜又欣慰地說上一句,這是巴燕割禮時用的碗。那么多款式一樣的碗,但奶奶總是能認出那一只。
院子里靠河的一角長有幾棵白樺樹,樹下拴著一匹小馬駒,一匹棗紅色的小馬駒。從開始到結束,那里出奇地安靜,好像這個世界的聲音都無法打擾到那里。陽光滑過樹梢壓落了幾片金黃的葉,一片落在了它額頭的星斑上,其余的幾片落在了大地上。它油亮的皮毛上,染了棗紅的光,稀疏地折射到樺樹潔白的身軀上。如果不是偶爾落下的幾片葉,確實會讓人誤以為是一幅畫。
沒過多久我睡了過去,做了一個很長的夢。我在夢里感受到了時間,像克蘭河的水一樣流逝。河水撞擊在石頭上,濺出的幾滴水珠落在地上變成了幾棵樺樹,開出的一朵水花變成了一匹棗紅馬沿著河畔奔跑。帶有白色斑紋的四蹄有力地踩向地面,不等揚起的塵埃在空氣中作舞,它的蹄聲已在不遠處再次響起。陽光從正面照在它的星斑上,長鬢隨風飛揚。沒等翻起的浪花恢復平靜,時間就停止了,流動的河水、搖擺的樹枝、空中麻雀也停止了似的,除了那匹棗紅馬依舊在向前奔馳而去……
我醒來時已經是中午了,想慢慢翻身,下身卻傳來一點刺痛,我把昨天剛掉了一點肉這件事忘記了。我躺著輕輕地叫了一聲奶奶。無人回應。我提高了音量:“奶奶!”
“哎!”一個年輕的聲音從隔壁房間應了我,聽到這熟悉的聲音,下身傳來的疼痛瞬間減輕了許多。小姑推門進來:“怎么了?”
“奶奶呢?”
“在河邊洗衣服呢”
“爺爺呢?”
“在打掃牛圈呢,怎么了?”
“我要吃糖。”
小姑轉身去為我取來糖果,她總是能為我找到我想要的一切。記得有一次在城里,我告訴她要吃雪糕。她從外套自己縫制的口袋里掏出一個折疊了幾層的手帕,打開里面是一張滿是褶皺的綠色人民幣,那是我們回家的車票錢。小姑毫不猶豫地帶我去買了雪糕,然后硬是背著我走了二十里路,那時她十九歲。
一路上她的汗珠劃過發絲,一滴落在我的手臂上,一滴落在干燥的黃土地上。汗珠落在地上微微揚起一些塵埃,那汗珠被塵土包裹后變成了一顆黑色的小土豆。我從小姑的背上看著那些黃土地里的黑色小土豆,有那么一瞬間想撿起來放入口中嘗一嘗。我想,若忽略了那黃土的苦澀味,剩下的一定是甜的。
圣山
我們在往常放牧的草場上碰見了爺爺年輕時的好友,他與爺爺同歲,是住在村莊東北邊的蒙古族人。與他同行的是他的孫子,年長我三歲,高出我一個頭那么多。那蒙古族老人同爺爺用哈薩克語聊天的同時,又時不時用蒙古語和孫子交流著。待他們離開后,我問爺爺,為什么村里的蒙古族人和我們長得一樣,生活方式一樣,語言卻不一樣呢?
爺爺說:“阿爾泰這條山脈是游牧人心中的圣山,我們本是一個部落,同一個氈房下的生命。每天跟著牲畜,逐水草而居,哪里適合生活,就走向哪里。我們操著不同的語言,成為不同的民族。但不變的是心靈深處對自然的向往,對圣山的敬畏。”
放牧的生活相比于種地的生活要自由許多。牛羊們在草場上埋頭吃著,爺爺從馬背上取下厚氈子鋪在巖石平坦的一面,隨即側身臥著。經過太陽暴曬后,巖石表面的溫度足以燙手,不一會兒氈子下就遞來溫暖,爺爺看著遠方就那么舒服地躺著。一切都是那么安靜,整片草場上只剩下牛羊咀嚼青草的聲音。那聲音常能誘惑我低下身子去品嘗地上的青草,每次嘗到的味道都不一樣,清爽、苦澀、極苦。終于離開了那片樺林,我對樺林外的大地和萬物充滿了好奇。山上的石頭與克蘭河中的石頭不一樣,河中的石頭光滑又圓潤,而山上的石頭有棱有角,顏色單一。完全無法讓我喜歡它們。
突然一顆陌生又顯眼的小石粒出現在我眼前,我伸手撿起它放在掌心。它和這些山石及巖石的碎片不同,它有著不屬于石頭的顏色,我抬頭看向周圍,好像把它放在哪里都格格不入。我將綠豆大小的小石粒放在掌心,緊緊攥著拳頭向爺爺跑去。
“爺爺!爺爺!”我興奮的聲音在山谷間回蕩。
奔跑時我頭頂兩側的圖倫(哈薩克族民間習俗,給未做割禮的小男孩留的兩撮長發)向后隨風揚起,爺爺坐起身子將正讀著的書折了一頁后合閉。我氣喘吁吁地跑到爺爺身旁,撲到爺爺的腿上打開了緊攥著的拳頭。
“這是什么?”爺爺先是不可思議地笑了一下,他拿起小石粒看了看。
“你從哪兒撿到的?”爺爺問我。
我指著山溝另一側的山腳下說,那邊。
爺爺向我指的方向看去,又摳了摳小石粒上的土,吹了兩下后說:“這是小金粒啊。”
小金粒?這是金子?我的腦海中不斷重復著“金子”這個詞,此前我只知道金子是一種珍貴且稀有的東西。奶奶寵我時會叫我金寶,爺爺懷念游牧生活時會說金山阿勒泰,小姑還有個同學叫阿勒騰古麗。阿勒騰是金子的意思,古麗是花的意思,翻譯一下就叫金花。大家都習慣于將喜歡的事物稱呼為“金什么什么”,那這金子就一定是寶物了。
正當我以為得到了全世界時,爺爺大手一揮,小金豆向空中飛去,之后便無影無蹤。爺爺將它丟出去很遠很遠,讓我再也找不到。正當我準備哭鬧,讓爺爺見識一下我的小少爺脾氣時,爺爺將我抱坐在身前。“我的小馬駒,那是屬于圣山的,如果不是急需的情況下,就應該將它還給圣山。”爺爺撫摸著我的頭說。
我委屈地說:“難道金子不是很珍貴的東西嗎?”
爺爺說:“當然是,阿勒泰七十二條溝,溝溝有黃金。但幾千年來,阿爾泰山給予游牧人的已經太多了,過度索取只會帶來災難。”
太陽即將落山,牛羊們也離開了草場,踏上了回家的路。我和爺爺收拾好東西,跟在牲畜的身后下山。遠遠望去,群山中的小村莊顯得那么孤獨,這里的科技、醫療、教育都遠不及內地的城市,我們好像落后了世界太多。圣山到底給予了我們什么?我想也只有“生命”一詞能成為它的答案。那些曾游牧于阿爾泰山中的祖先,一步一步,慢慢變成了我。而我也將一步一步,慢慢變成這里的一草一木。
想搶走奶奶的人
我們共同的祖訓——“祖輩留下的財富有一半是留給客人的”,讓每一個哈薩克人對客人獻上了所有的熱情。
在諾改特村,幾乎每一戶哈薩克人家都是一個“能量驛站”。村里每天來來往往的除了諾改特的村民外,也有附近其他鄉村的,還有一些往返于草原的牧民們。每當這些人感到口渴或者饑餓時,便會就近找一戶人家做客。那戶人家會將客人請到屋里上座,家中的女人開始準備餐點,燒起奶茶。家里的孩子飛奔著去父親正在干活的地方,通知父親家中來了客人。男人放下手中正忙著的活,先去與客人見面問候。人們在這樣的環境下建立起友誼和信任,周圍鄉村的消息和新變化,包括草原上的近況也都被人們所了解到。
在那樣的社交背景下,我認識了那個想搶走奶奶的人——朱馬希。他與爺爺是同輩人,是一位長著藍眼戴著花帽的維吾爾老人。那樣的花帽十分少見,有獨特的花紋,形狀也與哈薩克人的不同(那時的我還分不清不同民族的傳統服飾)。諾改特村除了人口居多的哈薩克族之外,還有蒙古族、回族、維吾爾族等,雖然民族不同,文化及相貌也略有差異,但幾乎所有人都會用哈薩克語進行交流。
第一次見到朱馬希的那天,爺爺跟小叔趕著家中的牛羊去了我們的草原。每年夏天牧民上山之后,我們就要將牛羊趕去草原交給葉爾蘭哥哥家。因為爺爺在十幾年前就已經在諾改特村定居,結束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臨走前,我哭著鬧著要跟爺爺一起去草原,任誰哄騙也不好使,連最具誘惑的糖果也失去了魔法。爺爺不忍心看我哭鬧,便將我抱坐在腿上。
爺爺說:“我跟你小叔一去就是三天,如果你也跟我們走了,那家里怎么辦啊?”
我沉默許久不語,但心里已經在糾結,舍不得奶奶和小姑。
爺爺說:“總要有個男人留下來保護奶奶和小姑吧?”
我點了點頭。
爺爺說:“你的名字可是英雄的名字,是勇士的名字。你不留下來保護她們,誰保護她們,對不對?”
爺爺短短幾句話,在我幼小的心里激起了使命感。他們趕著牛羊在河道上背影漸遠。我手握馬鞭,騎坐在戰馬上,模仿著一個騎兵孤身陷入重圍的壯烈感。
我的戰馬,其實就是一根比較直的樹枝,剝去了一半的樹皮,留下了枝頭的綠葉。我騎著戰馬屋前屋后地巡邏,搞得塵土飛揚。沒一會兒,我便力竭躺在了屋前的草地上。
“喂,你爺爺呢?”
一個陌生的聲音傳來。我起身看去,有人站在院內,該死,有陌生人進到院子里我居然沒有第一時間發現。我騎上戰馬飛奔到了他跟前,先和他握手并禮貌問好,下一步就是查明他的身份。
我說:“您是誰?”
他說:“你爺爺去哪兒了?”
我說:“爺爺和小叔送牛羊上山去了。”
他說:“啊呀,那真是太好了,我是來接你奶奶和我女兒走的。”
我說:“誰是你女兒?”
他說:“當然是夏卡爾。”
我向屋門靠近了兩步,小手緊緊攥著馬鞭。
奶奶剛好從屋里走出來,看見我竟攔著客人在門外,還在沒大沒小地問著問題。
奶奶訓斥道:“哎,巴燕。快讓朱馬希爺爺進屋來,不能沒禮貌!”
我騎著戰馬快速離開。奶奶將朱馬希邀請進屋里,小姑有說有笑地為他倒著奶茶,奶奶坐在一旁的大板床邊,仿佛他們才是一家人 。眼前發生的這一切被正趴在窗外偷看的我看得一清二楚。
夏日烈陽下的河畔萬物沉靜,諾改特村最后的勇士失去了他最珍貴的奶奶和小姑。突然出現的敵人并不可怕,但眼見的親近早已令戰士喪失了斗志。他用撕心裂肺的哭聲同克蘭河一起演奏著悲歌——勇士的眼淚。
小姑聽見我的哭聲從屋里跑了出來,但以往最親近的小姑此刻已經是別人的女兒。我傷心地逃離,甚至忘了騎上我的戰馬。小姑在后面追著,一遍一遍叫著我的名字。我跑到河邊爬上了一棵白樺樹。小姑在樹下叫我下來。我多么想下去抱住我親愛的小姑,多少個日夜我從她身上獲得了母愛,但不理會她是我最后的尊嚴。我趴在一棵較粗的樹枝上哭著,小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么,她以為我想父親了,便一個勁地騙我說過兩天父親就會來看我。
不知道過了多久,我爬在樹枝上睡著了。小姑蕩著那樹枝上爺爺為我做的秋千。
“我的小羊羔呢?我的黃丫頭呢?”
是二叔的聲音,我向下看去,二叔站在樹下。本已經盡力克制的情緒在一瞬間爆發,我邊哭著邊爬下樹。二叔將我抱回家。
晚上,奶奶、二叔、小姑和我一起委屈地喝著晚茶。我將朱馬希爺爺所說的話和我從窗戶外看到的一幕都告訴了二叔,沒想到卻引來所有人的哄堂大笑。
再遇朱馬希
那年家里除了牛羊,還有幾只雞。我記得應該是有七八只。那些雞都是奶奶養的,因為那時雞蛋可是我們村里的硬通貨。我和奶奶經常一起去將雞蛋賣給村里的小賣部,或者直接從小賣部里置換一些生活用品。
每隔兩三天,奶奶便帶著我去雞窩里取雞蛋。上個冬天大雪成災,雞窩的一側土墻被積雪壓塌了,小叔一直沒有時間修繕塌了的墻壁。所以,每次都要靠我從小洞鉆進去,才能將雞蛋取出來。
陽光明媚的一天,奶奶因腿疼走不了遠路。便讓我獨自去賣雞蛋,不然收集了幾天的雞蛋該壞了。她小心翼翼地將雞蛋一個個規整地放進了手提包里,讓我背上。幾十個雞蛋雖說有點重量,但背起來并不算吃力。我背著雞蛋向小賣部出發。
正午的陽光照得花草直低頭,好在河道的一旁有一排樺樹沿岸生長,我走在樹蔭下,走走停停。尋找一朵夏天的蒲公英,欣賞克蘭河中魚兒戲水,抓一只有尾巴的四腳蛇。阿勒泰夏天的陽光火辣辣,我的夏天都藏在了這樹蔭之下。
走過了近一半的路程,背著的手提包感覺越來越沉重。十幾個雞蛋,都是沉甸甸的生命。坐在樹下休息了一會兒,決定把包放下來拖著走。我那時真的沒有考慮到雞蛋會碎這個問題,就那樣一路拖到了小賣部。
小賣部在村子的中心,是一個平房的小儲物室,被改造成了店鋪。我從朝著大路的小門進入,抹去了頭上的汗珠,吃力地將手提包放上了柜臺。老板是一位回族奶奶,她打開包后用很蹩腳的哈薩克語跟我說:“喂,巴郎(孩子)這些雞蛋都碎了呀。”
我沒明白碎了是什么意思,便爬上一旁的凳子,打開包一看,十幾個雞蛋碎得一塌糊涂。包里滿是蛋清和蛋黃在流動,老板從里面挑出了五個完整的雞蛋,給了我幾毛錢。回家的路上我再也沒有心情去摘一朵完整的蒲公英了,一路上只有擔心。雖然奶奶從未因我犯下的錯誤責怪過我,但畢竟是做錯了事,而且最重要的是浪費了食物。
當我垂頭喪氣地走在回家路上時,遇見了朱馬希爺爺。是的,那個想搶走奶奶的老人又出現了。
“哎,斯哈克的小兒子(斯哈克是我爺爺的名字)。見到長輩為什么不問好?”朱馬希坐在路邊的木樁上說。
“您好,朱馬希爺爺。”我秉著即使再討厭也不可以對長輩沒禮貌的原則向他問好。
他說:“你好,來,過來。”
我走過去時他將我拉到身前,親了我的額頭。我的額頭可不是誰都可以親的,是爺爺和奶奶的專屬。我下意識地將朱馬希推開,后退了兩步。
朱馬希說:“你個小狼崽子,過來,不過來晚上把你奶奶偷走。”
我說:“我爺爺會把你耳朵割下來的。”
這已經是我能想到的最殘酷的懲罰了。
朱馬希戲謔地說:“我今晚就去,看好你奶奶。”
“找你自己老婆去!”我說完撒腿就跑。
朱馬希在我身后笑著,我腳下加快了速度,生怕他有什么魔法比我先一步到家里將奶奶搶走。
回到家后,我將幾毛錢給了奶奶,并將我打碎了雞蛋的事情一五一十地都告訴了她。本以為她會罵我兩句,沒想到奶奶聽了我拖著雞蛋的壯舉后忍不住大笑。在她眼中,這種只有童年純真無知的情況下才會犯下的錯誤是那么的可愛。那晚,我從自己的被窩出來鉆進了奶奶的被窩,一晚上都抱著她的手臂,生怕她被那個壞人搶走。
第二天一早,我睡醒時屋里已經沒有人了。見奶奶不在我身邊,以為她被朱馬希搶了去,我號啕大哭起來。聽見哭聲的小姑進屋來。
我問:“奶奶去哪兒了?”
小姑說:“怎么了你?奶奶在院子里做牛糞餅(牛糞與碎煤的混合物,耐燒且火旺)呢。”
聽到小姑這樣說,我懸著的心便安穩了下來。我拿著肥皂準備去河邊洗臉,
早晨克蘭河的水冰涼刺骨,洗了把臉立刻睡意全無。洗完臉我坐在河邊撿著奇形怪狀的石頭,竟無意間發現朱馬希爺爺家就住在克蘭河對岸,跟我爺爺家只隔了一條河。我看見他正蹲在河邊洗著什么東西,我大叫一聲他的名字:“朱馬希!”
要是在平日里我絕對不會傻到敢這樣叫他,可今天有克蘭河給我撐腰才讓我壯起了膽子。他驚訝地抬頭看過來,看見是我在叫他后便笑著說:“今天晚上我就把你奶奶偷走!”
“老青蛙!”我狠狠地罵了他一句,對,算罵。因為青蛙是我當時最討厭的動物,也是我能想到用來罵人最解氣的動物。當他聽到我這樣喊他時,便假裝露出很兇的樣子并做出要追我的動作。我往后跑了幾步,將撿起的一顆小石子向他扔了過去,小石子落在了離岸邊不遠的河水里。我光著腳丫往家里跑去,連鞋子都丟在河邊了。
那天晚上我一直擔心他會報復我,來偷走奶奶,所以我就像個跟屁蟲一樣跟著奶奶進進出出。到了晚上睡覺時緊緊地抱著奶奶才肯入睡。
許多年后,我早已離開了諾改特村,回到了父母身邊生活。那位常揚言要搶奶奶的人也漸漸淡出我的記憶,留在了那個烈日陽光的夏天。后來通過爺爺的講述我才知道,朱馬希爺爺跟我爺爺是許多年的好友,又是同鄉。聽爺爺說,他一直詢問我現在的情況。
小皇帝
我在諾改特村的生活可謂是小皇帝的生活。
因為我喜歡甜食,所以奶奶會在大板床的床頭放兩個碗,碗里分別裝著葡萄干和杏干。每當我三更半夜迷迷糊糊地醒來,便伸手抓一把放進嘴里,吃著吃著就睡著了。不光這些,家里的所有好吃的,甚至連奶奶偷偷藏起來的糖果也只能給我一個人吃。雖說那時的生活條件已經慢慢變好了,但在我們家,糖果這種東西還屬于稀罕物,只在有客人來時才會拿出來。
只恨好景不長,我為愛吃甜食這一壞習慣付出了代價。兩側的后槽牙都成了蛀牙,令我痛不欲生。
在克蘭河邊洗好的地毯上,我用哭聲和克蘭河一起表演了兩天的雙重奏。哭累了,只有從那樹葉間照射下來的陽光能讓我好受點。爺爺看我這么忍著也不是個辦法,便打電話給父親。當我知道父親要來時,牙不痛了,人也精神了。一下午都忙著在大板床上收拾我的衣服和玩具。那時父親和母親在城里租著一間平房,早出晚歸的生活讓兩人很少能有時間來看我。
下午,太陽離屋前的高山越來越近。屋后一陣摩托車的聲音逐漸變大,我扔下手中的小鐵鏟向屋后跑去。父親騎著他那輛日產的摩托車,歪歪扭扭地從岸邊的一排樺樹下駛來。我高興地向他奔去,頭頂兩側的圖倫隨風向后飄去。那時我對父親的愛,從不需要藏著掖著。
父親載著我去城里補了蛀牙,一周后,他又將我送回了爺爺家。還記得那天萬里無云,我很是喜歡這樣的天氣。陽光總是令人心情愉悅,但離別的時刻又令我身體里的那片小天空烏云籠罩。我的整個童年就是這樣,在爺爺家和父親家中徘徊。那樣的生活讓我突然有種在城市和村莊之間迷失的錯覺,同時對父親和爺爺這兩個角色的愛,也時常感覺忽近忽遠,患得患失。
我趴在爺爺家的大門上,看著父親急匆匆離去的背影,河道上摩托車的聲音逐漸微弱,世界恢復了原本的平靜。
小姑拿來爺爺的剃須刀,準備給我理發。作為這個家的小皇帝,我怎么能輕易向小姑低頭呢?于是,一場大戰在院子中展開。我拼命反抗,堅決不讓小姑給我理發。雖然敵軍論力氣等各個方面都占優,但在我軍戰士的奮力抵抗下,我和小姑簽訂了《諾改特理發條約》。
條約內容:小姑要去村里的小賣部給我買兩個泡泡糖,作為交換,我會乖乖讓小姑理頭發。
按照條約,小姑去了村里的小賣部,買了兩個泡泡糖回來。當她忙著準備洗頭的熱水時,我就跟在小姑屁股后面進進出出,鬧著讓她先把泡泡糖給我。
我說:“我要邊嚼著泡泡糖邊理發。”
小姑說:“那你先坐到凳子上來,坐好我再給你。”
我屁顛屁顛地跑去坐到了凳子上,小姑從口袋拿出了兩個泡泡糖給我,我趕忙拆開了一個塞進嘴里嚼了起來。看小姑還在忙著準備毛巾什么的,我心想,糖都拿到手了,為什么還要聽小姑的話呢?我跳下凳子,撒腿就跑。目標是我方最后的陣地——奶奶的身后。我一溜煙跑到了屋子里,跳上大板床,躲在了奶奶身后。熟睡中的爺爺被我跑進屋子的動靜給吵醒了,奶奶也嚇了一跳,連忙問我怎么了。
我對奶奶說:“小姑要打我。”
我可真是個討厭的機靈鬼,小姑剛追進來便被奶奶狠狠教訓了幾句。我躲在奶奶身后幸災樂禍地享用著戰利品,小姑看了我一眼就出去了。當我天真地以為就這樣占了小姑便宜時,她居然趁著我睡覺,將我的頭發剃了個精光。更可惡的是我自己居然也是過了幾天后才發現的,這下想哭想鬧也已經來不及了。
父親和母親為生活奔波的日子里,爺爺奶奶和小姑為我拼湊了童年缺失的愛。
莎莉
莎莉是我童年時期唯一的玩伴,大姑離婚后,我們便生活在一起。從此爺爺又多了一個小跟班,那片樺林、河道、草地上,又多了一串小腳印。
我沒有午睡的習慣。午餐過后,河邊吹來的微風從窗外悄悄探進了身子,一絲木香和涼爽在屋內蔓延開來。此刻,牛羊遠在草場,狗不知躲進了哪里避暑,人們也在熟睡中。午休是一天中最令我討厭的時間段,我仿佛成了整個世界唯一的動物。
我悄聲出門到河邊去,在村莊原本就安靜的角落里,從風中聽出另一種聲音,從河中聽出一首小曲兒。每到午時,我能做的只有像爺爺奶奶那樣巴巴地坐著,目光始終落在那條唯一連接著外面世界的河道上。直到院子里發出一個人的動靜,然后是兩個人,三個人,一只狗……
看著那條靜靜的河道,期待著外面世界的同時,我看見一大一小的兩個身影從老橋旁走上了河道。小道的終點只有一個,就是樺林中的爺爺家。我不知道來者是誰,卻依舊滿心歡喜。就好像真的離開世界太久,才使一種似久別重逢的喜悅一下一下地觸動著我小小的心臟。兩個綠豆般大小的黑點,變得土豆那么大,西瓜那么大,越來越大。短短的時間里我想起了河道上父親騎著摩托車的樣子,二叔仰頭大步朝前邁去的步伐,還有母親、二姑、三姑、村里我認識的幾個人。唯獨沒有記起大姑,她結婚后就和丈夫生活在另一個村莊,我不知道那個村具體的位置和名字,只是常聽大人們說大姑在“2817”。因此,我對她的最初記憶從河道開始,從兩個漸行漸顯的黑影開始。
認出是大姑和莎莉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沖向家里,去告訴爺爺奶奶這個好消息。這是我每天的工作,每當有人走下老橋,走上河道時,我就要興奮地跑回家告訴爺爺奶奶這個消息。就算最后那人的目的只是經過我家去草場上找牛,或澆地,我也還是會跑上前去邀請他到家里喝個奶茶再走。
“大姑和莎莉來啦!大姑和莎莉來啦!”
我向樺林中的萬物宣告著她們的到來。跑進院子,爺爺正用他自制的大掃帚清掃著地面。進屋里,就見奶奶穿上了她珍藏的羊毛衫。那是大姑買給她的,平時都不舍得穿。小姑在北屋的客桌上擺滿了糖果和特色油炸美食。看到桌上的美味,我一時間忘記了告訴她們好消息,兩眼直勾勾地盯著糖果就過去了。小姑見狀立刻將我抱起來,遠離了客桌。
“你大姑和莎莉在路上了,別亂動桌子上的東西。”
我從美食的誘惑中清醒過來。當我為第一個知道大姑歸來而沾沾自喜時,爺爺奶奶和小姑居然已經做好了迎接大姑的準備。
我說:“你們為什么不告訴我!”
小姑說:“提前告訴你,你能消停嗎?肯定一天到晚問個沒完……”
莎莉剛到家中時我就迫不及待地帶她到處認家里的財產。
我說:“那頭最高大的牛是高個子黑白花,那頭白色的是白姑娘。以后要小心那頭黃的,它叫暴躁黃……”
莎莉在旁邊認真地聽著我講,臉上充滿了好奇。說完,我又讓她重復一遍。
她說:“那是白姑娘,那是暴躁黃……”
我和爺爺的放牧二人組壯大為三個人了。清楚地認識自家的牲畜,是學會放牧的第一步。但在新生活開始前,有個必須經歷的儀式,就是離別。大姑在市里租了一間小房子,在一家維吾爾族老板開的餐廳打工。這便是莎莉來樺林中與我們一同生活的原因。
我和莎莉屋前屋后地玩耍著,完全忘記了時間,太陽幾乎是在一瞬間墜入山后的。我們在河邊撿著大大小小的鵝卵石,再和泥巴將河中撿來的石子壘成一個個小屋。莎莉來之前,我常這樣自娛自樂。神奇的是,我剛和起了泥巴,莎莉便跑到河邊撿起一捧一捧的小石子送到我跟前。人類最原始的基因推動我們不約而同地配合著完成一件偉大的事情——建房屋。正當我們建造出了一個小村落時,小姑的呼喊聲打斷了我們。
“巴燕!莎莉!回家,大姑要走了。”
聽到小姑的聲音,莎莉丟下手中的石子向房子跑去。我留在原地恍惚了幾秒,也起身慢慢跟了過去。我本是很不情愿跟去的,因為我知道接下來將發生的事情。一進院子,不出我所料,大姑蹲下身子正和莎莉溫柔地講著。
大姑說,我的小羊羔很乖,媽媽明天開始要打工了。等下周我會再來看你的,帶著你最喜歡的棕色玩具熊。
莎莉意識到這是一次離別,她開始抓著大姑的袖子不讓她離開。她開始哭,開始鬧。大姑依舊溫柔地安慰著她。
我已經猜到了事情接下來的發展流程。莎莉哭一會兒看媽媽沒有離開,以為自己挽留住了媽媽,便會慢慢停止哭聲。而大姑看莎莉不再鬧了,心里則有了一點安慰。結果就是,大姑起身急忙道別,快步離開。莎莉準備追時被小姑抱起,只能痛哭。爺爺在一旁哄著莎莉,一邊讓奶奶去拿些她珍藏的糖果來哄莎莉。雖說已經習慣了這樣的場面,但還是會控制不住情緒低落。如果說人是一棵樹,那情緒就是風。風雖吹過,但仍然無法阻止幾片葉的掉落。
大姑在河道上的背影漸漸遠去,重新變為一個無法辨認的黑影。莎莉被留在屋里,我在屋后的一棵樺樹下替她恨著大姑。就像往日里恨父親離去的背影一樣。與以往不同的是,心底多了一絲安慰。因樺林中多了一個新玩伴,她便是新的期待,也代表了新的事情即將發生。
生命是一列行駛的火車
生命是一列行駛的火車,上上下下的人們攜著不可言喻的東西。如帶來一個永恒的春天,或帶走一些生命的碎片。
不知道何時起,我的生命變得十分脆弱,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事情也能使我熱淚盈眶。正如此刻,坐在院內抬頭,發現去年種下的兩棵蘋果樹發芽了。出圈的小牛犢在屋旁的草場上撒野。小表弟會走路了……春天第一次給予了我新生的錯覺。又或者,不是我的生命過于脆弱,而是這些平凡的小事總能勾起一些美好的回憶。每當我從其中抽離出來時,一股復雜的情感便會涌上心頭。我不善于理解情感,所以并不能分清那是痛苦還是感激,或其他什么的。我只能感受到悶在胸口的力量慢慢向上移動,到咽喉,到口腔,通過鼻子,最后在眼眶化作一滴淚。水是多么神奇的事物啊,有時我需要它進入我的身體,有時我也需要它離開我的身體。
每年春天總有那么幾日,奶奶要在院子的一角制作牛糞餅。利用冬天剩下的煤末和牛糞合在一起,用小鐵盆塑形后曬在墻上。這種牛糞餅比撿來的干牛糞要更耐燒一點,產生的熱量也更多。奶奶已經步入了七十歲高齡。或許日復一日的生活狀態,早已讓她身體里的那列火車失去了方向。所以她不得不找一些事情來做,好讓今天活得跟昨天不一樣。但大部分時間里,奶奶還是無事可做。她就在大板床邊巴巴地坐著,從早到晚,偶爾被自己的自言自語逗笑。其實她并不是突然這樣的,她還是像以前一樣,只是少了另一個人。
怕奶奶一個人孤單,父親和其他子女經常來看望她。父親和叔叔不善言辭,只是偶爾陪奶奶靜靜地在大板床邊坐著。而我的幾位姑姑則不一樣,女人們永遠心細,又有耐心,懂得如何哄奶奶高興。她們常常陪著奶奶一起刺繡,或帶來一些城里的美食和華麗的衣裳。她們在身邊時,奶奶總是笑得合不攏嘴,而剛學會走路的小表弟更是讓家里多了一些喧囂聲。小表弟十分好動,一會兒扯下奶奶的頭巾,一會兒將黃白相間的老貓當馬騎,又一會兒跑到院子里追趕老母雞。安靜的院子里一下子“雞飛貓跳”。小表弟的活力感染了周圍的萬物,也包括我們。他身體里的那列火車正鳴著汽笛,向著世界的深處駛去,而我們則是他的第一批乘客。
下午的太陽沒入了群山的懷抱,路上的泥濘漸漸堅硬,并記住了一天的痕跡。奶奶的子女們都走了。人們只是在生活的路上互相取暖,孤獨才是我們真正的歸屬。
奶奶脫下新衣裳,又穿上了那套破舊的開襟羊毛衫。那些兒女們帶來的食物和新衣裳都被她壓進了箱底,不止這些,奶奶習慣將所有美好的事物存起來,自己默默品嘗生活的平淡。一直到最后,那些食物會發霉過期,新衣裳在箱底被老鼠咬出幾個洞來。那時奶奶才會開始后悔。但對于一個已經習慣了困苦的女人來講,享受美好事物是一種奢望,同時也是一種罪過。
奶奶又重新坐回了大板床邊。坐在大板床邊,對面的窗戶正對著一小片菜園,后面是牛棚,河邊是一排白樺樹,遠處是連綿的群山。所有的一切好像靜止不動,只有我們在萬物間徘徊,并在徘徊中留下影子后老去。留下來的人走走停停,在身體里的這列火車上尋找著某些殘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