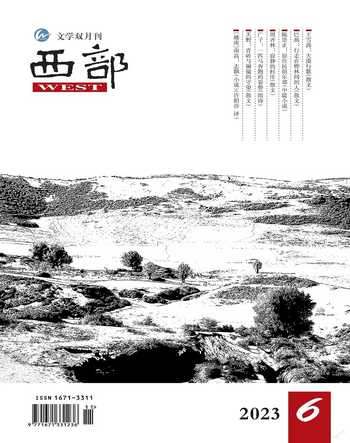小徑斑駁的公園(外二篇)
連亭
他和他的小屋縮在濕地公園的一隅,就像貝殼被海浪沖到沙灘的一角,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一脈濁流,三畝荷塘,參差岸柳,高低叢花,勾勒出還算入眼的風景。這風景都由他看管,也就是說都屬于他。在濕地面前,他成了一個既富有又孤單的人。
有時我路過小屋,他坐在門口“刷抖音”,身子佝僂,影子虛弱地落在地上,好似一枚脫色的枯葉。他從不抬頭看路人,世界仿佛都在他的掌上,又仿佛根本不存在。有時他不在門口,小屋中傳出嘈雜的手機聲,告訴濕地的草木他還在監護這方水土。
在這片還算繁茂的濕地,我見過灰鷺、白鷺、水雞、野兔……它們使我心情愉悅。我每次到公園散步,眼光都在搜尋它們。在我眼中,它們是構成風景的元素,而非無關緊要的生命。或許,這點衍生價值正是政府建設濕地公園的目的之一。城市擠滿高樓,在這東北角開辟一處后花園,興許能給單調無趣的生活添一抹亮彩。只可惜,主城區離此太遠,周邊新建的幾處樓盤業已爛尾,公園的人氣就旺不起來。可惜大好的流云落花,日夜空對一個半百老人。
我這個閑人,似乎是唯一欣賞濕地風光的人。或許,這是因為我無所事事,恰與野禽惺惺相惜。或許,這是因為我終究會離開,周遭的死寂囚禁不住我,便萌生出些許蟄伏的律動。在我不注意的時候,小屋中的人有沒有貓在窗前打量我,正如我對他看似無意卻有心的觀察。在他眼中,我是不是一個可疑的人,一個游手好閑不務正業的潛在犯罪分子?在審視中,我們之間似乎一覽無余,又總是隔著無形的觀念和認知差異,終究無法彼此理解和認同。
公園的小徑只有半米寬,是被人工裁剪出來的,工人也許知道這里有朝一日落荒,活就干得很潦草,沒多久道旁的灌木雜草旁逸斜出,掩蓋了路面。這樣以后,它已經不像一條路。即便我的腳印時時落在上面,也挽救不了它荒蕪的頹勢。我用手機照相捕捉春梅秋英,噪蜂舞蝶,幻想留住這些活一季的生命,直至落入我個人的虛無。
我在小徑上什么也不干,只是閑著。我遇見的春花燦爛、秋葉枯索,不是為我而在。我來到時,它們正好進行著緩慢生長,僅此而已。并不比別處少的陽光,從碧天灑下,照亮濕地的水面,荷花便在她們的季節婀娜。看著綠葉紅荷,我想起楊萬里。他看見映日荷花別樣紅,也看見小荷才露尖尖角。從尖角小荷到映日荷花,是日月輪轉,也是蛻變成長。誰也改變不了她們的節律,誰也阻止不了她們綻放。她們愛風露蝶影勝于我,就像我愛她們勝于其腳下的淤泥。
小徑的北邊,有座矮山。山上有座紀念范增的廟,有些年歲了。平日沒有人來,廟中的塑像就有些落寞。若是不熟悉,一般人不知道這是座古代名人的廟。從山下往上看,它和那些遍布山間的墳墓毫無區別。那些墳墓里,躺著與當地居民血脈相連的先人。小徑與山本不連通,但只要不在意雜草和荊棘,人還是能越過障礙上山,漸漸地就踩出一條似有似無的路。山墳一律朝南,從墳墓的角度看,它們似乎也坐擁南面的大片濕地和流水。我沿著草木的間隙慢慢攀爬,矮山掩藏在褶皺中的事物就抖落出來。一些碎石塊述說著范增的事,也喧嚷著曹操的事。這兩個人,一個出生在此,一個將戰馬的鐵蹄留在此,二人的一生都在為一個“霸”字奔忙,終也抵不過暮色的侵蝕。其實,矮山能承受的不多,草木枯榮,日出日落,已耗盡它的血氣。對于人,它只能提供最后的歸宿。它收納人的尸骨,猶如泥土收容落葉。從來沒有人出生在這座矮山上,除了烏鴉,其他鳥似乎也很少到來。
我靠近那些記錄姓氏的石碑時,暮色正落在山上。山下吹來的長風掃去碑上的殘葉,斑駁的字跡顯露出來。這些文字遠不如范增、曹操的偉業重要,卻更牽系這方水土的人心。霞光映照在漫漶的字跡上,恰似一聲命運的嘆息。有些石碑上的字很遒勁,雕刻的花紋亦精致,讓人猜想石碑主人的兒孫懂得感念先人,并且家業興旺。也有一些石碑經久無人光顧,歪斜殘斷,倒伏在雜草叢中。我很想像扶起老人一樣扶起這些石碑,又怕驚醒一些我害怕的東西,只能心里默念阿彌陀佛轉身離開。此時,我若是喊叫,聲音就變成鳥鳴。我若是站住,就變成一棵樹。我若是蹲下,就變成一塊石頭。我只能往前走,追著退去的陽光下山。
我又回到小徑上,像是被風吹落到地面的種子,只是無法生根發芽。東邊霍霍生長又戛然而止的樓盤,在寂寥的小徑上投下狹長的陰影。它們讓我想起人生中無奈的挫敗。這些磚石怪獸,不光耗費金錢堆砌,更關乎無數人的家園。那些把所有積蓄交給開發商的人,也像我一樣渴望有一間遮風擋雨的房子,一個溫暖甜蜜的家。但是,陰影悄無聲息地籠罩一切,美好的期盼變成了風中的干咳。小徑該通往何方,或許連兩旁的草木都不知道答案。
我只能朝著有光的地方胡亂走,試圖走進那近黃昏的余光中。在陰影中待久了,會影響人對事物的判斷。所幸我只是匆匆走過,而光并未拋棄我。這些年我曾在深夜的十字街頭落淚,也曾在謊言與是非中跌足,但光從未在我心里消失。因為有光,沒有人能把我困在黑夜。
光落在水面,水波變成無數黃金。我再次看到水岸邊的小屋和屋檐下的人。那人依然沉默,但在這個角度,我們之間隔著一片荷塘,罩在他身上的那層孤獨就淡了。他沒有看花,但花在他身旁,這就與沒花有所不同。有了花影點綴,我可以把他想象成隱者。他看破紅塵,遠離喧囂,萬千波濤歸于平靜,所以看淡這秋月春風。但這終究只是我的想象,他是或者不是,都是我的一廂情愿。我們之間的隔膜始終存在,哪怕阻隔的東西百般不同。也許我可以走過去問他,摸清他的背景和經歷,但他愿意對我坦誠相待嗎?說不定他會將我視為侵略者,要么把我趕出領地,要么給我當頭一棒。
在我認為我會離開此地時,我已是個異己者。我非生于斯,非長于斯,也不會留于斯,憑什么闖入他的世界?我這個因為生活困頓寓居于斯的人,始終是這里的旁觀者。我來這里的路上,看過一個煙波浩渺的大湖,見過湖上鷗鷺成群,航船繁忙,游人不絕,于是就看穿這里的狹小。相比之下,這兒盡顯流放地的氣質,溝淤水淺,蘆葦橫生,水質黑臭,生養出的事物也失了光彩。就連一向高雅端莊的白鷺,尾羽腹毛也沾著泥垢,露出臟兮兮的可憐樣兒。最可恨的是,它們永遠也壯觀不起來,永遠不能像大湖上那般群飛紛舞,永遠零星散落龜縮一角,而且一旦我靠近,它們就驚嚇得飛走,卻又飛得不高不遠。那黯淡無光的羽翅無力地扇動幾下,它們又在一兩百米開外落下,露出呆頭呆腦的神態。我若繼續走近,它們又再次飛起,匆忙而草率地降落。這模樣看起來毫無自主意識,只會在隱忍退讓中守著這貧瘠的棲息地,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明明長著一雙能振翅高飛的翅膀,明明遼闊的大湖一刻鐘就能抵達,它們竟然甘愿桎梏在這逼仄的空間,是它們局限,還是我不安分,只有天知道。
水終究沿著河床流走,即便它留戀荷花的倩影。如此說來,世人言流水無情也不冤枉。扎根太深的事物,總是被風和水甩在原地,慢慢地沾滿原生環境的氣息,不爭不搶,不怨不怒,不知是根須讓它們如此,還是它們本性如此。我折下一枝荷花,帶回出租屋,養在半尺深的水瓶中。僅僅過了一夜,花瓣就驚心動魄地掉落在地,徒留光桿子怵目地插在瓶中。我這才意識到,我讓它失去了長出蓮子的機會。
一場無籽葡萄引發的戰爭
為一盤無籽葡萄,母親坐在餐桌邊默默流淚,我毫無招架之力。她嘮叨,我可以左耳進右耳出。但對眼淚,我一點兒辦法也沒有。
我買葡萄,只是覺得它們甜,根本沒考慮它們有沒有籽。從我們的角度來看,無籽吃起來還更方便,有什么值得流淚的呢?
母親似乎與一切無籽無核的東西杠上了。我擺在陽臺的盆栽,凡是長不出果實的綠植,她都嗤之以鼻,澆水時還強打猛攻,像是要故意淹死它們,如同她試圖用淚水淹沒那盤葡萄。
后來,她對有籽實的東西也產生了“仇恨”。起初,她只是偷偷摸摸收集各種水果的籽實與核仁,然后畢恭畢敬地埋進土里,虔誠而焦灼地等待它們發芽。后來,事態就發生了轉變。她把小區里的空地都禍害了一個遍,折騰了一個又一個無辜的水果,熬過了一次又一次漫長的等待,仍然一無所獲。她不知道這些從超市買回的水果,由于使用農藥、激素和早采的原因,早已失去繁衍后代的能力。辛勞換來的是無望,她的怨氣與日俱增。
“我在你這個年紀時,你小學都快畢業了。”她終于向我宣戰。
我把葡萄丟進嘴里,無言以對。
二十六歲以前,我在上學。二十六歲至今,我居無定所。兜中無余錢,腳下無寸土,我連根都扎不了,遑論開花結果。
受過的磨難我不想再說了。這次回家,我只想給自己放個假。母親的眼淚還在流著,她吸鼻子和擦眼淚的時候,特地弄出很大聲響,濕答答的紙巾被她揉成一團緊緊捏在手里。
這本該是一個令人心曠神怡的下午,剛入初秋,風沁出迷人的清涼。窗外響著陣陣秋蟬的鼓噪,丘陵和平地搖曳著二季玉米、禾谷的綠影。蜻蜓和麻雀似乎感知到季節的饋贈,在風中忽左忽右地盤旋,為生命的蓬勃狂歡。它們單純地飛著,不問天地道義。
隔著餐桌望去,哭泣的母親有些枯黃,不是風干的玫瑰式的,而是飛蛾斂翅式的。我坐在她對面,屁股下的椅子就像燒烤板。
我的呼吸急促,拼命假裝自己不在這兒,而在別處,在遠離淚水的地方,在藍天白云下,在田野花叢中,在神秘、富饒的大自然里。如果我大哭一場,可以讓母親止住眼淚,我真想把體內的淚水都傾瀉而出。
我不想惹母親傷心,想像小時候考高分那樣哄她開心。可不知為什么,事情總不能稱心如意。此時,我的丈夫在另一個城市找工作,我們結婚五年了。
這時,有鄰居過來敲門。我從椅子上逃離,打開門看到拎著一籃黃瓜的三嬸。她遞給我四根黃瓜,臉笑得跟南瓜花似的,很歡騰,又不免讓人覺得太濃烈。她問我什么時候回的,什么時候走,在哪兒上班,一個月掙多少錢……問到她想要的一切后,她心滿意足地拎著剩下的黃瓜走了。她這一走,我回家的消息將很快傳遍能傳到的地方。
“人家問我你的情況,我要怎么說。”母親望向正在關門的我說道。“怎么著都行,您不必放在心上。”說完我把三根黃瓜放到餐桌上,把另一根往嘴里塞。那盤葡萄我是再也吃不下了。
今天可能有一番不同尋常的談話,也可能什么話都談不下去。母親老了,我年紀也不小了。我的皮膚仍然細嫩,臉龐看起來像個二十出頭的大學生,這能在陌生人面前掩飾我的年齡,卻騙不了我的母親。
“你得有打算。”她說。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說。
“萬一將來……”沒說完她的眼淚又掉下來了。
“怎么會呢,您想到哪里去了。”說著我想遞給她一張紙巾,又怕她情緒變得更激烈。
“我們把你養大不容易,好不容易上了大學,你呀……”
“媽媽,您知道的,您和爸爸都不能到我的身邊,我實在沒有幫手。他哥哥和爸爸都病了,我沒有辦法呀,誰也不知道會這樣。”
她沉默片刻,想再說點什么,但噎住了。三十多年來,她在我面前一直是這個樣子,一點也沒變過。她對我說的很多話,以前都說過很多遍了。有時我覺得我們之間有點可笑。
生活可能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吧,總有很多不可理解的東西。我繼承了她的基因,沒有繼承她的大腦,這就產生了很多麻煩。
現在,我只關心晚飯吃什么。我在外面餓壞了,什么好東西都吃不到。我想念這兒的許多食物,白切雞,白切鴨,香蔥蒸魚,夾心肉炒菜心,香腸蒸飯……
我看向窗外,樓下的那棵樹影子變長了些。那些蜻蜓和麻雀還在飛舞著,像在齊心協力編織一張布滿黑點的大網。
其實我的事沒什么好說的。我們沒有錢,沒有父輩幫襯,干著急也沒用。既然如此,我就很少去想這些事情。我把更多的時間用在看書和寫文章上,有了點不值一提的成績。我沒什么可羞愧的,但在母親面前,我卻恐慌和不安,總覺得有什么事必須解決,否則就不安生。
“滴滴,滴滴……”水泥路上駛過車子。我不在的日子,窗外修了兩條路,交通設施更好了,車流也更多了。坐在窗邊望出去,可以直觀地感覺到車子朝我開過來,轉個彎又開走了。
車子開遠后,一些麻雀落到樹上,嘰嘰喳喳地叫起來,遠山的霧氣慢慢變濃。
時間過得很慢。母親不哭了,沉默還在延續。
我吃完手中的黃瓜,給母親倒了一杯水。
“你表妹昨天打電話來叫我們全家去吃滿月酒,我想著她比你小幾歲,現在都有孩子了,免不了覺得時間過得很快。”母親像是在解釋她今天的失態,又像是進行另外一種暗示。她說完喝了一口水,過了很長時間才轉而問我想吃什么。
我如釋重負,母親終于變回慈愛的母親了。每次我們在不愉快之后,總能以一頓熱乎乎的飯菜重歸于好。即便我們此生都不能互相了解,我們也能因為一頓飯而深愛對方。
吃飯的時候,我有意討好母親,一個勁兒地夸她的菜做得好吃。她的臉色舒展開了,浮現出一絲笑意。
“你當初聽我的話就好了,聽我的話也不至于像個餓死鬼……”她嘆氣。她指的是想讓我放棄讀研究生的事,或者是我遠走他鄉的事。哎,吃飯的時候最不適合說起這類往事了。就算我相信內心的聲音,我知道自己要怎么活,這種話聽多了也會自我懷疑的。
我沒有把日子過好,或者說沒有把日子過得像母親那樣的人期待的那樣,自然無法對母親的話做出反駁。
晚上,我早早地回了臥房,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愿意想,就是睡不著。明天就要去表妹家了,我要不要去呢?她家屋后有一片小樹林,小時候我和她在那里蕩過秋千,建立了女孩子之間才有的深厚情誼。去年表妹出嫁時,我在北京沒能回來參加婚禮,已經有點對不住她了。
我醒著,想起在另一個城市的丈夫。他的工作有著落了吧?
夜里下了一場雨,早晨推開窗戶,那棵樹的葉子還在滴水。
“我不想去。”我對在做早飯的母親說。
“這不像話,別人問起來我沒法交代。”母親有些生氣。
“又是別人,為什么總是要按著別人的意思,或許別人根本不在意呢。”我也生氣了。
三嬸來催我們出發了,真令人沮喪。呵,出發。呵,一堆人坐在一個車子里,吵吵嚷嚷地說話。呵,一堆人圍著新人,說著重復的祝福。呵,一堆人擠在一間屋子里,吃糖,嗑瓜子,大聲說話……
新婚夫婦居住的房子,是一幢三層樓房,墻面和地面鋪滿瓷磚,嬰兒抱在有點發福的年輕母親懷中,廚師們當當當地做菜、上菜。
我看著幸福微笑的年輕母親,感覺很陌生,很難相信她曾是那個和我要好的女孩子。她和嬸嬸們越來越像,掀開衣襟給孩子喂奶時,直接而粗獷,毫不避人,甚至很享受一屋子人看她喂奶的樣子。一屋子的人,千篇一律地夸孩子天庭飽滿,天生富貴相……站在這些人中,我覺得所有人都變了,只有我還是老樣子;又覺得所有人從沒變過,只是我成了一個離開的人而已。我感到窒息,虛弱,慚愧。周圍的一切都讓我恐懼和厭煩。我不知道這些人為什么而活著,盡管我一直在想活著這件事。年輕的母親輕輕搖著孩子,溫柔地哼著歌兒,一切完滿得令人眩暈。
宴席散后,回來的路上又刮風又下雨。我感冒了,母親把她的外套脫下來給我:“還冷不冷?”我說不出話。
車子駛過山河,田野,我曾在這些土地上勞作,啊,那美好的過往在車后飛逝……
“我明天就走了,有工作要做。”回到家我就跟母親說。
“怎么這么快,你不是說要待一星期嗎?”母親非常意外,完全不明白為何如此突然。
“臨時有急事。”我艱難地解釋。
母親的眼睛又紅了。而我不能心軟。
“你和你弟弟都讓人操心。”她幾乎哽咽。這時的她蒼老,弱小,可憐。
我回到自己的房間,開始收拾行李。那一晚,我坐在窗邊對著那棵樹等天亮。
太陽出來后,我在樹下攔了一輛車。我走了,把母親留在了家里。
一只劃過車窗的白鳥
五月,我和朋友爆發了一場關于白鳥的論爭。那時我們坐在行駛于大湖邊的別克轎車上,一只白鳥從車窗邊劃過,她脫口而出:“真見鬼!”
我看她眉頭緊皺,就問:“出什么問題了嗎?”她指著那只遠去的白鳥說:“我奶奶以前常說白鳥不吉利。”這話讓我詫異。雖說我知道民間有些傳聞,但多是些無稽之談,毫無科學依據,只是人們在混沌時代因為巧合而編出來的“經驗之談”而已。
為此,我和她就民間傳聞的生發機制和科學原理展開了論爭。我堅持調動元認知去厘清事實和本相,而她則固守祖輩相傳的說法。最后的結果是,那天我們沒有好好看大湖,也沒有興致看野鳥,而我們原本是開車自駕來旅行的。
從大湖邊回來,我打算就白鳥寫一篇文章,以平復被爭論激起的情感波瀾。這個事既要從先輩們的認知經驗說起,也要從文化的源流去辨識。
我小時候也是在口說奇聞的祖輩們身邊生活的。我這些手揮鐮刀的爺爺奶奶們,看見白鳥從院子上空飛過,他們就會內心拔涼。要是白鳥從他們后腦勺掠過,他們準會嚇得幾天睡不著覺。要是白鳥飛進屋里,簡直叼走他們半條命。每當白鳥不請自來,他們就會燒香禱告,或者在大門前焚燒一堆柴火,試圖驅走看不見的瘟神。直到煙消云散,他們依然憂心忡忡。
關于白鳥的諸多不祥觀念由來已久,卻源頭模糊,無從深究。它們像那些世世代代的祖傳經驗一樣,來去失考,真偽難辨,卻從始至終被頑固地千古流傳著,比長城還要堅不可摧。我曾努力讓我的外婆放下對一只白鳥的執念。在我眼里,那只從大門飛進廳堂的白鳥可愛伶俐,叫聲悅耳,不可能有一丁點兒惡意。我的外婆卻如臨大敵。她揮舞掃帚,把那只驚恐的小鳥兒嚇得四處亂撞,全然不顧我可憐兮兮的眼神。事后,她對我進行語重心長的教育,企圖把警惕的細胞植入我的大腦。
“白鳥不吉利!”這話在我的大腦紛飛亂舞,卻總也理不出一絲頭緒。
這白鳥,是泛指一切白色之鳥,還是指某類鳥,或是某種鳥?沒有一個明晰的標準,我怎么辨別和執行呢?若說是指一切白鳥吧,可祖先們不也對白鷺、丹頂鶴之類的白色鳥愛之彌深嗎?且不說王維“漠漠水田飛白鷺”的詩情畫意,單是看看那些威嚴肅穆的部族圖騰,那些軒敞豪華的客廳掛畫,有幾幅不是畫著白鷺繞日而翔、松鶴點綴南山?既然風調雨順、福澤延綿都要靠白鷺、丹頂白鶴護佑,又何必讓潔白之色蒙上恐怖的陰影?若說是某類鳥,又是哪一類呢?有沒有具體的名單,供我對號入座?或者那些見證過白鳥魔力的人,有沒有留下白鳥的畫像,讓我按圖索鳥?我虛懷若谷地前去詢問德高望重的老人們,竟然無一人清楚,只是反復強調是白色的。我只好求助龐大的文獻資料庫,然而翻遍古籍,閱盡文獻,竟也找不到蛛絲馬跡。在關乎生死的事物面前,我們連哪一類都不知,更別說是明確哪一種了!我該哀哉,還是怒哉?
我能不能去白的對立面尋找答案呢?比如“黑白分明”,我們找到了黑,就能凸顯出白。或者我們明確了黑,就能在比對中抓住白的特征。《唐伯虎點秋香》的電影中,大才子不就是用了這一招嘛!
只要留心,我們就不難發現民間也有很多黑鳥不吉利的說法。只是相比之下,這種觀念的來源卻清晰得多,所指也明確得多。首屈一指的是烏鴉。它們聚集在腐尸腐肉旁饕餮的模樣,早就將死亡的標簽貼在自己頭上。它們嘶啞刺耳的叫聲,聞之令人胸悶,比報喪的鐘聲還陰森恐怖。其次是貓頭鷹,前有賈誼長沙鵩鳥集舍之悲,后有民間口耳相傳疊加渲染,人們是一提到貓頭鷹就想到兇殺現場或者墓地。腐尸腐肉也位列貓頭鷹的食譜之首,瀕死動物身上暗藏的死亡氣味,它們隔著老遠都能聞到。如果說烏鴉的叫聲只是難聽,那么貓頭鷹的叫聲則堪稱驚悚。在我的故鄉廣西,人們既怕夜貓子叫,也怕夜貓子笑。它們叫起來像鬼哭狼嚎,笑起來像嬰孩快斷氣的哭聲。本來,貓頭鷹的羽毛黑的不多,但由于它們總是披著黑夜出沒,也就被人當成黑鳥。
民間有句俗話:兩鳥入宅,無病也有災。這話說的就是以上二鳥。可見人們對二鳥的厭惡和恐懼,如同對災難和死亡的厭惡和恐懼。這是因為它們長得黑嗎?略微看看人們對燕子的歡迎態度,瞅瞅房梁下碗狀的燕子窩,就能感到人們對這種黑鳥的喜愛。玄鳥生商,燕子來福,這種觀念借由《詩經》的聲韻,早已在中國人的腦海中回蕩幾千年。
色白色黑,原本無義。我們只能在文化的根脈中,去探尋一些幽微意識在時光中衍生的觸須。
白鳥,黑鳥,皆是鳥,所異者,唯色也。白色黑色,寓意為何?《周禮》以白色為肅殺兇煞,《月令》以秋氣為白,喪服為白。無論自然還是人文,白色都被賦予兇殺之象征。然而,洗白之白,清白之白,雄雞一聲天下白之白,卻也是代表嘉和美好。《易經》以黑色配天,將之看作眾色之母。秦朝服色旌旗尚黑,秦始皇一身黑龍袍雄視天下。黑色,既作為皇室身份的標志,也是臣民們眼中尊貴的顏色。古代人家喜歡將大門漆成黑色,《紅樓夢》的榮國府大門即是黑色,彰顯著豪門貴族的氣派和威嚴。如今一些關東人家,還保留著黑大門的風俗。黑門,有時還代表一種精神追求。明清時期官府衙門的大門是黑色的,門墻則是白色的,寓意黑白分明公正無私。然而,在風水學中,黑色對應著死亡、沉悶和陰暗。可見,人們的顏色觀念沒有統一的標準,而是沿著長短不一的半徑隨時、隨地、隨事、隨物變遷。
這種模糊的傳統沒啥不好的,較真的人卻犯難了。那只劃過我們車窗的白鳥,是不是先輩們說的惡靈?好與歹,若是隨時、隨地、隨事、隨物遷轉,我們如何定性這一次遭遇?在我眼中,它是一只美麗的鳥兒,或許剛在湖邊飽餐一頓,正要趕往戀人所在的巢穴,而它的必經之路恰好在我們的車窗外而已。那時,我們的車窗外,遠山淡影,蒹葭蒼蒼,湖水浩瀚,白鳥翩躚而過,真是一場充滿詩意的邂逅。但在朋友眼中,由于某些觀念根深蒂固,這只白鳥無比危險。
如果不能達成共識,我們可以求同存異嗎?
面對寧可信其有的防范心理,即便不信這個邪,也很少有人能夠承受制造風險的精神壓力。就算世上所有的厄運都與這只鳥毫無關聯,它也被籠罩上某種原罪。它可能只是出現的不是時候,不對地方,但這也只是我們人類自己認為而已。大自然以它的方式運行,白鳥以它的節律生活,不為人類而存在,也不為人類而改變。誰能說那只白鳥不該劃過我們的車窗?
親愛的朋友,我們曾一起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山深溪凈,一灘鷗鷺乘風而起,帶來遙遠的澄明與禪意。那時,我們在王維營造出的一個磁場中心有靈犀,無垢無塵。
呵,文化是人的產物!我們被文化塑造,被文化保護,也被文化傷害。我們能做的,往往只是與既有文化相處,然后試圖在磨合中創造出新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