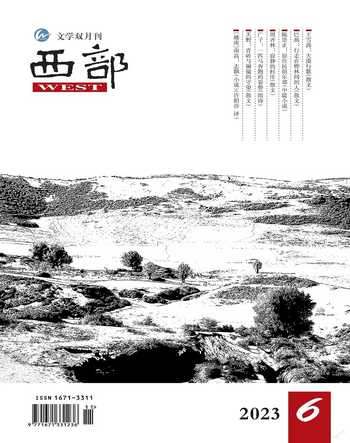半坡起步(短篇小說)
姜繼先
車又一次停在了半坡上。
這已是第五次了。前四次,科目二都在坡道定點(學員稱為“半坡起步”)上折戟沉沙,鎩羽而歸。再考,路夢蕓還是有些緊張,這次如果再考不過,就將前功盡棄,從頭開始,她在心里已做好了改考自動擋的準備。
為了不再折騰能拿到“本”,路夢蕓交了補考費后,把時間全部放在了練習半坡起步上。教練是個退伍的汽車兵,說到駕考的事就跟說打仗一樣,他對她說,半坡起步對她而言,就像一個碉堡,必須攻克,要不然,縱有千軍萬馬,也是白搭。因為當過兵,教練還算講文明,一般不罵人,氣不過時頂多訓斥學員幾句,在路夢蕓第四次也沒有考過后,卻對她發了脾氣,罵她腦子被水淹了。為此,在回家的路上,她一直在不停地抹眼淚。
眼下的考試,倒車入庫、側方停車、直角轉彎、曲線行駛全都順利通過,又該考半坡起步了,路夢蕓看了考官一眼,臉一熱,不好意思起來——也許是巧合,每次考試給她安排的考官都是同一個人,一個留著板寸、身體強壯、不茍言笑的中年男人。前四次,都是在半坡起步上中止了考試,現在又碰到這位考官,路夢蕓不免有些難為情。
考官并沒有注意路夢蕓的表情,面色嚴肅地看著她做著準備工作。考試開始,考官小聲提醒著,穩住、小心,不要緊張,平時怎么練,現在就怎么考。路夢蕓為了消除緊張感,把眼睛閉了一會兒,然后,又從衣兜里摸出一塊口香糖放進嘴里,這才開始點火。踩離合、掛擋、松離合、松手剎、加油……就在離合松開的一瞬間,她深踩了一腳油門,車子猛地躥了出去,她突然意識到,給油太多也不行,趕緊把油門穩住,像是欺生的狗見人走遠了,不再狂吠蹦跳,邁著碎步小跑起來——車穩穩地前行,終于駛到了坡頂。
科目二過關!
路夢蕓很是激動,想順嘴嚼幾下口香糖,卻感覺嘴里并無東西,什么時候把口香糖咽進了肚里,她全然不知。向考試場地外走時,她遠遠看到兒子大峰,便舉起手來,向大峰不停地揮舞。然后,她又做了個“ok”的手勢。大峰知道她考過了,也不顧考場紀律,沖進考場內把她抱起來原地轉了一圈。隨著轉動,她響亮地笑了起來。
母子倆走出考場,大峰對路夢蕓說:“那就給我爸打電話了。”還沒等路夢蕓回應,大峰已撥通了高默然的手機,讓他把車開過來。
一家人幾日前就商量好了,不管路夢蕓今天能不能考過,他們都去阿山看山花去。阿山是有正式名稱的,但人們卻習慣叫那座山為阿山。每到春夏之交,山谷里開滿山花,特別是野芍藥,姹紫嫣紅、搖曳生姿。這日是星期六,活動也都提前規劃好了,他們從烏城出發,到達阿山將是傍晚,他們就在山里找個地方燒烤野餐,露營一晚,第二天上午游山戲水看花草,下午返回,天黑前趕到烏城,不耽擱路夢蕓第二天上班。
剛考完半坡起步,路夢蕓還沒有從考試的氣氛中掙脫出來,聽了大峰給他爸打的電話,她突然覺得,自己和高默然現在的婚姻狀態,也像車停在了半坡上——這是一個很難預判的狀態,如果手腳配合默契,操作得當,車還能爬坡前行,保持前進的方向。倘若操作不當,出現差池,車子就有可能熄火下滑——婚姻終結。
剛開始考駕照時,路夢蕓就察覺到了自己的笨拙和遲鈍,面對機械,就像狗咬刺猬,找不到下嘴的地方。起初,她是非常自信的,自己當老師多年,領悟力是沒有問題的,科目一考試,一次過關,得分一百。但是一操作起來,腦子就發蒙,總是手忙腳亂,因此,科目二練習,她比別人付出了更多努力,甚至在夜間加班練習,就算這樣,半坡起步還是屢試不過。鑒于自己的狀況,她曾產生了放棄的想法,之所以堅持了下來,其實是為萬一離婚了在做準備。
高默然曾經也是教師,和路夢蕓在同一所學校教書,他教物理,她教語文。他們是在單位認識的,后來發展成戀人,最終睡在了同一張床上。結婚后,高默然看到很多大學同學都發了財,自己卻還在吃粉筆末拿死工資,心有不甘,也想著能過上花錢不用眨眼的日子,于是辭去了教師的工作,受聘到一家經營廣播電視業務的私營公司,拿起了年薪,每年有二十多萬的收入。因為高默然是學物理的,進入廣電行業,知識儲備綽綽有余,很快便摸清了行業內的生意門道。他在這家公司干了七年后,拉了兩個人,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公司初立之時,他深知做生意拓市場,就像開路架橋一樣,沒那么簡單。一開始他把公司的定位放得很低,主攻各地州的縣市和兵團的團場,主要經營線纜、線路施工和演播室設計。路子算是走對了,每年有兩三千萬的營業額,賺了第一桶金后,又經營起廣電設備,眼下公司已小有規模。為了方便業務,公司先后買了三輛車,一輛奧迪轎車、一輛的士頭皮卡,還有一輛豐田越野。高默然曾開玩笑說,駕車就像睡女人,開自動擋如同和老婆睡在一起,駕輕就熟,而開手動擋猶如和情人在一起,需要挑弄撩撥,翻山渡水。所以,在買豐田時,他選的是手動擋的。他自己駕車,只開豐田。
大峰打了電話,半個小時后,高默然就開著豐田趕到了駕考場地,一切都準備好了,所用的東西把后備廂塞得滿滿的。路夢蕓在車的側面,背著人換了外套和鞋子,三人上了車,向著阿山而去。
到阿山去游行,是大峰出的主意。
路夢蕓記不起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她與高默然之間處在了車停半坡的狀態。但有一點他記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在大峰上高二時,兩人已不在一個房間里住了,也不再關心對方,有時要加班,她打電話告知他,他不會說一句關愛的話,也從來沒說過要去接她,甚至還提議,要是太晚了,就不用回家了,在學校教師周轉房里湊合一晚,免得來回折騰。而有時夜深了,他還沒有回家,她也懶得問他在干啥,時間到了就上床睡去,半夜起來小解,發現他仍沒有回家,她也不會產生太強的失落感。在一些寂寥的夜晚,路夢蕓會思考或者說反思一下自己的婚姻,結婚二十多年來,她和他似乎并沒有產生過太深的矛盾,甚至連真正的紅臉爭吵也不曾發生,事物發展總得有個理由,可她始終沒有把這個理由找到。由此,她想起了高默然關于駕車就像睡女人的理論,曾經,她半真半假地問他,外面是不是有了情人,他聽了露出一臉的疑惑,甚至說不屑,還是語文老師呢,怎么連比喻都聽不出來。她心里說,比喻誰不知道?用乙比喻甲,對乙也得熟悉呀,不然如何能想得到。要是他在外面真的有了別的女人,疏遠自己也順理成章。可自己呢?自己并沒有移情別戀呀,咋也不再依戀他看重他了呢?難道這就是所謂的“愛情之痛”“婚姻之癢”,或心理學上稱之為的“倦怠期”?屈指算來,這種狀態已有六年時間了,她心里十分明白,照此下去,他們不可能白頭到老,只是目前兩人都還沒說出“離”這個字罷了。
路夢蕓、高默然的這種狀態,兒子從兩人分室而居中看出了端倪,他向他們詢問,兩人都語焉不詳,就猜出了事情的八九分。也許是想做一番努力,挽回殘破局面,大峰提議了這次旅行。他們聽了兒子的提議,都沒有表現出太大的興趣,她倒是沒有一口回絕,而他卻說公司里的事很多,沒有時間。大峰也沒有強求,只是淡淡地說:“過幾天我就要回學校了,然后就要去大連,以后我們一家人想在一起,就難了。”大峰已和大連的一家私企簽了就業合同,返校進行論文答辯后,大學就畢業了,說好了離校后直接去大連上班。聽了大峰的話,她立即就同意了,他雖然猶豫片刻,也點了頭。
豐田的性能優良,行駛在高等級公路上,就像駿馬奔馳在坦蕩如砥的草原。大峰坐在副駕駛的位置,并不安心坐著,像一只活潑的猴子,一會兒轉過身子給路夢蕓講“王者榮耀”,一會兒面向高默然說NBA,更多的是扯著嗓子唱歌,唱庾澄慶的《情非得已》,唱何鵬、安東陽的《甘心情愿愛著你》,唱蘇勒亞其其格的《收獲愛情》……路夢蕓知道兒子的良苦用心,他想通過“王者榮耀”和NBA,讓旅途不至于過于沉寂,而所唱的歌“難以忘記初次見你,一雙迷人的眼睛,在我腦海里,你的身影揮散不去……”“紅塵中和你相遇相知相許,片片相思把你裝進夢里。愛情的軌跡有過聚散別離,就算再多坎坷不改本意。風雨中和你緊緊相偎相依,歷盡世事滄桑此情不渝……”之類,是想喚起她和高默然對往事的回憶,有點說教的意味,提醒他們應當珍惜知遇和愛情。她覺得大峰此時像一個園丁,在秋風蕭瑟的衰敗與飄零中,還想做一番拯救。這種努力也不是不可能,比如給秋季里的花木上足肥水,精心修剪,等到來年再抽枝萌芽,將會更為茂盛,只是需要較長的時間。也許是大峰的刻意觸動了路夢蕓的心弦,每一句歌詞都像一片綠葉在她心中拂過,以至于眼中有淚花閃動。她不知道高默然是否被歌聲觸動,直觀到的是,他不想被分心,一直專心致志地開車。
從高等級公路上下來時,大峰似乎累了,睡了過去。高默然曾邀請過一些廣播電視臺領導來過幾次阿山,對在此山的旅行還算熟悉,既然是野餐露營,他就沒有順著當地人規劃好的旅游線路走,進山后,選了一條山道,將車開往有山花開放的山谷,在夕陽掛在山尖之時,把車停在了一個地勢較為平坦的山坡上。
在山道行駛時,盡管十分顛簸,但一點也沒有影響到大峰,他一直在酣睡,可是車一停下,他立即就醒了,不帶絲毫從沉睡中醒來的惺忪慵懶,精神飽滿,下車來選了一個背風處,指揮著路夢蕓和高默然安裝露營帳篷等。安頓好,太陽已落入山中,天就要黑了。大峰把烤箱、木炭、鋼筋鍋、應急燈、自熱米飯、鹵制品和放在車載小冰箱里穿好的肉串拿下來,在帳篷旁把烤箱支好,于烤箱里放上木炭,開始生火。這時,過來一個騎馬的牧民,大呼小叫地阻止他們,說山里不準點火。高默然上前解釋,說他們用的是家庭木炭,不起明火,只是做點飯吃,不會有啥事的。野餐時,大峰啟開一瓶酒,父子倆就著鹵制品和羊肉串喝了大半瓶,又吃了點米飯,酒足飯飽后,大峰跑到車里,把自己帶的U盤插進車里,歡快的《風情吉特巴》像泉水跳動一樣播放出來后,去拉父母和他一起跳舞,路夢蕓和高默然都搖手說不會,他就說他來教他們,硬是把他們拉到車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地教起來……在大峰的攛掇下,三人在星空下瘋了一個多小時,路夢蕓說累了,想早點休息。她的話音剛落,高默然就鉆進帳篷里,抱出一個睡袋,準備到車上睡去。大峰卻一把搶過睡袋,說今晚他在車里睡,要好好體驗一下野宿大山的感覺,以后去了大連,這樣的機會就不多了。
路夢蕓和高默然沒有辦法,兩人只好鉆進了帳篷里。幾年沒有睡在一起了,躺下后,她覺得十分別扭,似乎身邊的人不是自己的丈夫,而是一個陌生人。盡管不自在,路夢蕓也沒有生出太多的反感,大峰一路上又說又唱,讓她頗受觸動,已邁入人生五十歲的坎,就算她和高默然不散,也只是一個伴兒,如果能正常過下去,時間也不豐裕了,咋就不能遂了兒子的心愿。產生了這些心思后,她想,如果他現在要對她做些什么,她將不予拒絕。可他卻沒有任何動靜,躺下不久就扯起了鼾。她也曾想著自己主動一下,可他此起彼伏的鼾聲,破壞了她心情,把這個念頭打消了。
路夢蕓的心思重,一夜都沒睡安穩,天顯亮后,她就起來了,鉆出帳篷,到車上看了看大峰,見兒子睡意正濃。兒子并沒有鉆進睡袋中,只是把睡袋隨意地搭在身上,她上前把睡袋給兒子蓋好,走到不遠處的一個高坡上,向四周望去。黎明中的大山,山巒起伏,像橫臥著一條巨龍,最遠的山體還處在一片朦朧之中,東方的天空像是被清掃擦拭過似的,異常潔凈,升起一片紅光,映紅了好大一片天宇。太陽馬上就要升起來了。多年生活在鋼筋水泥架構的生硬之中,很難見到日出的生動,她渴望著紅日東升。她靜靜地望著東方,過了一會兒,東方的山脊上現出一條紅線,眨眼的工夫,那條紅線就變成了紅坨,瞬間,半個太陽就臥在了山尖。她想對著太陽喊上幾聲,還沒等她發出聲來,太陽就躍到了空中,渾圓、奇大、赤紅,像一個大火球。她終于喊出聲來,引得山鳴谷應,她流淚了。旭日東升,蓬勃輝煌,嶄新的世界不容辜負,所有的境遇、心情都應當在朝陽紅霞中受到啟示。
路夢蕓被宏偉的日出震撼了。這時,她的高亢興奮陡然下降,沉默下來,稍待,她突然向著帳篷和車小步跑過去,來到昨晚沒有拆掉的烤箱邊,投入幾塊木炭,引著火,把鋼筋鍋放到烤箱上,倒上半鍋水。等把水燒開后,她喊大峰和高默然起來。高默然起來后,看到她正在烤箱前準備下掛面,一時間有些蒙。在他的印象中,她是不善于也不樂于做飯的,只要他在家,一日三餐都是他來做,他不在家但兒子在家時,她不得不做飯,也是浮皮潦草,啥簡單做啥,要是他和兒子都不在家,她就會拿方便食品來對付。他趕緊跑過去,滿臉愧疚地說:“昨晚喝了點酒,睡死了……我來做,我來做。”她說:“你和兒子洗漱去吧,面條馬上就好。”他似是不解,看了她一眼,也就沒爭,和大峰一起洗漱起來。兩人洗漱完,一鍋面條也就下好了。三人吃了面條,太陽脫離開山頂已有三竿,他們一起動手,拆帳篷、收氣墊、歸物件、拾垃圾,全部收拾清爽后,把車發動著,向著一片草豐花艷的山坡開去。
來到那個山坡上,路夢蕓和大峰都十分興奮,不停地拍照拍視頻。大峰給路夢蕓拍照時,會讓她擺出不同的pose,拍視頻時,又會讓她從遠處走來、向遠處走去、張著雙臂轉圈、拿著絲巾跳躍。其間,大峰還招呼路夢蕓、高默然一起拍合照,或給他們兩人拍,或把三人都框進鏡頭里,拿著自拍桿自拍……母子倆一直歡快地笑著,像是放飛了一群鳥兒,玩得不亦樂乎。間歇時,兩人又靜靜地坐在草地上,把拍的照片和視頻,發抖音發朋友圈。兩個小時后,大峰突然發現,這里的山花并不像傳說中的那樣,漫山遍野花團錦簇,稀少不說,很多都已經凋零,便問高默然是怎么回事。他想了一下,說現在不是賞花的最好季節,在五月下旬或六月上旬,花開得最旺,現在都六月底了,過季了。
正說著,昨晚來阻止他們生火的那個牧民,又騎馬過來了。大峰忙跑過去,問牧民,有沒有比這里花開得更好的地方,牧民聽了連連點頭,順手指了一個方向,說翻過前面的那座山,花開得好。大峰問路怎么走,牧民伸出手臂比畫著,認真地給他們指路。牧民走后,大峰向路夢蕓和高默然提議,到山那邊看花去。她表示支持,他卻面露難色,擔心時間不夠。大峰執意要去,說返回時,他和高默然換著開車,就是晚一點也沒事。
大峰高考后,考了駕照,每個假期都把高默然公司的一輛車開回自家用。說來,也有四年的駕齡了。
二比一,高默然只好同意,三人上車,順著牧民指給的路,向前面那座山開去。半個小時后,車行到了一個大下坡處,看到坡對面果然五彩繽紛,盡管影影綽綽,也判斷得出那里定然是一片爛漫山花。大峰高興地呼喊起來。而在這時,高默然看到山的深處卷起了烏云,疑惑起來:“會不會下雨呀?”大峰從車窗看了看天,見頭頂上艷陽高照,應高默然道:“這么大的太陽,咋會下雨呢。”高默然說:“山里可說不準,天說變就變。”大峰說:“我們有車在,就是下雨也不怕。”
高默然開車繼續前行。路是下坡路,不平整,很多地方還潛伏著一些土坑,高默然開得十分小心。車快至半坡時,三人都聽到很響的水流聲。山深處的烏云,此時已把整座大山覆蓋住了,正在向他們頭頂上移動,毫無疑問,山深處正在下雨。又行了一段路,在坡底前橫起一條小河,高默然趕緊把車停下,剛才聽到的水流聲,就是因為山雨導致小河漲水發出的喧嘩。水下情況不明,也許存在危險,高默然決定去查看一下。大峰也下了車,兩人一起向坡底小河走去。
沒多大一會兒,高默然和大峰就回來了。高默然對路夢蕓說:“前面是一個過水山路,也許平時從路上流過的也就薄薄一層水,現在小河漲水了,不知道水下是什么情況,絕對不能再往前走了。”是大峰堅持要過來的,現在遇到了情況,他低著頭不說話,像是在內心做著檢討。路夢云發現,烏云已壓在了頭頂,隨時都有可能下雨,便對高默然說:“那就別猶豫了,趕緊回吧。”山路狹窄,前方沒有調頭的地方,高默然聽了,開始倒車,誰知車一啟動,就熄了火,他趕緊把車踩死,把手剎拉上。他長出了一口氣后,再次倒車,同上次一樣,油門還沒有完全松開,車又熄火了。
半坡起步,并且是倒車起步!路夢蕓突然想起了駕考。
兩次沒能把車開動,高默然不由得緊張起來。路夢蕓看到他手足無措,突然想起,高默然并沒有經過嚴格的駕校練習,他的駕照是托關系花錢搞到手的,在平坦的公路上行駛早就嫻熟,而在關鍵的時候,像眼前的半坡起步就露了怯。她心里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不能催促,越催也許情況越糟,她就沒有言聲,讓高默然自己駕駛。他又試了幾次,均是車剛啟動就熄火,他不由惱怒地狠狠拍打了一下方向盤。
開始下雨。路夢蕓從車窗看了一下天,烏云越積越厚,看來這雨不會小,前面小河的水又漲了一些,已有了咆哮之勢,響聲越來越大。大雨下下來后,會發生什么?山體滑坡、道路沖斷、車被顛覆……她不敢想下去,看到高默然無法把車開動,路夢蕓說:“要不讓大峰試試。”
路夢蕓信任駕校,篤信苦練出的技術。
高默然聽了,回頭看了一眼路夢蕓,然后把目光投向大峰。被人信任讓大峰興奮,聽了她的話,立即下到車下,跑到了車的另一側,高默然只好換到副駕駛座位上。大峰上了車,握起拳頭在眼前猛地晃了一下,自己給自己打氣,開始起步。誰知,車啟動后,非但沒有向后倒駛,反而向前方滑躥了出去,大峰一時慌亂,緊張地喊叫起來,眼看著車就要栽到小河里去了,才回過神來,一腳把車剎住,高默然也順手把手剎拉上。車停穩后,大峰的身體一直在戰栗。
雨大了起來,如瓢潑一般。必須抓緊時間離開這里,要不然,就算不發生意外,也一定會被困在山里。
“讓我試試吧。”這時,路夢蕓說。
高默然和大峰聽了,都回過頭來看她,眼神里滿是不信任——你還沒有拿上駕照,沒有正式駕過一天車……
“我剛考過科目二,通過了半坡起步。”
高默然和大峰都沒有說話。路夢蕓下了車,順眼看了一下山坡,她估計,這個坡傾斜有30度,比她考試時的坡度還大。她把大峰換下來,坐到駕駛座位上。大雨如注,車離小河也就幾米遠了,路夢蕓正準備發動車時,突然對高默然和大峰說:“你們兩個下去。”兩人聽了這話,一時沒有回過味來,但很快就明白過來,她是在想,如果車真栽到了河里,可以確保他倆無虞。兩人不干。高默然說:“我們兩個男人……要是真的……”
“滾下去——”路夢蕓發起火來,隨即又軟著聲說:“你們在車上,我會緊張的。”
兩人只好下車,冒雨站在了山坡的側面。他們下車后,車立即被發動著了,卻遲遲不見動靜,大約十幾分鐘后,見車還是沒有動靜,高默然準備把路夢蕓從車上叫下來。他的想法是,車就扔在這山坡上,他們徒步離開這里,找一戶牧民的氈房去避雨,等雨停了再說。他剛邁開步,車身晃動了起來。
其實,這期間路夢蕓的腦子在飛速旋轉,她在默習半坡起步的要領。那位退伍軍人出身的教練所說的話全都刻在了她腦子里:半坡起步有幾個關鍵點必須連貫操作:點火——踩離合器——掛擋——松離合器,使車處于半聯動狀態——快速松掉手剎,解除制動——加油,保證足夠的動力——行進數米,完全松掉離合器,使車正常行進。在這個過程中,每一個環節都很重要,不得有絲毫差錯。離合器松到半聯動點,就不能再松了,因為車是制動著的,再松,發動機就會熄火。已是半聯動狀態,且松開了手剎,這時一定要給足油,因為車處在半坡,阻力增大,沒有足夠的油促進動力增加,前面所做的一切都是無用功。
路夢蕓開始駕駛。
教練還說了,要是對半坡起步的要領記不住,可以拋開理論,通俗地理解,那就是慢慢地松離合器,把離合器松到半聯動的極點,讓車的全身都強烈地抖動起來,使車像一匹急于出征的暴躁的戰馬時,然后松手剎給油門。
車成功起步,在山坡上倒行。
車倒到了剛才停車的地方。
車倒到了坡的三分之一處。
車倒到了山坡的中央。
車繼續倒行,終于爬到了坡頂。
高默然和大峰一直盯著車跟行,當車在坡頂停穩,他們向車跑來,路夢蕓打開車門,一頭扎進了高默然的懷里……
回到烏城時,已是凌晨一點多了,三人都十分疲憊。路夢蕓洗了澡后,進到臥室里,用電吹風把頭發吹干后,扯開被子,準備熄燈躺下時,高默然推開門,進到了他久違的這間臥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