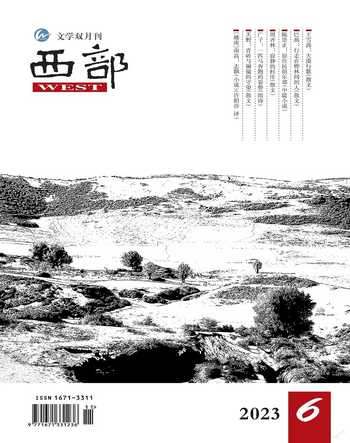他寫詩的手多么鎮定(組詩)
周舟
羽毛在飄
羽毛的每一次離開
都會有一種沉醉
仿佛夜晚對夢境的信任
——一個任性的詞語
身體的邊緣
鑲著有弧度的金邊
林中空地
為了證明林中有一塊地是空的
樹木后退了一大截
中間又多出一塊石頭
樹木這時幾乎不明白自己
是杉樹槐樹抑或紅松
他們熱愛的影子與影子
重重疊疊
鳥在拉一張大網
辨不清是什么鳥
鳥只把聲音落下來
但空地上什么也沒有
整整一個下午
太陽在森林頭頂行走
地上卻沒有什么變化
而林中空地的石頭上
已多出一副安靜的棋局
舒家壩一夜
黃昏時分我們
才到舒家壩
你躺在那兒
讓我們感覺黃昏
就這樣來臨
好幾次來看過你
只有這一次讓人覺得多余
坐下來不對
站著
還是不對
一只手握著一只
越來越涼的茶杯
一只手
把香煙卡在手指間
像是盛著時間的盒子壞了
手一抖動
就掉下你的聲音
殯儀館
沒有暮色也下沉
事物下沉
只顯現灰蒙蒙脊背的生活下沉
此刻是早晨
早晨下沉
這里不只我一個人
但我一個人盯著青煙自高高的煙囪
鳥伸展羽毛那樣往上飛
我很聽話
站在山上
九點鐘的太陽不升起來
哦,殯儀館的空曠照著我和我們
蜘蛛
墻角的那團網狀物什
因為并沒有蜘蛛
還不能算是蛛網
也許是一些不愿離開的塵埃
相愛著
當我這樣想
馬上意識到
我在這個房間已經住了
快二十年
此刻的我就位于它的右下方
但此刻的寂靜
正把某個關節捏得咔吧響
像是持續了一會兒
我看見光的粉塵飄浮著
又在我身上歇下來
于是我猛地戰栗了一下
可我的戰栗似乎有著
騰挪的技巧
就在我扭頭去看的時候
發現一只蜘蛛恍惚之間
已經爬到了蛛網上
洗杯子
洗到最深處
杯子可以只剩下玻璃
一遍一遍
玻璃也可以消逝
只有水
越來越具體
伸一下水的脖頸
并看不見水的腳趾
看見的時候
一只鳥
在左手與右手的枝條間
跳過來又跳過去
死亡的體積
他們在侍弄一只盒子
專注緊張
裊裊香煙繞過手指
接著繞過眾人的面孔
很多事開始模糊又開始清晰
清晰了又變得模糊
直到盒子與土地融為一體
這些繩子綰在一起的煙縷
還不解開
還不散去
像有人反復將手
填進火焰里去
這時死亡才仿佛漸漸形成
讓包括一排楊樹
一朵云一只落在樹上的鳥
和一片空曠地帶在內的所有事物
秘密集結
像是死亡有龐大的體積
早間日記
摸黑吞下一粒藥片
踅身再次躺下時
竟有點恍惚
新的一日
是否已經將藥片吞服
多年了
這些耀眼的顆粒狀物體
在漆黑的胃里
仿佛一直拒絕融化
作為一方浩渺的星空
它既與我疏離
又與我明顯對峙
凈土寺
從寺院出來的時候
香煙裊裊
他敲鐘,只把手臂抬起
他叩頭,頭尚未著地
香煙裊裊
寺院的寂靜尚未到來
我離開
只是給寂靜讓開一條甬道
在醫院門診大廳
在熙攘的醫院門診大廳
一個埋頭寫詩的人看過去有點孤獨
他在手機屏幕上開著這個世界
從未曾見過的處方
大廳的人不斷增加又不斷消失
尋找著窗口,房間,白色床單和藥片
醫院的光線會不會
把他的臉一直涂成白色的
他寫詩的手多么鎮定
看上去就像一只劇毒蜘蛛
孤獨的光
昨天晚上
他和自己一生里所有的事件在一起
他驚異所有的事件一件一件
都是磚塊
有人命令他用它們
蓋一間房子砌很大的窗
把月亮也砌進來
可是他的手里還有一件事
像是用盡所有事件之后剩下的一件事
他不知該把它擱在哪兒
試試所有辦法
最終他把它隱藏
不留線索
蓋好的房子一下子空起來
桌子上落滿灰塵
看不見的月亮用低音說話
聽不清它在說什么
但他身上有一種孤獨的光
一瞥
從殯儀館出來
能看得見
背后的天空
正被什么覆蓋
死亡待在房子里面
像盒子套著盒子
死亡在盒子里
講一個死亡故事
這時候的聲音
是死亡給的
他帶好死亡分給他的那一點點
站在院子里
有點茫然
前方的天空
正沒入黃昏
但一扇門
還卡在那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