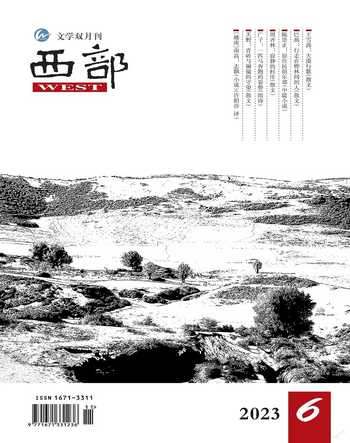青磚與銅鏡的守望(散文)
天野
怎么說(shuō)呢,登長(zhǎng)城不是件容易的事。
每邁出一步,腳下所踩青磚都是有名字的。名字可不是一個(gè)符號(hào)那么簡(jiǎn)單,那是一個(gè)個(gè)活生生的人。這些人里有普通的士兵,也有將領(lǐng)。
每一批修筑長(zhǎng)城士兵的名字都寫(xiě)在了冊(cè)頁(yè)上,也刻在即將進(jìn)入磚窯的磚坯上。不知有多少將士的腳印留在了長(zhǎng)城上。真是沒(méi)法說(shuō)清楚的事。要是哪個(gè)人,拍著腦門(mén)和胸脯,像相聲演員在臺(tái)上報(bào)菜名一樣,說(shuō)得門(mén)兒清,倒覺(jué)得可疑了。
青磚是有記憶的。
一九八一年的暮春時(shí)節(jié),父親陪同祖父回了趟酒泉。酒泉城里有六十多公里的明代長(zhǎng)城。祖父是喜歡舊物的人。沒(méi)能找到要尋的親戚。在昏暗簡(jiǎn)陋的招待所里,祖父以他慣常的慢動(dòng)作,卷了一支莫合煙,點(diǎn)著抽了一口,又夾在右手食指與中指的指縫里,青煙擋不住他的目光,他看著街道上的行人,向父親提議去看長(zhǎng)城。
父親嗯了一聲。
祖父跟著父親走出招待所。公交車(chē)加步行,在晌午時(shí)分到了長(zhǎng)城。父親想給祖父在長(zhǎng)城前拍張照片留作紀(jì)念,可那時(shí)候,照相須去照相館。待有擺攤照相的人,那都是十來(lái)年以后的事情了。
祖父清瘦高挑,目光悲慈。我得知祖父回來(lái)后,風(fēng)一樣躥進(jìn)他的屋里,他放下手里的搪瓷茶缸,慢悠悠地說(shuō)起那不成樣子的土墻。
我才知道,不是所有的長(zhǎng)城都是青磚修筑的。說(shuō)實(shí)話,心里多少有些失落,甚至覺(jué)得這個(gè)消息不實(shí),懷疑祖父看到的并非真正的長(zhǎng)城,而是一座故城的舊址。
世界上的事情很奇妙,有的事情很早就為人所知了,而有的事情至死也無(wú)人知曉。這是再正常不過(guò)的事情,沒(méi)有哪一個(gè)人能窮盡天下所有的事情,包括神仙。
是的,只有在有黃土的地方才有可能燒制青磚,沙質(zhì)土無(wú)法完成窯溫一千度裂變的光榮使命。這是一次重生。如此看來(lái),重生是需要條件的。
我第一次面對(duì)長(zhǎng)城青磚,是祖父見(jiàn)到長(zhǎng)城后的第十二年。我像熟悉臉上的雀斑一樣熟悉這個(gè)日子。
九月十日,空氣里擠滿果香。我與新婚的丈夫從杭州坐綠皮火車(chē)抵達(dá)北京。綠皮火車(chē)九號(hào)車(chē)廂的一號(hào)座位是靠窗的位置。半開(kāi)的窗戶,視野虛晃飛馳,我一次次想象登臨長(zhǎng)城的心情。
我們坐車(chē)到了八達(dá)嶺長(zhǎng)城。
心情這種東西真是不好說(shuō),在滾燙的人流中推搡擠壓后,所有期許的美好瞬間被瓦解撕碎。
我胸腔里翻滾一股難以抑制的氣流,大有將我就地撂倒的圖謀。臉色煞白的我,嚇到了丈夫。一臉焦急的他,要我就地休息。粗大的手?jǐn)v扶我在就近冷飲攤前的凳子上坐下。
姑娘,來(lái)瓶汽水吧,瞧你這臉色,還沒(méi)登長(zhǎng)城呢,就這樣了,可不敢急著上去。那個(gè)大眼睛、短發(fā)的中年女人,從冰柜里拿出一瓶橘色汽水。
喝了汽水,又點(diǎn)燃了我登長(zhǎng)城的信心。在一個(gè)個(gè)背影中,我看不清長(zhǎng)城的模樣,眼前是一塊塊寬窄不一、高低不一的擋板。
裹在風(fēng)里的香水味、汗味、玉米味、草木味,還有青磚與黏土的味道,爭(zhēng)先恐后擠進(jìn)鼻孔。我無(wú)意辨析更多的味道,只是覺(jué)得這青磚味里有一種氣息,似乎很久之前遇到過(guò),如今又在這里重逢了。
太陽(yáng)曬爆了我的皮膚,這是之前未曾料到的事。按說(shuō)入秋后,陽(yáng)光就友好溫和了,哪里想,偏偏刀片似的,似是一層層揭去皮膚,這疼痛令人無(wú)處躲藏。
我扶著青磚繼續(xù)向上走。
丈夫愧疚地說(shuō),太粗心了,應(yīng)該戴頂帽子,或者帶把傘。過(guò)去這兩樣?xùn)|西并非我日常生活的標(biāo)配,甚至覺(jué)得多余。
我說(shuō)沒(méi)事,要不了命,回去緩幾天就好了。
我趴在城墻上,端詳著青磚砌成的長(zhǎng)城,青磚從齊整的墻上走下來(lái),向著東面集結(jié)而去。再看,那山谷低處,七八列士兵隊(duì)伍向上而來(lái),他們身穿布衣,傳遞青磚,徒手接過(guò)來(lái),再送過(guò)去。
初夏的風(fēng)拉長(zhǎng)了我的視線,清楚地看到士兵黑紅的臉,有的是更濃一層的黝黑。手也皴裂了,掌心一道道深淺不一的裂紋里是黑褐色的泥。若再細(xì)看,那個(gè)闊面士兵的胡茬里都據(jù)守著塵土。
他們那么年輕,想來(lái)也不過(guò)十七八的年紀(jì),青澀稚嫩得很。在長(zhǎng)時(shí)間的修筑過(guò)程中,他們不止一次望著夜空,想家,想他們的父母和姊妹兄弟們。想來(lái)有的也娶了妻,有了尚不會(huì)叫爸爸的幼兒。
我望著他們的面龐,不是經(jīng)年累月從時(shí)光里走來(lái)的人,而是巷子里和村子里走來(lái)的人,也就那么一瞬間,眼窩發(fā)熱,淚珠落在城垛的青磚上,以萬(wàn)馬奔騰的速度散去。淚水是咸的,汗水也是咸的。我沒(méi)有被別人撂倒,卻被這看不見(jiàn)的咸扎扎實(shí)實(shí)撂翻在地。
一個(gè)女人,不管你多大,沒(méi)有誰(shuí)要求你必須成為好漢。那是男人們的事情。好漢,不是評(píng)判女人的標(biāo)準(zhǔn)。
但我在右腳趾磨出血泡后,咬牙堅(jiān)持,一點(diǎn)點(diǎn)挪動(dòng)到寫(xiě)著“不到長(zhǎng)城非好漢”的牌子前,禁不住淚奔,一個(gè)胸肌發(fā)達(dá)的男人蹲下來(lái),拍了拍我的右肩說(shuō),不哭。
我想從嘴角擠出一縷笑容,可吝嗇的笑容始終不肯出來(lái)感謝這個(gè)給我鼓勵(lì)的好心人。
丈夫右手搭在我的肩頭,頭靠攏過(guò)來(lái),蜜月登長(zhǎng)城的照片,在寶麗來(lái)一次成像相機(jī)的咔嚓聲中跳出來(lái),穿馬甲的中年男人很快把照片交到我的手中。背景就是那塊已經(jīng)疲憊得不成樣子的牌子。
風(fēng)撩起我額頭的劉海,腦門(mén)亮閃閃,恍惚間覺(jué)得那不是我的腦袋,而是一面鏡子,發(fā)亮的鏡子,照出我的臉,以及臉上的疲憊、淚痕和興奮。
風(fēng)的肌膚上有可追溯的密碼。我的解碼從一枚銅鏡開(kāi)始。
提到鏡子,真要說(shuō)一下一九九八年六月在嘉峪關(guān)新城鄉(xiāng)長(zhǎng)城村墓葬出土的魏晉“位至三公”銅鏡,這銅鏡體量不大,直徑9厘米,厚0.2厘米。背面沒(méi)有幾何圖案,或者花卉及人物圖案,真是素凈。許多時(shí)候,你會(huì)發(fā)現(xiàn),越是素凈的器物,越能啟動(dòng)想象的鏈條。
我站在展柜前,銅鏡身影孤零零的樣子,喚醒了我的思鄉(xiāng)之情。外出三月有余,返回的途中,猶豫再三,我在嘉峪關(guān)下了火車(chē)。去干什么呢?起初沒(méi)有清晰的目標(biāo),只是想隨意走走,畢竟這地方?jīng)]有來(lái)過(guò)。
嘉峪關(guān)這個(gè)名字,無(wú)論從歷史層面還是文化層面去講,它都像一枚紐扣,系在大地的門(mén)襟上,不管你怎么走,總有一次要經(jīng)過(guò)這里。何況我這個(gè)從新疆來(lái)的人,出入都需從這里經(jīng)過(guò)。
這座城市與其他北方城市幾乎沒(méi)有什么區(qū)別,穿行在街道上,從不虧待嘴巴的我,打聽(tīng)著當(dāng)?shù)氐拿〕浴脑绯块_(kāi)始,燴麻食、搓魚(yú)面、油爆駝峰、燒殼子、絲路駝?wù)啤⑴谡堂妗擦岁惔椎尼勂ぃ粯訕釉谘例X下碾碎。在血液里我再次與它們相會(huì)。熟悉的不僅是眼神,還有共同的美食、文化。別浪費(fèi)時(shí)間,去看看長(zhǎng)城,看看銅鏡,看看博物館里的寶貝。
我堅(jiān)信,腳印就是信使。
年輕的解說(shuō)員露出職業(yè)微笑,為游客講解:中國(guó)新疆、甘肅、青藏高原及其邊緣地帶、北方長(zhǎng)城地帶等區(qū)域出土的銅鏡則多有帶柄的草原元素動(dòng)物紋飾。總體來(lái)看,幾何紋銅鏡和素鏡是中國(guó)早期銅鏡的主流。我對(duì)他如此不帶感情的描述很不滿意,懷疑一次次敲擊心房。我選擇了沉默,藍(lán)色中加了糖的沉默,以至于在整個(gè)午餐時(shí)間,我咀嚼青菜的聲音勝過(guò)鍘刀砍下頭顱的聲音。
是誰(shuí)?那個(gè)按下鍘刀的人是誰(shuí)?那個(gè)被砍下頭顱的人是誰(shuí)?難道真是那個(gè)沒(méi)有按工期完成修筑長(zhǎng)城的年輕士兵?我的眼里,他不過(guò)是一個(gè)少年,十六歲或者十七歲,也許會(huì)更小一點(diǎn)。暮秋的塞外,寒氣帶著刺,穿透的不僅是枯黃的葉片,也切碎了這些勞碌了半年,甚至更長(zhǎng)年月的稚嫩軀體。
我在嘉峪關(guān)長(zhǎng)城博物館里徘徊,偌大的展廳,我和幾個(gè)陌生人游蕩漂移在一件件文物簡(jiǎn)短奧秘的文字里。我試圖揭穿不為人知的秘密,卻是超越宇宙的妄想。在那一刻,我靠近箭鏃陳列的柜子,握住那枚銹跡斑斑的箭鏃,刺向我的胸膛。我甘愿流干軀體的血,只為縫合一塊長(zhǎng)城青磚的裂縫。讓年輕的士兵早日回家,與銅鏡前的親人團(tuán)聚。
我狹隘地以為,這樣會(huì)讓我的子嗣們?cè)诙嗄旰蟮纳钋铮唤?jīng)意間路過(guò)這里時(shí),聽(tīng)從長(zhǎng)城青磚的感召,進(jìn)入深邃幽暗的另一端,看到最初修筑長(zhǎng)城時(shí),年輕士兵青春的模樣。
站在青磚城墻前的我,似已被時(shí)光侵蝕。慌張是有的,不過(guò)壓制在血管與怦怦跳的心里。我并沒(méi)有漠視過(guò),從來(lái)都沒(méi)有。我小心、乖巧地注視銅鏡,亦如我注視長(zhǎng)城的青磚一樣。我坦誠(chéng)面對(duì)它,正視它的殘缺、暗淡、凋敝、頹廢與不安。亦如面對(duì)自己出生到現(xiàn)在的悲傷、怯懦、恐懼、無(wú)知和期待一樣。
我從沒(méi)有像現(xiàn)在這樣寧?kù)o忠實(shí)地面對(duì)自己,每一塊青磚也是一面銅鏡,清晰照出我清醒的心緒,不再畏懼那可怕的嘲笑、蔑視、焦慮和謊言。我接受一切,亦如長(zhǎng)城接受坍塌、潰敗、侵蝕、冷落與消亡,銅鏡接受暗淡、銹蝕、遺棄與忘記。我與它們有一樣的終極宿命,只是它們演化成一種精神,無(wú)色有聲地進(jìn)入人們的血液里,任何溢美華麗的詞對(duì)它們都不過(guò)分。我只是想,我這個(gè)比塵埃都微小的人,多么渴望在某年某月的一天,在空氣里風(fēng)馳電掣般撲向一個(gè)附著物的時(shí)候,會(huì)有幸落在青磚上,落在任何一處長(zhǎng)城的青磚上或者腐朽的銅鏡上,那該是多么幸福的事。
我沒(méi)有忘記自己是一個(gè)女人,是一個(gè)女兒,是一個(gè)妻子,是一個(gè)母親,也不能忘記,我是一個(gè)姐姐。妹妹小我四歲,屬虎,兇猛不代表她真實(shí)的表達(dá),我甘愿在她遍體鱗傷后守護(hù)在她身邊。
我那矮小戴著流蘇耳環(huán)的妹妹喜歡照鏡子,隨身帶著鏡子,她沒(méi)有銅鏡,是一枚小小的普通鏡子。看著她照鏡子的模樣,仿佛回到我們年少時(shí)手拉手買(mǎi)冰棍的幸福時(shí)光。她是一名邊疆衛(wèi)士的女兒,她的剛烈、勇敢、曠達(dá)遺傳自那個(gè)在邊境線上馳騁守邊的父親。
我想送妹妹一枚銅鏡。何止是妹妹,那些千百年以來(lái),家中有男子奔赴邊疆的女人們都渴望一塊銅鏡,銅鏡里有親人熟悉親切的面容。一次次月缺月又圓時(shí),她們不會(huì)孤單寂寞。
在慕田峪,修葺一新的長(zhǎng)城,機(jī)械化生產(chǎn)出來(lái)的青磚依然保留著原來(lái)的模樣,可斷然失去了燒制工匠的體溫,也沒(méi)有留下一枚工匠的指紋。
我背棄了對(duì)同伴的承諾,逃兵似的,偷偷向右轉(zhuǎn),急切地買(mǎi)了一張纜車(chē)票,向六號(hào)垛口的方向跑去。
座椅式纜車(chē),樸素靜溫的椅子,懸浮在空中,零距離接觸樹(shù)木,分外歡喜。俯視山谷里的側(cè)柏、紫椴、蒙古櫟、糠椴、胡桃楸、葛藤、小葉白蠟、山楊、油松,以及林間的酸棗和荊條。
我將遠(yuǎn)山與纜繩收納起來(lái),輕放進(jìn)我的口袋里。
一方垛口就那么大,相機(jī)鎖定的畫(huà)面也那么大。用物理的概念來(lái)描述沒(méi)有意義。當(dāng)年駐守這里的將士們熟悉了長(zhǎng)城內(nèi)外深深淺淺的景致。
他們中,戚繼光是最為人熟知的一位將領(lǐng)。明隆慶二年(1568)夏,從南方快馬飛馳來(lái)的他,是薊鎮(zhèn)總兵,帶領(lǐng)兵卒民夫,東起山海關(guān)、西到居庸關(guān),完善了長(zhǎng)城防御設(shè)施。
這個(gè)初夏,我從西北以北的地方再次登上慕田峪長(zhǎng)城,立于樓臺(tái)里,目光撫摸殘缺的青磚,它似乎早忘記了傷痛,那藏著秘密的豁口,已經(jīng)成為傷口愈合后的一塊印記。向我訴說(shuō)曾經(jīng)在這里響起的震耳的炮聲、佩刀出鞘的聲音、鼓手敲擊軍鼓的聲音,以及遠(yuǎn)處古剎里傳出的雄渾綿實(shí)的鐘聲。
我必須記錄下此時(shí)正欲搭乘陽(yáng)光的羽翼向西而行的云朵,它不會(huì)偏離航向,在嘉峪關(guān)以西,還有眾多的烽燧、青磚砌成的城墻和銹跡斑斑的銅鏡。它們與我腳下的這段長(zhǎng)城血脈相連,都在扼守邊防。
誰(shuí)能告訴我長(zhǎng)城青磚的數(shù)量,誰(shuí)又能告訴我將士們親人手里有多少面閃著光芒的銅鏡。這樣無(wú)解的追問(wèn),一次次令我感傷,虛無(wú)的想象倒是綿密悠長(zhǎng)。
一只松鼠,從樓臺(tái)一角跳到椴樹(shù)枝上,以報(bào)信者的身份告訴我,每一塊長(zhǎng)城的青磚都是一枚圖章,不是蓋在北方遼闊的山川,是蓋在修筑者妻子和親人的心上。
我也是丈夫的妻子,我也會(huì)跟他們的妻子一樣,心中的夙愿是登上長(zhǎng)城,不是看冒著寒光的劍戟炮槍,是想確認(rèn)那個(gè)刻有親人名字的青磚,以及墻縫間編織井然的蛛網(wǎng)。
丟開(kāi)時(shí)間的鞭子,我和更多的人,走向長(zhǎng)城深處,那里你我不再孤獨(dú)。這里有青磚,有銅鏡,也有安撫彼此的狂風(fēng)、星辰和熟悉的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