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圈”的倫理困境及其正向引導
武夢美 連冬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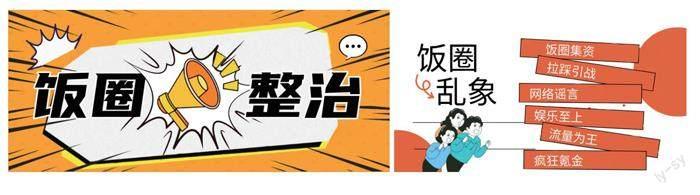
摘? 要:“飯圈”作為組織化了的追星群體,從偶像價值引領功能到青少年粉絲的自我價值定位以及群體間的交往都面臨著亟需解決的倫理困境。“飯圈”倫理困境的出現有其根本原因、外部原因和內部原因,化解“飯圈”倫理困境必須強化“飯圈”的思想道德建設,但不能將措施僅停留在倫理框架內,必須堅持鐵腕治理與教育引導相照應,“堵與疏”相結合的基本路向。
關鍵詞:“飯圈”文化;青少年;倫理問題;道德建設
“飯圈”是當代青少年追星的主要場域[1]。近年來,“飯圈”群體性亂象在資本邏輯主導、“娛樂至上”理念的宰制以及青年群體自身薄弱問題的催化下層出不窮。因偶像經濟與網絡空間的飛速拓展,“飯圈”將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青少年納入以偶像為中心的單一文化圈層中,使“飯圈”面臨多種倫理問題。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通過演講、座談等方式與青年頻頻互動,對當代中國青年寄予了殷切期望,并在二十大報告中再次提到“全黨要把青年工作作為戰略性工作來抓”[2]。因此,審思“飯圈”倫理困境的現狀,剖析其生成的主要原因,并進而找到化解倫理困境的路徑,對青少年的未來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是培育社會主義接班人的應然路徑。
一、“飯圈”倫理問題的現實表現
(一)交換邏輯下流量偶像的自我異化傾向
馬克思認為商品是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統一體。資本生產的直接目的不在于為生產者生產使用價值,而在于商品的交換價值。交換邏輯是“飯圈”資本在片面、過度地追求交換價值過程中造成的交換概念、交換形式的泛化,資本的無序擴張將“飯圈”置于交換邏輯的規制下。
人的本質是勞動。人在勞動中表現出自由自覺性、主動創造性和自我意識性[3]。在當下的社會條件下,藝術創作過程比其他任何工業生產過程都能更高程度地確證和展現人作為“人”的個性與特點,而交換邏輯的泛化卻使得從事創作的主體乃至這一活動本身的異化傾向逐漸顯現,這一問題在當代人精神產品的來源從文藝界供給向娛樂圈供給的轉變中得以印證:流量明星的批量生產證明了展現人本質力量的文藝創作正畸變為娛樂工業流水線式的生產模式,尤其是“流量”這一概念的引入,意味著偶像作為人的本質異化為了可量化的、直觀的數據呈現,“打榜”機制的出現更象征著偶像“商品”屬性的日益凸顯。為了贏得更多的“流量”以便在“榜單”中脫穎而出,從而抬高自身的商業價值,流量明星不得不想方設法獲得曝光度以奪取觀眾注意力。由此有了“吃貨人設”“學霸人設”等與藝術價值相去甚遠的表現形式,而且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交換價值,將利潤抬高到極限,流量明星不得不豐滿自身的“人設”以滿足觀眾快節奏的心理變化,甚至不惜用整容、賣慘等方式來維持觀眾的喜愛,其最終結果是與真正的自我徹底背離。在交換邏輯的膨脹中,流量明星用“人設”綁架自己,將自身及其作品作為滿足欲望的手段,在矮化藝術價值的同時否定自己作為人的價值,造成文藝市場“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二)情感依賴中“飯圈”青少年的身份建構困境
“飯圈”對偶像的情感依賴首先基于認同感。“飯圈”粉絲大多數為處于學齡期的青少年,獲得認同與圈層支持的需要同心理不成熟、社會經驗不足的矛盾是這一時期青少年所面臨的現實,所以當青少年被偶像的行為、特質所打動時,就極易產生對偶像的迷戀進而形成情感依賴。
“飯圈”極度推崇盲目崇拜。合理追星無可厚非,追星是自身欲望的投射,從這一角度來看,理智追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對明星的情感化作自身動力,從而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但當個體追星行為演變成“飯圈”的群體狂歡時,結果卻大相徑庭。追星被粉絲視作個性的表達與釋放,但極度狂熱的追星行為最終造成的是個性的磨滅與自我的消解。在“飯圈”這樣一種宗教式的崇拜下,青少年難以形成對自身真正的身份認知與認同。“飯圈”以對偶像的忠誠來維系這個龐大的網絡組織,卻意外的具有穩定性,主要原因在于單個的粉絲因喜愛聚集成為了“圈”,正是因圈層的出現,個人聚集成了群體,個人的意識在群體意識的渲染與裹挾下逐漸被同化,并使得圈層逐漸封閉,形成“飯圈”所獨有的特殊圈層文化。身處于封閉的“飯圈”文化中的個體,長期接受來自“粉頭”(“飯圈”中的意見領袖)的信息及情感灌輸,便會日漸喪失自我反思、自我思考的能力,并最終造成自我意識的消解,致使青少年在向“社會人”轉變的關鍵時期,無法形成對自身價值、目標理想等形成有效的認知,比如在流量偶像的天價片酬影響下,青少年極易產生不勞而獲的思想。據2021年新華網調查數據顯示的“95后”最向往的新興職業中,網紅主播行業拔得頭籌,其次是影視配音行業,并且在這些調查對象中超過半數的人認為“顏值”大于能力。可見,“飯圈”文化對青少年的自我理想的確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從而使“飯圈”青少年面臨一個身份建構的困境。
(三)互動框架下群體的道德沖突危機
在過去偶像與粉絲之間的交流,往往是偶像對粉絲單向的文化產品輸送,除了線下之外的空間中偶像難以得到粉絲的及時反饋,而信息技術的更迭使得偶像與粉絲、粉絲與粉絲之間的交往更加便捷,從而使得溝通形式變為一種雙向互動,而在這樣一種互動框架下也極易出現不同“飯圈”之間、偶像與粉絲之間的道德沖突。
一方面,“群體極化”行為在“飯圈”時有發生。網絡罵戰是“飯圈”常見的非理性行為。在網絡空間中,不同“飯圈”各自為“主”,偶像之間的資源爭奪與競爭激化了不同“飯圈”之間的矛盾對立,加之網絡的虛擬性和個人身份的隱匿性,使得“飯圈”群體的活動更加肆無忌憚。為爭奪資源而出現的抹黑、造謠等事件層出不窮,一旦自家偶像遭遇這種情況,借助群體優勢,粉絲便會群起攻之,為維護偶像的形象進行辯護,甚至上升到網絡暴力、人肉搜索等侵權行為。另外,因“飯圈”是一個封閉的圈層,粉絲長期接受的信息是對偶像的贊美,以至在偶像失德違法行為出現時,“飯圈”的第一選擇是將道德與法律拋諸腦后,為偶像作辯護,維護偶像的形象成為了“飯圈”的最高法則,此時客觀發表評論的普通網民也會成為“飯圈”的攻擊對象。“飯圈”非理性的群體行為,對網絡空間的公共性與平等性造成沖擊,在群體的沖突中給現實的人們造成了道德選擇的困惑。
另一方面,流量偶像對“人設”的接受意味著其讓渡了行使自由人格與暴露真實自我的權力。實質上,“飯圈”粉絲所鐘愛的是資本打造的、照應了粉絲欲望的虛擬“人設”。偶像作為“人設”的物質載體,被“飯圈”粉絲投注了對“人設”的全部熱愛。在媒介信息高度發達的當代社會中,偶像的私人行程、情感生活、家庭瑣事成為信息賣點,跟車、偷拍等侵權行為成為了“飯圈”粉絲窺探偶像滿足好奇心的常態,偶像被全然暴露在“飯圈”粉絲的“監視”之下。此外,當“飯圈”粉絲發現偶像“人設”與其現實狀態不相符時,出于失望產生的抱怨在網絡輿論的發酵下會上升到對偶像嚴厲的譴責,甚至是對其人格的完全貶損,進而形成對偶像的全然否定,此時的輿論越過對偶像的客觀討論之維,演化為群體審視下的語言暴力,對偶像產生極大的精神壓力。據《2022國民抑郁癥藍皮書》中顯示,文化服務行業已成為抑郁癥的高發職業之一,這表明即使是受粉絲喜愛的偶像,也難以避免地陷入到了沖突危機中。
二、“飯圈”倫理問題的歸因分析
(一)催生:資本邏輯為軸心的偶像經濟運轉秩序
資本邏輯主導的偶像經濟是對“飯圈”青少年以及偶像作為“人”的主體地位的挑戰。偶像經濟是架構在偶像與粉絲互動關系上的一種創收性經濟活動[4],作為偶像經濟的產物,“‘飯圈的本質邏輯是資本操縱的邏輯”[5]。“飯圈”既是資本利用抬高偶像商業價值的工具,又是資本為偶像經濟瞄準的主要消費對象。所以,“飯圈”倫理困境出現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邏輯對偶像經濟生產、流通、消費各個環節的宰制。
首先,偶像經濟在一定意義上屬于文化生產,因此也是商業性與精神性、利己性與利他性統一的過程。在流量的紅利面前,經紀公司通過“造星運動”賺取收益,其商業目的覆蓋過精神追求,產品的利己性質超越了其社會責任,導致文藝市場上充斥著毫無精神營養的文化商品,呈現給大眾的是一個虛假繁榮與道德墮落并駕齊驅的文化市場。馬克思把文化創作看作一種精神上的生產過程:生產不僅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6]。有鑒于此,畸形的偶像生產產生了審美扭曲與理智迷誤的主體價值異化的群體。
其次,資本邏輯與現代技術合謀的產物——數據媒介平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何種文化產品能夠進入文化市場,它們將目光聚焦到了偶像經濟巨大的流量變現功能,向受眾精準投送,構筑與強化著人們對圖像畫面的“視覺依賴”,更為關鍵的是,憑借以“微博”為代表的媒介平臺,資本邏輯以輿論來誘導“飯圈”的欲望,由此催生了各類營銷機構,將偶像的成功與高流量、高曝光掛鉤,鼓吹“為愛發電”,為粉絲“氪金”的合理性作辯護,通過誘導粉絲賺取其代理費、營銷費來實現資本增值。當偶像因粉絲構筑的商業價值獲取廣告代言時,又是粉絲為其品牌的溢價買單。于是,資本邏輯串聯起經紀公司、偶像、媒介平臺、營銷機構、廣告商等多個利益平臺,日益把粉絲拋入一個欲望被制造、被滿足又不斷匱乏的文化消費陷阱,形成了一種看似自由與毫無強迫性卻不易掙脫反抗的“文化軟暴力”,規制著“飯圈”群體的行為。
最后,當資本邏輯塑造起偶像經濟市場媚俗、享樂、利己的風氣后,它便可以堂而皇之地以大多數人的喜好為噱頭,繼續為自己的產品開辟更開闊的市場,最終會荼毒文化的先進性,進而給現實社會生活中的人帶來道德困惑。
(二)形塑:“娛樂至上”為主流的“飯圈”文化場域
“娛樂至上”宰制的文化場域對“飯圈”群體的形塑更加深了倫理困境對青少年的不良影響。商業資本的注入不僅使得文化的經濟功能被放大,而且也使得文化的娛樂功能走向極端化。“飯圈”的話語體系也早已突破了理性娛樂的邊界。
一方面,從“娛樂至上”觀念的本質來說。“娛樂至上”現象背后是泛娛樂文化的蔓延推進。泛娛樂文化是大眾文化的負面效應及其帶來的文化發展形式,本質則是大眾文化人文教育功能的異化[7]。“娛樂至上”則是這種異化形式衍生出的異化理念。娛樂本是為休閑、向善、盡美、充盈生命主體而生,大眾文化也將娛樂作為填充教化功能的手段,而“飯圈”的文化氛圍是用娛樂解釋一切并且包裝一切社會現象,將娛樂奉為最高圭臬,使娛樂性成為評判大眾文化的標準。“娛樂至上”理念表現為手段與目的的顛倒,成為對人文化主體地位的顛覆。
另一方面,從“娛樂至上”觀念所承載的內容來說,“娛樂至上”常常與消費主義、極端利己主義等消極思潮相伴相生,這類文化并不具有深刻的精神內涵,用毫無底線、極致娛樂的形式給人帶來直觀的視覺沖擊、滿足人的感官享受欲以及即時的快感,將人的欲望外化得淋漓盡致。在“娛樂至上”宰制的文化場域中,“飯圈”群體不再追求對自身以及對社會的深度思考,用淺層的欲望表達替代對現實的關切以及對自身心靈的關照,并且由于“飯圈”極端強調娛樂性,將娛樂看成唯一的準則,“飯圈”成員的個性特征逐步被消解,內部逐漸趨同。更為嚴重的是,由于泛娛樂文化對應了人的內心欲望,它便擁有了在大眾之間合理運作的“通行證”。向大眾尤其是“飯圈”青年群體潛移默化地傳輸扭曲的價值觀,造成個體獨立思考能力的退化與理性思維的消逝,不斷消解著人的主體意識,進而使個體的理性行動能力受到抑制。
(三)助推:思辨能力低幼化的青年群體
易煽動性與非理性的特征是“飯圈”全面發展能力塑造的薄弱環節,是“飯圈”倫理困境問題形成的基礎。“飯圈”以青少年為主力軍,整體呈現出低幼化的特征。青少年處于審美與道德觀的形塑階段,他們往往會受到來自外界的不良信息的誤導,對能夠帶來視覺沖擊、滿足低俗趣味的文化產品產生向往,從而難以形成關于“美”與“德”的正確認識。同時,僅依靠發達的物質生活難以填補粉絲空白的精神空間,借助網絡媒介憑空而降的流量明星因某些特點博得粉絲的青睞,被粉絲當作“信念替代品”來填補欲望的缺口,外加青少年對自身欲望的控制力較差,更使得無孔不入的娛樂文化通過誘導欲望來潛移默化地塑造他們的審美判斷、價值取向與道德認知,進而不知不覺地影響著他們的行為。
另一方面,學校美育仍然是教育中較薄弱的一環,當現代傳媒在不斷地擴大自身社會影響力尋求社會認同的時候,無論是人才隊伍還是教學創新方面,審美教育仍存在短板,青年處于審美迷茫到確認的轉折階段,在紛繁復雜的信息世界中,如果缺乏堅實有力的正向引導,青年轉而就會被充滿低級趣味的文化產品所吸引,并日漸失去文化的審視與自我反思能力,習慣性地接受娛樂媒體的灌輸,這種情況下產生的結果,使青年群體極容易被利用,成為偶像、媒介平臺等利益團體實現資本增殖的工具,在追星中喪失個性、迷失自我進而出現價值觀扭曲、道德觀念模糊以及逾矩行為,最典型的就是“飯圈”非理性的消費行為以及非理性的群體事件。
三、“飯圈”的道德建設路徑
(一)治理與監管相結合規范“飯圈”資本有序運行
“飯圈”問題的治理根本在于其資本的合理運行,這是對人作為“人”在資本面前主體地位的歸正。“飯圈”資本問題治理的關鍵是要在明晰資本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的前提上進一步厘清兩個前提,其一是何種資本能夠匯入娛樂文化市場中;其二是資本進入娛樂文化市場后被用于何處。前者重在以制度律法進行調控,后者重在形成對資本運行全方位的監管。
一方面,要為娛樂業資本劃定明確嚴格的準入“紅線”。2021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為資本設置‘紅綠燈,防止資本野蠻生長,支持引導資本規范健康發展。”娛樂文化市場也要控制資本作用的發揮,相關部門要完善相關法律政策,對明星經紀公司、商業平臺、營銷機構等利益集團制定具有針對性、具體性的法律法規。對于無良的資本要及時斬斷,控制無底線的“造星”“選秀”運動,嚴厲打擊以獲取高額利益為目的誘導青年過度消費、大額消費等行為,推進行業規范體系建設,定期對娛樂業資本進行治理,引導資本以社會服務為目標,朝著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要的方向流動。
另一方面,已經進入娛樂市場的資本,也要對其進行控制與監管,以保證資本能夠發揮其正向的作用。首先,針對造星選秀、媒體運營、熱度營銷等環節的資本運作過程要進行重點關注,嚴防流量造假以及不同利益主體相互勾結謀取利益,利用粉絲的情感收割錢財等惡劣行為的出現,以保證從各個環節來抑制娛樂行業資本的無序擴張。其次,政府相關部門要強化對明星工作室的監管,加強對明星人設劇本設置的監督,督促藝人專注精品力作的創作,重拳整治明星公眾人物的“洗錢”等違法行為,同時,要加強輿論監控,規范媒介平臺粉絲應援渠道與群體賬號的使用,打擊惡意抹黑、粉絲控評、非法集資等行為,并及時進行正向的輿論引導。最后,建立政府部門、媒介平臺、社會用戶的全方位監督模式,政府定期開展網絡凈化行動,整治“飯圈”違規事件,對相關事件進行披露,叫停“刷榜”軟件的運行;此外,用戶要監督媒介平臺的傳播內容,學會善用舉報功能,及時舉報誘導粉絲消費的行為,凈化藝術環境。
(二)正確輿論導向支撐“飯圈”文化的供給與傳播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塑造主流輿論新格局[2]50,鞏固壯大奮進新時代的主流思想輿論。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飯圈”倫理困境,必須要使“飯圈”處于更高層次價值觀的統攝下。“飯圈文化”主要作為一種青少年“亞文化”在社會上形成影響[8]。因此,必須強化社會主流價值觀念在青少年輿論場中的導向支撐作用,這是消散“泛娛樂”迷霧、化解“飯圈”倫理困境的重要渠道。黨的二十大傳遞出新聞傳播體系建設的根本是加大內容供給側改革力度,助力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一切脫離人民的理論都是蒼白無力的,一切不為人民造福的理論都是沒有生命力的。”
第一,要強化社會主流價值觀念在偶像產品供給機制上的導向力量,以堅定的人民立場為核心的文藝道德來引導偶像文化生產,用真實的精神內涵來充盈偶像形象,杜絕虛假“人設”的構建。其一,要嚴格把控偶像產品的質量,偶像要以優質作品作為衡量自身價值的標準,以社會效益為落腳點,服務于培養大眾的高尚趣味,提高作品的文化厚度,摒棄文化生產的“工業化”模式,通過對“美”的生動刻畫、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深刻表達、宣揚道德先進事跡等引導正確的輿論風向,扼制大眾浮躁的文化心理,樹立公民正確的文化審美觀。其二,明星偶像要擔當起榜樣的帶頭作用,偶像對“飯圈”有著極大的聚合能力,其自身言行對“飯圈”群體的行為變更起著統攝作用,因此,要引導偶像規范自身言行,嚴禁失德藝人以各種形式曝光、復出;引導對主流價值觀進行示范,使偶像承擔起社會責任來關切社會、投身公益,使其倡導粉絲理智追星,關注處理粉絲之間因自身而起的“拉踩謾罵”“惡意刷榜”等行為,以正向的榜樣力量來引領“飯圈”粉絲價值觀的塑造。
第二,要確保社會核心價值觀在偶像產品傳播環節中跟進的全程性,在于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來引導媒體平臺的自我糾偏。其一,媒介平臺要摒棄“唯流量論”,取消偶像“打榜”機制,并將目光聚集到文化產品的精神性與教化功能上,及時處理煽動對立、惡意“拉踩”以及誘導消費的言論與行為,清理“注水數據”,為“飯圈”提供清朗的表達空間。其二,媒介平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何種文化產品能夠進入大眾視野,因此,媒介平臺要注重自身的公共性,以公共性為前提不斷完善自身功能及體系構建,封停無良營銷號,使媒介平臺不至淪為資本進行輿論引導的工具,以正向的企業責任感優化產品推送,推動公正公開的網絡輿論場的構建,成為公眾理性表達的渠道。其三,媒介平臺要加強對粉絲網絡社區的管理,強化內容監管,規范粉絲言行,設置年齡限制,警惕未成年粉絲的非理性行為,并及時進行警告和勸阻。
(三)“堵疏”相濟,釋放“飯圈”正能量
當資本邏輯試圖把“飯圈”群體的追求異化為僅僅是欲望的投射時,就必然貶低甚至否定人的價值,所導致的后果必定是信仰、理想等人的根本導向性因素的淡漠,必須以有效的教育手段,實現道德規范從他律性向自律性的轉變,樹立起自覺的價值觀,才可為超越“飯圈”倫理困境搭建橋梁。可將“堵疏”結合的方式作為化解“飯圈”倫理困境的關鍵環節,在此過程中,圍堵的是“飯圈”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疏通的則是“飯圈”正能量的釋放之路。
其一,從“飯圈”倫理問題對青少年生活的影響范圍和深度來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然是必要的。“飯圈”群體對應了處于學齡階段的青年群體,思想教育工作稍有懈怠,“飯圈”消極思潮就會乘虛而入,首要的必須以主流價值觀的灌輸與引導來切割圍堵“飯圈”對青少年群體的消極影響。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關注思政課的建設問題,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關注到祖國的未來與明天,要教育引導廣大少年兒童樹立遠大志向、培育美好心靈,讓少年兒童成長得更好,要將積極偶像觀的形成、主體意識的確立與全面發展能力的完善教育融入到思政課程體系建設中,貫穿于大中小學教育全過程。尊重不同年齡段青年的實際情況,注重不同階段的思想教育的針對性,針對年齡稍長,接受能力稍強的中學生可以引導其建立正確的偶像選擇觀,引導其自我完善與自我發展;對于思維活躍、個性意識彰顯的大學生可以增強其身份認同,回應現實關切,著重培養其奉獻社會的能力,將對偶像的崇拜磨練為趕超偶像的意志。
其二,要正視“飯圈”的正能量。因“飯圈”具有高度的聚合性、組織性,以及極強的行動力,所以疏通“飯圈”正能量的釋放通道會產生巨大的社會效益。“飯圈”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會對偶像的言行起到監督規范的作用,無論偶像出于自愿或是輿論壓力都會傾向于在公眾鏡頭面前展示良好形象,而這樣一種良好形象又會對粉絲產生引導作用,比如有粉絲以偶像的名義進行修建圖書館、設立公益基金、捐建希望小學、成立“公益應援站”等公益事業。因此,問題不在于“飯圈”存在的合理性,而是應當如何釋放出“飯圈”的正能量,并引導其向社會發展方向上靠攏。堅持“疏導”的原則,尊重青少年心理發展規律,循循善誘,引導青少年在深層次上感悟作品的藝術內涵與精神價值,從而塑造學生對“美”的正確理解,同時,強化榜樣的力量,鼓勵青少年在實踐中將道德規范發展為自身道德人格,從而提高抵御“飯圈”不良文化侵蝕的能力。在給予青年選擇偶像的自主權的同時引導青年增強是非明辨能力,認識到何為“正”何為“負”,實現用青年的主體價值構建“飯圈”生態,用“飯圈”的正向效應渲染青年的雙向互動。
參考文獻:
[1]毛奕峰,王巖.“飯圈”亂象及其意識形態批判[J].中國青年社會科學,2022(5):52-59.
[2]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77.
[3]張思寧.心理分析視域下的信仰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36.
[4]牛文科.泛娛樂時代畸形的粉絲文化與偶像經濟[J].青年記者,2022(2):42-43.
[5]欒軼玫.飯圈失范的表象及糾偏[J].人民論壇,2020(26):136-139.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
[7]韓升,畢騰亞.大眾文化發展的“泛娛樂化”傾向及其批判[J].思想教育研究,2020(2):61-65.
[8]張頤武.“飯圈文化”反思[J].中國文藝評論,2021(10):4-11.
作者簡介:
武夢美,江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連冬花,江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科技哲學、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