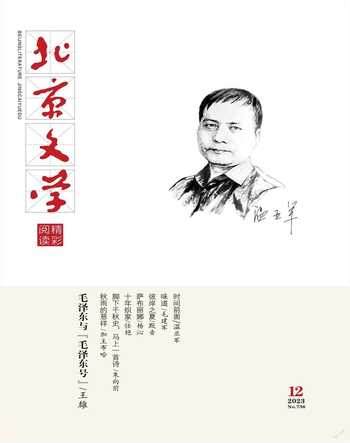味道

1
清明前一天的夜里,老黃上廁所,結果一聲不出地栽倒在廁所里,尿流了一地。
120來,說老黃已經死了。后來醫生給老黃開的死亡證明上寫著:心臟驟停。
84歲。
老黃和老伴只有一個兒子。老黃老伴對兒子說:“你爸真好,走也那么痛快,肯定是上天了。”
說這話時正逢上午10點,國家為抗擊疫情犧牲的烈士及逝去的同胞公祭的笛聲鳴響。
三分鐘。
老黃老伴聽了,兩眼發直,待鳴笛結束,喃喃地說:“他也真是值了!”當然是說老黃。
老黃的兒子也60幾了,30多歲離婚就沒再找。女兒隨著前妻,自己單著。他是開一輛三輪摩托來的,北京又叫三蹦子、殘疾車。又開著這輛車去到醫院太平間,跟人商量好三日后火化。
回到家冷冷清清,老母親一個人孤單地坐在沙發上。老黃兒子說:“我以后就跟這兒住吧?”老黃老伴說:“那你的房子怎么辦?”老黃兒子說:“出租、賣了。錢咱娘兒倆花。”老黃老伴說:“成!”
下午兩點,老黃兒子拉著母親去北街,上彩擴部給老黃放大一張遺照。回來時在小區門口測體溫,85歲的沈騰云拄著一根登山杖在桌子后面坐著,問:“老黃呢?怎么沒出來?”老黃老伴說:“沒了。昨夜里沒的。”沈騰云一嚇,坐著的身子向后一仰,道:“我操!”把周圍人嚇一跳,紛紛看他。因為想不到他會說出這么倆字。
沈騰云卻沒覺得,問:“哪天火化?”
“后天。”
2
老黃活著時愛說這倆字,“我操”。幾乎是他的口頭禪,高興、驚訝、沮喪,等等,隨口就來。
老黃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恍恍惚惚記得有過母親,可不知怎么,后來就是他一個人在北平城里討飯。新中國成立被送進育幼所,13歲,學習文化兼干一些雜活。一次育幼所組織孩子們看《三毛流浪記》的電影,因為育幼所的孩子大多都有和三毛相似的經歷,所以看電影中很多孩子哭,不哭出聲也流眼淚。他不哭,也不流淚,基本不看電影,而是轉著腦袋看哪個哭了,哪個流淚,嘻嘻地笑,被老師揪出電影院,問他為什么嘲笑人家?你沒有相同的經歷嗎?為什么不傷心?一開始他還笑,后來臉紅,可就是不回答老師。老師說:“想想你的名字?”
老黃初到育幼所時,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只知道叫生兒,因為不認識字,哪個生他也不知道。當時管登記的人說:“你是解放軍同志從黃寺大街領來的,你就姓黃吧。現在是新社會了,你要過上新生活了。我給你起名,你就叫黃新生吧。”
老師讓他想自己的名字,他就連眼睛也紅了,瞪得老大,面向馬路上行駛的汽車。到底一個字沒說。
正值夏天,老師看他一頭的汗,就把他領回影院,因為影院里有風扇。可不一會兒,聽見他小聲地笑,根本沒看電影。
老黃19歲時分到醫院上班。就是那年,他和在育幼院里好上的女朋友成親,兩人都是孤兒。
老黃只有小學四年級的文化,進醫院后在鍋爐房上班,為全院供熱供暖。這個工作冬天忙,推煤鏟煤,往爐子里送煤。過了冬天只供應熱水,就比較輕松。
有一次午休時間老黃見一個工友看小說,才知道院圖書室里不光都是醫學方面的書,也有小說。老黃借的第一本書是《水滸傳》,因為聽過別人講《水滸傳》里的故事。從此后愛上了看小說,不過只看俠義和演義小說,都是從院圖書室借的。
老黃到醫院的第九年,給病房垃圾道掏垃圾的工人王師傅得了肺結核,住進傳染病院,后來死了。很多人都說王師傅得肺結核是因為掏垃圾染上的。
于是沒有人愿意接替王師傅空缺去掏垃圾,后勤領導動員、分配,全不管用,甚至引得家屬在領導屋里哭鬧。
那個時候,醫院里不招臨時工,也不允許有臨時工。所以一段時間里,都是后勤干部帶幾個科員去掏垃圾。
后勤科召開全科人員大會,先由后勤科書記講勞動模范時傳祥,一個淘糞工人,國家主席和他握手。后勤科長不講這些,干脆利落地說只要國家再漲工資,掏垃圾的排第一個。
還是沒人去。
一天,?后勤科書記來到鍋爐房,直接找老黃,問老黃生活如何,工作怎么樣?噓寒問暖。
老黃只是一個普通的鍋爐工,既不突出也不落后,頭一回被領導這么關心,有點不明所以。后來書記說一句話,道:“你想過沒有?不是共產黨和新中國,你能不能活到現在?”老黃用眼睛翻棱書記,說:“不就是沒人掏垃圾嗎?我去。”
書記笑了,說:“你寫份入黨申請,現在就寫。”
那年老黃28歲,只因為長得老,當時就很多人戲謔地叫他老黃。書記拿著老黃的入黨申請一走,工友就說老黃:“你傻不傻?”老黃有點后悔,說:“我操!那怎么辦?我都答應了。”工友瞥瞥老黃,說:“那就只好去了。”
老黃掏垃圾,全副武裝:帽子、口罩,嚴嚴實實,甚至工作服的領口袖口都用小繩扎嚴,穿長筒雨靴,戴電焊工的手套。而且每天都要往垃圾道里噴消毒水、敵敵畏。倒真見效,后來到了暑日,垃圾口處也沒有蚊蠅堆集。
一到下班,老黃脫下工作服,嘩嘩地洗大澡。所謂大澡,就是比別人洗的時間長,比別人費肥皂。
只是掏垃圾后,老黃發現醫院里所有人都開始躲著自己,看見自己,遠遠地繞開,包括領導、醫生護士、后勤的工友。
老黃在鍋爐房時只負責燒鍋爐,不管維修,不到別的班組和科室去,那時年輕也沒得過病,醫生護士基本不認識,但是作為一個鍋爐房的工友,一些后勤工人還是熟悉的。這些人遇上老黃也是繞開老黃,當然也不叫老黃,老黃叫他們,他們就當沒聽見,頭都不回。一次兩次,老黃便誰也不叫了。不管看見誰都昂著頭過去,不看人家,不過心里知道其實人家也沒看他。
老黃騎自行車上下班,掏垃圾不久,一天下班的路上正看見一個鍋爐房的工友,他叫人家,要并排騎。人家說:“你別過來!別跟我一塊兒。”老黃說:“什么意思?”那人說:“一身垃圾味。”老黃說:“我操,我洗過澡了,自己的衣服。”那人說:“那也不行。有味兒。”一開始老黃還是笑著說,這時不笑了,說:“真是狗鼻子!我天天和我媳婦一床上睡覺,她也沒說我有味兒。”
那人聽都不聽,一陣猛騎,甩開老黃。
后來老黃就不往任何一個人跟前湊了,不和任何人說話,走路躲著別人,經常低著頭,尤其掏垃圾和運垃圾的道上。
這年年底,院總結大會上,院黨委書記表揚了后勤科,說尤其在垃圾衛生方面做得好,市里幾回愛國衛生運動檢查都得滿分。
里面當然沒提老黃。
老黃大會小會都不參加,小會沒人叫老黃參加,全院大會應當是每個職工都要參加的,老黃主動不參加,不知道坐誰身邊。這次也是,全院下午開職工大會,老黃在垃圾站邊上一間容不下一張小床的屋里讀《三國演義》。老黃看書有個不好的毛病,非要輕輕讀出聲來,遇到一時沒讀明白的句子還要回讀一遍。所以一套《三國演義》他要讀很長時間。這個工夫正讀到:“關公起身曰:‘某雖不才,愿去萬馬軍中取其首級,來獻丞相。張遼曰:‘軍中無戲言,云長不可忽也。關公奮然上馬,倒提青龍刀,跑下山來,鳳目圓睜,蠶眉直豎,直沖彼陣。河北軍如波開浪裂,關公徑奔顏良。顏良正在麾蓋下,見關公沖來,方欲問時,關公赤兔馬快,早已跑到面前;顏良措手不及,被云長手起一刀,刺于馬下。”
老黃微微笑。
3
老黃家距醫院很遠,從家到醫院要穿半個京城,所以老黃愛人即使看病也不會到這里來。況且老黃愛人沒病。
老黃剛掏垃圾時,雖天天回家,卻是一年多后老黃愛人才知道他掏垃圾。緣于老黃的兒子課間鬧著玩時把一個同學的腦袋撞流血了,一時害怕,溜出學校。弄得學校里找不著人,家里也找不到人。
老黃兩口子只有這么一個兒子。
老黃愛人找不到兒子就到醫院找老黃,正看見老黃掏垃圾……
老黃愛人沒有潔癖,不過愛收拾,喜歡整潔。老黃愛人正告老黃:“回鍋爐房!”口氣、表情,異常嚴厲。老黃說:“那整天鏟煤不也臟嗎?”老黃愛人說:“不一樣!這個我說不出口。”老黃說:“你看,我答應人家了,而且我干這么長時間了。”老黃愛人說:“不行。”
老黃愛人不讓老黃靠近自己,一靠近便作嘔,好像老黃真的滿身垃圾的味道。到了晚上也不讓老黃上床,驚恐地叫:“你別上來!”老黃在屋子里也不行,說:“哎呀,垃圾味兒,受不了,受不了!”頭疼,喘,說:“你出去,出去!”點一根檀香,嗅一嗅,簡直要哭。說:“更不是味兒了!”
老黃的住房只有11平方米,即便沒有床,他也無處躲藏,因為他已經不是老黃,是一種叫作垃圾的味道。盡管他從穿在身上的衣服上聞到的只是一點肥皂味道。可正如愛人所說:“你聞也沒用,你天天弄垃圾,早不知道臭了。”
老黃騎車到了醫院。
垃圾站邊上有一間小屋。這間小屋是專為老黃換工作服砌的,里面一張椅子外還有一個床頭柜,可以坐下休息,換工作服,卻橫豎都躺不下一個人。
老黃就在椅上坐了一宿。
老黃愛人在一家童裝廠上班,踏縫紉機。上午工作出了一次想都想不出的錯誤,把一條花邊軋錯了地方,還當成品交出去,被組長好一通批,問她腦子在想什么?吃過午飯,老黃愛人向組長請了半天事假,沒回家,直接來到老黃工作的醫院,找到后勤領導,要求讓老黃回鍋爐房。后勤書記告訴老黃愛人要提高工人階級的革命覺悟,怎么能把革命工作分成高低貴賤?我們做的每一項工作不是為社會主義建設作貢獻?挑三揀四、嫌臟怕累不是我們工人階級應有的覺悟。大家都嫌掏垃圾臟、丟人,都不去做,那革命工作還怎么進行?
老黃愛人是醞釀一夜加一上午,鼓足勇氣才來,但是一說革命道理她就啞口無言,又撕不下臉來撒潑打滾、哭哭啼啼。賭氣說不讓老黃回鍋爐房,我就和他離婚。書記說:“你因為這事跟老黃離婚?你們廠領導知道了不會對你有看法嗎?”
憋了一肚氣的老黃愛人在老黃運垃圾的路上堵住老黃,為防有人聽見,站在老黃身側,用恨急的表情小聲說:“你要不回鍋爐房上班,就別回家!永遠別回!”然后氣沖沖地離開。
老黃在醫院大樓的地下室里找到一個四方的空間,因為設計的時候沒有想把這里弄成一個房間,所以沒門。空間不大,卻足以搭上一個鋪,而且頂上有燈,墻上有開關。他便不回家了,就是禮拜天也在醫院。每個月開支回家一次,擱下錢,吃頓飯,回醫院的地下室睡覺。
不久以后,老黃在醫院的廢品庫里找到一扇其他地方更換下來的舊門,安在那里,便真的成了一間房。
那時候,醫院的各種用房一點也不緊張,地下室更沒什么用處。只有幾個房間里堆一些一年兩年也沒有用的雜物。不管白天黑夜沒有人到地下室來,甚至很多通道里的燈長年沒人打開。通道頂上的燈很遠處才有一個,燈泡的度數也小,如果有人下來,打開燈,一條通道也是幽幽暗暗、寂靜無聲。老黃自記事就在北平城里討飯、流浪,什么破廟空宅、荒郊孤墳的野外全待過,害怕不害怕的早就習慣了。
這一年的夏日,暑熱里,老黃有幾日咳嗽,沒當回事。這一天早起卻頭昏腦漲,行走如踩棉花,在垃圾站勉強算更衣室的小房里刷牙洗臉時,發現鏡子里的自己臉紅耳赤,一摸額頭發燙,立刻想起肺結核,輕聲說一句“我操”,就全身發軟了。
老黃軟著身子去了內科。
接診的大夫就是沈騰云。
之前兩個人沒有過交集,也很少碰見,碰見了也不打招呼,不過互相知道都在院里上班。看到老黃,沈騰云沒有絲毫厭棄的樣子,說:“黃師傅,您哪兒不舒服?”老黃愣了一下,第一沒想到這個大夫知道他姓黃;第二沒料到人家會管他也叫黃師傅,還問您哪兒不舒服。緩過神來,不敢太靠前,站著說:“沈大夫,我可能得肺結核了。”
沈騰云笑笑,問了幾個問題,看體溫計,說不像。戴上口罩,讓老黃坐下,說:“我給您查查。”用聽診器聽完,又讓老黃躺上診床,掀起衣服,按了幾下。摘了口罩,說:“沒有肺結核,感冒發燒,現在正流行。吃點藥。”開一張單子,讓老黃去驗血。
驗血回來,看著沈騰云寫診斷、開藥,老黃長出一口氣,自言自語說:“這把我嚇得,嚇一大跳。”沈騰云邊寫邊說:“黃師傅,您前邊的王師傅得肺結核不是因為掏垃圾,是家里老人染病又傳給他。我見過您掏垃圾、拉著垃圾車運垃圾,您防護做得很好的。以后就是干完活一定勤洗……”
講了一堆,開了假條:兩日休息。
老黃沒有休息,覺得要是感冒也沒必要休息,況且休息了沒人掏垃圾。而且吃上藥,當天就好了許多。
后來,有幾回老黃和沈騰云在路上遇見,沈騰云也躲老黃,可不像別人那樣夸張得恨不能跑著躲開,躲到很遠。沈騰云只躲開一兩步,而且沖老黃笑,叫一聲黃師傅。老黃一定答應,并且回叫:“沈大夫。”兩個人相互走過去。
自掏垃圾之后,沈騰云是老黃在這個醫院里唯一可以打招呼的人。
老黃每遇到沈騰云都會避讓,一看見沈騰云笑,就主動招呼:“沈大夫。”
不過老黃和沈騰云很少遇見,在下面的故事發生之前,攏共也不過三四回。
而且,只叫一聲,沒有站住說點什么的時候。
4
老黃沒入過黨,掏上垃圾后沒人再問他是否入黨,找他談心,寫思想匯報。他自己似乎也忘了有過寫入黨申請書這件事。
1966年夏天,這派組織、那派組織突然地往外冒,敲鑼打鼓地成立,尤其歡迎出身貧苦的工人階級加入。奇怪的是沒有任何一派組織找老黃或者動員老黃加入。就像入黨一樣,老黃好像也沒想過加入。照掏他的垃圾,下班了洗澡。晚上睡倒之前在院區里走走、遛遛。
以前老黃愿意用這個工夫讀小說,讀累了才會出來走走。現在院圖書館被查封了,任何小說都借不出來。老黃就有許多時間在院區里走,遇到沒人觀看的大字報也讀一會兒。
這年沈騰云31歲,對政治一直積極,要求進步,正是這一年成了預備黨員。他是緊跟院領導的,一段時間后,在院領導的布置下串聯了一些醫生護士成立了一派組織,先當副司令,后來當了正司令。時間不很長就和幾個院領導一起被打倒。他是“保皇”分子,成立了“保皇”組織,是“保皇”急先鋒。而且他的家庭出身也不好,舊官僚。沈騰云的爺爺、父親都在國民黨政府任過職,只是沒什么罪惡,沒入過國民黨,以后又擁護共產黨,被中央政府定為民主人士。
沈騰云一時風云的時候,有一天老黃運垃圾,拉車走到廣場處,看見幾乎全院的人聚在廣場處開群眾大會,沈騰云站在搭起的臺子上演講。
其實換任何一個人站在臺上老黃一定走開,因為是沈騰云便不自覺地在人后遠遠地站住了看,沒想到沈騰云會有這么慷慨激昂、口若懸河的一面。
一個人在專注的時候會忘了自己,老黃放下車不由得慢慢往前湊,走了幾步突然發現那些站在最后面的人突然波開浪裂,在他面前形成一個半圓的空場,老黃腦子里馬上閃出一個鬼剃頭的腦袋……在育幼所時,一個和老黃同屋的小伙伴一天早上起床后,被大家發現腦瓜頂上突然禿了一塊,就是滿頭頂的黑發中間禿了一塊硬幣大小的圓形,一毛沒有,如同打了蠟一般锃光瓦亮……
老黃毫不猶豫地拉起車走了。
便如一種味道,去了……
后來沈騰云被打倒老黃也知道。看見過批判沈騰云的大寫報以及標語,卻不知道沈騰云被關在地下室。
醫院樓的地下室空間很大,七拐八繞有幾條通道。老黃隱約知道在一條通道的幾間屋里關著一些被打倒的人,卻沒想過沈騰云也在。
那里離老黃睡覺的通道要走兩三個拐彎,老黃從不過去。
一天,下班后的老黃出醫院買些掛面,回來時在院子里碰見了后勤科長。后勤科長姓張,此時身后還有兩人跟隨。張科長看著老黃說:“你紅袖箍呢?哎?你是哪派的?”老黃說:“沒有,哪派也不是。”張科長就從兜里掏出一個紅袖箍扔給老黃,說:“給你一個!”老黃套在胳膊上,也沒看紅袖箍上寫著什么,到底加入了哪派組織。張科長見老黃套上了袖箍要走,說:“回來。交給你個任務,從明天起,下班后去地下室看人,11點回去睡覺。”老黃說:“我操,那垃圾誰掏?”跟隨著張科長的其中一個人叫孫寶祥,沖老黃說:“老黃,你嘴干凈點啊,跟司令說話敢帶臟字?”老黃有一點發愣地看著。張科長現出一點小傲驕,保持嚴肅地說:“你掏!白天上班,晚上5點半到那兒值守。”老黃說:“算什么?加班還是上班?”司令說:“怪不得哪派組織都不找你,革命覺悟哪兒去了?多少人爭著去,我是考慮他們都有老婆孩子……”老黃說:“我操,好像我沒有。”司令搶到孫寶祥前面說:“你不回家!住在醫院,下了班也是在醫院里逛。”老黃說:“你知道我住地下室?”司令說:“廢話,全都知道。你有這時間為什么不為運動作點貢獻?”老黃了,小聲說:“我得睡覺,要不第二天怎么掏垃圾?”司令說:“你就值前夜,不用干什么,坐那兒守著就行。11點回去睡覺,還能耽誤白天掏垃圾?”老黃說:“好、好吧。”
第二天,下班洗澡時,老黃比平時多打了一遍肥皂,換上自己的干凈衣服。先到自己住的地下室里吃過煮面條,這才到看守的地方。去的路上要一路開燈,那也是幽幽暗暗,在多年沒人行走的地上留下一串腳印。
他拐了三個彎兒才到,一條死路的短通道,頂上只有一個燈泡。北面兩間房,門上掛鎖,關著那些被打倒的人。南面一間房,房門敞開,老黃到時,從里面出來聽見動靜的兩個人,都是工人,年輕一些的小李和年長的老劉。小李對老劉說:“走了。”盡量避著老黃去了。老黃看看站在門口里只露出半個身的老劉,說:“咱們兩個?”老劉點點頭,沒出聲,退了進去,緊接著在里面放出一個屁。
老黃見通道頂燈下有一把椅子上,便坐下,想一想無事可干,從衣兜里掏出院里新發給大家的《毛主席語錄》,打開看。
頂上的燈15瓦,在老黃的斜上方,昏昏黃黃,不是很亮,卻也看得清語錄上的字。一會兒,屋里的老劉可能對老黃輕輕地念叨聲奇怪,走到門口處見老黃讀《毛主席語錄》,又退回去。在里面抽煙,因為常有煙味兒飄去,偶爾咳嗽,放屁,放得挺響。
老黃念一會兒會站起來走走,或者立著。可是不到關押人的門前去。也不到老劉待著的門前去,不知是嫌老劉抽煙還是偶爾放屁,或者覺得自己其實是一種味道。
老劉在屋里也不出來。
老劉這個人是真老,這年54歲,因為一條腿微跛,一直坐傳達室。
讀一陣語錄讀累了,老黃站起來正要走走,看見兩個人押著一個審問過的人從幽遠的通道那頭往這邊來。地下室靜,鞋底接觸地面的聲音一步又一步。因為通道很遠才一個燈,三個人便走一段明亮走一段黑暗。被押的人一直深低著頭看不到臉,一行一仄,一手還抱著一條胳膊,大約是被擰壞了。
老黃看著被押的人從身邊過,說:“我操,毛主席說‘要文斗,不要武斗。”
三個人都愣了一下,包括正打開關押門的老劉。被押人不敢抬頭,不敢停留,愣一下后,反而緊走兩步,直接進了關押室。可他身后的兩人卻一齊看老黃,老黃無所謂的和二人對視。二人中的一個孫寶祥,30多歲,輕賤地對老黃說:“傻逼。”老黃說:“反動啊,我背毛主席的話要文斗,不要武斗。你說傻逼,什么意思?誰是傻逼?”孫寶祥的臉色立刻變了,急道:“我說你傻……”老黃說:“說背毛主席語錄是傻逼?”孫寶祥急看身邊人,老黃對那個說:“你聽得清清楚楚吧?我背毛主席語錄,他說傻逼。”那人趕緊笑,說:“沒說你,說他。”意指被押回來的人,問孫寶祥:“是不是?”孫寶祥無奈地點頭,轉身就走。
老黃轉回來,發現老劉立在房間門口看著自己。可一見自己轉身,立刻回屋里了,弄得老黃連老劉臉上什么表情都沒看清。
5
老黃坐下,拿起語錄,翻開,卻讀不下去。想一會兒,放下了語錄,看著關押室門。
熟悉的人有時不用看臉,在黑黑的夜里,憑借身影也會認出來,何況有燈。
老黃起來,走到關押門前,透過門上的玻璃往里面看,沒想到,沈騰云進去后就靠門后倚墻立著,一手抱著被扭傷的胳膊。老黃一到門邊,兩人就對視了,誰也沒出聲,但是老黃從沈騰云的眼睛里聽見了一聲黃師傅。這一聲黃師傅輕似耳語。
沈騰云很快把頭低下。
老黃覺得自己想了很久,想到一句話:“喝不喝水?”沈騰云不抬頭,輕輕一搖。
老黃覺得自己又想了一陣,想不出話,便把頭轉回來,卻見老劉又站在門口里,正看自己。這一回老劉沒有立刻回去,反而一抬下頜,輕輕說了一句:“保皇派。”
老黃坐回到椅子上,歪頭正要交流,卻見老劉已經進屋了,放了兩聲響屁,同時抽煙,因為一縷青煙從屋里出來,葉子煙的辛辣在通道里散開。
老黃和老劉從前也不熟,現在也是。
后來老黃又到關押室門前看了一次,看見沈騰云和屋里的其他三個人一樣,躺在地鋪上,用一只手抱著似乎受了傷的胳膊。
可能因為老黃沒趴玻璃,沈騰云沒發現老黃。只是老黃一回頭,發現老劉又在門口處站著,一聲不出。這回因為距離近,老劉的眼睛在昏黃的燈光下有些深不可測,老黃覺得自己的身體顫悠一下,心一哆嗦。
差幾分11點,值后夜的來了,老黃走回到自己的住處睡覺。
白天,老黃先去外科開了幾貼狗皮膏藥,然后才換上工作服,去掏垃圾。
下午5點半,老黃到地下室接班,待值白班的人一走,他就取鑰匙,打開關押沈騰云的屋門,徑直進去,一直走到沈騰云身邊,對沈騰云說:“解開衣服。”
老黃打開門時,屋里四個人都在地鋪上坐著。見老黃進來,一齊直著眼睛看老黃,不知老黃要干什么。直到老黃走到沈騰云身邊,說把衣服解了。沈騰云還是不明白老黃要干什么,愣愣地看老黃,見老黃拿一貼狗皮膏藥,掀開一角。突然明白,沒解衣服,擼起扭傷胳膊的袖子,一手來接老黃手里的狗皮膏。老黃沒給,撕開膏藥,握著沈騰云胳膊看了一下,將膏藥貼到肘彎處,撫平。從兜里又掏出兩貼,扔給沈騰云,便向外走。將到門邊,聽見沈騰云小聲叫:“黃師傅。”便回身,沈騰云小聲問:“黃師傅,有吃的嗎?餓,餓得受不了了。”
老黃愣了,看看其余三人,說:“沒、沒有。”出屋,見老劉又在屋門處站著,大約看見了自己的舉動,說:“他是保皇派。”老黃不吱聲,回身上鎖。再轉回來時,見老劉又向屋里走,遂問:“他們吃不吃飯,一天幾頓?”老劉便轉回來看著老黃說:“三頓窩頭,寡湯。早上一個窩頭,沒湯。中午晚上兩個,一碗寡湯。”說完,轉身進屋。
老黃吃過職工食堂做的窩頭,二兩一個。如果照飽了吃,老黃一次要吃四個,加菜。通常也會吃仨。
老黃坐在椅上,一直發呆,總聽見小時的自己可憐巴巴地說,有吃的嗎?有吃的嗎?一仰頭,不自覺地說出一句:“我操!”
老劉沒出來。
醫院的職工食堂,早中晚三餐,晚上十點還有一次夜餐。老黃很少上食堂。原來帶飯,住到地下室后買了一個小電爐子,就是那種老式盤電熱絲的,瓦數不是很大,但做開水,煮個面什么的都沒問題。為了吃到菜,還備了醬油鹽,一瓶香油。炒不了菜,就是煮,從食堂買回饅頭,只有饞了才買回菜。
通常晚飯老黃都吃面條。有菜有鹽有面,今天也是,老黃吃的面條,加一個雞蛋。
老黃有手表,看看將到10點,咳嗽一聲,走到值守門前,見門大敞,老劉在里面坐著,說:“我離開一會兒,就回來。”大約老劉以為老黃去廁所,說:“去!”
老黃先去自己住的地下室里拿飯盒,去了食堂。
賣飯的說,新鮮,你怎么來了?老黃離窗口半步遠,看一看說:“怎么沒有饅頭啊?”賣飯的說:“一看你就從沒吃過。夜餐不是正餐,不炒菜,饅頭怎么吃?包子和粥,純肉餡和豬肉茴香的。你來肉的吧?二兩一個,香,一咬一流油。”老黃猶豫了一下說:“行,仨。”賣飯的正要夾,老黃反悔,說:“茴香,茴香,不要純肉的。”賣飯的一笑,夾茴香的。老黃又說兩個。賣飯的諷刺地看著老黃,說:“不是仨嗎?”老黃說:“倆,倆。”
走回去,聽見老劉在屋里問:“回來了?”老黃說:“啊。”坐了一會兒,自語道:“瞧這一地的煙頭,多少天沒掃了。”其實地上沒有幾個,都是值守白天的兩個人扔的,老劉不抽煙卷。遂拿鑰匙,開門,沖里面說:“沈大夫。”忽見四個人驚愕,急忙改口,稍帶嚴厲地一指沈騰云,說:“你,出來,掃地!”
沈騰云出來,老劉見沈騰云掃地,轉回屋里。
老黃指揮沈騰云:“這兒。”“這兒。”引到拐角,拿出飯盒打開,亮出包子。沈騰云一愣,伸手抓起一個包子就吃,狼吞虎咽。
沈騰云這年31歲,正能吃,一天三頓飯五個窩頭,兩碗寡湯;又加生死渺茫,諸多精神壓力,身體和精神只剩下對食物的貪婪了。即使吃第二個包子時,沈騰云也不抬眼看一看老黃,出個表情或小聲說一句謝謝。只是快速地吃,兩個包子吃完,用袖子擦嘴,擦嘴的時候也不看老黃,擦了又擦。然后不說話,像犯了大錯的孩子在家長面前,低頭站著,不看老黃。
老黃很滿意地向回走,沈騰云跟著,看老黃開門,放下笤帚,低著頭進去。
老黃上鎖時,看見沈騰云一直向里走,低著頭,一直走到地鋪,先跪下,一撲,直接趴在地鋪上,臉埋在彎曲的雙臂里,一動不動。旁邊人推了他一下,小聲說了什么,他也不動,死死地趴著,不抬頭。
老黃不解,有些納悶,看了一會兒,沈騰云還是那個姿勢,一動不動。一回頭,發現老劉站在門口,正看自己,手里拿著一個磕去煙灰的煙袋。老黃不語,老劉亦不語。不知怎么,可能還是燈光照射的緣故,老黃發現50多歲的老劉的眼睛特別亮,他站在門口的里面,門里的燈照出他的剪影,門外的燈照不到他的臉,只有眼睛帶著兩點光,臉上卻沒有表情。
老黃突然聞到了空氣中茴香餡包子的氣味,立刻扯出一些假笑,道:“我、有點餓,仨包子沒吃了,給他半個。怕、怕你不吃。”老劉突然還了一笑,眼睛不再亮,說:“你剩的包子,也就他吃。”轉身進去。
6
第二天,上個班的人一走,老黃就打開門,說:“出來。”沈騰云就出來。不說話,低著頭,看不見他的臉,拿起掃帚掃地。老黃不再跟著,坐在椅上,一抬頭,看見關押室門玻璃后有兩張臉,趴著小心地往外瞅,看沈騰云掃地,也看老黃。老黃說回去,他們便回去。玻璃后就再無人。
沈騰云自己掃到拐角處,看見了飯盒。打開,見里面一個饅頭,一小塊咸菜,便吃,一口饅頭,一口咸菜。老黃這邊就連他咀嚼的聲音都聽不見。歪頭望,也看不見沈騰云。扭回頭望,看見老劉像個蝸牛似的從門口露半個腦袋,但是沒往這邊看,正視著前方吸煙。卻不知他剛才看見了沒,不過自己看不見沈騰云,想必老劉也看不見。老黃嗅了嗅,空氣當然不會有饅頭和咸菜的味道,只有老劉的葉子煙味,兩個關押室也如往常那般寂靜。
其實這個時間沈騰云大可以溜,他不在任何人的視線里。他不溜,也就是不逃跑。因為全中國的形勢一樣,他能去哪兒?即使溜的時候沒有老黃老劉追,一到地面上還是被人抓。
沈騰云把饅頭和一小塊咸菜不出聲地吃完,使勁兒擦嘴。掃地掃回來,還是不看老黃,笤帚放歸原處,自己仄身擠進關押室。老黃這才從椅子上起來,把門上鎖。
以后幾天都是這樣,除了老黃說一聲“出來”,通道里無言語。沈騰云從頭至尾不看老黃,或小聲、或用表情道個“謝謝”。低著頭出來,低著頭回去。
從老黃坐在椅上的位置扭頭望,一趟通道很長,幽幽暗暗、寂靜無聲。在這一段時間里,或只有老黃喃喃讀語錄的聲音,若不讀,就是幽幽的沉寂,聽得見空氣的聲音,如果有味道,就是老劉吸的葉子煙散發的味道。
開始兩次老劉總要站在屋門口,把沈騰云從出屋到回屋看完。他不說話,當然他看不見沈騰云站在拐角里吃饅頭,但是沈騰云起碼從他的視線里消失了一兩分鐘,他也不去看,無聲地等沈騰云出現,進了關押室,他也回屋。
兩次之后,他連出也不出來了。
老黃對老劉的感覺就是偶爾聽見他在屋里放屁,放得很響,有時咳嗽,因為抽煙。
白天老黃不到關押人的地下室去,接交班時也不問白天的事。每天老劉都比老黃早到,或許5點他就到了。所以老黃去時值白班的只有一個人,他不和老劉閑聊,看見老黃來了更是不說話,不等老黃走到他就繞著老黃走了。
在鍋爐房的時候老黃也算不上不愛說話,幾個人坐在一起也說閑話,別人讓他講一段,他就講一段讀過的演義,跟認識的人也打招呼。就是掏垃圾后變得不愛說話。因為沒人給他機會說,別人都不理他,他沒辦法,漸漸地變得不愛講話。
奇怪的是老劉這個人也不愛講話。下午5點半至11點,兩個人全都坐著。老黃在外,老劉在里,奇怪的是兩個人都不怕寂寞,從來沒有坐一塊兒聊點兒什么的時候,或這個愿望也不曾有過吧。
關押室里的人通常也不交流,即便有交流,聲音也會小到關押室外的兩個根本聽不見。所以這個時間里,能聽見的也只有老黃喃喃讀語錄的聲音。
白天,有人會把關押的人帶走審訊、調查,讓他們交代問題認識罪惡,別的什么,老黃不知道,也沒再看見。
第五天,早上8點,老黃正要全副武裝,突然有一個戴著紅袖箍的后勤工人站在垃圾站門口大聲喊老黃。老黃從更衣間出來問干嗎?那人說:“司令找你,讓你過去。”
“干嗎?”
“我哪兒知道。就是叫你過去,立刻。”
老黃把穿好的武裝卸掉大半,只穿著工作服岀來,說:“找我干嗎?”那人也不答,已經在前面走,老黃跟著。走進樓,老黃以為要上樓,或去一層的什么地方,沒有,下了地下室。三拐兩繞,來到一處,突現一片光明。
老黃沒到地下室的這一段來過,是一條通道的盡頭,頂上的燈換成了四十瓦的白熾管,像樓外面的白天。五個房間,門上都沒有玻璃,也都關著,聽不見里面的聲音。老黃說:“我操,還有這么個地兒。”帶他的人已經拉開一個門,探進頭說:“司令,他來了。”便見司令隨著那人出來,隨手關門,看老黃,面無表情地說:“來了?”
老黃點頭。司令就對那人說:“讓他去那屋,先讓孫寶祥問。”那人就拉開司令房間斜對面一屋門,叫老黃:“來吧。”老黃看著司令說:“干嗎?問什么?還孫寶祥,他算什么?”司令說:“去吧,幾個問題,他問你就如實答。沒有什么。”老黃就跟著那個人進去了。是一間空屋,沒有孫寶祥。那人說:“你等一會兒,我去叫孫寶祥。”關門出去。
老黃環視,眼前有一張桌子,桌子后面并排兩把椅子。本想過去坐下,一想穿著要掏垃圾的工作服,沒坐。這時孫寶祥進來了,拿著幾張紙,從一進門就歪頭看老黃,繞過老黃一直走到桌后,坐下,放下紙,拿出筆。一切妥當,抬頭直視老黃。老黃說:“我操,你要干嗎?”孫寶祥不語,臉上一絲詭異的微笑,精瘦的兩肩和一個不大的腦袋還輕輕顛動。老黃煩了,道:“什么事?趕緊說,我還得干活呢。”孫寶祥還是盯著老黃。老黃覺得他簡直就是一副你終于落到我手里的樣子,便生氣地說:“你說不說?”見孫寶祥還不開口,扯著嘴角微笑,老黃說:“再見!”轉身就走,這才聽見孫寶祥厲聲叫:“回來!”老黃轉回來道:“說!”讓孫寶祥一愣,似乎覺得自己跟老黃調了位置,瞪瞪眼道:“你自己說!”
“我說什么?”
“說什么?說你跟大保皇派沈騰云是怎么回事?又給膏藥又送包子,什么意思?什么立場?”
7
老黃一愣,馬上道:“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什么送包子?你調查了嗎?問誰了?那天我餓了,買仨包子沒吃了,剩半個。他正在我身邊掃地,就給他了。不行啊?”孫寶祥說:“不是行不行,而是你為什么要給沈騰云?沈騰云……”老黃說:“那給你?你在嗎?”孫寶祥說:“老劉在。”老黃說:“老劉不吃。”孫寶祥說:“那就扔了也不能給他!他是……”老黃說:“毛主席說貪污和浪費就是最大的犯罪。你學不學《毛主席語錄》?你讓我犯罪,違背毛主席指示?”孫寶祥瞪大眼睛叫:“你可以留著早上吃!”老黃說:“地下室!半拉包子,擱到早上吃不拉肚子嗎?”孫寶祥就氣得上下翻眼瞪老黃,道:“那、那、天天給他帶吃的呢?”老黃斬釘截鐵地說:“沒有!”孫寶祥得意了,開始微笑:“有人可說有哇,而且肯定了,饅頭、咸菜。”老黃說:“誰?誰說的?”孫寶祥看著老黃不語,老黃說:“我操,三曹對案唄!不過,從今兒個起,我不去了。看著他們又沒補助又不算上班,我還得多吃一個饅頭。以前八九點我就睡了。現在坐到11點我餓!毛主席說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最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孫寶祥上下翻看老黃,懷疑地問:“這是毛主席語錄?你能背那么多語錄?”老黃不說話,掏出上衣兜里的毛主席語錄,翻到第3頁,舉著向前走,只兩步就到桌后,要把語錄舉到孫寶祥眼前。孫寶祥噌一下起來,急向后躲,喊道:“你別過來!躲開,臭烘烘的,起開!”老黃的臉頓時漲紅,舉著語錄向前一步,道:“臭?你說《毛主席語錄》臭?”孫寶祥臉色變白,說:“你別又來啊,我沒說《毛主席語錄》,我說你,身上的垃圾味。”老黃說:“怪不得當初找人掏垃圾你們誰都不去?我去了。我是為革命掏垃圾,為社會主義建設掏垃圾,你說我垃圾味,臭。看不起革命工作,嫌工人階級臭!只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才會說我們工人臭。毛主席教導我們,在社會主義的國度,革命工作,只是分工不同而已,沒有任何高低貴賤之分!看來我得讓你聞聞工人階級到底臭不臭!”一步向前,貼住孫寶祥,問:“臭嗎?臭嗎?”孫寶祥連連后退,說:“滾!滾!來人!”架不住老黃步步跟進,問他:“臭嗎?”
剎那門開,司令進來,先是一愣,然后厲喝:“干什么呢!”老黃說:“他說我臭!嫌掏垃圾臭!”孫寶祥已經跑到一邊,說:“他拒不交代,還要打我。”老黃舉著手里的語錄說:“我用這個打你呀?我是讓你看語錄。”司令就走過來看老黃舉著的語錄,看看,說:“怎么回事?”孫寶祥跟老黃重復剛才的對話。說著說著,孫寶祥突然想起,說:“對了,膏藥的事他還沒講呢,拿包子遮。你還真狡猾呀,說,為什么給他膏藥?還給他貼上。”司令突然煩了,對孫寶祥說:“行了!你出去!”孫寶祥嚇一跳,看司令一臉厭棄的表情,不再出聲,氣哼哼地出去,把門關好。
老黃對司令說:“是,他是胳膊扭了,我給他貼了膏藥。這怎么了?耽誤和他做斗爭嗎?因為這個我就反動呀,和他站在一個立場了,您去調查一下,我們兩個人說過話嗎?我可是最無產的工人階級。”把司令說得一愣,看著老黃,說:“行啊老黃,不知道你這么能說。毛主席語錄背得也好,值得向你學習。毛主席這段語錄不知你學了沒有?”說著坐到椅子上,掏出一本語錄,翻到一頁,念: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還有這段: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方面,他就是反革……
這時孫寶祥突然打開門,神秘緊張地說:“司令,快接電話!”司令有些不高興,說:“干嗎?你要干嗎?”孫寶祥就進來,快步走到司令身邊,手擋著嘴,附到司令耳邊說了兩句,司令猛地起來向外走。對老黃說:“你別走,等著我。”
屋里一空,老黃開始皺眉,心事重重。一會兒、兩會兒,不見有人進來,把語錄翻到司令剛才念的那一頁,開始小聲讀。正讀,門一響,司令進來,見老黃不再讀,說:“好,帶著問題學習,最容易領會。”
老黃說:“我可是最無產的無產階級。”司令又一愣,馬上笑了,說:“是。所以我把你叫來,就是提醒你,一定要站穩無產階級和咱們工人階級的立場。”老黃還要開口,司令說:“行了,我還有事,你先回去吧。記住,班還要值,垃圾照常掏。沒事的時候就好好讀讀毛主席語錄,結合今天問你的事好好想想。過幾天我再找你。”說著司令轉身出去。老黃慢慢往外走,走出來,見司令跟孫寶祥在一起,便問:“晚上我還去?”司令點頭,說:“去!為什么不去?”
老黃走出來,拐個彎,一片光明立即消失,前面的通道又是一段亮一段暗,幽幽長長,只有老黃一個人行走。走出地下,走出大樓,大好的太陽光眩目,他便低著頭,垂頭喪氣。
上午,掏著半截垃圾,老黃突然停下,兩手支著鐵鍬在那里發呆。終于想那個拐角處只有自己從地下室的住處到看押處時經過,其他人,不管老劉還是白天看守以及后夜的看守,都不從那里過!
但是一回頭,老黃恍然看見老劉立在身后,兩只眼睛盯著自己。不由得一退,再看,眼前空空。四周圍,只有自己!
8
將下班時,老黃邊洗大澡邊猶豫還要不要到職工食堂去買饅頭。后來想想還是要買,并且決定,還買一個。
買饅頭時他盯著賣饅頭人的眼睛,因為這幾天都是這個人賣饅頭。可是賣饅頭的人絲毫不理會老黃,也沒注意到老黃的眼睛。很多人等著買饅頭,他對老黃又沒什么好感,一身垃圾味,巴不得他快走,把一個饅頭放入老黃的飯盒就去招呼其他人。
老黃拿著飯盒走出食堂,想了又想,覺得和賣饅頭的人沒有關系。
他先去地下室自己的住處煮了掛面,吃完出來。
他拿著飯盒走到關押處時,老劉已到,在值班室門口站著。值白天的兩個人已經走了一個。另一個人看見老黃,像往常一樣,不說話,繞著老黃走了。老黃看看那人背影,再回頭,發現老劉正要進屋,便哼了一聲,足以讓老劉聽到。老劉便看老黃,然后不動。
兩人對視片刻。老黃感覺老劉的眼神有一點點的怯,越來越不自在,甚至是要問自己,你干嗎?老黃彎腰,把飯盒輕放到椅子上,其間一直抬著頭,盯住老劉。老劉看看老黃的飯盒,轉身回屋。
老黃挪一挪飯盒,坐到椅上。
不一會兒,夾雜著辛辣味的輕煙從老劉待的屋里面飄入通通。老黃掏出語錄,翻到了一頁卻沒心思讀,放下,暗暗生氣。
他和老劉沒有過交集,原來是他在鍋爐房,老劉在傳達室,一年到頭,幾乎沒有碰面的機會,碰上也不招呼,因為不熟。后來他掏垃圾,老劉還在傳達室。依舊沒有交集,因為誰也看不見誰。
這時從老劉屋里傳來一串響,是老劉放屁。老黃就皺眉,頭回覺得老劉這么討厭。不想聽到老劉叫自己,一看,老劉站在屋門口面向自己,說:“這兩年我腸胃不好,所以放屁。憋不住,一直喝中藥,現在放得少多了,只放響屁,不臭。我沒嫌過你掏垃圾,你也別嫌我放屁!”老劉一開始說得還算平靜,至最后一句顯然動氣,不待老黃有表示或者張嘴,扭頭進屋。
老黃愣愣磕磕了,糊了糊涂地想,大概也不是老劉,他又看不到沈騰云吃東西。便盯住關押著沈騰云那屋的門。心里翻來覆去,要不要叫沈騰云出來掃地。一會兒,下定決心,取鑰匙,開門,剛要說出來,愣了,問屋里人:“沈騰云呢?”屋里三個人,有原來的院領導、專家主任,都看老黃。其中一個說:“早上被叫走,就沒回來。黃師傅,我去掃吧?”老黃說:“不用。”把門關上,上鎖。一回頭,看見老劉站在屋門口,正想不起要說什么,老劉開口了,說:“白班人說,沈騰云放了。”
“放了?”
老黃呆呆地看老劉。老劉卻不再說話,好像等老黃。過一會兒,老黃說:“怎么放了?他沒事了?”老劉說:“沒問。他們說放了,就放了唄。”老黃說:“噢。”想要走到椅邊坐下,卻半途停下,拿起笤帚,嘟囔一聲“我操”,彎腰掃地。老劉就看著,看著老黃把地掃完了,轉進屋里。
掃完地,老黃坐在椅子上,一腿搭著另一腿,像廟里的塑像。過了好久,拿出語錄翻開來看。
老黃看書速度慢,因為每個字都要讀出聲來,讀得也慢。還有,他習慣順序著看,這一段沒讀完,不會跳到下一段。所以一本語錄,他也才讀到217頁,喃喃地念:“我們要把我們黨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和紀律的原則之下,堅強地團結起來。不論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從黨綱、黨章和黨的決議的,我們就要和他團結。”
突聽見老劉問:“你是黨員?”一抬頭,不知什么時候,老劉站在門外,正看自己。便搖頭,說:“不是。”老劉說:“新中國成立前我是拉車的,從一開始拉車我就拉包月。輕省,也不少掙。最開始是給一位大學教授家拉包月,后來他要到重慶教書,主動把我介紹給下一家,一個當官的,在市府里不知管什么,反正是官。我給他拉了七年,當中沒過說我一個不字或有把我換掉的意思。1948年冬天下大雪,我摔個跟頭,把腿傷了。從那以后拉不了了,跑不起來,走也不行,不能遠,而且不敢使勁。我去辭包月,人家不讓走,說車拉不了給我這兒看門吧。愣把原來看門的人辭了,讓我看。一直看到解放。知道為什么嗎?我嘴嚴,從不多言少語,看見的事就跟沒看見一樣。這一輩子不打聽事兒,不摻和事兒,不多說話,也不跟誰閑聊。”
老劉說話時,老黃一直愣著,聽到這里,愣愣磕磕地說了一句:“沒看出來。”老劉便回屋里,沒有任何不快。進了屋開始抽煙,因為煙味又從屋里出來了。
那以后老黃一直呆坐,偶爾拿起語錄,也不打開。9點多鐘,老黃開始猶豫,猶猶豫豫,終于打開飯盒,拿出饅頭和咸菜自己吃,吧唧吧唧,看老劉沒出來,還故意咔了一聲。果然老劉露頭,老黃舉著咸菜說噎了一下。假裝喝水。老劉就又回屋。
11點,老黃回到自己睡覺的地下室,睡了。
第二天一天,老黃都在等司令或孫寶祥過來找自己,可惜沒來找。掏垃圾或運垃圾時也總往病房樓、門診樓里踅摸,沒看見沈騰云。
老黃的工作只負責掏垃圾,掏出的垃圾運到垃圾站,一天兩次,然后由清潔場來車拉走。院里衛生不歸他管,像清掃院子有專門的職工。墻上貼的大字報他也不管。路過時有新貼的大字報他會看。下午運垃圾時老黃就看見一張新貼的大字報,題目是我要揭發,把老黃嚇一跳,放下垃圾走過去看,卻是揭發院領導。回頭看見司令往這邊來,快到身前,就主動招呼:“司令。”司令看老黃一眼,直接走了過去。
老黃抄起車把。
晚上,老黃又帶一個饅頭,9點來鐘吃了。
老黃每天都在院里干活、走動,卻一直沒見過沈騰云。問題是每天晚上9點來鐘,他都得堅持吃一個饅頭,漸漸吃成習慣,到時就餓。一個饅頭四分錢不說,還要二兩糧票,老黃很心疼,卻堅持吃。
幸好,沈騰云放沒多久,院里幾派組織就聯合了,成立革委會,關押室取消,那里邊的人有的去掃廁所,有的去掃院子,下班后回家。
老黃不用值守了,白天掏垃圾,5點下班后愿干嗎就干嗎,八九點鐘睡覺。忍了好一陣,八九點鐘才不餓了。當然老劉也不值班了,只坐傳達室。就是老黃一直沒看見過沈騰云,不知他在不在院里了。
9
半年后的一天早上,老黃要去掏垃圾的路上,突然迎面看見沈騰云,沈騰云穿著醫生的白大褂,胸前別著一個毛主席像,一邊走一邊和一個同樣穿白大褂的大夫說話。老黃一時無措,沒動也沒吱聲,看著沈騰云。沈騰云將走近時也看見老黃,一愣神,突然把臉扭向身邊的大夫,甚至拉了一下他的胳膊,說著什么,然后隨著那個大夫遠遠地繞過老黃,進了門診樓。
中午,吃過飯,老黃特意洗了個澡,穿上干凈衣服,走到傳達室。一看果然是老劉一個人在里面坐著抽煙,便推門進去。拉一個凳子,和老劉拉開一點距離坐下。
老劉沒有驚詫或者嫌棄,沒招呼,不說話,只是看了一眼老黃,穩穩地繼續抽煙。
坐了一會兒,老黃開腔,眼睛看著窗外,輕輕說:“我看見沈騰云了。”說完,看老劉。老劉像沒聽見,眼望窗外。過一會兒,老黃道:“你說那時怎么就把沈騰云放了?他不保皇了?”老劉這才看老黃,一臉奇怪,又轉向窗外,悠悠地說:“到現在你還不知道?沈騰云他爸是民盟的什么頭,民主人士,夠得著上面。我也是聽傳,說是中央的一個什么地方打過電話讓放人。那趙司令接的。當時正審著沈騰云,立刻不審了,直接把他放了。”
老黃輕輕說了一句:“我操。”老劉等了一會兒,看老黃沒有下言,又看窗外。
窗外零零散散有人走過,醫生、護士、后勤工人、病人。
老黃不語,在凳上枯坐。老劉亦不語,臉向外面。
過一會兒老黃突然想起似的問:“肚子好了?”老劉說:“嗯。沈騰云常看見,早上晚上,上班下班。早就出門診了。”
老黃無語。
又坐一會兒,老黃走了,推開傳達室門,頭也不回。不知道老劉在傳達室里,有什么反應。
一轉眼,過了二十五年,老劉早就退休,活沒活著老黃也不知道。老黃還是掏垃圾,55歲了,掏垃圾、運垃圾還和從前一樣,不見老。
這些年,沈騰云早就從醫療科室出來,開始做行政,先是醫務處、改革辦、副院、黨委副書記、黨委書記,至這一年,沈騰云已經當過一任院黨委書記和一任院長,見到他的人,莫不恭敬,隔很遠就要微笑,近了喊一聲沈院長。一般時,沈騰云都會微笑地答應,至少點頭。
不包括老黃。其實老黃能和沈騰云碰見的時候很少,二十五年里,兩人當真碰見、臉沖臉的次數手指頭也能數過來。老黃碰見了沈騰云不微笑不叫院長,還要故意地把頭別過去,閃出距離,與沈騰云交錯而過。
沈騰云也從沒叫過老黃,更別說黃師傅,或者微笑、點頭,都沒有。當然現在的他不會特意地把臉別向一邊,從來都是直面過去,只是不看老黃。
這一年醫院建了兩棟宿舍樓,不到兩百個居室,卻有一千多個人申請福利分房。為此房管科長每天上班時間都不敢在自己辦公室待著。由書記院長主持的打分會、分房會也開了多少回。可是樓都建完了,分房方案遲遲不公布。
申請房時,老黃也交了申請。只是沒有哪個院里的人會找老黃議論分房的消息,老黃自己也找不到人打聽分房的進展,并且老黃知道自己根本分不到房。
申請是老伴和兒子督著老黃交的,她們的理由是你爭取都不爭取,怎么知道分不到房?
順便說一下老黃50歲時,老伴的童裝廠倒閉,老伴正好退休。從那時起,突然不嫌老黃臭了,允許老黃回家,允許一張床上睡覺。只是原來那間11平方米的公租房讓給了結完婚的兒子,自己和老伴在11平方米的房子外搭了一間3平方米多一點的棚屋,睡覺和看電視。所以到了夏天太熱的時候,老黃偶爾還會睡那間地下室。
饒是這樣,老黃也知道自己分不到房。醫院這個地方,醫生護士才是一線人員,老黃只是一個掏垃圾的后勤工人。
終于,打分榜公布出來了,貼在院區的公示欄里,一時間,幾乎全院的人都去看,人頭攢動,看有沒有自己的名字。
打分榜其實也算分房榜,根據每個申請人的住房狀況、工作年限、職稱職務,以及獲沒獲過獎等諸多條件打分,上了打分榜,不出意外,基本就能分到房了。
老黃每天去掏垃圾都要路過公示欄,連續兩天,聽到有人歡呼,有人咒罵,有人沮喪,也沒往公示欄里看一眼。倒是有人看老黃了,這么多年老黃頭一次被人注視,可是他篤定地相信,他們只是奇怪自己為什么不去看打分榜。
第三天,老黃從公示欄過,聽見一個人激動地罵大街,有人附和有人勸解。那人看到老黃走來,突然一指老黃,憤憤地說:“他都能分房,我不能?”老黃撇嘴,說:“我操,我能分著房?”可還是不由自主瞥了一眼打分榜,再巧不過,正看到自己的名字黃新生在打分榜下邊的位置。
老黃有些愣怔、有些激動,慢慢走過去,看那三個字,黃新生。被人擠開、擠離,出了人群。
老黃在醫院里雖然每天都像一個天馬行空的人,獨來獨往,沒一個人和他說話。可是不妨礙他知道為了分到房有人送禮,有人走關系,有人和領導鬧。況且回到家里老伴也跟他講這些,諄諄教誨,警告提醒,要怎樣怎樣。老黃什么都沒去做,他是一股垃圾的味道了,能做什么?
他走出來,覺得自己能上打分榜,全是因為自己的住房確實困難。
老黃偷偷高興,那一上午干活都很高興。就是中午吃著飯時提心吊膽,甚至開始煩躁。回到家里也不敢說自己上了打分榜,他覺得自己在打分榜上待不住。
打分榜公示,就是讓全院職工看看有沒有不公正、虛假,或許一兩個上榜的人就因為什么原因什么事被人提出來,從榜上掉下來。老黃覺得自己一定會掉下來,他唯一的強項只有住房困難,可是那個時候,住房困難的人很多,更不用說優勢。所以那段時間,對老黃來說,就是煎熬。
10
老黃天天都要從榜前過,天天不敢近前,偷偷地用眼睛瞥,毛筆寫的名字,一瞥就能看見,黃新生。就是、還是一榜。
一天回家,老伴說:“你們院里來人了,我讓他們進咱倆住的棚子房!”問老黃:“打分榜出來沒有!”老黃說:“還沒。”
兩天后,老黃去掏垃圾,遠遠地看見一群人圍著公示欄,他趕忙急走,又慢走,從一群腦瓜后瞥見了新貼出來的二榜。看不全,尤其看不見下面,他又不敢往人群里擠,怕呼啦一下波開浪裂,一片嫌聲。就站在外面,站在遠處。聽見鼓掌,聽見笑聲,看見有人出來,憤憤地喊:“我找他們去!”
老黃還是不動,心卻撲騰得慌。
一個鍋爐房的工人從人群里高興地擠出來,大概是榜上有他。他看見老黃,沖老黃說:“有你!”
老黃愣了一下,慢慢往前湊,竟沒有人聞到他臭,他靠近人群,站在最后,終于發現黃新生這個名字,后面寫著無房。
“還有三榜,還有三榜。”就是掏著垃圾時,老黃都在心里念叨這四個字。下班到家,依舊沒說。
三榜很快出來,有黃新生!
很快,分房榜出來了,黃新生。雖然分到的是一層,卻是一個獨立的兩居!
回到家,一見到老伴,老黃再也忍不住了,說:“分到房了!是個兩居!”
第二天上午,老黃和老伴一起去領鑰匙。
領鑰匙的人很多,站滿樓道,老黃和老伴都在下一層樓梯平臺處等著,直到聽見喊黃新生。老黃一個人上樓梯進去。房管科長看是老黃,親手拿起鑰匙遞給老黃。
從前,房管科長也不搭理老黃,把鑰匙交老黃時第一次叫老黃,是親切地叫。老黃接鑰匙,房管科長親切地說:“老黃,沒看出來啊。”老黃說:“什么?”房管科長不語,笑著看老黃,見老黃一臉蒙,說:“沒什么,走吧。”見老黃不走,笑道:“不走?把鑰匙給我。”老黃縮著腦袋一笑,趕緊轉身。
自從進了育幼院,老黃頭回這么縮頭弓腰對著別人笑。
老黃住上了兩居室,大間屋給了兒子兒媳,小間和老伴住。比起3平方米多一點的棚屋,實在是寬綽太多了。
這一天,掏運完垃圾,10點來鐘,老黃背著噴藥桶要去給垃圾道噴藥,行在路上,看見三個人,沈騰云、副院長、房管科長。三個人站在辦公樓下說話。
三個人都沒看老黃,老黃自然也沒必要把臉別向另一邊,只是繞開距離,正常走路。不想將要走過三個人時,聽見沈騰云叫:“老黃!”聲音興奮。
老黃一愣,錯愕地看著沈騰云。沈騰云滿面春風,示意那倆人等等,自己一個人笑吟吟地走到老黃身前,說:“樓房怎么樣,滿不滿意?住得夠寬綽吧?”老黃還在錯愕,愣愣地點頭,說:“啊。”沈騰云一臉笑容,臉幾乎湊到老黃耳邊,小聲說:“沒有我,你可分不到房。我說了,這次分房,必須有你!嗯?”
沈騰云的臉退后,笑看老黃。
老黃的臉突然通紅,錯愕漸成憤怒,兩眼漸漸冒火,死盯著沈騰云。沈騰云開始錯愕,正要說話,老黃開口,說:“去你媽的吧!”然后死死地盯著沈騰云。
沈騰云變得氣憤,說,“哎……”
老黃卻轉身走開,頭都不回。走出幾步,聽見了身后房管科長在問:“院長,怎么了?”老黃還是往前走,沒聽見沈騰云說話,不知是離遠了聽不見沈騰云的說話聲,還是沈騰云根本就沒有說。只是突然痛快,好像一個二十五年憋在肚子里的憤怒,突然散了。
不過很快,老黃擔心了,擔心房子。
過了幾天,不知道幾天,老黃路經公示欄,偶然看見公示欄里貼著一張新一屆院領導的公告,忍不住過去看,找沈騰云的名字,竟沒發現。無論院長還是書記,甚至往下,都沒有沈騰云。不覺納悶,一路向垃圾道去,一路疑惑。意外地看見了房管科長,因為有上次分房領鑰匙的事,方才又在公示欄看到他兼任了后勤處長,便一笑,房管科長回了一笑。老黃便站住,說:“科長、處長。”科長處長本已走過了,聞叫回頭,笑看老黃,說:“你倒會叫!干嗎?”老黃說:“問您一下,沈、沈院長,不干了?”科長處長說:“調局里去了,你不知道?”
老黃搖頭。
“升了。”
老黃便覺自己松了一口氣,說:“噢。”要走,被科長處長叫:“別走,我也問你個事。老黃,那天和沈院長你們倆講什么來著?沈院長臉都白了?”
老黃愣了一下,說:“沒講什么。”科長處長又笑了,說:“老黃,真沒看透,堂堂的沈院長為你在分房會上跟那么多人拍桌子,你行啊。”
老黃說:“啊?”
科長處長舉起手,笑瞇瞇地伸食指點點老黃,走了。
老黃如木雕,被陽光照耀,終于能轉身走時,輕輕說了一句,我操。一回頭,哪里有人?
一年后,垃圾站承包給了外方,處長科長讓老黃回鍋爐房。
老黃說:“現在的鍋爐房我還會干什么?我掃院子得了。”
處長科長想了想,說:“行。”
后來老黃就臂上戴一個戒煙的紅袖章,挎個小鐵斗,拿把笤帚,每天在院區里轉,勸人別抽煙,發現煙頭掃入鐵斗。這時候沒有人再說老黃臭了,也不躲老黃了,但是老黃很少和誰說話,偶爾說兩句話,也保持距離。
11
老黃再和沈騰云相遇竟又是二十五年后。
沈騰云調走后沒回過醫院,或者回來一兩次,憑老黃掃地的身份也見不著。
當初分房,也有沈騰云一套,和老黃不是一棟樓,一前一后,老黃住前面樓,沈騰云住后面樓,沈騰云上下班有車接送,并且不久沈騰云就搬走了,這兒的房給了兒子。
老黃不知道誰是沈騰云的兒子。
漸次,這里又蓋起幾棟樓,城中東西南北拆遷的人住進來,四周圍上欄墻,形成一個小區。
小區外面不遠處有個小公園,出了小區步行十分鐘就到。里面青草綠樹,花叢甬路,幾塊廣場,一灣活水。老黃80了,還每天早上到公園里走,走上一圈需半個多小時,再觀觀唱歌跳舞、寫書法的,然后回家。
一天早晨,老黃走完一圈,坐在廣場邊的長椅上看一些人在地上沾水寫毛筆字,一個人從旁邊走過來站在他身邊叫:“黃師傅。”老黃一看,竟是沈騰云,拎著一根漂亮的登山杖,笑吟吟地望著自己。
兩個人都老了,老得幾乎沒有了從前,卻一下子認出來,毫無違和及驚訝,老黃轉不過彎來,一時沒明白沈騰云為什么出現,半天才輕輕哎喲出來,一只手下意識地拍拍身邊空出的座位。沈騰云笑著說:“我在那邊坐著,一看走過來的就是你。你多大歲數了?”
“80。”
沈騰云這才往老黃身邊坐,邊坐邊說:“那我比你大一歲,81。”老黃看看沈騰云說:“不像。你頭發還是那么黑,沒一點白的。瞧我,全白了。”沈騰云一手擋嘴,歪過頭來,略帶俏皮地說:“染的。不染,一樣的白!”老黃笑道:“知識分子!”沈騰云笑出聲,說:“對!”問:“你怎么樣?好吧?”老黃說:“好,沒病,就是老了,渾身上下都不行了。你行,身體比我強。”沈騰云說:“強什么……”于是身體、家里、兒女,二人就聊,聊完這些還說雞零狗碎,你來我往的,停不住嘴。等到終于沒話,各自喝水。沈騰云看看老黃的水杯說:“別喝花茶了,你該喝點普洱,刮刮你這肚里的油!”老黃就笑,拍拍自己的大肚子,說:“待得!吃得。我問你,你不是早搬別處去了嗎?”沈騰云點頭,說:“那邊房讓給兒子了,我們兩家換了一下。他不是干點事業嗎?那邊住的都是有頭有臉的,有人脈。我們老兩口呢,是嫌那邊房間多,太大了,空得慌。覺得這邊好,雖然三居室,緊湊,感覺不出空來。而且原來我想這邊熟人多,醫院的老人,不講身份,坐一塊兒能說說話。沒想到活著的沒幾個了,還都不怎么理我。”老黃說:“為什么?”沈騰云說:“當領導當的唄。他們不像你。對我有什么不滿,我當領導時不敢說,現在不當領導才敢表現出來。哪像你,面對面你就敢罵我。呵呵。”
老黃沉默了一會兒,見沈騰云一直看著自己,硬硬地說:“是你過分!”
沈騰云便不再看老黃,看著眼前過來過去的人,自言自語地說:“唉,當時生氣,一個人時一想,也不氣了。那時我被他們關了6個月,那天把我放了。我走出來時,愛人在醫院大門外面等著我,坐公共汽車回我父母那兒。全程我都沒說話,我愛人問過兩句就不敢問了。到了我爸媽那兒,父親、母親沒說什么,就講坐下吃飯。我不說話。桌上一盤紅燒肉,我就一塊一塊地吃,吃一塊又一塊,也不就飯,還專夾肥的。原來我不吃肥的,那天我專挑肥的吃。我媽想說什么,被我爸攔了。攔時我看見了,也知道他們都在小心翼翼地看著我。他們都不夾肉。我卻像不知道似的一個勁兒吃,急不可耐的,一塊連一塊,往嘴里填。其他的飯和菜,一動不動,看也不看。我愛人看不下去了,起身離開,我卻還在吃。連吃兩盤,我才放下筷子。什么也不說,直接躺在床上。暈暈乎乎,迷迷瞪瞪,就像喝酒喝醉了,可是心里清楚,什么都明白。明白得我難受、哪兒都難受!耳朵聽著他們收拾桌子,出屋。他們把門一關,我的眼淚就下來了,一個勁兒流,我就覺得我是那么可恥!”
停了一會兒,沈騰云好像平靜了,轉回頭來注視老黃,見老黃一副沒明白的樣子,接著說:“其實我早應當跟你說聲謝謝。很多機會,吃包子時想說,沒說出來,吃饅頭時也沒說出來。想不到的是,這一聲謝謝,往后就說不出來了,當了這個當了那個以后更說不出來了。”
老黃說:“為什么呀?”
沈騰云看著老黃,突然尷尬地一笑,小聲說:“分房的事,我不應該說……”
老黃說:“我操,我可不是因為這個。我是惱你揭發我。我就給你帶個饅頭、一塊咸菜吃。你揭發出來干嗎?那有什么可揭發的?能幫你什么?害得他們要搞我?”
沈騰云愣愣地看著老黃,說:“怎么會?怎么會是我揭發?”老黃說:“誰?你在拐角里吃饅頭,那老劉即便出來也不往拐角去,看不見你吃,關在屋里的人也看不見。就你知我知的事,你不說我不說,他們怎么知道的?還把我叫過去,審我……”
沈騰云說:“也審我呀。那是味兒!”老黃說:“什么味兒?”沈騰云道:“嘴里吃過茴香餡包子的味兒和吃過饅頭的味兒……”老黃說:“我操,那包子有味兒我信,饅頭也有味兒?”沈騰云說:“讓你連吃六個月窩頭,喝稀湯,還永遠吃不飽。別說吃了嚼了,當時我從房里一出來就聞見拐角有饅頭。吃完回屋,誰能聞不出來?”
老黃說:“我操。”然后兩個人臉對著臉看了片刻,突然爆發,哈哈大笑,身體亂抖。把周圍人嚇一跳,紛紛地看這兩個老人。
后來,兩個人沿著一條甬路向園外走。老黃雖然80了,卻不拄拐,只是行得慢,輕甩著兩只手,像個鴨子。沈騰云拿著登山杖,雖然拄著,其實就是為了風度。身板、腰腿,看著就比老黃有勁兒,步子堅實,卻不超過老黃,二人并肩,走著、聊著。
正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溫暖明媚。
作者簡介

毛建軍,北京市朝陽醫院退休人員。曾在《北京文學》發表中篇小說《北京人》《虎烈啦》《小捷的故事》,在《當代》發表中篇小說《第三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長篇小說《美順與長生》。中篇小說《北京人》獲《北京文學》新人獎。
責任編輯?侯?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