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我的老師
華霖
每次有畢業(yè)多年的學生回來看我,我總是為之感動,總會問我的兩個孩子,你們有回母校看望老師嗎?不等他們回答,我總會自己先答,其實我也沒有回去看望我的老師。
在教過我的老師中,常常讓我想起的是小學時期的李老師。
李老師擔任我們班班主任那年,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據(jù)說她之前因為超生被取消了老師編制,帶著孩子在農(nóng)村喂豬好幾年。現(xiàn)在,是以代課老師的身份來擔任我們的班主任。因為是代課老師,她每月拿到的薪資很少很少,因此她在教書之余,還得繼續(xù)喂豬增加收入養(yǎng)家。
當時我們班是出了名難管的班級,換了幾任班主任也沒能解決同學們上課吵鬧的不良習慣。上課故意刁難老師者有之;埋頭吃零食者有之;甚至有同學上課打架……但李老師來擔任班主任后,我們班的紀律明顯轉(zhuǎn)好。
“你們現(xiàn)在不好好讀書,將來男的只能下地扶犁耕田,整天臉朝黃土背朝天;女的只能提潲桶喂豬。”這是李老師擔任班主任以來,每次上課前要對我們說的話。
那時的我們不諳世事,不懂得讀書的重要性,跟我們講大道理,我們也絕對是左耳進右耳出。但經(jīng)李老師這樣提點,作為農(nóng)村的孩子,很容易體會到其中的要點。
每次上課鈴一響,她準會大踏步進入教室。習慣性地拿起教鞭,板著面孔,先在黑板上大力地敲幾下,待同學們都安靜下來時,她才來到講臺前,兩手撐住講臺,面帶微笑,圓而大的雙眼如探燈一般在全班來回掃射。
“你們現(xiàn)在不好好讀書,將來男的只能下地扶犁耕田,整天臉朝黃土背朝天;女的只能提潲桶喂豬。”李老師的聲音如洪鐘般在教室回蕩。同學們聽了,停止喧鬧,幾十雙眼睛齊刷刷地看向講臺,靜待李老師開講。在確保教室里沒有搗亂者了,她才開始講課。除了書本上的知識,她總要講一些歷史故事或一些幽默小笑話。
一個金秋十月的傍晚,我背著書包踽踽而行在回家的路上,為放學后還要回家?guī)湍赣H干農(nóng)活而苦惱。我習慣性地抬起頭望向遠處半山腰——我家的那塊番薯地,我經(jīng)常去那里幫母親割番薯藤喂豬。隱隱約約,我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已在番薯地里勞作,我滿心歡喜,覺得那肯定是母親,這樣我可以不用上山割番薯藤了。
可是,在不遠處田間勞作的父親告訴我,在番薯地里勞作的是李老師。那年我們家種的番薯特別多,來不及收割,正好李老師養(yǎng)豬需要飼料,來幫我們收割。這次后,父親常跟我提起李老師,說她不僅書教得好,而且還能上山勞作,跟農(nóng)民也合得來,是一位好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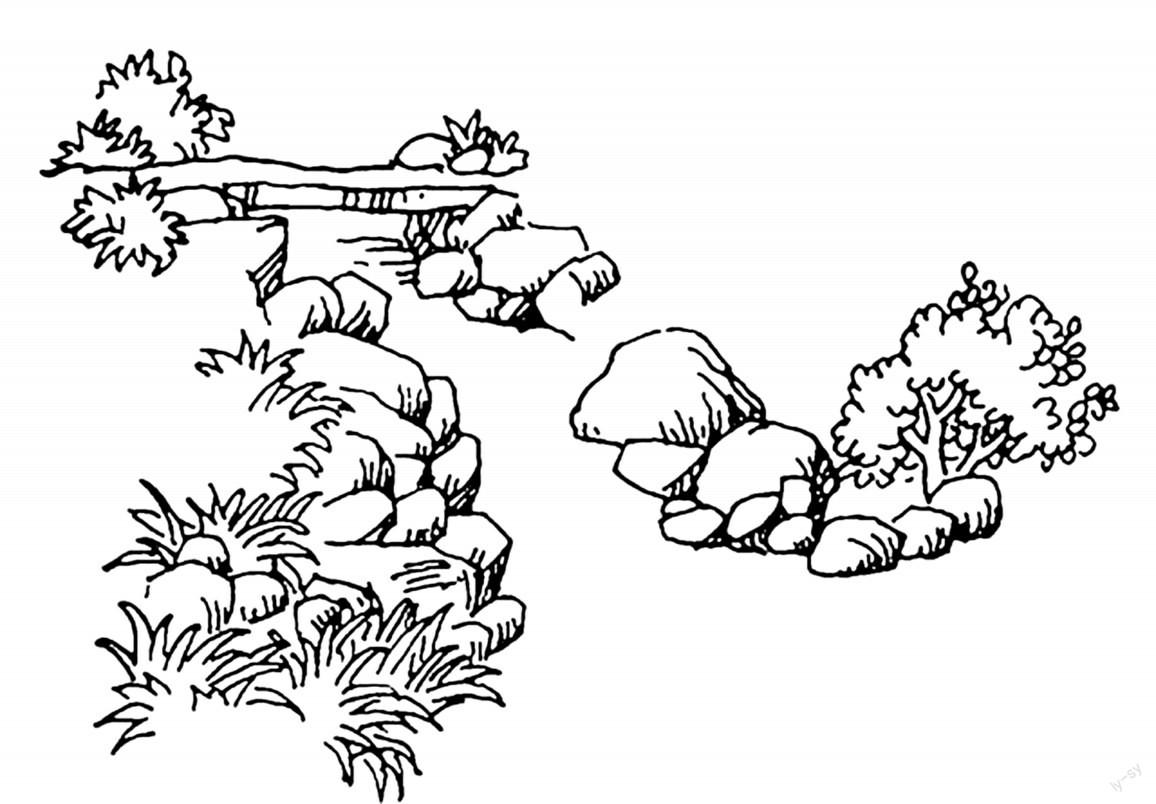
遠遠地,我看見李老師挑著重重的兩捆番薯藤,艱難地行走在陡峭的羊腸小道上,一股莫名的感動涌上心頭。我不禁想起了常年在山里田間辛勤勞作的父母及祖祖輩輩生活在這山里的人們;想起小小年紀的我及小伙伴也要上山勞作的艱辛……
“你們現(xiàn)在不好好讀書,將來男的只能下地扶犁耕田,整天臉朝黃土背朝天;女的只能提潲桶喂豬。”李老師的話語再一次在我耳邊響起,想必,她在農(nóng)村喂豬幾年及現(xiàn)在教書之余還要喂豬養(yǎng)家,著實很辛苦,因此才這樣深切地呼喚我們要好好讀書。我頓時明白了她反復強調(diào)我們要好好讀書的苦心。
回到家放下書包,我第一次不等母親吩咐,主動上山割了番薯藤回來后,拿起書本認真閱讀。也就是從那時起,閱讀成為了我的終身伴侶,改變了我人生的軌跡。
晚飯后,母親開始準備喂豬的飼料,一直忙到深夜。我在煤油燈下做作業(yè),心卻無法平靜。看著忙碌的母親,李老師的身影在我眼前浮現(xiàn),想著她此時是不是也在忙著喂豬呢?是不是也要忙到深夜呢?那堆積如山的作業(yè)改完了嗎?第二天會不會耽誤給我們上課呢?
第二天上課的預備鈴聲響起,我盯著教室門口,看見李老師仍是那樣神采奕奕,如期大踏步進入教室,那如圓月般的臉龐上沒有一絲倦意,鼻翼上那顆黑痣把她的皮膚襯托得格外白晳。
下課時,家住李老師附近的同學告訴我,李老師昨晚不僅工作到深夜,還因一些家庭瑣事和她男人吵架了,他聽到了李老師的哭泣聲。我轉(zhuǎn)頭看向還坐在講臺前埋頭為同學們批改作業(yè)的李老師,試圖從中看出點什么,但除了看到她時而點點頭;時而面露微笑外,看不出一點悲傷與苦惱。
我十九歲離鄉(xiāng),定居惠州,很少回去,一直沒見過李老師。前不久,聽兒時的玩伴說李老師一家子都遷往了Y市,也很少回去。我希望,下次回老家時,能遇見她。
李老師,我之所以常常想起她,不是因為她有卓越的學識,主要是她以最樸實的方法,教會了我讀書的重要性。
——選自西部散文學會微信公眾平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