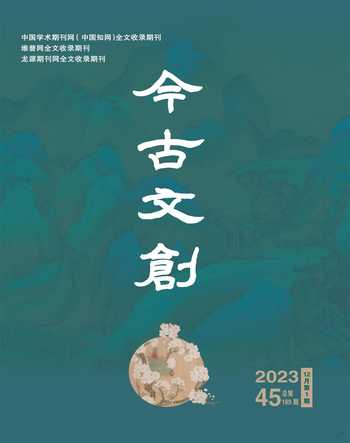“大時代中拚發出來的一朵火花”
【摘要】本文以光華書局于1930年創辦的《讀書月刊》為研究對象,在“書業廣告雜志”的發展脈絡、光華書局的經營計劃,以及1930年代的文化環境中考察《讀書月刊》的性質與傾向,由此討論該刊的辦刊策略。
【關鍵詞】《讀書月刊》;光華書局;1930年代
【中圖分類號】G259?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45-007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5.021
1930年秋,《讀書月刊》由光華書局創辦于上海,由顧鳳城主編,其“征稿簡章”列出的五大板塊——各科學習法及研究法、讀書經驗談、書報介紹與批評、讀書錄與讀書札記、各地文化的情形及文壇消息[1],大致概括了刊物的主體內容。1931年下半年,受戰事等因素影響,該刊遭遇了嚴重的脫期問題,最終于1933年停刊。《讀書月刊》是逐漸被人們遺忘的“小刊物”,但它的自我定位、整體面貌與辦刊策略是值得研究的話題。
一、《讀書月刊》的創辦及刊物性質
面對剛剛問世的《讀書月刊》,一位讀者立刻想到先前出版的同類型刊物的不盡如人意之處,表達對于“‘出版界’或‘開明’似的那樣廣告式的小冊子”[2]的不滿意。“五四”以后,伴隨著新文化與新書業的共同繁榮,評議出版動向、分享讀書心得的文章獲得了不少受眾,專為它們搭建的發表平臺也應運而生;同時,各大書局探索出了新的自我宣傳方式,即通過創辦書報介紹類期刊為讀者提供便利,并借此集中宣傳該書局的出版物,潛移默化地引導讀者的購買意愿。由出版商創辦、以書報介紹為主題的期刊陸續問世,在當時的期刊界中形成了一個門類,它們被稱作專門的“書業廣告雜志”[3]。而被上述讀者批評的《出版界》與《開明》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它們多登載自我宣傳、書報介紹、文化批評類文章,呈現出“廣告式小冊子”的形式。相較而言,《讀書月刊》有著別樣的面貌,它的頁數較多,內容豐富多樣,并多次設置主題明確、頁數增多的“專號”;其編者還提出了理想化的辦刊目標,著眼讀者的實際狀況,解答讀者普遍關注的問題,有較強的知識普及意識。因而,在當時的出版環境中,《讀書月刊》給人以鮮明的印象,而促成這一效果的種種因素值得考察。
光華書局是出版界的后起之秀,其創始人與泰東圖書局、創造社關系親密,該書局對新文學潮流有著敏銳的洞察力,出版了不少帶有左翼傾向的書刊。然而自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當局發布了一系列針對進步書刊的禁令與審查條例,這對“小書局”來說是較為嚴重的打擊,為了持續、穩定地運行下去,光華需要適當轉變經營方針。此時,學生需要的、意識形態傾向不明顯的書籍,如教科書、辭典、指導用書等,遭到查禁的可能性相對較小,不少新老書局以此作為出版的重頭,光華也采取了這一策略,這便催生了作為讀書指導刊物的《讀書月刊》。
《讀書月刊》本是光華讀書會早期的入會贈品之一,亦是發表會員作品的平臺,在“讀書會會報”(即《光華讀書會月刊》)創刊之前,它擔任了光華讀書會“機關刊物”[4]的角色。讀書會是光華書局的一次“大膽的嘗試”[5],其程序是讀者繳費成為會員后便能獲贈書報,可以優惠價購買該書局的出版物,還能借助專門的刊物與其他會員互通聲氣。讀書會既能聯絡讀者,為志同道合者提供交流結伴的平臺,又以多樣的優惠、附贈品減輕讀者的購書開銷;成功募集到一定數量的會員后,讀書會便有了為書局吸納資金、開拓市場,增強書局知名度的效用。讀書會的制度與組織興起于國外,1920年代末,開明等書局已經開始了讀書會的嘗試[6],之后,不少新興的、小有名氣的“小書局”為了在文化界站穩腳跟,也借助讀書會融資、宣傳,并紛紛創辦與讀書會掛鉤的刊物,以便更好地凝聚讀者。光華書局吸取了前人的經驗并取得了較好的成績,在30年代成立了一個規模較大的讀書會,并為其他出版機構后續創設的讀書會提供經驗。《讀書月刊》最初的刊名“光華月刊”[4]也值得注意,這意味著它能夠與光華讀書會及光華書局的出版計劃互相配合,樹立起書局的品牌形象,并且,它是展現書局為青年學生群體服務、致力于文化事業的宗旨的一個窗口,幫助光華書局通過書籍、報刊、讀書會等渠道走進讀者的生活。
辦讀書會、書業廣告雜志是出版商重要的盈利手段,不過出版商總是努力掩飾其追名逐利的動機,同時,光華書局本身并非唯利是圖的出版機構;因而,書局同人將讀書會的組織納入“讀書運動”[7]的設想,以推進出版界的良性發展為目標,努力給讀者留下可靠、高尚的印象。相應地,《讀書月刊》的編者也明確地提出該刊的“使命”,希望“養成青年讀書興趣,指示青年讀書方法”[8],編者還自詡“最近全國讀書空氣之濃厚,亦讀書月刊鼓吹之力也”[9]。這些宏大的理想也反映于《讀書月刊》多樣化的內容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它作為廣告刊物的特征,使書局樹立品牌形象、把握商機的意圖變得間接化、隱形化。可以說,《讀書月刊》突破了書業廣告雜志的傳統辦刊模式,兼具商業性與獨立性的面貌,《讀書月刊》的復雜屬性在其辦刊策略、實際運作、讀者反響之中得到體現。
二、《讀書月刊》的辦刊策略
光華書局在宣傳其辦刊成績時提到,《讀書月刊》“創刊號出版后,銷路甚廣,蓋專以讀書為標的之刊物,在中國尚屬創見,亦為現時一般青年群眾所迫切需要者”[10]。一位讀者也提到“像貴刊那樣的刊物,在目前的國內的出版界,可以說尚是創見的”[11]。書業廣告雜志已有多年的發展歷史,因而《讀書月刊》的“創見”與其受歡迎的原因,便不只是選擇“專以讀書為標的”,而是它基于這類期刊的已有辦刊模式展開的拓展與革新。
(一)讀書、學生與文學創作:對于刊物主題的選擇
伴隨著新文化的廣泛傳播、出版業的趨于成熟,新書出版也有繁榮以至“泛濫”之勢,面對不斷涌現的書刊,對于青年學生來說,“讀什么書”與“怎樣讀書”成了亟待解決的兩個問題。《讀書月刊》不僅考慮到了當時學生群體的興趣與需求,介紹了新文學作品、外國文學、社會科學等方面的書籍,還注意到了讀者們對于基礎學科入門的普遍困惑,將“讀書指導”與“一般基本學識及各種學科的學習方法”[8]作為重點。《讀書月刊》向青年學生群體傳遞知識的方式也較為多樣。其設置的欄目有書業廣告雜志中常見的“介紹與批評”,分享讀書方法和學科知識的“讀書經驗”與“講座”,發表研究論文的“作品研究”,以及傳遞書報發行消息、各地文化界動向、文人軼事的“出版界”等。《讀書月刊》還設置了“各科研究法”“我的讀書經驗”“文學研究”“各科研究入門”專號,既幫助期刊吸納訂戶,刺激了期刊的銷量,又能將多篇文章聚集于同一話題下,使頁數較多、內容專門的期刊具備了教科書、輔導書的性質,拓展了期刊的功能。可見,從文學到各類學科,從基礎知識到專門研究,《讀書月刊》為學生群體提供了多領域、多層次的指導。此外,當該刊物被讀者視作教科書時,它便發揮了學生類期刊的另一層價值。如《青年的自學問題》一文所述,青年可以通過訂閱雜志進行自學,將雜志視作自己的導師[12]。當時社會中有許多沒有機會接受學校教育或無法繼續升學的青年,他們對知識的渴望極其強烈,而通過閱讀這類被稱作“現代讀書人的課本”[13]的期刊,他們仿佛獲得了學生的身份,擁有了許多學習資源,這也是該刊受讀者認可的一大原因。
《讀書月刊》與文學創作的關系也值得注意。該刊中的文學創作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讀者的投稿,發表于“全國學生創作選”專欄。“全國學生創作選”與光華書局舉辦的征文活動有關,它為沒有機會在雜志中發表作品的一般讀者搭建了平臺,對青年學生的創作予以認可。另一類是“小說”“詩”“青年園地”等欄目下的創作與少數譯作,其中小說占據的篇幅較多。此類作品的登載也引出了一些問題。編者發現來稿的十分之九是小說創作,不得不向讀者聲明“因為本刊不是一個純粹的文藝刊物,所以決既容納不下這許多小說的”[14]。也有讀者提出,《讀書月刊》“似乎太偏重于文藝方面”[11],希望編者重視對其他領域的介紹。這些現象指向了夏丏尊面對出版界提出的引人深思的疑問:“為什么一般人都喜歡把學生雜志編成了文藝雜志,須知學生所要看的并不完全是文藝呢,我真是不得其解!”[15]
事實上,在30年代讀書人的思想與生活中,文學占據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尤其對于青年讀者來說,與時代、現實息息相關的新文學作品有著極強的感染力,讀者往往在文學中寄寓自己想象與情感,他們的生活方式也在有意無意間受到文學敘事的影響。于是,期刊編者有意識地凸顯刊物的文藝色彩,登載各類文學作品(尤其是極具影響力、易于在青年之間流行的小說)。這樣的安排一方面是繼承了在報刊中設置一定文藝欄目的傳統,用以調節期刊內容,滿足讀者的興趣,為讀者提供放松休閑的材料,進而提高期刊的銷量。另一方面,在注重思想、理論的傳播,希望啟蒙、指導青年讀者的刊物中,文學能夠承擔引導的作用[16]。讀者對于《讀書月刊》的文學式接受頗有深意,這樣的印象也為研究文學在30年代語境中的位置與價值提供了材料。
(二)“Journalism”與時代:對于刊物傾向的塑造
在談及對于《讀書月刊》的印象時,一位讀者說“像介紹與批評,作家論,現代中國作家錄,出版界消息,文壇消息等欄,極為我們所歡迎”[11],編者也意識到“本刊的出版界消息,文壇消息,各地文化通信等,極為一般讀者所贊賞”[17]。文藝新聞、文人印象、文化通信等受讀者歡迎的欄目位于《讀書月刊》的后半部分,有時這些版面之前還有作為提示的文字或插圖,顯得較為醒目。不過,這樣的設計同樣并非《讀書月刊》的“創見”。這一時期,刊物要想長久生存下去,就必須考慮讀者的閱讀偏好;若設置一定的“軟性”內容,則能調劑期刊的整體氛圍,引起讀者的興趣與購買欲,而名人軼事、文化類新聞可供人在茶余飯后翻閱消遣,成為各類期刊津津樂道、用以吸引讀者的話題。在報刊固定的位置登載篇幅短小、輕松有趣的內容也早已成為報刊編者使用的一種常規策略。于是,面對新創辦的《讀書月刊》,讀者很自然地依據已經形成的經驗與習慣,首先尋找他們愛讀的版面與欄目:“先生,你猜我接到月刊以后先讀那些東西?呵,我先讀那篇‘本刊的使命’及‘編輯以后’,而后讀‘出版界消息’,‘國內文壇消息’及‘中國現代作家錄’,再而后始讀‘介紹與批評’及小說等等。”[2]
事實上,上述欄目的設置既是出于吸引讀者的考慮,也反映了《讀書月刊》的另一個重要的辦刊策略。在第二卷第三期《讀書月刊》中,編者提出了一條富有深意的設想:“我們預備把讀書月刊的下面一部分完全成為一種Journalism一樣,變成一個純粹的文化新聞的樣子”[18]。“Journalism”被譯為“集納主義”,它是一個多義詞,可以指稱新聞事業、報紙雜志、報刊文字風格等[19]。在當時的語境中,“Journalism”常被用來描述30年代上海報刊界呈現出的新趨勢,即收集、展示多樣的材料,“注重有時間性的報告材料,并在極短的時間內供給讀者以多方面的知識”[20]。一些報刊將其視作理想的辦刊效果。
1932年,魯迅面對文藝類期刊的標榜“Journalism”提出“各省,尤其是僻遠之處的文藝事件通信,是很要緊的”,“各國文藝界消息,要多,但又要寫得簡括”[21],而《讀書月刊》對“文藝新聞”類欄目的設計與此要求有一致之處。《讀書月刊》不僅登載了讀者習以為常的文壇名家軼事,還招募外地文化通訊員,以較多篇幅介紹地方、外國文藝界的動向,這類消息不僅幫助新文學作家、研究者、批評家便捷地獲取文藝界的新聞,也為一般讀者打開眼界。各類具有時效性的新聞、通信等在雜志中營造了文藝的“空間”,通過閱讀期刊,讀者能夠展開一種囊括了國內與海外的“文藝界”的共時性想象,并意識到自己也能直接參與到“空間”之中,感受時代的氣息。
《讀書月刊》對時代的觀察不僅體現于雜志的后半部分。“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中國民間與文藝界紛紛發出抗日救亡的號召,《讀書月刊》也立即對時事動向予以回應,于1931年10月出版的《讀書月刊》第二卷第六期是“反日運動特刊”,設置了“反日運動特輯”,發表了多篇研究、評議國際時局的文章。此后,編者有意識地調整了刊物卷首的內容,以有關世界經濟、政治局勢的文章作為開場白,展現了對于時事的關注。書局一方也對這一傾向加以宣傳,強調該刊“第三卷起,更革新內容”,“俾青年明了國際情勢之轉變,以及當代文壇之動態”[22]。此外,該廣告詞中的“當代文壇之動態”之語也值得注意,這一話語與《讀書月刊》中有關新興文藝思潮的討論相呼應。光華書局是左翼文藝的重要出版機構之一,《讀書月刊》的創刊號中就有“我們介紹和批評書報的態度,當然是要站在時代的前面,以推進社會的進化為原則”之語[23],《讀書月刊》介紹了不少進步的作家作品,發表了左翼作家的文章,并且編者將該刊第三卷第五期設為“文藝論戰專號”,其卷首登載了涉及普羅文學、文學階級性、大眾文藝等話題的討論文章。“革命文學”是20世紀30年代文壇中最為重要的話題之一,對于相關作品、思想、理論的討論不僅直擊讀者普遍關注的問題,也使得《讀書月刊》與時代潮流靠攏。
三、結語
《讀書月刊》的創刊與運作歷程反映出了書局、出版界、文壇、讀者之間的緊密聯系與交流互動,它的出版策略背后有著對于特定讀者群體的想象,以及吸引讀者興趣、影響讀者精神世界的意圖。在這一層面,《讀書月刊》是“大時代中拚發出來的一朵火花”[24],人們可以通過該刊管窺20世紀30年代初上海的文化環境。
參考文獻:
[1]讀書月刊征稿簡章[J].讀書月刊,1931,1(3/4).
[2]國揆.讀書會信箱(二)[J].讀書月刊,1931,1(3/4).
[3]吳永貴.民國出版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340.
[4]上海光華書局啟事(一)[J].讀書月刊,1930,1(01).
[5]沈松泉.關于光華書局的回憶[A]//俞子林.百年書業[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32-33.
[6]夏孝萍.民國書業讀書會研究[D].武漢大學,2019.
[7]云生.擴大我們的讀書運動[J].光華讀書會月刊創刊號,1931.
[8]編輯以后[J].讀書月刊,1930,1(01).
[9]出版界與著作家(八)光華出版刊物近況[J].讀書月刊,1931,1(06).
[10]出版界消息(一)光華書局一九三一年出版計劃[J].讀書月刊,1930,1(02).
[11]姚如響.讀書會信箱(四)[J].讀書月刊,1930,1(02).
[12]維文.青年的自學問題[J].讀書月刊,1931,1(3/4).
[13]鐘天培.讀書會信箱(三)[J].讀書月刊,1931,1(05).
[14]編輯以后[J].讀書月刊,1930,1(02).
[15]賀玉波.夏丏尊訪問記[J].讀書月刊,1931,2(03).
[16]唐小兵.民國時期中小知識青年的聚集與左翼化——以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為中心[J].中共黨史研究,2017,(11).
[17]編輯后記[J].讀書月刊,1931,2(01).
[18]編輯后記[J].讀書月刊,1931,2(03).
[19]張勇.“集納主義”與30年代海派文學[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9,(03).
[20]張炳鈞.集納主義的報紙副刊 中國報紙副刊的新趨勢[J].眾志月刊,1934,1(02).
[21]魯迅.我對于《文新》的意見[A]//魯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368.
[22]讀書月刊廣告[J].文學月報,1932,1(01).
[23]本刊的使命[J].讀書月刊,1930,1(01).
[24]鳳城.編者的話[J].讀書月刊,1932,3(1/2).
作者簡介:
孫麗麗,女,漢族,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