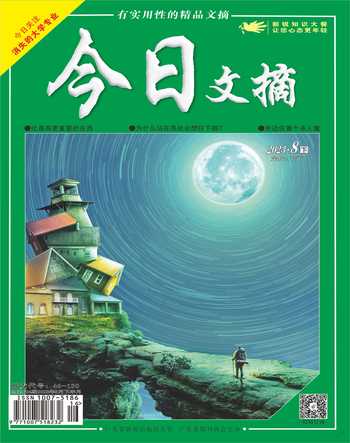返老還童,真的有可能實現嗎?

塞思·庫克患有一種十分罕見的遺傳病,他是目前美國患有這種疾病的人中最長壽的幸存者。他的頭發已經全部掉光,皮膚上布滿皺紋,動脈血管也開始硬化。他的關節也因為關節炎而時不時地疼痛。他每天都要服用阿司匹林和血液稀釋劑。
而他只有12歲。
早衰癥是什么
塞思患的是早年衰老綜合征,通常被稱為“兒童早老癥”或“早衰癥”。早老癥是一種極端罕見的疾病——在每400萬至800萬名新生兒中,僅有1例這樣的病例。
患有早老癥的兒童,其身體衰老的速度是正常人衰老速度的10倍。當早老癥患者長到大約1歲半的時候,他或她的皮膚就開始起褶皺,頭發也開始脫落,心血管疾病,比如動脈硬化,以及像關節炎這樣的退行性疾病,很快也會隨之而來。大多數的早老癥患者通常會在十幾歲時死于心臟病發作或者中風,目前還沒有早老癥患者活過30歲。
另有一種早老性疾病叫作“維爾納綜合征”,攜帶這種疾病致病突變的人通常到青春期才會表現出臨床癥狀,因而它有時候也被稱為“成人型早老癥”。青春期過后,維爾納綜合征患者便開始快速衰老,通常在50歲出頭的時候就死于與年齡有關的疾病。維爾納綜合征雖然比早年衰老綜合征更為常見,但是它仍然非常罕見,其發病率僅為百萬分之一。
由于這些導致快速老化的疾病都太不常見,所以它們一直以來都不是科學家研究的焦點。但是隨著科學家意識到,他們已經掌握了正常老化過程的線索之后,情況開始有了改觀。
2003年4月,研究人員宣布他們已經分離出了導致早老癥的突變基因。這一突變發生在負責產生一種叫作laminA(核纖層蛋白A)的蛋白質的基因上。
在正常情況下,laminA為細胞核膜提供了結構上的支持,而細胞核膜的作用是把基因物質集中在靠近細胞中央的一個區域內,以利于實現其功能。laminA就好比是支起帳篷的支柱——細胞核膜圍繞在它的周圍,并由它支撐著。在早老癥患者的體內,laminA是有缺陷的,因此細胞老化的速度要快得多。
2006年,另一組研究人員在laminA突變與正常人類衰老之間建立起了聯系。他們發現,正常老年人的細胞表現出了與早老癥患者的細胞相同的缺陷——它第一次證實了,在基因水平上,早老癥的加速老化與正常人類的老化過程有關。
這項研究的意義是很深遠的。自從達爾文描繪了適應、自然選擇和進化的藍圖之后,科學家就一直在為老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爭論不休。
老化難道只是一種日久磨損的過程,就像是你最喜歡的一件襯衫在穿著多年以后,染上了污漬、破了洞,最終磨損殆盡、不能繼續再穿了嗎?或者它是進化的產物?換句話說,老化是偶然發生的還是有意而為之?
早老癥和其他加速老化的疾病表明,老化是預先設定好的過程,它是程序設計的一部分。想想看,如果單個基因錯誤能夠導致嬰兒或者青少年加速老化,那么老化就不僅僅是由一生的經久磨損造成的。
早老癥基因的存在恰好證明了可能是基因控制了老化過程。
當然,這也引出了一個你毫無疑問會想到的問題:我們是按照程序走向死亡的嗎?
逆轉老化的可能
我相信程序性老化會給整個物種而不是個體帶來進化上的好處。按照這種想法,老化就像是“計劃報廢”的生物學版本。計劃報廢是工業上的一種策略,雖然產品制造商們經常會否認這一觀念,但是依然會廣泛采用:從冰箱到汽車的所有制造商都有意為其產品設計了有限的使用壽命,令產品在被使用了有限的幾年之后就報廢。
這樣做是為給制造商帶來更多利益。首先,這使得產品可以不斷地推陳出新、更新換代。其次,這意味著你需要不斷地購買新的產品。幾年前,一部分人指控蘋果公司在超人氣的iPod的開發中采用了計劃報廢的策略——它們的電池只有18個月左右的壽命,而且無法更換,從而迫使消費者在電池壽命耗盡時不得不購買新型號的產品。
而生物上的報廢,也就是老化,可能是為了達到兩個類似的目的。首先,通過清除舊的型號,老化為新的型號騰出了空間,而其最終的目的是為改變,也就是為進化提供空間。其次,老化可以通過消滅病魔纏身的個體來保護整個群體,防止它們感染下一代。通過交配和繁殖,物種便可以不斷地改良和升級。
程序性老化的研究前景為各種激動人心的可能性打開了大門。科學家已經在探索將老化機制關閉或者重新開啟可能會給人類帶來的益處。
研究人員也通過研究證明,人類有可能逆轉由早老癥引起的細胞損傷。他們在實驗室中給早老癥細胞貼上了一種“分子創可貼”,并且消除了有缺陷的laminA。一周之后,他們治療的細胞中有90%以上看起來都恢復了正常。雖然研究人員目前還不能在人體內逆轉早老癥,但每一種新的嘗試都是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的充滿希望的一步。
“老化”和“逆轉”——這是很值得我們期待的事情。科學家已經能夠在實驗室中逆轉這些老化過程了,“長生不老”與“返老還童”,也許已經近在咫尺。
(林月桂薦自《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