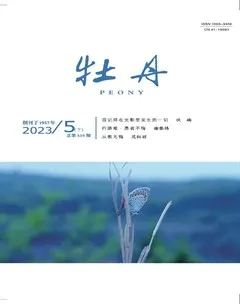基于陌生化視角分析《瓦內姐妹》中的加密策略
俄裔美國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1899—1977年)是20世紀具有顯著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他不僅在文學和翻譯方面博采眾長,在昆蟲學和象棋等方面也卓有建樹。《瓦內姐妹》是他出版的68部短篇小說之一,其中高超的隱喻、互文、反諷、雙關等藝術手法的應用無一不體現他精湛的文字處理能力,而敘事手法的選擇亦體現出作者的時空錯置觀念。
陌生化,亦曰離間效應,是俄羅斯形式主義者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年)首創的術語。它是一種創作方式,通過解構傳統并加以創新,產生欣賞者與作品之間的距離美。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游戲精神源于其童年時追捕蝴蝶和下象棋的體驗,這在他的文學創作中表現為各種加密策略的運用。“我沒有社會目的,沒有道德信息;我沒有一般的想法可以利用,我只是喜歡用優雅的解決方案編寫謎語。”他的聲明非常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本文運用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論,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對《瓦內姐妹》進行研究,分析其在語義轉換和敘事結構上的具體應用,以此探索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加密策略和游戲精神。
一、《瓦內姐妹》中的語義轉移
陌生化手法的首要要求是“克服語言的自動化傾向”。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加密意識和游戲精神首先體現在《瓦內姐妹》中的命名游戲和戲仿與用典,目的是使讀者在看到人物名字時能自然聯想到相關的隱含含義,使讀者“不會留下第一印象,最終甚至忘記了它的本質”。因此,從語言層面來看,陌生化有意利用語義轉移使話語意義部分或完全偏離,阻礙讀者的閱讀過程,以延長其閱讀時間。
(一)命名游戲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善用藏頭詩,他在《瓦內姐妹》的前言中暗示了藏頭詩是故事核心的“獨特戲法”。故事的開始,當敘述者在小鎮漫步觀賞融化的冰柱時,他遇到了D教授,并得知了畫家辛西婭·瓦內(Cynthia Vane)的死訊。正文是“我”對瓦內姐妹的回憶,講述了西比爾·瓦內(Sybil Vane)逝世后給姐姐辛西婭的生活帶來的各種超自然現象,但“我”視之為天方夜譚。故事的最后,敘述者開始混淆現實與虛構的關系。每個單詞的首字母拼接起來,組成了一句話,即“冰柱是辛西婭所為,停車計時器來自我,西比爾”(Icicles by Cynthia, meter from me, Sybil)。因此,藏頭詩是辛西婭從彼岸世界傳達信息的方式之一。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筆下的頭韻與諧音變幻多端,或是元音、輔音相同,或是多個單詞首字母相同,它們可以是名詞、動詞、形容詞或副詞,變化無常,無規律可循。“閃亮的冰柱往下滴答淌水”(brilliant icicles drip-dripping),“這對孿生的閃爍很好看”(This twinned twinkle was delightful),“反射出鉆石般炫目的光”(the dazzling diamond reflection),“一連串被我觀察和觀察著我的事物”(the sequence of observed and observant things),“撕心裂肺的回憶”(wailing and writhing memories),“考爾克蘭或是考蘭斯基”(Corcoran or Coransky)……大量頭韻的使用反映了作者對“詩的精確和純科學”的追求,而諧音的出現一語雙關,體現了作者熟練的駕馭能力。標題“The Vane Sisters”與“The One Sisters”發音相似,意指辛西婭與西比爾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體。下文中重復出現的意象鏡子則再次暗示了兩姐妹互為鏡像,是現實與想象、時間與空間的并置。
象征是文學創作的一種藝術手法,它借助具體的形象表現抽象的意義,揭示事物本質。作為文中唯一一個以大寫字母命名的人物,D教授的名字也是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設置的文字游戲之一。作者借用美國浪漫主義作家霍桑《紅字》的寫作手法,賦予D教授的名字豐富的象征含義,而這種寫作手法的運用與《紅字》中女主海絲特戴在胸前的字母A如出一轍。結合西比爾生前的感情遭遇可以推斷出,字母D象征著西比爾的逝世(Death)、黑暗(Dark)、惡魔(Demon)和欺騙(Deceive)。
此外,在希臘神話中,月亮女神阿爾忒彌斯本名叫辛西婭Κυνθια(Kynthia),而《瓦內姐妹》中辛西婭的名字則是希臘語的拉丁化形式,意為“來自月亮的女人”。西比爾的名字“Sybil”是中世紀古英語“Sibyl”的變體。在柯林斯詞典中,它指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被認為是神諭或先知的婦女。值得注意的是,西比爾與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另一短篇小說《微暗的火》中虛構詩人謝德的妻子西比爾(Sybil Shade)同名。而shade有“陰影”之意,引申為現實世界的對立面,即鏡像世界。結合文中西比爾自殺后辛西婭生活中存在的種種超自然現象不難發現,西比爾雖然來自彼岸世界,但對現實世界仍會產生不可抗拒的影響。鏡像在小說中無處不在,如人名與地名的重復、相似或相同單詞的并列及情節布局等,這些是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加密策略的最佳例證。
(二)戲仿與用典
什克洛夫斯基認為,戲仿是一種“裸露藝術手法”,是打破詞語的“自動化”,使文學形式“陌生化”的手段之一。對于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來說,“諷刺是一堂課,戲仿是一場游戲”。因此,《瓦內姐妹》中對戲仿的靈活應用體現了作者的游戲精神。
一方面,辛西婭的家庭變故真實地影射了作者自己的人生經歷。文中提到,辛西婭癡迷于無序的詞語、雙關語和字謎等,而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也擅用這些藝術手法。此外,“辛西婭出身于一個良好的、受人尊敬的家庭”,但是當“轉移到一個新世界”時,這個家庭沒落了。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出生于俄羅斯圣彼得堡最繁華的地區——斯卡亞街的名門望族,在父親被沙皇主義者暗殺后,家庭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事實上,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對辛西婭的家世敘述是對自己家族過往的回憶,是一種思鄉懷舊情緒的寄托。而這種回憶解構了情節發展的線性邏輯,引導讀者偏離敘述進程,增添了文本的閱讀難度。另一方面,《瓦內姐妹》在內容上對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其他小說進行了模仿,構成了文本間的相互指涉。D教授對西比爾的感情戲仿了《洛麗塔》中亨伯特對少女寧芙的感情,而《瓦內姐妹》和《洛麗塔》不謀而合的感情模式又戲仿了19世紀美國偵探小說之父愛倫·坡《厄舍府的倒塌》的主題。因此,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通過引用原作中的人物特征和主題安排,建立起與原作的互文關系。
戲仿憑借神話典故、圣經原型和經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來展示小說主題。在《瓦內姐妹》中,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把戲仿變成一種虛構且無序的語言游戲。作者在文中提到,波洛克去世后,辛西婭曾讀到“一首不朽的詩(一首她和其他容易上當的讀者都相信是在夢中寫成的詩)”,這首詩正是柯勒律治的名詩《忽必烈汗》。它是柯勒律治服用完藥物后在夢中創作的,但被“一個來自波洛克島上的商人”打斷。“波洛克島”與文中的人物波洛克吻合。此外,“詩中的‘Alph’正是預示性的序列,由‘Anna Livia Plurabelle’的詞首字母縮略而成;這個詞組指的是另一條圣河,流過或流經另一個虛構的夢”。Anna Livia Plurabelle是詹姆斯·喬伊斯的小說《芬尼根守靈夜》中的女主人公安娜·麗維雅,在書中,作者用芬尼根的逝世和復活來隱喻人類歷史的循環發展,他還用大量的雙關語和迷宮般的結構建構出一個龐大而復雜的夢境,這與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文學創作手法不謀而合。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引用詹姆斯·喬伊斯的典故,旨在贊同他強調事物無序性和形式重要性的觀點,反駁弗洛伊德認為夢起源于人的潛意識的觀點。在《瓦內姐妹》中,制謎高手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或隱或顯地與詹姆斯·喬伊斯的作品構成參照和平行類比關系。讀者可以將它看作一部諷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小說,其中體現了對詹姆斯·喬伊斯和柯勒律治寫作傳統的繼承。
二、《瓦內姐妹》的敘事結構
什克洛夫斯基認為“情節”是敘事中事件被安排措置的時序。在《瓦內姐妹》中,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通過運用“發現”和“突轉”及環形結構對情節結構進行重置,表現他復雜的時間和空間意識。因此,從敘事層面來看,陌生化手法通過對既定風格和流派的反處理,避免單一線性敘事,表達作品的主旨和內涵,最終達到陌生化的效果。
(一)“發現”與“突轉”
“發現”與“突轉”起源于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發現”是指“從不知到知的轉變”,它可以是敘述者對自己身份或是他人的重新認知,或是對事實真相發現;而“突轉”指行動從一個方向發展至相反方向。什克洛夫斯基常將它們用于敘事結構的陌生化處理,以此達到使讀者驚奇的效果。
在《瓦內姐妹》中,辛西婭首先講述了一連串來自彼岸世界的神秘力量在現實世界的運作,比如母親對其藝術創作的影響、妹妹西比爾的種種暗示等。讀者或許會和敘述者一樣,對辛西婭的無厘頭講述感到荒謬至極,判定辛西婭為一個精神失常的畫家。然而,故事情節在敘述者得知辛西婭去世后開始“突轉”。當他晚上獨自待在房間時,各種古怪的聲音朝他襲來,使他無法安心入睡。于是敘述者的觀念發生轉變,他開始相信辛西婭生前所述,并明白自己無法對抗來自彼岸世界的力量。故事的最后,敘述者把每個單詞的首字母重新組合在一起,組成一句話,“冰柱是辛西婭所為,停車計時器來自我,西比爾”。這句話既是瓦內姐妹對無知的敘述者的無情嘲諷和有力反擊,也是讀者和敘述者達到精神頓悟的時刻。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通過“發現”與“突轉”手法的聯合運用,構建出跌宕起伏的情節,激發讀者的想象力,引導讀者站在敘述者的視角,層層撥開真相。
(二)環形敘事
一般說來,“小說乃是由于拓展而變得復雜的環形和梯形結構的組合”。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在《瓦內姐妹》中采用首尾環形結構,刻意打破傳統敘事“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的模式,變為“開端—發展—高潮—結局/開端”,使小說結尾又重新回到敘述的起點。正如謎面和謎底的關系一樣,“明亮的冰柱”和“拉長的計時器”意象的首尾重復出現,不僅賦予故事圓形結構,也揭示了時空錯置主題:“我”所在的現實世界受彼岸世界的瓦內姐妹所控制,她們通過把“我”的思想和記憶與自然事物聯系起來,實現與現實世界的自由交流。小說自由穿梭于過去和現在,敘事時間并不與故事時間保持一致,敘事之始即敘事之尾,呈環形發展。
此外,與辛西婭形成對比的西比爾雖始終未出場,但卻如影隨形般出現在辛西婭的日常生活中,造成一種神秘效果。現實世界的辛西婭與彼岸世界的妹妹西比爾是一組鏡像關系,這組人物的并置彰顯了時空的主題,而時空主題是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敘事迷宮的重要元素,是探索其加密策略的關鍵。
三、結語
加密策略的進行是隨著讀者對小說大量細節的注意和建立聯系才得以發生的,一次又一次的重讀和聯想建構讓讀者參與“我”的回憶和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藝術創造。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在語言和敘事方式上設置謎語,不僅層層加密了熟悉的字母和詞語,也以一種新的方式呈現出時空主題。他諷刺性地戲仿或反諷傳統小說,打斷敘述時間的線性發展,創造出離散的敘事內容和去情節化的結構,首尾呼應的環形結構鮮明地表明了作者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看法。這不僅達到了陌生化的效果,延宕了閱讀進程,還使讀者以全新的視角審視已知事物,體驗到審美快感,從而將遠與近、光與影、現實與想象連接起來。
(西安外國語大學英文學院)
作者簡介:江心月(1998—),女,河南信陽人,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美國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