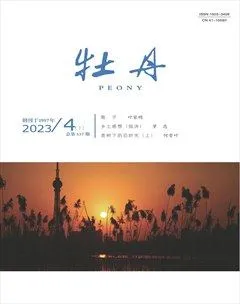論愛瑪陷入愛情悲劇的必然性
《包法利夫人》是法國文壇巨匠福樓拜的作品,它講述了年輕貌美的愛瑪因過分追求情欲和物欲,無節制地揮霍財產,欠下巨款,最終自殺而死的悲劇性命運。表面上她是因欠債過多無力償還而自殺,實質上她的悲慘命運是外部的時代不良風氣、家庭情感關照的缺失與其內部的激情錯誤轉向共同造就的。由于外部環境的限制與愛瑪自身的局限性,她必然會走向悲劇的結局。
一、不良時代風氣的犧牲品
《包法利夫人》的創作背景是在19世紀40年代,七月革命推翻了復辟的波旁王朝,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在法國建立起來,法國資產階級取得了主導地位。盡管封建貴族階級在經濟、政治領域上受到了嚴重打擊,日趨敗落,但他們長期以來在中下層人民中產生的精神領域上的影響仍然根深蒂固,整個社會彌漫著向往貴族奢靡生活的不良風氣。盧歐老爹便是深受貴族之風影響的人物之一,他認清了自身的局限性:祖上是放羊的,自己是地地道道的農民,一輩子都在鄉下經營著貝多爾農莊,和貴族完全沾不上邊。于是他把愛瑪看作了自己的理想載體,希望愛瑪能夠實現他在自己身上沒能實現的貴族理想,從女兒的身上獲得慰藉和心理滿足。在這種心理的驅動之下,他把愛瑪送進修道院接受教育,培養貴族式的言行舉止和興趣愛好,希望愛瑪日后能夠嫁給貴族,躋身上流社會。然而,修道院并沒有制定嚴格的規章制度用以督促修女們貫徹崇拜圣徒、克制肉欲、拯救靈魂的思想,這為愛瑪接受世俗讀物創造了客觀條件。
有一個老姑娘,“是大革命摧毀的一個世家的后裔”,每月來修道院一次,她給她們講故事、唱情歌,私下里還總帶傳奇小說給修女們看,這些世俗讀物讓涉世未深的愛瑪每天都沉浸在對貴族愛情生活的向往和幻想中。“進修道院頭一陣子,她并不覺得枯燥乏味”,但久而久之,平靜事物的枯燥更加刺激了愛瑪的性格,愛瑪天生充滿激情、生機勃勃的個性與修道院禁欲壓抑的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她讀司各特、巴爾扎克等人的作品,卻看不到他們作品中的現實主義批判精神,所關注的僅僅只是能給人帶來一時享樂的風流韻事,“她讀司各特,愛上了古代的風物,夢中也看到蘇格蘭鄉村的衣柜,衛士的廳堂”。
隨著客觀條件與主觀感情的雙向推動,愛瑪被幻想中的自我帶偏,希望自己能與風度翩翩的貴公子相愛。這位貴公子一定要是博學多才的,上曉天文,下通地理,能帶領她共同領會生命的力量、宇宙的奧妙。而當愛瑪離開修道院回到家后,農村的惡劣環境一下子使她從美好的幻想之中抽離出來,誘發了她對于現實生活的不滿,而她對現實生活的不滿情緒越高漲,在行動上就越趨向于逃避。理想生活與現實狀況的巨大落差,性格思想與自身境遇的極大錯位,讓她再也忍受不了平淡無味的日常生活,她任由自己沉浸在想象的溫床里,這便是墮入悲劇的開始。
二、家庭情感關照的缺失
原生家庭對孩子性情、心理的塑造有很大的影響。愛瑪的原生家庭并沒有給予她足夠的情感關照與正確的價值引導,這是導致她陷入愛情悲劇的重要原因。她四歲喪母,從小就缺乏細膩的母愛,沒有人教她如何自尊自愛,如何從自身尋找價值。盧歐老爹作為愛瑪唯一的監護人,沒有給予愛瑪足夠的情感關照。在物質上,盧歐老爹不懂得投資理財,花錢大手大腳,“他不高興操勞,生活方面,一錢不省,衣、食、住,樣樣考究。他喜歡釅蘋果酒、帶血的烤羊肉、拌勻的光榮酒”。他的這些生活習性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愛瑪:在婚后并不殷實的家庭條件下,愛瑪仍然花錢如流水,買上好的窗簾、地毯、沙發料和衣服,只為滿足自己向往奢靡的情懷;婚后愛瑪多次出軌,在和情人幽會時堅持要排場,為維持巨額開銷,在奸商勒樂先生那里欠下高額債務,簽下一張又一張期票,期票到期時又想盡辦法變賣舊手套、舊帽子等各種物品,最后甚至把盧歐老爹送的六把鍍金小鑰匙也拿去換錢了。在資本主義金錢觀的引誘下,她親手把自己送進了債臺高筑的深淵,走向了愛情和生命的終點。
盧歐老爹對愛瑪精神需求的忽視,是導致愛瑪把愛情寄托在遐想的人的身上的直接原因。在婚姻大事上,他自始至終都沒有想過要真正地去了解愛瑪的想法,走進愛瑪的內心世界,自然也就不知道愛瑪需要的是一位能與她旗鼓相當的精神伴侶。盧歐老爹挑選女婿完全出于他自己的立場,為了減輕自己的物質負擔,他認為盡管查爾不是出身于貴族,不是他期待的完美女婿,但聽說“人家說他品行端正,省吃儉用,很有學問,不用說,不會太計較陪嫁”,在一番權衡利弊之后,還是決定把女兒嫁給他。而查爾對愛瑪越界行為的包容,只會更加助長愛瑪的虛榮氣焰,越來越肆無忌憚地向外界追求物欲與情欲。愛瑪不滿于原有的平靜的婚姻生活,相繼陷入與羅道夫、賴昂的不正當關系中,可愛瑪愛的真的是羅道夫、賴昂這兩個人嗎?實質上,愛瑪愛的不是具體的人,而是抽象的、遐想的一類人,她所迷戀的是與這類人交往時的曖昧氛圍。給羅道夫寫情書,愛瑪“見到的恍惚是另一個男子、一個她最熱烈的回憶、最美好的讀物和最殷切的愿望所形成的幻影”。歸根結底,愛瑪的愛不僅僅是渴望博得以子爵為代表的貴族的關注,更是內心最深層次的精神需求的一種反映。愛瑪之所以會把精神需求寄托在遐想的幻影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幼年時期并沒有受到父親正確價值觀的引導和足夠的情感關注,長久以往,她不能看到自身的價值,就走偏鋒,把自己當作貴族男人的附屬物,向他們尋求情感
寄托。
三、激情的錯誤轉向
愛瑪豐富細膩的女性情感,加之幼年在修道院受到浪漫主義愛情小說的熏陶,她對浪漫的、傳奇性的愛情充滿了憧憬。然而,懷揣著這樣的幻想,她卻在盧歐老爹的安排下嫁給了包法利先生——一個呆板木訥的男人。他的見解平庸,不會游泳,不會騎馬,不會使劍,與愛瑪心中理想丈夫的形象大相徑庭;他也聽不懂愛瑪吟誦的情詩、彈奏的樂曲,無法和愛瑪產生思想上的碰撞和精神上的交流。查爾雖然很愛她,但卻不知如何去愛,無法給她想要的精神上的愉悅,她“好像沉了船的水手一樣,在霧蒙蒙的天邊,遙遙尋找白帆的蹤影”。
渥畢薩爾之行讓愛瑪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貴族的生活,舞會上,一位“子爵”邀請她跳了一輪回旋舞,這不正是她傾慕的理想對象嗎?她享受著紙醉金迷的舞會,搖曳著婀娜多姿的腰肢,希望時間能夠永遠停留在這美好的一刻。然而,那位請愛瑪跳舞的子爵沒有任何越界之舉,也沒有給她任何暗示,她理想中的愛情終究只是鏡中花、水中月,美好的幻影經不起現實的敲擊,一碰就滅。舞會結束,愛瑪回到家里,她忍不住悲嘆生活的辛酸,憎恨命運的不公,想不明白為什么那些腰身比她粗、舉止也比她俗的公爵夫人過上了她幻想中的美妙生活,而有著精致臉蛋的她卻只能在狹小的屋子里日復一日地辛苦操勞。在幼年時期就已種下的虛榮的種子,在物欲的刺激下以驚人的速度肆意生長起來,從此她的心中片刻不得安寧。她的浪漫情懷逐漸變為無法言說的失望,只能把激情錯誤地轉向對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已經變得乏味而危險的世俗的貪戀,在肉欲和物欲的雙重引誘下,踏上了一條浪蕩的不歸路。
在永鎮她結識了賴昂,他年輕而富有詩意,對自然充滿好奇與探索心,與向往風雅的愛瑪情投意合。但愛瑪礙于廉恥,只得克制住自己的情感,把欲火壓在心里。肉體的渴求、金錢的欲望和情感的抑郁夾雜在一起,使她更覺痛苦。而賴昂由于本身怯懦的性格,加之不明白她的態度,很快就厭倦了沒有結果的愛情,轉向浮華的巴黎求學。愛瑪燃起的激情再次跌入了谷底,這時羅道耳夫來到了他的身邊。羅道耳夫自負、風流,是個十足的情場老手,他垂涎于愛瑪的美色,一心想把愛瑪搞到手。愛瑪自然經不起他的調戲,很快就投入了羅道耳夫的懷抱。而當羅道耳夫享受夠了情欲的歡愉,對漂亮女人的征服欲得到滿足之后,這個逢場作戲的花花公子就對愛瑪失去了興趣。終于,在愛瑪慫恿他帶她一起私奔時,羅道耳夫寫了一封“絕交書”與愛瑪徹底了斷。羅道耳夫的決絕給沉溺于情欲的愛瑪帶來沉重的打擊,她幾乎昏倒了。
在激情的自我放縱之下,她并沒有迎來理想中的愛情,婚外情帶來的后果卻只能由她自己來承擔。為了維持奢靡的生活和幽會的開銷,她一直暗中預支金錢,一次次賒賬、借貸,一次次簽字畫押,延期還款,導致欠下的高利貸遠遠超出了她的償還能力。為了還債,愛瑪先后向曾經的情人賴昂、羅道耳夫求助,但他們都以各種理由推脫,和她撇清關系;去向居由曼律師借錢,卻被他下流的舉止侮辱,她果斷拒絕了用出賣肉體來換取金錢。愛情理想的破滅,鋪天蓋地的欠款,情人的欺瞞背棄,澎湃激情的無處投放,重重壓力下,愛瑪選擇用服下砒霜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大概,在異乎尋常的平靜之中,她又感到了最初信仰宗教時的那種快樂,并且看到天國的永恒幸福已經開始”,在她去世之時,她認清了理想與現實之間無法調和的矛盾,在恍惚中找回了最初信仰宗教的純潔與虔誠。
愛瑪死后,在整理妻子遺物時他卻發現了愛瑪的婚外情,他是多么的難以置信!查爾的心情跌入谷底,整日在屋中喝酒消愁。后來在某天遇見了羅道耳夫,面對愛瑪曾經的情人,查爾默默地把所有痛苦壓在心里,只是無奈地把所有的不幸都歸咎于命運。最終,查爾坐在葡萄棚下的長凳上平靜地離開了人世,他年幼的女兒也被迫送入紗廠工作,老太太離開了人世,盧歐老爹癱瘓了。愛瑪及其親人接二連三地陷入了慘痛的悲劇命運,但那些直接或間接置她和家人于死地的資產階級的代表們的日子卻蒸蒸日上:羅道耳夫在莊園里高枕無憂,賴昂生活得安安穩穩,勒樂“商界驕子”運輸社開業了,郝麥的藥店顧客盈門……福樓拜有意塑造這些丑惡不堪的資產階級形象,他們的命運與愛瑪及其親人的悲劇結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給人以強烈的心靈沖擊,揭露了社會的階級性與不合理性。
愛瑪的悲劇是社會的悲劇,并具有普遍意義。她的閱歷與眼界讓她有了脫離實際的幻想,每當她以為她已經找到救贖時,現實又給予她沉重的一擊。毀滅愛瑪的是一個充滿惡俗、精神貧乏的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下的金錢、物質、欲望引誘著她拋棄心靈的純潔,變得世俗、丑惡、貪得無厭。理想與現實、物質與精神之間的巨大沖突,使她在現實生活中痛苦不已,卻又無力改變,她在追求物欲的過程中被心靈和精神世界拋棄,精神逐漸變得扭曲。愛瑪帶有浪漫與悲劇色彩的愛情具有揭露社會的現實意義,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任何置于其中的女性都難以避免走向毀滅的結局。
四、結語
愛瑪的悲劇不僅是其自身的悲劇,還是社會的悲劇,她是資本主義的犧牲品,必然會走向悲劇性的結局。她墮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追根究底是受到墮落的宗教生活、崇尚貴族奢靡生活的不良時代風氣的影響,也和家庭關照的極度缺失有關。她把澎湃的激情轉化為對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已經變得乏味而危險的世俗的貪戀,在一步步的墮落中逐漸被純潔的心靈和精神世界拋棄,無可避免地陷入了愛情悲劇。
(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