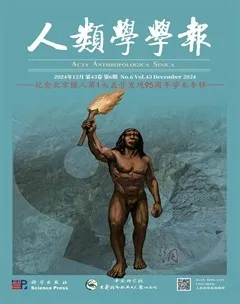青藏高原舊石器時代考古發現與研究



關鍵詞:青藏高原;舊石器時代;石器技術;人類活動
1引言
青藏高原位于亞洲中南部,是大約45 Ma前印度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相互碰撞的結果,也是全球隆起最晚、面積最大、海拔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的隆升歷經多個時段,并非一次性事件。從晚上新世開始,高原整體開始隆起,同時局部地區快速抬升,最終形成北達帕米爾高原北緣、西昆侖山和祁連山山脈北麓,南抵喜馬拉雅山等山脈南麓,西起興都庫什山脈和帕米爾高原西緣,東至祁連山東端、橫斷山等山脈東緣,總面積308.34萬平方千米、平均海拔約4320m 的“世界屋脊”[1,2]。
高聳的“世界屋脊”深刻地改變了世界構造格局,更對全球環境與生物演化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氣候層面,強烈的隆升改造了亞洲的海陸分布,增大了海陸熱力差異,塑造了東亞季風氣候與陸地景觀的基本模式,并在此過程中形成了新的水循環格局,促進東亞硅酸鹽風化和有機碳埋藏,從而成為地球環境變遷的驅動因素[3]。在生物演化方面,早至晚始新世胡頹子科等植物的早期代表已在西藏出現,之后擴散并廣布于其他地區[4]。札達動物群等青藏動物群的發現,指示一些高原物種自晚中新世開始適應寒冷環境并進化,且在此后向歐亞大陸與北美中高緯地區擴散,挑戰“冰期動物起源于北極圈”的假說[5]。而這些證據說明青藏高原是現代生物多樣性形成過程中的“演化樞紐”[4] 。
青藏高原在人類演化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與地位長期被忽視。青藏高原海拔高,有效積溫低,凍土廣布,生物量密度小,紫外線輻射強烈且氧氣稀薄,季節性氣候變化顯著,資源斑塊質量時空變化大[6],對古人類的遷徙、交流和開發構成了嚴峻的挑戰,通常被認為是人類,尤其是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難以踏足的“生命禁區”。青藏高原處于隆升區域,從客觀條件看,古人類文化遺存的保存條件較差,同時該區域自然環境和交通條件較為惡劣,科考工作開展困難,因此青藏高原的古人類- 舊石器遺存發現非常少。近二十年來,隨著考古工作的持續開展,不斷涌現的考古材料使青藏高原正逐步成為古人類適應輻射研究的一大焦點。本文聚焦于高原腹地西藏自治區境內的打制石器遺存的發現與研究,以期管窺青藏高原的舊石器考古學發展。
2 西藏舊石器時代考古工作回顧
青藏高原的舊石器時代考古可追溯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人愛德加(J Huston Edgar)與包羅士(Gordon T Bowles)在西康(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發現兩件手斧[7],但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并沒有針對舊石器遺存的系統調查與發掘。解放后的很長一段時間之內,舊石器考古仍然未得到重視,許多發現是由地質等工作者偶然所見。1956 年,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現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趙宗溥等開展青藏高原地質普查時在西藏黑河以及青海沱沱河、可可西里和格爾木等地發現十余件打制石器,正式揭開了青藏高原舊石器考古發現的序幕[8]。1966~1968年,中國科學院西藏科學考察隊于珠穆朗瑪峰地區開展綜合考察時,在定日縣與聶拉木縣發現了打制石器遺存[9,10]。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隊在那曲、阿里、日喀則等地區又發現多處石器遺存地點[11-14]。上述地點的標本均為地表采集,考古學者并未參與野外調查,僅在室內對標本進行了觀察研究。這一時期的研究者一般根據階地位置或者石器風格對遺存的大致年齡進行推測。
1984年起,西藏自治區文管會先后組織三次“全區文物普查”,標志著西藏田野考古進入新階段。其中1990-1992年開展的第二次普查,有陜西省文物局、湖南省文物局和四川大學考古系等多家區外單位參與,于雅魯藏布江上游、獅泉河及象泉河流域以及那曲、山南和拉薩等地區調查發現多處新的石器地點。前后兩次全區文物普查中,較知名的打制石器地點有仲巴縣城北地點、哈東淌、卻得淌、夏達錯等[15]。除普查外,西藏自治區也開展了數次專題性調查,如2003-2004年,西藏博物館考古部、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考古系與西藏地市及文物文化部門在青藏鐵路(西藏境內)考古調查中發現多處石器地點;2004年,西藏文物局和四川大學考古系、藏學研究所組成“象泉河流域考古調查隊”也發現少量石器地點[16-18]。這一時期,隨著專業考古人員的加入,西藏舊石器遺存的數量與分布廣度均大幅增加,進一步豐富了西藏舊石器文化的面貌。不過需注意的是,新的發現仍然以地表采集為主,缺乏遺址年代學與地層埋藏證據支撐。
在上述工作進行的同時,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青海鹽湖研究所、蘭州大學等機構與美國沙漠研究所、亞利桑那大學等在青海省也開展了一系列工作,發現了一批打制石器遺址[19-22]。這些位于青藏高原東北緣的遺址雖然未經正式發掘、文化面貌不甚明了,但是剖面中保存的炭屑和動物碎骨提供的可靠碳十四測年結果,大大推進了高原舊石器時代考古的研究。研究者提出人類可能在更新世晚期擴散到這一區域,其留下的遺存大多不超過30 kaBP,并隨著氣候和環境變化,經歷了領地的擴張和收縮[23,24]。
二十一世紀初,青藏高原舊石器考古不斷取得重大突破。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蘭州大學和四川大學等研究機構在“考古中國”、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等項目的助推下聯合攻關,擴大了舊石器時代考古調查規模,并發掘了一批遺址,通過多學科研究手段,逐步解決了高原舊石器遺存的埋藏與年代問題,實證了舊石器時代人類對世界屋脊的探索與開發歷史。隨著工作的深入,高原舊石器時代的時空譜系正在逐步建立,新的成果也不斷成為國內乃至國際學界的熱點,考古學研究從發現、發掘、文化面貌闡釋、年代框架建立、人類行為解讀、人地關系分析、人群互動與遷徙歷史溯源、高原適應機制探討等多個維度全面鋪展。
3 西藏舊石器時代考古發現
經過幾代學者數十年工作,青藏高原迄今發現的打制石器遺存已達110余處(詳見本文網絡版附屬材料),涵蓋了手斧、石葉、細石葉、石核- 石片等四種技術模式,時間跨度長達十多萬年(圖1)。
3.1 手斧/阿舍利技術
手斧是一類特殊的兩面器,“典型的”手斧長度應在10 cm 以上,兩面、兩側基本對稱、輪廓呈淚滴或梨形。這一“典型”定義通常關聯著阿舍利傳統或“模式Ⅱ”概念,并與薄刃斧、手鎬等組成聯系緊密的石制品組合。近幾十年來,百色盆地、秦嶺等地區的發現使得東亞阿舍利產品逐漸得到學界認可[25]。
皮洛遺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縣西2km,平均海拔超過3750 m,地處金沙江二級支流傍河的三級階地上。遺址南北長約2000m,東西寬約500 m,總面積約100萬平方米。初步的光釋光測年結果顯示,遺址第3 層的年代不晚于距今13萬年前,出現了以板巖為主要原料制作的手斧、手鎬、薄刃斧等器物,特別是手斧呈三角形或水滴形,兩面修理,加工程度高,器形對稱,修長薄銳,顯示出高超的修理技藝。皮洛遺址的發掘,揭示了“目前東亞地區形態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術最成熟、組合最完備的阿舍利組合”[26],結合高原周邊區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有關手斧發現的線索,顯示阿舍利技術人群最晚在中更新世末期到晚更新世之交曾經擴張到了青藏高原東南緣地區。
西藏自治區僅報道了夏達錯、尼阿底兩處疑似手斧地點。其中,尼阿底的所謂手斧“只是形似、或偶爾為之的器物”[27],不屬于阿舍利工業。有研究者認為夏達錯早期采集的兩件石器“器身兩面都保留有局部平整的礫石面,器體經交互剝離的兩面加工,刃部呈之字型,基部有調整”,“屬確鑿無疑的早期手斧”。此外,夏達錯還發現一件薄刃斧和單邊砍砸器。這些證據被用于表明“擁有阿舍利工業的早期人類可能在舊石器時代中期已經到達西藏西部一帶”[28]。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這些石器與尼阿底情況相同,“是石核、硅質巖角礫或者偶爾剝落的、較大的石片刃緣經初步修理,修理疤痕非常淺,形似手斧和薄刃斧”,并且周邊石制品和火塘炭屑的測年結果都顯示這批材料屬較晚時期,不符合阿舍利技術存續的時代[27]。由于這批材料公布不詳,難以對其技術屬性進行深入探討,且暫無年代與共生器物組合信息作為參考,因此,現階段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阿舍利手斧技術在海拔4000 m 以上的高原腹地出現。
3.2石葉技術
石葉作為石葉技術的標志產品,通常被定義為兩側邊中上部平行或近似平行,背面有平直的脊,長度一般為寬度的2 倍或以上,寬度超過12mm 的石片。然而在實際操作中,由于不同的剝片技術可能產生相似的產品,這一重視測量屬性的定義容易擴大石葉的范圍。因此,還需分析石器整體組合面貌和技術流程來確定遺址石葉界定的準確性, 進而綜合判斷是否屬于石葉技術[29]。
青藏高原眾多石器地點的報道中時常提及石葉。但是由于學者對術語的使用有差異、且材料刊布有限,許多地點是否真正存在石葉技術仍然有待甄別。據已發表的圖版,青海省西北冷湖1 號地點發現有石葉[19,24],而在其南的羌塘自然保護區內的數個地點也發現了一定數量石葉和石葉石核遺存[19,30]。在藏北,色林錯及其衛星湖周邊[31] 及此區域內的青藏鐵路沿線那曲河地點[18] 也疑似采集到石葉,但并未發現明確的石核等其他石葉技術標志物。另外,劉景芝認為各聽遺址存在石葉但并未提供翔實的證據[32],該遺址最新的調查和發掘也未能驗證這一點。
迄今為止,青藏高原僅有西藏尼阿底一處遺址出土了技術特征明確、年代可靠的石葉技術遺存。作為石器加工場所,尼阿底遺址第1 地點的文化遺物包括了石葉石核、石葉產品及以石葉為毛坯制作的石器在內的全套石葉產品技術組合[33],這也為早年在色林錯周邊石葉的發現提供了佐證。最新的測年結果顯示,尼阿底人群早至距今45ka以前便已在此活動[34]。尼阿底的石葉技術主要利用成熟的棱柱狀石葉石核,并未發現勒瓦婁哇技術要素[33],羌塘遺址亦可見近棱柱狀的石葉石核技術[30]。青海省冷湖遺址發現的石葉則有似勒瓦婁哇的特征,與水洞溝遺址相似[19],然而這一觀察沒有得到詳細的技術分析支持。此外,筆者近期在冷湖的調查中也未發現石葉技術相關的產品,因此,高原上是否存在勒瓦婁哇技術產品仍然存疑。
目前,高原上缺少更早或同時期的石葉技術遺址,因此該技術傳統來源指向低海拔地區。根據現有的考古學證據,毗鄰高原的低海拔地區(比如南亞、東南亞以及中國南方等)罕見同時期的石葉技術遺存,僅中國西北地區的寧夏水洞溝遺址具有典型石葉產品,可能與高原存在一定的聯系。從更大范圍來看,以石葉技術為標志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初段(InitialUpper Paleolithic)遺址廣泛分布于高原西部的帕米爾高原、西伯利亞阿爾泰、貝加爾湖,以及蒙古國北部等地區。因此,尼阿底石葉技術應為早期現代人在亞洲中部及北部和中國西部之間人群遷徙和文化互動的結果。研究者利用最低成本路徑分析方法基于地形和坡度對人群向高原擴散的最優路線進行的模擬表明,高原腹地與周邊地區石葉技術人群的交流存在兩條可能性較大的路線:一是從西伯利亞和蒙古北部橫穿戈壁,經水洞溝連接高原腹地;二是從北亞地區繞戈壁邊緣經中國東北部連通水洞溝及青藏高原[35]。由于缺乏足夠的考古學證據,石葉技術人群的遷徙與擴散之路仍是一個待解的謎題,有待于更多發現和高精度綜合研究厘清。
3.3 細石葉技術
細石葉技術產品是高原發現最多的打制石器遺存,相關遺址已經超過了百處[36],幾乎遍布青藏高原的各個區域。細石葉技術在高原的延續時間較長,在后期與陶片、磨制石器等新石器時代因素共存。不過在眾多細石葉技術遺址中,有絕對測年的僅占約五分之一,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東北側,西藏域內有年代數據的細石葉遺存更為罕見。因此本文僅對有絕對年代和采自地表、但無新石器時代文化遺物共存的細石葉技術地點進行討論。
通過技術類型學對比與有限的年代學數據結合,靳英帥等勾勒出了細石葉技術在高原出現與擴散的時空框架[37]。青藏高原最早的細石葉技術地點基本發現于靠近高原東北部自然條件較好、海拔較低的青海湖盆地- 東祁連山地區。這些早期遺址,如江西溝1 號、下大武、151、銅線3 號、黑馬河1 號、婁拉水庫、晏臺東,年代可早至距今14~10 ka,不過由于細石核發現較少,難以確定技術細節。距今8~7 ka,使用楔形石核或半錐形石核技術的人群向黃河源、通天河源和昆侖山口一線移動,并幾乎擴散到了高原的各個角落。青海境內的野牛溝、西大灘、參雄尕朔、拉乙亥,藏南仲巴縣城北遺址[38] 以及新公布的藏北伶侗遺址[39] 已有測年結果。而從技術特征來看,安志敏、劉澤純、Frenzel 與Brantingham 等報道的羌塘保護區、申扎、雙湖乃至普蘭的細石葉遺址也應處于此階段內。隨后這兩種石核逐漸減少,發達的錐形石核技術成為主流技術,在藏北出現了查勒多、亞司、巴家、綏紹拉和珠洛勒等僅有錐形石核或以錐形石核為主的遺址,但尚不能確定其年代范圍。距今5.5 ka 以后,陶器、農業和定居等文化因素進入高原,細石葉技術人群退回藏南、藏東和高原東北側地區的山間峽谷或盆地。
從與華北交界的高原東北側開始的細石葉擴散之路明確顯示出高原細石葉技術與華北細石葉技術之間的緊密聯系。不過一些新發現對該框架提出了新問題。尼阿底遺址第3地點[40] 與夏達錯[41] 分別獲得了距今11~10 kaBP與8.9~8.5 kaBP的細石葉遺存,明顯早于框架所預測的到達時間,因此,進一步探討細石葉人群在高原上快速擴散的驅動因素與條件是十分必要的。另外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當前的框架受限于已有的數據,低估了細石葉人群進駐與擴散的時間節點,未來的研究工作可能為該路線提供新的時間坐標。
青海湖周邊一些細石葉遺址保存較好,文化內涵豐富,分布集中。研究者在技術研究的基礎上,還通過遺物類型、遺址形態對人群的活動模式進行推測,如Rhode 等[42]、Madsen 等[43] 與王建等[44] 對青海湖周圍與共和盆地遺址的比較分析區分出了短期營地、長期營地與動物加工場所等不同的遺址功能。
3.4 石核-石片技術
青藏高原從腹地到邊緣區廣泛分布著一系列石核- 石片技術地點,對于了解舊石器時代狩獵采集人群在高原的分布、傳播與發展十分重要。這些遺址發現的石制品數量較少、且多為地表采集,受材料所限,許多研究僅對采集的典型石制品進行初步整理和報道。相較于其他三類石器技術,高原石核- 石片技術的面貌因其時空跨度大,缺乏可靠的年代和完整的組合、技術分析標準不統一等原因而顯得更為復雜。
一般認為,晚更新世至早全新世的石片石器工業,以蘇熱遺址[10,45]、各聽遺址[32,46] 等為代表,石核均為簡單石核,石器修理程度較淺,原料多為就地取材,為典型的簡單石核-石片技術。石片較小,打片以錘擊法為主、偶見砸擊法;修理以劈裂面向背面的單向加工為主,次為反向和兩個鄰邊交互打擊的錯向加工,加工成的石器多以石片為毛坯,邊刮器、端刮器等各類刮削器較多。研究者根據蘇熱標本與云南宜良、寧夏水洞溝和巴基斯坦索安文化晚期等周邊文化的相似性,將其暫定為舊石器時代中晚期[10]。各聽遺址被定為舊石器時代晚期或新石器時代初期[46]。又有研究者根據珠洛勒等地的“橢圓形的長刮器、長條形圓頭刮器和尖狀器,均與水洞溝遺址出土的同類器物相近似或基本一致”,認為西藏地區存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初段的技術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其中一些地點,如珠洛勒[11]、多格則[14]、仲巴縣城北地點[47] 也采集到細石葉遺存,因此這類石核- 石片技術遺存中,有一部分有可能是與細石葉技術一同進入的,只因缺乏埋藏背景而與細石葉遺存分離。隨著上節所述的一些細石葉遺址的發掘,這些石制品與細石葉技術之間的關系會得到更清晰地認識。
一批采自色林錯周邊的石核- 石片技術產品則體現出刃部臺階狀或多層修整、石器毛坯去薄等特點,袁寶印等認為它們“從類型到技術都表現出濃厚的歐洲舊石器中期文化風格”、可能與“奎納修理法”有關,并根據階地推測其年代為距今40~30 ka[48]。由于這些石器均為地表采集,石器組合并不完整,其剝片技術仍不明確。色林錯周邊[31] 及其以北的羌塘遺址[30] 還報道了少量盤狀石核,但目前難以將二者直接聯系起來。因此,西藏可能存在舊石器時代中期遺存,但尚缺乏充足的年代學和技術類型學證據。
根據目前已有有限的報道材料看,西藏吉隆縣境內發現的哈東淌、卻得淌等打制石器地點,以礫石石器為主,少見石片石器,器型組合也以刮削器和砍砸器為主,不見尖狀器。根據地貌特征和石制品中有砍砸器等類型,研究者推測其屬于中晚更新世[49]。因該類型技術產品在高原上發現非常稀少,這里暫時不單獨列出并作為一個工業類型詳細討論。
目前,青藏高原有年代數據的石核- 石片技術遺址主要分布在東西兩緣。
甘肅省夏河縣白石崖溶洞遺址的研究始于1件距今160 ka前的人類下頜骨化石。古蛋白分析顯示這塊化石在遺傳學上與阿爾泰山地區丹尼索瓦洞的丹尼索瓦人親緣關系最近,確定其為青藏高原的丹尼索瓦人[50]。經過正式發掘和系統測年,目前該遺址已建立距今約190~30ka的年代序列;T2 探方的第2、3、4 和7層沉積物中包含石制品、動物骨骼,并提取出丹尼索瓦人線粒體DNA,測年為距今100 ka 和距今60 ka 前后,甚至晚至距今45 ka前,此外第6 層也出土了一定數量的石制品與骨骼。據初步觀察,其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石器與斷塊,原料多為其周邊石英砂巖和角頁巖,但修理石器較少,許多石片被直接使用[51]。
皮洛遺址的第2 層與第4-8 層兩期均有石核- 石片技術產品出土。其中,下文化層主體為砂巖石核- 石片石器,剝片策略簡單,石器組合以邊刮器、凹缺器、鋸齒刃器、砍砸器等為主;上文化層中,在保留前期砂巖制品的同時,剝片更加復雜與深入的石英小石核數量增加,板巖加工的手斧也有發現,但比第3 層的典型手斧小些。關于這兩期遺存的年代學工作正在進行中[26]。
獎俊埠01 遺址位于甘肅省永登縣境內,位于莊浪河支流的二級階地,光釋光測年結果顯示,文化層的年代為距今120~90 ka 的MIS 5 階段。石制品同樣包括石核、石片、石器、斷塊和斷片等,以附近石英和石英巖質河流礫石為原料。剝片以硬錘直接法為主,偶見砸擊法,而盡管石皮在石片上并不多見,但石片背疤數量較少且方向隨機、石核未展示預制或修理臺面等特征,仍顯示出比較明顯的石核- 石片技術特征。石器類型包括石鉆、刮削器、鋸齒刃器等,主要為片狀毛坯,尺寸較小[52]。
位于高原西部西藏阿里地區的梅龍達普遺址近期報道了早于53 kaBP與不晚于45 kaBP的兩期遺存。初步研究顯示,第一期石制品偏大,石核利用率低,修理較為粗糙,呈現出較早階段石核- 石片技術打制石器的特點;第二期石制品雖仍屬石核- 石片技術,但出現了單面向心剝片的小型盤狀石核和較多以厚石片為毛坯,精致修理的陡刃石器[53]。盡管目前無法判斷這一變化是外源還是內生驅動的,但這依然反映出高原上不僅存在著早期石核- 石片技術,且該技術還在高原內部發生了演化,進而說明梅龍達普的石核- 石片技術存續了一段時間,青藏高原各地區的石核- 石片技術也絕非曇花一現。切熱遺址的發掘顯示在全新世初期細石葉技術進入的前夜,高原西部仍然存在著石核- 石片技術[54]。
4 高原舊石器時代考古學存在的問題與展望
在高原上開展考古工作具有先天的劣勢。缺氧與漫長的寒冷季節嚴重影響考古工作者的野外工作,而廣布的無人區與相對落后的基礎設施也限制了調查與發掘的進行。因此,盡管中國境內的青藏高原面積約258.13萬平方千米[2]、占國土面積的四分之一,但考古遺存的相對密度和絕對數量均與其他區域有較大差距。更為重要的是,高原上強烈的剝蝕作用不利于遺跡和遺物的埋藏與保存。這些不利因素導致對青藏高原的舊石器時代考古文化面貌與年代學框架的認識長期以來相對薄弱。
現有的舊石器考古遺存集中分布于藏北色林錯湖區、羌塘自然保護區、藏西阿里地區和高原東、北部的河湟谷區與祁連山區。由于大部分地點僅經過地表采集,石制品發現零散,難以判斷器物組合特征,更無法建立起石器技術的時空譜系,除細石葉技術外,其余石器技術產品的來源與擴散的路線及時間節點均不明確。考古遺存的類型單一,除石制品外,少見動物骨骼與植物大遺存。人類骨骼目前僅見于白石崖溶洞遺址1 處。人類活動遺跡,如火塘等亦不多見。遺址年代數據缺失或僅有根據地貌位置、石器類型所做的間接推測。盡管青藏高原(特別是高海拔腹地)舊石器時代考古具有埋藏環境和保存狀況等方面的客觀缺陷,但近年來不斷涌現的驚人發現,既為我們展示了高原考古的巨大潛力,更為我們呈現了系統調查、精細發掘與多學科研究在極端環境中探索未知、深挖信息的美好前景。
除了因自然環境導致的材料層面的缺陷,高原舊石器考古學存在的另一個困難在于建立古人類在高原適應與擴散的理論模型。有關高原早期人類活動歷史的兩大核心問題是:人類何時最早踏足青藏高原以及人類何時永久定居于此。
關于該主題,Brantingham 等人提出的“三段跳”假說最具影響,并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很好地解釋了當時的考古學材料。該假說認為,距今25~15 ka,狩獵采集者從高原東北側的平緩地帶“漫游”到了海拔較低的高原邊緣進行季節性活動。在新仙女事件之后,狩獵采集者進入海拔3000~4000m的高原中海拔地區,并與海拔大于4000m的高海拔地區存在資源流動,從事季節性或全年性活動。距今8.2ka之后,高原上出現了一批較為特殊的石制品,這可能來源于因全年居留高原導致的“定向選擇(Directional Selection)”。距今6 ka 左右,農業人口進入則代表永居高原的完成[24]。
近年的考古發現表明,古人類進入高原的時間遠早于此前認為的距今25 ka 以前。更為重要的是,關于早期高原居民的來源也存在異議。正如呂紅亮指出的,此模型所描繪的是一個“東邊的故事”[28]。與此相對的觀點認為印巴次大陸的古人類通過西南側的通道進入高原,在數十年前童恩正提出此說時依據的是類型學猜測[7],但藏西早期人類活動證據的增加,使此說得到一定支持。古人類棲居模式的直接證據是遺址的空間形態與遺物內涵,在相應材料缺乏的情況下,則可根據遺址與高原外緣的距離,評估人類能否在一年之內進出高原。根據第二種方法,Zhao 等指出尼阿底第1 地點人群所處的縱深位置可能意味著他們已經全年居留高原之上[55],亦早于模型預測年齡。但是高原外緣地理條件的設定以及人群遷徙能力的評估標準目前尚無定論。例如,根據不同的遷徙能力模型,不同學者對邱桑遺址是否為永久居址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56,57]。
建立新的高原適應模型需要增進對于整個高原外圍舊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了解,明確潛在的人群來源,構建起更加完整的高原故事。同時,也需要改變對于考古材料的解釋方法,充分認識到技術演變與遷徙的復雜性[58]。時間范圍的擴大則對高原景觀歷時變化的認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這里,對于“景觀”的強調意在指出由于高原復雜的地理條件,通過少數氣候代用指標所獲得的環境認識,并不能很好的指示古人類棲息地的真實狀態。正如張萌指出,“青藏高原上的資源斑塊,尤其是指那些可以吸引食草動物的湖泊和內陸河流,而這些因素在賓福德構建全球狩獵采集者的參考框架時未能考慮,這正是形成青藏高原不適宜狩獵采集者生活這一論斷的因素”[59]。對于計算機模擬而言這一提醒尤為重要,由于數據精度有限,模擬結果可能會高估資源斑塊的距離,從而影響對人類行為的解讀[60]。
由于當前開展的工作有限,在現階段我們還無法精確推斷古代人群初入高原和永久占據高原的起始點與擴散路線。本文對現有考古學證據稍作梳理,以期引導未來的田野工作和相關研究能夠更有針對性、計劃性和前瞻性,通過多學科協同攻關重建史前人類向青藏高原擴散的翔實歷史,探索古人群適應極端環境的機制、策略與過程。
附屬材料 本文網絡版附有如下相關材料:附表1—青藏高原舊石器遺址信息表,敬請查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