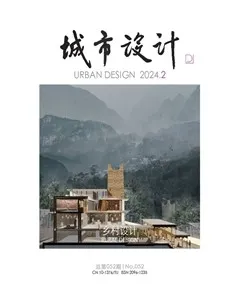桐廬舒羽山房設計














摘 要一個好的建筑應該成為觸媒,激活當地的文化與產業。本文以舒羽山房為典型案例,將其置于城鄉融合的視野之下,探討了經濟發達地區的近郊鄉村如何通過產業、人才、事件、營建等各方面的相互促進,持續提升當地的經濟發展與人居環境水平,推進深度城鄉融合與共同富裕。
關鍵詞:舒羽山房;近郊鄉村;城鄉融合;營建策略
0 引 言
因為新安江兩岸風景如畫,唐代詩人在這里留下了許多千古名篇。“浙西唐詩之路”講的就是唐朝浙江西部這一區域內發生的詩歌創作繁盛的情況[1],加之黃公望在此完成的《富春山居圖》《富春大嶺圖》,于是,如何傳承和發揚浙西詩、畫文化,以此推進地區發展,逐漸成為桐廬及其周邊縣市的共識與重要目標。“詩鄉畫城,瀟灑桐廬”,就是桐廬的城市發展形象定位。舒羽山房·舊縣國際寫作中心的建設,正好與此完全契合,也是城鄉融合、整體發展的具體體現。
舒羽山房由筆者2019 年設計,2021 年建成后,桐廬籍當代著名作家、詩人舒羽入住其間,她不僅在此創作與生活,也依托該建筑策劃了系列活動,深度參與了母嶺村的各項建設,使得該村在短時間內各方面的發展有了明顯提升。回顧該項目的建設,城鄉融合、整體性的思考與發展策略是其獲得成功的一個主要特點。這種整體性表現在多個方面:①區域層面,作為一個典型的近郊村代表,獲益于以人的雙向流動為特點的城鄉融合互促理念與實踐;②鄉村發展層面,展現了鄉村建設、鄉村產業、鄉村文化同步推進的策略;③項目建設層面,體現了以人和事件為中心的建設、運營一體化的思路。下文就此展開詳細闡述。
1 杭州近郊鄉村發展特點
一般認為近郊鄉村在空間上是城市的周邊地帶,與主城通勤在一小時左右的交通圈范圍[2]。杭州西、南側多山地,這里的近郊村往往具有豐富的風景資源與文化價值,與主城之間有著頻繁的要素流動與系統的多維交互,在發展上具有很強的活力。總體來看,杭州近郊村有著如下幾個特點。
1.1 產業多元發展,高度非農化
隨著社會的發展,經濟發達地區近郊鄉村的產業結構已經發生根本性調整,產業非農化特點十分顯著。從國家統計局數據來看,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不斷下降, 由1978 年的27.7% 下降至2022 年的7.3%[3]。產業高度非農化過程主要體現在農業內部的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以及在農業之外不斷向休閑、旅游、文化產業的轉型。一些區位良好的景中村,更是隨著市場的需求,產業不斷拓展、升級,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發展,這些村的村民可能比一般城市里的居民更加富有。杭州西湖龍井村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代表,該村落總面積只有3.5km2,村內家庭戶數不足400 戶,常駐人口約800 人[4],鄉村村民的生產和生活都是圍繞茶產業展開,不僅包括茶葉的種植、采摘、炒制、銷售,還有以茶和茶園景觀為特色的餐飲、休閑文化體驗。僅計算西湖區龍井茶產業,年總產量達545t,年產值1.8億元[5],非農化產業為該鄉村發展提供了強大支撐與動力。
1.2 人口規模相對穩定,城鄉之間雙向流動頻繁
近郊鄉村的人口構成相對復雜,且城鄉之間雙向流動化特點突出,這里也是大部分的外來人口暫住之地。隨著鄉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和鄉村人才引進政策的實施,越來越多不同教育背景的人參與鄉村新興產業和創新領域的工作。浙江桐廬蘆茨村的人口流動就值得一提,因為藝術賦能,蘆茨村很多村民從過去的“離土”到如今的“歸鄉”。早年的蘆茨村,因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產業空乏,是“窮得響叮當”的落后村,村民紛紛外出打工。但是依托富春江的豐富旅游資源,自從2012 年蘆茨村被納入首個省級慢生活體驗區后,村民被吸引回鄉開民宿、開辦農家樂,甚至吸引諸多外來青年設計師、藝術家來此創業,“新村民”數量逐年增加,至2022 年全村游客接待量更是超過了198 萬人次,旅游經營收入達到1.36 億元[6]。人群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城鄉互促發展成為近郊村的一個新動向。
1.3 鄉村風貌精致化、景觀化現象明顯
隨著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在杭州近郊,不少鄉村風貌變得如同城市小區般精致化,在學術界看來,這通常是一種被批判或者至少不被肯定的現象,因為其脫離了大家印象里鄉村應有的質樸與野趣,但是以一種動態、開放的觀念與態度來看待杭州周邊大量的景中村或者村中景,這又是一件合理的事情。鄉村演變的內生機制影響著村域內生產、生活、生態的綜合景觀系統及相應的空間表征[7]。鄉村不僅具有原初的自然屬性和演替規律,同時也承載著人們營建環境的訴求與文化內涵,是時空過程的歷史綜合體,是人地相互作用的文化進步史[8]。當產業由過去的農業轉向休閑、旅游、文化,城鄉界限變得模糊,人口雙向流動時,鄉村面貌也自然改變,特定地區的精致化、景觀化或許是一種必然的趨勢。
1.4 治理方式不斷采納數字技術,線上、線下社區一體化互動趨勢顯著
鄉村治理數字化也是經濟發達地區的近郊鄉村顯著特點之一。數字鄉村自2018 年黨中央提出后,鄉村治理致力于將信息化、數字化、網絡化技術應用于鄉村的社會治理過程中,以提升村級社會治理與綜合服務的智能化與便捷性,更好地應對基層在新發展階段面臨的各種新挑戰。湖州德清縣的 “數字鄉村一張圖”,將鄉村規劃、鄉村經營、鄉村環境、鄉村服務、鄉村治理5 大板塊收錄其中,實現鄉村的精細化管理和數據的集成應用[9]。杭州蕭山瓜瀝鎮75 個村社已建立“瀝家園”線上數字管理系統[10],“瀝家園”是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通過“數字身份”“數字互動”“數字公益”“數字信用”“數字福利”“數字服務”六大功能區塊,以“小程序、積分制、任務單、實體店”等途徑,實現基層治理各個環節在互聯網上的實時映射與互動,這不僅極大提升了管理的效率與智能化水平,也以一種線上、線下社區一體化互動的方式促進了新老村民的交流,強化了村民之間的凝聚力。
2 浙江桐廬母嶺村與舒羽山房,一個典型的杭州近郊鄉村建設案例
桐廬縣位于杭州城西,是富村江—新安江黃金旅游路線上的重要節點,也是浙西詩歌之路建設的落腳之地。本項目所在的杭州桐廬母嶺村是一個典型的近郊村,距離杭州市中心約一個小時。如果從桐廬縣城出發,開車順著富春江的支流分水江,向西南而行約15 分鐘,便到達該村。這是一個被群山環抱的村落,村域面積僅5.2 km2,戶籍人口1,356 人,農戶455戶[11]。近年來,該村一直在進行系列建設,具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但是一直不溫不火。2019年以來,建筑師與鄉賢詩人舒羽的介入,以及詩人舒羽對文學活動的策劃,為鄉村發展提供了新動力,在短時間內使得鄉村整體發展有了顯著提升,成為城郊村發展中的一個典型案例,其策略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 以關鍵人物為紐帶,城鄉之間的強力連接與互動
舒羽作為中國當代著名詩人、作家,是杭州市中心“舒羽咖啡館”的主人。這個咖啡館的位置堪稱完美,不僅枕著千年的京杭大運河,而且比鄰著始建于明崇禎年間的拱宸橋。坐在二樓居中臨窗的位置,正好可以看到拱宸橋的全景。 “大運河國際詩歌節”,是舒羽一直在創辦的活動,至2024 年已經走過十二個年頭。這是一個盛大的雅集,每次都會邀請來自國內外的著名詩人與學者,以水為媒,以詩為橋,展開關于城市、生活、藝術等全方位的對話。每年的詩歌節都有一個主題,很是別致,比如“城市、水域、心靈”(2012)、“穿越與漂移:兩岸三地詩會”(2013)、“水與詩的脈動”(2017)、“世界的要素之平衡”(2019)、“水磨的聲音:新詩與舊曲”(2020)。
京杭大運河、拱宸橋、桐廬、舊縣、母嶺村,這些看起來似乎沒有什么太大關系,不過,它們卻意外地因為詩歌構成了一個緊密的整體。先說富春江畔的桐廬,作為浙江首個“中國詩歌之鄉”,“蕭灑桐廬郡,春山半是茶”,是中國山水詩的發祥地之一。據統計,從南北朝到清代,共有千余位詩人到過桐廬,寫下三千余首吟詠桐廬山水、人文古跡的詩詞,堪稱文化奇跡。再說舊縣,它不是一個縣,而是桐廬縣的一個街道名稱。這個名字的來源很特別,因為此地曾是桐廬的舊縣治所在地,所以取名舊縣。據說元代大畫家黃公望在創作傳世名作《富春山居圖》之前,就曾在舊縣一帶游歷并進行創作。存世的另一幅名作《富春大嶺圖》,畫的正是舊縣母嶺村。母嶺村,則是舊縣的一個普通鄉村,舒羽的奶奶曾生活于此,她小時候也常從縣城來到此村玩耍,所以母嶺村對于這位詩人便有了特別的意義。如此,舒羽山房暨桐廬舊縣國際寫作中心或舒羽工作室,在此處的誕生便是順理成章了。于是,發源、興盛于京杭大運河邊的國際詩歌節便自然蔓延進了桐廬的鄉村,繁華都市里的拱宸橋與偏僻的母嶺村也因詩歌結緣、對話,許多知名詩人作家、學者在這兩處之間頻繁往來,城鄉之間也因此得以強力連接與互動,如圖1 所示。
2.2 產業的持續提升,從桂花系列產品到桂花旅游節、桐廬國際詩歌節的不斷轉型與迭代
也不知是出于怎樣的機緣巧合,村里很早以前就開始種植大量的桂花樹,如今自詡“中國桂花第一村”。依托桂花資源,母嶺村不斷做強桂花產業。從經營桂花苗到注冊“母嶺香”商標,嘗試開發桂花酒、桂花糕、桂花茶、桂花麻糍等桂花系列產品(圖2),不斷延長產業鏈,提升價值。至2017 年,村級集體經濟收入累計達到 200 余萬元[12]。從產業類型的角度來看,如果說從傳統農業是第一代,桂花產業是第二代,詩歌與文化產業的發展則是第三代。
母嶺村,確實也是有發展詩歌文化的條件與土壤的。該村房前屋后的坡地上種滿了桂花,村中心有一株據傳種植于宋代的“桂花王”,“桂花王”樹干粗壯,枝葉繁茂,每到中秋節前后,整個村里都飄滿了濃郁的桂花香。依托這份獨特的資源,村里不僅發展了相關桂花產業,還舉辦了多次的桂花旅游文化節(圖3)。我參加過其中的一次,是在2020 年國慶假期里,那天村里舉辦了特色農產品的展銷、小朋友們游戲、游客們的各種互動體驗,當然還有一場盛大的晚會,晚會上,舒羽帶著當地的小朋友朗誦了她創作的詩歌,那一刻,明月高懸,暗香涌動,清脆的朗讀聲宛若天籟。
古代許多文人對桂花也顯示出了特別的偏愛,寫進了中小學課本的唐代詩人王維的名句“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幾乎家喻戶曉。宋代的李清照更是不加任何掩飾地表達了對于桂花的最愛:“暗淡輕黃體性柔,情疏跡遠只香留。何須淺碧深紅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不僅國人喜愛桂花,很多外國人同樣如此,來自敘利亞的著名詩人阿多尼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2018 年訪問中國之后完成了一組中國題材的長詩,出版后的書名就是《桂花》。該書譯者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薛慶國老師問他為什么要選用這個名字,因為在阿拉伯的世界沒有桂花這種植物,阿多尼斯回答到,因為中國在他心目中的印象,就如桂花一樣。2019 年11 月,阿多尼斯再一次訪問杭州,不同以前只是呆在城市里參加各種活動,這次在舒羽的邀約下,阿多尼斯來到了桐廬母嶺村,和村民們一起談論詩歌,并且在當時即將竣工的寫作中心的院子里種下了一顆“詩人之桂”, 4 年過去了,如今這株桂花樹長得很好,似乎時刻等候著詩人的再次歸來。這些因桂花而生的詩詞、文化以及文化事件,在各種機緣巧合之下,成為促進該村產業不斷發展、轉型、升級的契機和動力。
2.3 基于聚落格局、場地脈絡的設計與建造
寫作中心所在地原來是一棟閑置的農宅,后來產權收歸村集體所有。原本是打算在老房子的基礎上加以改造,無奈質量太差,只能拆了重建。不過,建筑的主體部分基本上遵循了原有的宅基地,所以如今從空中鳥瞰下來(圖4),寫作中心依然如同一棟農居,安靜地處在村中一隅,周圍被蔥郁的大樹和竹林環繞,景觀甚是良好,如圖5 所示。
“桂花王”是村里的一個地標,也是進入寫作中心的真正起點。從這里拾級而上(圖6),穿過一片竹林,順著地勢幾個轉折,便到了一個院子的門口(圖7)。院子內外原本就有幾株長得很好的樹木,需要保留,其中幾株桂花,樹形舒展,枝葉茂盛,也正好成為初入院子的對景。還有一棵柿子樹位于南側院子居中的位置,它為入戶小道的轉折變化提供了依據,再輔以3 個淺淺的種植了荷花的水池,使得從入戶大門到院子這段短短的行程充滿了變化。
房子主體為3 層,形體方正簡潔,仿夯土的外墻似乎提示著這里原本是一棟農居的存在。外廊和會議室的外墻用當地的剖石砌筑,這也是本地的一種傳統做法,其中有不少石頭是原建筑拆毀后留下來的,剖石上深深淺淺的鑿痕,在陽光下有著細密的陰影,散發著獨特的韻味。外廊部分很是寬敞,與兩側的院子在空間上互相延伸,一層室內是公共區域,客廳、茶室、餐廳、書吧等空間融為一體,以滿足寫作中心舉辦多樣活動的需求。上面兩層則是作家居住與工作的房間,從房間或露臺上看出去,均有極好的風景,如圖8—圖12 所示。
房子南側和西側的兩處院子,或許是這棟建筑的最大亮點。因為場地的限制,不太可能、也沒必要建一個很大的會議室或多功能廳,所以一些人數較多的活動,必須考慮在戶外舉辦,因此,寬敞的院子在此就變得十分必要(圖13)。其實,這也恰恰體現了一處位于鄉間的作家工作室的特點與價值。詩人、作家們來到此處,就是為了更好地融入自然,獲得與城市里不太一樣的居住生活體驗,從而有更多的創作靈感。房子北側是山體,有著大約3m 高的石頭擋土墻,地上種植了爬藤,期待有一天能爬滿墻面。西側院子邊的擋土墻,則結合地勢跌落成幾個臺階,一方面化解了垂直擋土墻的生硬,另一方面也可以作為舉辦活動時觀眾的座位。順著院子的邊緣,種植了幾株梅花、櫻花,在院子的最東側,還保留了一塊菜地,每當春暖花開的時候,院子里都是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
2.4 順應新媒體時代的傳播特點與規律,以建筑作為觸媒,激發新的產業與生活
在新媒體時代,以建筑為觸媒,催生新的事件,獲取大眾關注與網絡流量,從而激發新的產業與生活,是鄉村建設的有效手段和重要方法。舒羽山房的建成,就有效利用了詩歌節的影響,焦聚了社會關注與社會資源,帶給母嶺村新的發展契機。2021 年9 月30 日,一場詩歌的盛宴,在“桂花王”下舉行,這也是舒羽山房·舊縣國際寫作中心揭幕儀式,暨桐廬富春江詩歌節啟動儀式(圖14)。著名詩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吉狄馬加親臨現場(圖15),為寫作中心揭幕,陳先發、樹才、沈葦、施施然等成為首批駐村詩人、作家。之后,芒克、歐陽江河、茱萸等也來此短暫居住、創作。
除了用以作家們在此居住、創作,舉辦各種文化交流活動,寫作中心也是母嶺村的一處公共客廳與鄉村博物館。寫作中心竣工時,舒羽甚至有一個大膽的想法,打算宴請一下該村的村民,以便寫作中心將來和他們能有更多更好的互動。同時,該處開放為鄉村博物館,舒羽已經將她收藏的部分名家的手稿、畫作精心裝裱后在寫作中心的各處展示出來,未來隨著作家們的入住與創作,相信這樣的展品會越來越多。在寫作中心,我也得以第一次看到余光中先生的親筆來信,欣賞到北島、歐陽江河的書法,阿多尼斯、芒克的繪畫,很是感嘆這些詩人、作家身上濃濃的藝術氣息和彼此間深厚的友誼,或許這是文學的力量,讓人變得更加敏銳、溫暖。
如今,依托寫作中心,母嶺村被授予了“舊縣詩歌研學中心”的稱號,設為了“桐廬富春江詩歌節·桂冠詩人獎”的固定頒發地點,“桐廬富春江詩歌節組委會”也落戶于此,使得寫作中心承擔起越來越多的職責,也有了越來越豐富的內涵,如圖16 所示。相信隨著這些活動的舉辦,詩人、作家將用文學的力量為母嶺村注入新的活力,助推村里走好農文旅融合發展的道路,為母嶺村的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3 結語:以人的雙向流動、新事件和新生活的激發為特點的近郊村發展策略
相比二十余年以前,當下的鄉村,特別是近郊鄉村早已經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當我們說起鄉村的時候,或許每一個人頭腦中出現的畫面,對于鄉村的理解都不相同,尤其是長三角地區的鄉村,呈現出更加多元發展的態勢。這里鄉村人口的流動趨于穩定與平衡,除了鄉村原有的居民,返鄉養老的“歸鄉人”、入鄉創業的“新鄉人”越來越多。在一些具有較好旅游資源的鄉村,周末、節假日來此旅游度假的游客也逐年增加,在農、文、旅融合和城鄉一體化的發展理念與背景之下,鄉村在這里不再是凋敝、空心的景象,而是作為與城市相互映襯的另外一種居住與生活方式。
作為當代鄉賢,舒羽以詩人、作家的身份再次回到桐廬舊縣,回到母嶺村,成為對接城市與鄉村、文學與大眾、桐廬與世界的一個新的橋梁,帶給舊縣和母嶺村新的發展契機。寫作中心落成儀式當天,舊縣街道就與浙江大學農業與生物技術學院、浙江現代優選公司簽訂了桂花產品開發合作協議,接下來,合作方將在桂花產品研發、品質提升上給與技術支持,并幫助村里拓展產品的銷售渠道。關于未來帶動母嶺村發展的構想,舒羽最近還在跟郭初陽、湯萌、顏煉軍等幾位國內知名的教師、年輕的學者探討,在母嶺村創辦研學基地的可能性。著名作家、《世界文學》主編高興也計劃來此村開設工作室,其方案由筆者正在設計之中,我們有理由相信母嶺村未來發展會越來越好,成為城鄉之間各類要素融合互促的近郊村發展樣板。
參考文獻
[1] 郭梅. 走在“浙西唐詩路”上的“田園詩”群[J].博覽群書, 2022(3):35-41.
[2] 張如林, 余建忠, 蔡健, 等. 都市近郊區鄉村振興規劃探索: 全域土地綜合整治背景下桐廬鄉村振興規劃實踐[J]. 城市規劃, 2020,44( 增刊1):57-66.
[3] 國家統計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N]. 人民日報, 2023-03-01(9).
[4] 武前波, 龔圓圓, 陳前虎. 消費空間生產視角下杭州市美麗鄉村發展特征: 以下滿覺隴、龍井、龍塢為例[J]. 城市規劃, 2016,40(8):105-112.
[5] 黃成彥.“互聯網+”及美麗鄉村背景下的茶葉經濟發展探究: 以西湖龍井為例[J]. 農村經濟與科技,2022,33(12):16-19,38.
[6] 浙江在線. 浙江桐廬:蘆茨村秉持“兩山”理念唱響鄉村“致富歌”[EB/OL].(2022-09-21)[2023-12-13].https://cs.zjol.com.cn/sc/202209/t20220921_24830042.shtml.
[7] 王竹, 王珂, 陳瀟瑋, 等. 鄉村“人地共生”景觀單元認知框架[J]. 風景園林, 2020,27(4):69-73.
[8] 王云才, 陳照方, 成玉寧. 新時期鄉村景觀特征與景觀性格的表征體系構建[J]. 風景園林,2021,28(7):107-113.
[9] 汪菁. 數字鄉村建設的發展現狀、行動困境和優化路徑: 基于浙江省德清縣數字鄉村建設的實踐[J]. 科技和產業, 2023,23(4):128-132.
[10] 賀勇, 陳鈺凡, 趙靜. 中國經濟發達地區城郊鄉村聚落的功能轉型與形態演化[J]. 西部人居環境學刊,2023,38(5):17-23.
[11] 桐廬母嶺村: 發展桂花產業助推共同富裕[J]. 新農村, 2022(8):2.
[12] 母嶺村: 飄香產業強村富民[J]. 新農村, 2018(6):18.
SYNOPSIS
Design of Shuyu Studio in Tonglu:A Case Study of Rural Construction inthe Integration and Mutual Promotion of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Hangzhou
Yong He, Xiangquan Chen Yufan Chen
The suburban villages are located at thesurrounding areas of citi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society,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most economicallydeveloped suburban villages has undergonefundamental adjustments, and the non-agricultural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es are significant. Itspopulation size is relatively stable, and there is afrequent two-way flow between urban and ruralareas; the refinement of rural scenery and landscapetransformation is obvious; the governance approachcontinuously adopts the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trend of integrated interaction between online andoffline communities is significant. The western andsouthern sides of Hangzhou are mountainous, and thesuburban villages here often have rich scenic resourcesand cultural values. There is a frequent element flowand systematic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with themain city, which has strong vitality in development.This paper takes Shuyushan Studio in TongluCounty, Hangzhou as a typical case, places it in the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exploreshow suburban villages in economically developedareas can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local economicdevelopment and living environment level throughthe mutual promotion of industries, talents, events,construction, and other aspects, so as to promote thedeep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Looking back 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project, aholistic approa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are majorcharacteristics of its success. This kind of wholenessis manifested in multiple aspects: First, at the regionallevel,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a suburban village,it benefits from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the urbanruralintegration and mutual promotion characterizedby the two-way flow of people; second, at the levelof rural development, it demonstrates the strategy ofpromoting rural construction, rural industries, andrural culture synchronously; third, in the constructionprocess of this project, the idea of integrating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centered on people andevents was reflected, and how to make buildings actas a catalyst to activate local culture and industrypractices was also stre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