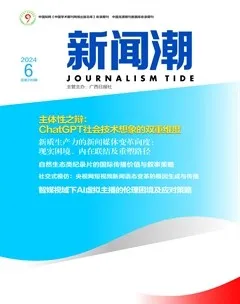博物館文物故事的沉浸式傳播路徑
【摘 要】隨著數字技術日益成熟,沉浸式傳播方式為博物館文物故事的傳播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博物館文物的展覽與傳播應回歸到“人”這一主體,利用短視頻、游戲、文化創意類節目等創新文物故事傳播路徑,為觀眾提供高度的沉浸式體驗,助力文物故事的傳播,展示講好中國博物館文物故事這一主題。本文試圖從沉浸式傳播的理論及創新博物館文物故事講述方式入手,對文物故事沉浸式傳播路徑進行研究,明確講好中國文物故事的意義與價值。
【關鍵詞】博物館;文物故事;沉浸式傳播;傳播路徑
博物館具有承載文化教育、進行文化傳播的功能。在歷史文物類博物館里,每個文物都有屬于它自己的獨特故事,這些故事不僅包含它的前世今生,也在向人們訴說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目前,除了較大的博物館采取了數字化傳播方式,多數博物館里的文物呈現方式都是以靜態展覽為主,伴隨一分鐘或者兩分鐘的簡短音頻。但這種故事講述的方式比較機械化,吸引力不足,難以深入講解文物背后的故事,沒有涉及文物的深層價值層面。本文認為一些特殊的歷史文物,尤其是具有特別歷史記憶的文物需要詳細講述它們的故事,例如,睡虎地秦墓竹簡是首次發現的系統性的秦律、楊貴妃曾使用過的葡萄花鳥紋銀香囊、敦煌出土的唐代“涂鴉”等。這些文物應該被重新“活化”,它們的故事也應該再現在觀眾眼前。博物館文物故事如何順應傳播方式的變革,正是本文要探討的主題。
一、沉浸式傳播的理論依據
沉浸式傳播是伴隨著科技的進步而興起發展的,在元宇宙時代以VR(虛擬現實)、AR(增強現實)、MR(混合現實)為代表的沉浸式技術搭配考古復原技術,4D、8K等高清影像技術,三維動畫技術,全息投影技術以及動作體感技術等影像實踐技術[1],共同促進了沉浸式傳播的形成。
目前,業界公認的沉浸式傳播定義是學者李沁在著作《沉浸傳播:第三媒介時代的傳播范式》中提到的概念,即“以人為中心、以連接了所有媒介形態的人類大環境為媒介而實現的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無所不能的傳播。它是使一個人完全專注的,也完全專注于個人的動態定制的傳播過程。它所實現的理想傳播效果是讓人看不到、摸不到、察覺不到的超越時空的泛在體驗”[2]。她認為沉浸式傳播是以人為中心,整個沉浸式傳播活動是圍繞主體“人”而展開,重回以人為主體的地位。沉浸式傳播活動集結了所有的媒介形態,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中提到“媒介是人的延伸”,因而沉浸式傳播是集結了人的所有感官,不再是單一感官或是兩三個感官的沉浸。沉浸式傳播呈現出“泛在”的體驗,人們每時每刻都在接觸不同的信息,沉浸在不同的內容里,專注于自身的沉浸式體驗。博物館借助沉浸式傳播理論講述文物故事,助力文物故事深入觀眾的內心,潛移默化地影響觀眾的觀念和態度,讓觀眾得到新的知識和啟發。
二、博物館文物沉浸式傳播路徑
大多數學者將文物定義為“文物是人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遺留下來的遺物、遺跡”[3]。文物是人類在歷史的發展中遺留下來的產物,兼具歷史文化性、藝術性和科學價值的特點。結合以上內容,博物館文物泛指有“故事”的文物,這些文物具有以下特征:有史料記載作為支撐、與特定的人物故事和生活場景相關聯、文物的神態姿勢造型等能反映現實。基于這些特征,用故事框定文物,利用故事講好博物館文物的真正價值。
博物館文物故事沉浸式傳播路徑有兩種,一是回歸以人為主體的傳播方式,二是創新博物館文物故事的傳播途徑。這兩者的關系是先回歸以人為主體的傳播方式,在此基礎上創新文物傳播的途徑。
(一)回歸以人為主體的傳播方式
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受者身份發生轉變,重新定義為用戶。作為用戶,主動權和話語權也隨之增大,會傾向于選擇自己感興趣的內容。為讓更多的觀眾了解博物館里的文物,博物館必須回歸以人為主體的傳播方式,讓觀眾重新歸于本位,站在觀眾的立場和角度思考問題,力求讓觀眾在體驗的過程中學有所獲。
1.搭建共享場景:故事還原
博物館利用沉浸式技術搭建共享場景,突破時間和空間限制,還原文物背后的故事,讓觀眾獲得接近現實的沉浸式體驗,更通過多模態融合的媒介形式進行信息擴充,在故事敘事中呈現出更為全面、多元的立體中國[4]。博物館里的文物基本上都有千百年的歷史,歲月的沉淀為文物添上神秘的色彩。因此,博物館作為展現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場所,積極利用沉浸式技術還原故事場景,能讓觀眾沉浸在“活化”的故事情節中,理解文物蘊含的意義與價值。
2.虛擬真實事件:感官沉浸
通過虛擬真實事件,觀眾的感官可以完全沉浸在事件中,強化了觀眾的空間感知。虛擬現實系統利用技術的進步,傳達給觀眾一種更加完整全面的身體和心理感受,使得人機交流中的人能夠越來越趨向于回到人的本原狀態,進而創造和產生出一種全新的傳播交流方式[5]。AR、VR、全息投影技術等沉浸式技術不僅產生身體上的沉浸,同時也有心理上的沉浸。身體和心理的共同沉浸將觀眾拉入現場,滿足觀眾的真實感和提供較好的體驗感,與此同時,觀眾與文物之間同屬一個空間,能夠增強文物與人之間的共鳴,助力文物故事的傳播。
3.尋找人與物之間的聯系:情感共鳴
沉浸式的傳播環境,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外界的干擾,強化了人的主觀感覺,進一步密切了人與物之間的聯系。在沉浸式傳播的過程中,人與物之間產生聯系,作為主體的人,由于身體和心理帶來的雙層沉浸,他們的情感能以更快的速度激發,進而影響到他們的認知、態度和行為。例如,湖北省博物館的越王勾踐劍,經過2500多年的歲月沉淀,至今仍削鐵如泥,但同時也讓人們回憶起臥薪嘗膽的故事。有些博物館的文物,它們的表情、動作、神態等也與人產生聯系,如陜西博物館館藏文物唐代彩繪陶縮脖俑委屈的表情,網友表示“簡直就是我本人”,這些聯系讓文物與人之間產生了情感共鳴。
(二)創新博物館文物故事的傳播途徑
博物館文物新型傳播途徑區別于傳統的靜態展覽方式,通過與其他形式相結合助力文物故事的傳播。博物館文物故事與沉浸式技術相結合,利用各種平臺的優勢傳播文物故事。
1.短視頻應用:以多種形式講述故事
網民數量的龐大為博物館文物傳播提供了新的機遇,故而博物館在短視頻平臺可利用各種形式講述文物故事。多數博物館有科普類的視頻,詳細講解文物的制作、修復等。例如,故宮博物院在嗶哩嗶哩網站上開設《紀錄片》《故宮邀你云看展》《故宮學人講故宮》等欄目傳播文物故事。河北博物館、安徽博物館、山東博物館、陜西博物館等緊跟潮流,相繼發表文物版“陽光開朗大男孩”等視頻,廣受年輕觀眾的歡迎和喜愛。
2.游戲應用:沉浸式體驗
由于網民年輕化的特點,博物館可與游戲平臺合作,促進文物故事的傳播。游戲從感官、心理等方面密切作用于人的“身體”,具有與生俱來的高度沉浸性,有研究結果表明游戲營造的虛擬環境甚至能影響玩家性別身份認同的建構[6]。例如,女性手游《奇跡暖暖》在2016年與故宮博物院以“清代皇后朝服”和“胤禛美人圖”為合作主題,共同推出明清宮廷系列服裝以及配飾,讓玩家在闖關的同時了解明清服飾的藝術美。敦煌研究院與騰訊合作打造了《數字藏經洞》游戲,通過復原藏經洞,觀眾化身為歷史的參與者,感受洞窟如何開鑿、文物流散到再次聚首的全歷程。這些游戲體驗會強化觀眾對文物的感知,有利于博物館文物故事的傳播。
3.文化創意類節目:增強文化認同感
文化創意類節目強化了觀眾對自身的身份認同,增強了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感。文化創意類節目又可細分為舞臺劇、情景劇、詩朗誦等。多數博物館主要以文創活動和社教活動為主,例如,國家博物館首部文物活化舞臺劇《盛世歡歌》,以秦漢擊鼓說唱俑為背景,帶領觀眾經歷東漢時期黎民百姓的人生。對以藝術講好中國故事,有效傳播舞劇國家文化形象(主要是傳統形象與當代形象的融合)做出了有益的嘗試,踐行著新時代主流舞劇“中國精神”的守正與形式語言的推陳出新、跨界融合,彰顯出中華文化富于歷史性、跨文化性的永恒魅力和當代精神氣韻[7]。
三、沉浸式傳播講好博物館文物故事的價值體現
沉浸式傳播以技術為支撐,消除工作和娛樂的界限,讓觀眾在娛樂中學習博物館里有關文物的知識,沉浸式傳播方式能夠講好博物館文物的內在價值,讓文物故事更加具有傳播力和影響力。
(一)賦予文物新的活力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系統梳理傳統文化資源,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8]沉浸式傳播賦予文物新的生機與活力,讓博物館里的文物不再只是以靜態的方式呈現,而是以動態的方式全方位展示。博物館通過技術搭建平臺,在講述文物故事的同時也讓觀眾能近距離感受文物的眾多細節,豐滿文物的形象。例如,揚州中國大運河博物館設置“運河上的舟楫”展區,觀眾可以站在船甲板上體驗清朝運河虛擬影像,感受運河文化的現實意義。沉浸式傳播能賦予博物館文物新的生機與活力,使文物“活”起來。
(二)消除文物時空界限
沉浸式傳播以虛擬現實技術為支撐,可以實現虛擬與現實相結合。沉浸式現象出現的原因是意識空間中物理空間感知與媒介空間感知的邊界模糊化,而沉浸式傳播就是要通過特定的手法讓這種邊界模糊化盡可能地延長時空[9]。沉浸式傳播通過不斷轉換場景,讓人在體驗的過程中因精神高度集中,從而沉浸在搭建的場景中。例如,世博會中國館《會動的清明上河圖》,用沉浸式的方式向觀眾全方位展現北宋都城汴京的面貌,讓畫里的人物動起來,消融了距今1000多年的時空界限,讓現代人看到了古人的生活方式。這種沉浸式傳播使人們穿梭在北宋和現實之間,仿佛北宋時期的生活就在眼前。
(三)塑造觀眾的“在場”體驗
觀眾通過虛擬的“在場”體驗,感受文物的文化內涵與時代價值。在沉浸式傳播方式中,觀眾沉浸在博物館搭建的場景中,時間概念變得模糊,感官的沉浸消除了不在場的體驗,讓觀眾仿佛就在現場。從空間延伸到感官,進而影響到人們的心理,沉浸在虛實交融的世界當中。人們在接收信息時,也會更加投入,專注沉浸在某一場景當中[10]。沉浸式傳播方式從感官層面的沉浸上升到精神方面的沉浸。博物館利用沉浸式傳播方式助力文物故事的傳播,也能讓觀眾深入理解文物本身具有的內在價值。
四、結語
講好中國博物館文物故事是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一環,講好文物故事需要有創新的思維。沉浸式的傳播方式賦予文物新的活力、消除文物與人之間的時空界限、塑造觀眾的“在場”體驗,這是講好文物故事的價值體現。因而,博物館文物故事的傳播應順應時代的要求,充分利用數字技術,以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展現文物故事。同時,要講好文物故事,關鍵在于講述的人,如何活化文物故事,使文物與人之間產生密切的聯系,更好地促進文物故事的傳播,是每個文物講述人都應該思考的問題。潮
參考文獻
[1]夏德元,盧宇奇.元宇宙時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影像傳播的新機遇[J].中國編輯,2023(Z1):15-19,53.
[2]李沁.沉浸傳播:第三媒介時代的傳播范式[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1.
[3]王云霞.文化遺產的概念與分類探析[J].理論月刊,2010(11):5-9.
[4]李華君,康敏晴.故事還原、具身體驗與主體回歸:中國故事的沉浸式傳播[J].新聞春秋,2023(2):41-49.
[5]杭云,蘇寶華.虛擬現實與沉浸式傳播的形成[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07(6):21-24.
[6]李沙沙.沉浸式傳播研究綜述[J].采寫編,2022(5):84-86.
[7]袁藝.詩性、沉浸、跨媒介:舞蹈詩劇《只此青綠》的美學建構[J].文化藝術研究,2022,15(2):78-83,115.
[8]李瑞振.不斷拓寬讓文物“活起來”的路徑[EB/OL].(2022-05-17).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2-05/17/nw.D110000renmrb_20220517_3-09.htm.
[9]孔少華.從Immersion到Flow experience:“沉浸式傳播”的再認識[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4):74-83.
[10]周凱,楊婧言.數字文化消費中的沉浸式傳播研究:以數字化博物館為例[J].江蘇社會科學,2021(5):213-220.
作者簡介" "羅歡歡,新疆財經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張莉,新疆財經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傳播學博士
基金項目" "新疆財經大學課題“讓新疆文物故事活起來的數字傳播路徑研究”(項目編號:XJUFE2023KG31)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