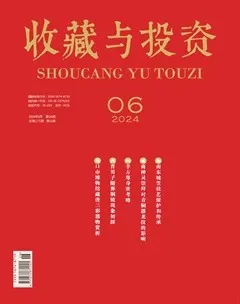論顧愷之“傳神觀”的美學(xué)思想
摘要:顧愷之的傳神觀在中國(guó)繪畫(huà)史學(xué)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的傳神觀主要談及對(duì)于眼神、形體和環(huán)境關(guān)系的把握。他認(rèn)為想要使人物傳神,首先,必須注重眼睛的描繪以及對(duì)于描繪對(duì)象特有動(dòng)作的把握,同時(shí)還要注意表現(xiàn)人物的突出特征。其次,在環(huán)境方面還要注重人物與人物以及人物與環(huán)境之間的關(guān)系,只有做好這幾點(diǎn),人物畫(huà)才能表現(xiàn)得更加生動(dòng)傳神。
關(guān)鍵詞:顧愷之;傳神觀;美學(xué)思想
一、目睛傳神
《世說(shuō)新語(yǔ)·巧藝》里有過(guò)這樣的一段記載:“顧長(zhǎng)康畫(huà)人,或數(shù)年不點(diǎn)目精。人問(wèn)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wú)關(guān)于妙處,傳神寫(xiě)照,正在阿堵中。’”①顧愷之在這里說(shuō)了一句很關(guān)鍵的話(huà),即“傳神寫(xiě)照,正在阿堵中”。正所謂,人的眼睛是人的靈魂之窗,人物畫(huà)中眼睛的好壞,直接影響人物的形象,眼睛是最能夠反映人物心理活動(dòng)和情緒的。因此,顧愷之十分注重醞釀感情,揣摩人物的神態(tài),直至熟記于心,一氣呵成,從而點(diǎn)明了人物眼神所傳達(dá)的神韻。這樣畫(huà)出的人物自然就精妙傳神、栩栩如生,例如顧愷之在其代表作《列女仁智圖》中并未過(guò)多地刻畫(huà)故事情節(jié),而是注重刻畫(huà)人物內(nèi)在的性格。在這幅作品中,顧愷之打破了過(guò)去死板的人物畫(huà)傳統(tǒng),沒(méi)有“觀念化”的表現(xiàn)手法,而是對(duì)十幾位女性的形貌、神情進(jìn)行了細(xì)致的描寫(xiě),使人物的動(dòng)作和表情更加生動(dòng),人物的神態(tài)和姿態(tài)的刻畫(huà)可謂渾然天成。
顧愷之還認(rèn)為,想要使得藝術(shù)形象“傳神”,還應(yīng)注意對(duì)角色特有動(dòng)作和意味的把握。“言談舉止”和“姿態(tài)動(dòng)作”是體現(xiàn)人物內(nèi)在的一種方法。因此,畫(huà)家只有善于把握最豐富的表現(xiàn)瞬間,才能獲得“悟?qū)νㄉ瘛钡乃囆g(shù)效果。例如在五代《韓熙載夜宴圖》中,韓熙載作為主角,其始終愁眉不展的神情、憂(yōu)傷的目光、無(wú)力的雙手,與當(dāng)時(shí)的歌舞場(chǎng)面形成了強(qiáng)烈的反差,從而將韓熙載的志向和野心表現(xiàn)到了極致,可以說(shuō)達(dá)到了人物情操和心境的完美融合。

此外,顧愷之的傳神觀在后世也有了一定的發(fā)展。例如晚唐時(shí)期的周昉,他擅長(zhǎng)用細(xì)部描寫(xiě)來(lái)表現(xiàn)仕女們豐富的內(nèi)心。他筆下的人物形象逼真,比如他的《揮扇仕女圖》(圖1)描繪了十三位仕女,形象各異。畫(huà)中的仕女多雙眉緊蹙,眼中滿(mǎn)是哀愁。她們或面朝鏡子,或獨(dú)自一人,或靠在椅子上,神色悠閑或憂(yōu)郁。這幅圖可以分成五個(gè)部分,第一段是手拿扇子的仕女。在這部分中一共有四個(gè)角色,一個(gè)女人懶洋洋地坐在中央,手里拿著一把折扇,一只手臂搭在椅背上,她的身體十分放松,但她的臉上卻帶著一種憂(yōu)郁的神情。我們可以看到,在裙子的包裹下,她的雙腿一收一放,姿態(tài)十分悠閑,給人一種寧?kù)o的感覺(jué)。第二段為一名宮娥捧著一把古琴,另一名身材嬌小的宮娥正在幫她打開(kāi)琴袋,她垂著頭,一言不發(fā),神情憂(yōu)郁。第三段的仕女正對(duì)著鏡子,表現(xiàn)出一副憂(yōu)心忡忡的樣子。第四段的宮女則獨(dú)自坐在梧桐樹(shù)下,與一位宮女對(duì)視,眉頭緊皺,眼中滿(mǎn)是哀傷與迷茫。作者用梧桐樹(shù)來(lái)表達(dá)凄婉的秋色,從而烘托了宮中妃子的寂寞、哀嘆和憂(yōu)愁,同時(shí)也反映了周昉對(duì)仕女的悲憫之情。

因此,眼睛對(duì)傳神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只有恰當(dāng)?shù)匕盐蘸萌宋锷袂橹g的情感,才能更好地創(chuàng)作出好的作品。
二、以形寫(xiě)神
顧愷之在《論畫(huà)》里曾說(shuō)過(guò):“美麗之形,尺寸之制,陰陽(yáng)之?dāng)?shù),纖妙之跡,世所并貴。”②作為一名藝術(shù)家,他認(rèn)為要有高度敏銳的觀察能力和將客觀事物加工成美的藝術(shù)形象的能力。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要注意“長(zhǎng)短、剛?cè)帷⑸顪\、上下、大小、點(diǎn)睛”等細(xì)微之處,稍有疏忽,就會(huì)造成嚴(yán)重后果。也就是說(shuō),脫離了描繪對(duì)象的“形”而直接寫(xiě)“神”,則與現(xiàn)實(shí)不符。“形”和“神”實(shí)際上是相互依存的,兩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們?cè)诒憩F(xiàn)上要格外小心。那么以形寫(xiě)神有哪些具體的表現(xiàn)方法呢?事實(shí)上有兩種。
一種是通過(guò)動(dòng)態(tài)的形來(lái)表現(xiàn)對(duì)象的“神”,這是對(duì)“形”的第一種理解。例如當(dāng)我們?cè)诋?huà)雜技演員時(shí),如果把他畫(huà)成站在原地一動(dòng)也不動(dòng)的人,那這幅畫(huà)肯定沒(méi)有“神”,但如果把他畫(huà)成正在表演,在空中翻跟頭或者腳踩風(fēng)火輪在走動(dòng),那么這樣的畫(huà)一定是有“神”的。因?yàn)檫@樣才符合雜技演員的特性。所以對(duì)于“形”的理解,就需要把它放在動(dòng)態(tài)的形象之中,這樣才能夠表現(xiàn)對(duì)象的“神”。
另一種是在塑造人物時(shí),主觀上突出人物的特點(diǎn),使得人物形象更具有辨識(shí)度。這就是對(duì)“形”的第二種理解。比如在蔣才《先賢》(圖2)這幅作品中,蔣才運(yùn)用“豐碑式”的構(gòu)圖手法,將人物放在畫(huà)面的中心,整幅畫(huà)以墨色為主,以大面積的黑灰色來(lái)表現(xiàn)人物的厚重感,再以革命軍人武裝起義為背景,從而加強(qiáng)了畫(huà)面在主題上的表達(dá)。在人物臉部的描寫(xiě)上,精雕細(xì)琢,突出細(xì)微的臉部表情變化,使得整幅畫(huà)帶有一種濃重的歷史感,盡管畫(huà)面中僅有一位主角,但觀眾仍能感到一股強(qiáng)烈的歷史氣息,從而達(dá)到了歷史和藝術(shù)表達(dá)的完美結(jié)合。從這幅畫(huà)中,我們能體會(huì)到蔣才對(duì)“形”的準(zhǔn)確把握,以及他對(duì)“神”的主觀感情的深刻認(rèn)識(shí)。正如齊白石所說(shuō)的“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只要掌握了一定的技巧,就一定可以做到以“形”傳“神”的境界。
此外,作為繪畫(huà)的基本語(yǔ)言之一,線(xiàn)條在以形寫(xiě)神中也發(fā)揮了巨大作用。顧愷之創(chuàng)造了一種“高古游絲描”的線(xiàn)條,在《歷代名畫(huà)記》中,張彥遠(yuǎn)是這樣評(píng)價(jià)顧愷之的線(xiàn)條用筆的:“顧愷之之跡,緊勁聯(lián)綿,循環(huán)超忽,調(diào)格逸易,風(fēng)趨電疾。”③這種寫(xiě)法細(xì)膩而富有彈性,就像“春蠶吐絲”“春云浮空,流水行地”一樣,屬于“密體”的一種表達(dá)方式,和張僧繇“疏體”的風(fēng)格截然不同。比如顧愷之《女史箴圖》這幅作品中的人物,從衣著到姿態(tài),再到容顏,都是那么纖細(xì),那么流暢,那么有節(jié)奏感。表情惟妙惟肖,五官也是極為精細(xì)。畫(huà)中男子的長(zhǎng)袍和女子的長(zhǎng)裙,在線(xiàn)條的表現(xiàn)上都極具藝術(shù)感染力。
因此,對(duì)形體的表現(xiàn)是傳神的基礎(chǔ),即在實(shí)際的繪畫(huà)創(chuàng)作中要注意對(duì)形的把握,這樣才能更加準(zhǔn)確地表現(xiàn)對(duì)象的神態(tài)和內(nèi)心活動(dòng)。
三、環(huán)境托神
人類(lèi)都是在特定的社會(huì)關(guān)系和自然環(huán)境中生存的,其生存環(huán)境的差異不僅體現(xiàn)了其社會(huì)地位,而且體現(xiàn)了其思想感情。所以,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環(huán)境和人物有緊密的聯(lián)系。
在環(huán)境表現(xiàn)上顧愷之認(rèn)為有兩種表現(xiàn)方式,一種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也就是典型環(huán)境。他曾說(shuō)道:“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視而前亡所對(duì)者。以形寫(xiě)神而空其實(shí)對(duì),荃生之用乖,傳神之趨失矣。空其實(shí)對(duì)則大失,對(duì)而不正則小失,不可不察也。”④換句話(huà)說(shuō),當(dāng)一個(gè)人在做某些動(dòng)作時(shí),在他的前面或者周?chē)欢ㄓ幸粋€(gè)人使他的行為和表情發(fā)生變化,而這些都是由他眼前的人引起的。否則,就違背了“以形為本”的精神,無(wú)法達(dá)到“神”的境界了。這在繪畫(huà)中是一個(gè)非常重要的問(wèn)題,所以必須明白。就拿顧愷之的《洛神賦圖》(圖3)來(lái)說(shuō),畫(huà)中曹植和洛神四目相對(duì),洛神低著頭,一言不發(fā)。除了這些,他還畫(huà)了一些簡(jiǎn)單的柳樹(shù),用了一些簡(jiǎn)單的筆法,讓流水的漣漪都變得安靜了下來(lái)。這一段簡(jiǎn)單的敘述,把主角的戀戀不舍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留下一種落寞的、仿佛憂(yōu)傷的想象空間。又如顧愷之曾對(duì)魏晉時(shí)期的畫(huà)家作了一次評(píng)述,由此可以看到他對(duì)“傳神”的要求。他特別強(qiáng)調(diào)在某些情況下,當(dāng)發(fā)生矛盾的時(shí)候,要怎樣才能使人物具有神韻。顧愷之在他的書(shū)中寫(xiě)道:藺相如的性格就像與秦昭王在和氏璧中發(fā)生沖突的性格一樣,藺相如作為一個(gè)政治家具有超高的智慧和敢于為國(guó)犧牲的勇氣,而秦昭王則是一種貪婪、食言的性格。所以在畫(huà)的時(shí)候必須找到一個(gè)合適的角色,要表現(xiàn)出君臣的不同,不能畫(huà)得太過(guò)火,這樣才符合人物的要求。
以上是人與人的社會(huì)關(guān)系。除此之外,顧愷之對(duì)周?chē)h(huán)境的描寫(xiě),也是很有價(jià)值和意義的,通過(guò)環(huán)境氛圍的營(yíng)造,強(qiáng)調(diào)以景托人。例如《世說(shuō)新語(yǔ)》中寫(xiě)道:“顧長(zhǎng)康畫(huà)謝幼輿在巖石里。人問(wèn)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guò)之。此子宜置丘壑中。’”⑤很明顯,顧愷之并沒(méi)有通過(guò)謝幼輿的外貌來(lái)展現(xiàn)他的才華和修養(yǎng)。而是以周?chē)沫h(huán)境為參照,這就是所謂的“荃生之用”,即人之神的化身。顧愷之認(rèn)為畫(huà)畫(huà)一定要“化自然為人的無(wú)機(jī)軀體”。人與自然之間的關(guān)系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體的,不可分割的。例如《韓熙載夜宴圖》(圖4)里的人物有很多,從第一首曲子開(kāi)始,到最后的告別,作者有意識(shí)地使家具變得越來(lái)越少。在作品的前半部,共設(shè)置了12個(gè)人物,加上床、椅、屏風(fēng)等各種家具,構(gòu)成了整個(gè)作品中最為繁復(fù)的一部分。如果說(shuō)《韓熙載夜宴圖》是一部電影的話(huà),那么前半部分這一幕就像是一個(gè)小小的高潮,會(huì)讓人瞬間進(jìn)入宴會(huì)的氛圍。從整個(gè)畫(huà)面來(lái)看,顧閎中畫(huà)的這個(gè)場(chǎng)景給人一種“曲終人去樓空”的感覺(jué),從最初的賓客滿(mǎn)座,到后來(lái)的客人全都散去,家具也逐漸變少,最后只剩下韓熙載一個(gè)人,他的悲涼和苦悶通過(guò)這些表現(xiàn)全都被巧妙地表達(dá)了出來(lái)。
因此,注重環(huán)境和人物的結(jié)合以及人物與人物的結(jié)合也是傳神的一種重要手段。
四、小結(jié)
顧愷之的“傳神”思想正是通過(guò)對(duì)形體的把握來(lái)傳達(dá)神韻的,注重人物性格特征的表現(xiàn),用人物所處的環(huán)境烘托畫(huà)面的氣氛。“傳神”思想不僅構(gòu)成了顧愷之繪畫(huà)美學(xué)的中心問(wèn)題,也構(gòu)成了中國(guó)古代書(shū)畫(huà)美學(xué)的一個(gè)基本問(wèn)題,他的理論思想和美學(xué)觀點(diǎn)深刻地影響了以后的繪畫(huà)發(fā)展,追求神韻和內(nèi)在美成為中國(guó)審美品格的重要基點(diǎn),也成為衡量和評(píng)價(jià)中國(guó)繪畫(huà)藝術(shù)重要的品評(píng)標(biāo)準(zhǔn)。如今,社會(huì)不斷發(fā)展,但是藝術(shù)的實(shí)質(zhì)未發(fā)生改變。當(dāng)代的中國(guó)人物畫(huà)家在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應(yīng)追求“傳神寫(xiě)照”的藝術(shù)效果,而這也是藝術(shù)的靈魂所在。

作者簡(jiǎn)介
盧莉華,女,江西贛州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yàn)槔L畫(huà)的名家名作的品鑒與賞析。
參考文獻(xiàn)
[1]蔡英余.論顧愷之人物畫(huà)論中形神關(guān)系的美學(xué)內(nèi)涵[J].寧波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科學(xué)版),2006(4):135-139.
[2]曹順慶.中西比較美學(xué)文學(xué)論文集[M].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5.
[3]傅慧敏.中國(guó)古代繪畫(huà)理論解讀[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12.
[4]方立天.魏晉南北朝佛教[M].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6.
[5]顧愷之.畫(huà)論[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9.
[6]侯亞盟.淺析工筆人物畫(huà)中的“傳神寫(xiě)照”[D].濟(jì)南:山東藝術(shù)學(xué)院,2020.
[7]羅小珊.傳神論的起源[D].杭州:中國(guó)美術(shù)學(xué)院,2014.
[8]孔維強(qiáng).顧愷之形神理論的文本邏輯初探[J].藝術(shù)百家,2004(6):133-135.
[9]劉義慶.世說(shuō)新語(yǔ)[M].北京:中華書(shū)局,2004.
[10]汪瀾.從顧愷之的形神觀談中國(guó)人物畫(huà)創(chuàng)作[D].長(zhǎng)春:東北師范大學(xué),2008.
[11]謝靈運(yùn).謝靈運(yùn)集[M].長(zhǎng)沙:岳麓書(shū)社,1990.
[12]袁有根.顧愷之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13]詹景鳳.東圖玄覽:詹氏理性小辨[M].上海:上海書(shū)畫(huà)出版社,1988.
[14]朱良志.中國(guó)美學(xué)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6.
[15]張彥遠(yuǎn).歷代名畫(huà)記[M].北京: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64.
注釋
①劉義慶:《世說(shuō)新語(yǔ)》,中華書(shū)局,2004年第21頁(yè)。
②顧愷之:《畫(huà)論》,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9年第47頁(yè)。
③詹景鳳:《詹東圖玄覽編》,上海書(shū)畫(huà)出版社,1988年第66頁(yè)。
④張彥遠(yuǎn):《歷代名畫(huà)記》,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64年第45頁(yè)。
⑤劉義慶:《世說(shuō)新語(yǔ)》,中華書(shū)局,2004年第34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