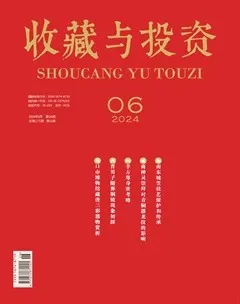南陽春秋玉琥紋飾分析及設計應用探究
摘要:虎形玉器稱為琥,玉琥是六大瑞玉之末,分為虎形和虎紋兩種基本形式,大多作為配飾使用。文獻記載琥以白虎身份祭祀西方。本文以淅川縣下寺楚墓和桐柏縣月河一號墓出土的玉琥為研究對象,探討南陽春秋玉琥紋飾特征與藝術價值,通過對紋飾元素的提取、變形等,使其在設計應用中煥發生機,將傳統紋飾與現代設計有機結合,希望能夠對傳統紋飾的發展與傳承起到促進作用。
關鍵詞:春秋時期;南陽玉琥;紋飾;設計應用
在春秋時期,各個諸侯國在政治上保持獨立,彼此之間存在軍事沖突,導致局勢紛亂動蕩。然而,正是在這種政治背景下,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手工業領域取得了重大進步。河南省南陽市是一個三面環山、南部開口的盆地,具備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楚國正是在這塊土地上崛起成為一個掌控全局的強國。在丹江流域,楚人的活動頻繁,他們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并留下了許多珍貴遺產。河南南陽春秋墓中出土大量配飾類玉器,做工細膩精美,紋飾豐富,其中動物造型的玉佩所占比例最大,且形象生動,栩栩如生。本文將以淅川縣下寺楚墓和桐柏縣月河一號墓出土的玉琥作為研究對象,對玉琥紋飾進行分析探究并進行再設計,為傳統紋飾的傳承與創新應用提供新的思路。
一、春秋玉琥紋飾的歷史沿革與形態發展
(一)虎形玉佩紋飾的起源
虎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起源比較早的圖騰文化之一。虎的形象最早出現于新石器時期,類虎的紋飾在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中出現,抽象玉虎的形象出現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江淮流域的安徽凌家灘遺址出土了一批玉虎或虎頭裝飾的玉器 。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玉雕虎形態是兩件虎首玉璜。將虎符號與玉結合所形成的虎形玉器擁有豐富的文化內涵,依照其總體屬性及雕琢技術的差異,虎紋玉飾可被劃歸為虎面圖案、單面雕琢的玉琥、圓雕玉琥及虎紋玉器等多個種類。依據虎的姿態等特性,虎的圖案可以被劃分為步行虎、站立虎、躺臥虎以及雌雄虎。在玉器裝飾上,虎紋常與云紋、龍首紋等圖案結合出現。
(二)虎紋飾的形態發展
新石器時期虎的形象最早出現在巖畫上,以群虎形象出現,線條突出,姿態各異,雌雄有別。到了夏商周奴隸社會時期,青銅器、玉器皆出現了虎紋飾,且直接以虎為造型,其形象或斑紋被廣泛刻畫。商代虎紋飾動態感弱,造型簡單,虎身多飾云紋或條形紋等;商代中期和晚期,虎紋飾逐漸復雜化,西周時期繼續繼承商代虎紋飾裝飾簡樸、動態感弱的特點[1]。直至春秋時期虎紋飾線條流暢,轉角圓曲,身以雙陰線飾龍首紋、云紋等,具有極強的裝飾性美感。
二、春秋時期南陽玉琥紋飾的構成形式
(一)春秋時期南陽玉琥墓群出土對比
春秋年間,玉琥經歷了一個嶄新的成長過程,其產出大幅度提升,造型各異,設計創新且紋理精致,裝飾華麗,它被視為中國傳統玉雕的杰出代表,備受矚目。為便于研究,本文甄選了南陽出土春秋時期玉琥最具有代表性的兩大墓群:淅川縣下寺楚墓和桐柏縣月河一號墓。選擇同一時期不同墓群的玉琥,對玉琥的尺寸、形狀樣式和紋樣特征進行對比研析(圖1)。
淅川下寺一號墓出土兩件玉琥尺寸為14.6 cm×7.35 cm×0.4 cm,大小形制相同,青白玉,白色微黃,透明,呈片狀。正面呈虎形,垂首、翹尾、弓背虎首和虎尾各有一穿孔,系供穿戴之用[2]。三號墓出土六件玉琥尺寸為6.4 cm×2.05 cm× 0.3 cm,大小形制相同。朱紅色,虎俯首,口微張,橢圓眼、凹背、凸腹、屈肢卷尾作臥俯狀,虎口、背、尾各有一穿孔,系供穿戴之用 。紋樣裝飾為虎紋、龍首紋、云紋、絞絲紋。桐柏月河一號墓共出土13件,尺寸為:13.5 cm×6.5 cm×0.23 cm、14.3 cm×6.8 cm× 2.8 cm(2件)、14.4 cm×6.6 cm×0.2cm、12.8 cm×6.2 cm×0.3cm;14.4 cm×8.4 cm×0.4 cm、14.4 cm×8.2 cm×0.4 cm;13.6 cm×6.1 cm×0.2 cm、13.4 cm×5.7 cm×0.3 cm;10.7 cm×3.0 cm×0.3 cm、12.5 cm×31.1 cm×0.3 cm;7.2 cm×1.9 cm×0.14 cm;4.6 cm×1.9 cm×0.3 cm。透閃石質,有紅、黑褐色沁,器體扁平,虎體肥碩,垂首或俯首,拱背或凹背,屈肢,卷尾 。個別虎口微張,頭部由上下疊加的兩只虎首組成。首、尾、背或兩足部各有一個圓孔。大多兩孔或四孔,系供穿戴之用。紋樣裝飾為虎紋、龍首紋、絞絲紋、云紋。
(二)虎形紋飾
南陽春秋時期的玉琥紋飾與工藝有很大發展,形式美的標準深入人心,逐漸形成鮮明的地域和時代風格。相比于商代的玉琥行虎紋,南陽春秋玉琥的虎紋多為臥虎紋飾,通常為頭下垂,尾上卷,虎口微張,四肢蜷曲,腹部懸空,且虎的輪廓與結構線相吻合。如淅川下寺1號楚墓出土的一對玉琥,有具體描述:“白色微黃,透明,玉質細潤。玉琥一面刻虎紋,正面呈虎形,垂首、翹尾、弓背,虎首和虎尾各有一穿孔,系供穿戴之用。”[3]再如桐柏月河一號出土的M1:48式玉琥,首尾伏地,弓腰曲背,呈臥狀,巨尾垂而尾尖回卷,正面頭部飾龍首紋造型向前張口,前后肢飾云紋,整體線條生動自然,這是春秋時期迄今為止最精美、最典型的屈身咆哮玉琥[4]。這種玉琥一般為兩件一組,有學者認為這種成對的玉琥后來發展演變成發兵的信物,也就是虎符。
(三)輔助紋飾
1.龍首紋
春秋時期的玉器以龍首紋為核心裝飾,其源頭可追溯至商代的龍首飾,如婦好墓出土的玉器上便已有其身影。根據制作工藝的不同,龍首紋可分為雙線、寬線和單線等類型。桐柏月河一號墓出土的M1:143式玉琥則更細致地展現了龍首紋的特點,云氣形短小且不相連,額部平滑,前端尖銳收縮,沒有內勾,鼻部有明顯的翻卷。淅川下寺出土的臥形玉虎以及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的臥形片狀玉龍,其龍首紋的雕刻和布局都遵循一定的順序。此外,龍首紋還影響了戰國時期的紋飾發展,如云谷雜相紋和谷紋等。整個發展演變的過程符合從具體到抽象、從繁復到簡約的規律。
2.云紋

云紋起源于古代人們對自然現象的觀察和崇拜等。云紋最早出現在玉器上,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晚期。云被認為是一種吉祥、神圣和高貴的象征,春秋時期的玉器制作技術進一步發展,玉器的紋理和光澤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春秋早期的云紋特點如下:一是以陰刻線勾勒的勾云紋;二是卷云紋形象生動,緊密相連;三是玉器表面的平面紋飾,尚未發展為后來的立體凸雕。在多數南陽春秋玉器上,云紋多作為適形紋樣,裝飾于虎身,南陽春秋玉琥多以寬大的卷云紋表示虎的四肢[5];而單線勾云紋作為二方連續樣式和四方連續樣式,排列在主體紋飾造型的周圍,使整個玉佩更加生動活潑,顯示出當時玉器制作技術和美學觀念的進步。
3.絞絲紋
絞絲紋又稱繩紋、扭絲紋等,它的出現可以追溯到商代晚期,在春秋時期被廣泛應用。這個時期的絞絲紋常呈現對稱設計,這種對稱美展示了古人對和諧平衡的追求。絞絲紋的盤旋交織具有無限延伸的寓意,象征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絞絲紋玉器最早可見于良渚文化的玉鐲,紋飾精美,春秋戰國時期絞絲紋主要為貴族享用,南陽桐柏月河一號墓出土的玉琥,正面頭部和尾部均飾有絞絲紋;淅川下寺1號墓出土的兩件玉琥,正面呈虎形,上下皆飾有絞絲紋。紋飾簡單精美,琢磨細致,整體富有節奏感和韻律感[6],充分展示了古代工匠的技藝水平和古人的審美追求。
三、玉琥紋飾的當代設計應用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消費市場呈現迅猛的增長態勢,這為文化創意產品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眾多知名文化品牌,如故宮博物院和敦煌博物館,成功地將傳統文化元素與現代生活相結合,推出的文創產品受不同年齡層消費者的青睞 。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對春秋時期南陽玉琥的紋飾進行創新設計,并將其融入現代文創產品設計,探索傳統藝術與現代設計理念的融合。
(一)“琥韻風華”系列文創產品設計展示
“琥韻風華”系列作品(圖2)通過提取和創新設計,融合了虎紋、龍首紋、絞絲紋、云紋和鱗紋等元素。在這一設計過程中,設計者從玉琥的原始形態和特征中提煉出文化符號,經過概括和重構,創造出既符合現代審美又蘊含傳統文化精髓的新穎設計[7]。在現代文化創意產品設計中,這些具有代表性的獨特元素被融入產品設計中,使得產品在保留文化韻味的同時,也展現出獨特的現代魅力。
(二)“南陽玉琥”系列文創產品設計展示
“南陽玉琥”系列作品(圖3)運用提煉簡化法對玉琥造型紋樣進行高度概括,同時將玉琥原有的內部裝飾圖案、紋樣進行處理之后,使復雜繁冗的元素通過改良變得更符合現代審美。設計出更有個性、更符合現代需求且更符合民族文化的視覺符號,將其運用到掛歷、盒子、膠帶等日常用品上,對玉琥的傳播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能讓消費者了解文化,以達到產品的文化含義與大眾生活相契合的效果。
四、結語
本文對南陽春秋玉琥紋飾進行了深入分析和系統性的梳理與歸納,將元素進行提取、擴展,在實踐中加以應用。有助于春秋時期玉器紋飾的文化內涵傳承與創新發展,并以此為基礎,對南陽春秋玉琥文化元素進行再設計,將其文化內涵與產品外觀進行融合,形成具有時代感的文創產品,為文創產品的設計提供了創新思路。

作者簡介
郭苗,女,漢族,河南南陽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藝術設計(工藝美術設計)。
通訊作者
雷保杰,男,漢族,河南蘭考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藝術設計。
參考文獻
[1]安哲靜,裴學勝.虎形紋飾的演變與分析[J].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4):29-34.
[2]唐新.淅川楚墓玉器精粹[J].收藏界,2007(8):62-64.
[3]多麗梅.東周時期的玉琥[J].文物天地,2016(10):99-107.
[4]董全生.桐柏月河一號春秋墓出土的玉虎鑒賞[J].文物鑒定與鑒賞,2023(7):5-8.
[5]任義玲.南陽春秋墓出土佩玉選粹[J].收藏家,2008(11):37-42.
[6]唐新.丹淅楚玉—河南淅川楚墓出土玉器鑒賞[J].收藏家,2018(1):75-80.
[7]曹婕,沈瑩.以魚紋為例探討傳統紋飾在現代設計中的應用[J].今古文創,2022(14):93-95.